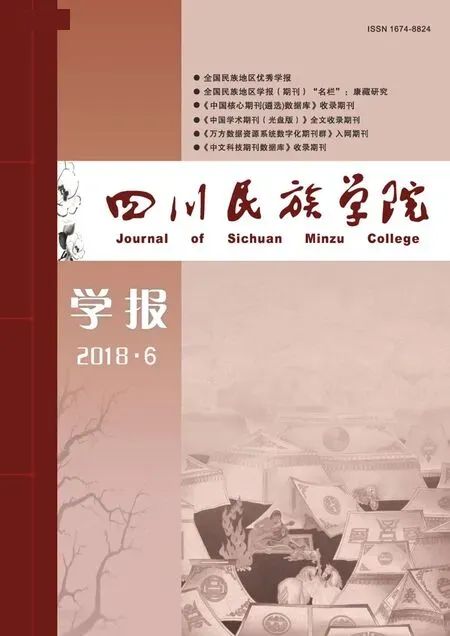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达斡尔族萨满民间仪式
——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例
杜 楠
一、问题的提出
萨满信仰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深受多民族和地区的信奉推崇,它在人类社会原始阶段自发产生[1],绵延至今已成为世界民俗宗教组成中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文化形态。随时间推移,萨满宗教呈多样性分裂重构,而达斡尔萨满信仰在历史进程中较少受现代宗教的冲击和影响,其民族性和原始性特征仍体现于该族群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典型的族群聚居地仍然保存着萨满信仰和民间本土化的巫术活动。
民族宗教多起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是迷信抽象化和系统化的表现[2]。达斡尔族群这种充满原始性的民族文化无论在信仰者或非信仰者的观念中,均贯穿着迷信色彩。在现代文化广泛传播和城市化对生活观念的强劲冲击下,科学与理性成为时代的符号。而被“迷信”冠名的达斡尔萨满仪式为何绵延至今?仪式在现代生活中是否发挥了某种功能或作用?民间仪式作为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达,是一种社会变迁的影像[3],也是文化内涵的凝聚。被称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作为中国最典型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是保留萨满文化宗教仪式较多的地区。正因如此,关于达斡尔族群的研究在学术界经久不衰,剖析该地区民间仪式的内涵对于世界诸民族的萨满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存的达斡尔萨满仪式具有特定的形式和规则,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该族群的文化心理和需求。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基于民族仪式的研究大多是以语言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的角度,或部分以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此类研究以宏观视角基于纵向的历时性视角建构民俗文化意义的同时,也开始着眼于挖掘仪式在个体微观层面功能的重要性和意义。而从积极的角度对迷信进行审视似乎有悖科学研究的初心。但逐渐有研究证实从个体心理健康角度而言,迷信也有其贡献[4]。追溯仪式的变迁,从功能主义的宏观及微观的视角透析达斡尔民间仪式,能够通过其折射出的文化意向了解该群体的多元需求。基于外化表露的显性特征,探索存在于观念中的隐形特征。最终来回答充满“迷信”色彩的仪式何以在科学理性当道的时代得以延续和留存的问题。
二、达斡尔族萨满信仰与文化表征
(一)萨满教与萨满信仰
萨满教是一种自然、原始而古老的多神宗教。《宗教词典》将其定义为“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在原始社会后期,“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中巫师的称呼,后流传于各部族。各部族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形成统一的信仰,但彼此间的信仰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崇尚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5]古代时期的萨满教作为一种信仰在我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的女真、鲜卑、柔然、契丹、回鹘等现代北方民族的祖先中普遍流传。这些阿尔泰语系民族利用萨满巫术,在战争前后举行仪式,也在战争中利用巫师智慧预言战争得失,控制和影响战争局势。在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诸多外来宗教传入前,萨满教在北方民族的信仰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成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主流信仰后萨满文化及萨满教信仰活动仍存在于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民族之中[6],其中达斡尔族群的主要信仰仍是萨满教。
(二)达斡尔族群与其萨满信仰文化
达斡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少民族”之一。究其民族根源,历史学家认为现今的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族的后裔[7]。古代使用的契丹文字早已失传,达斡尔族虽具备独立的民族语言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却面临文字的丧失。先人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身教、言行示范的方式,但随着达斡尔族地区社会的不断发展,过去丰富的口述史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传承危机,达斡尔族文化被主流文化严重同化[8]。该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地处呼伦贝尔市东部,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大兴安岭东麓中段,嫩江西岸,地域广阔且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革的同时,该地区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经济文化等社会方面也发生剧烈变迁。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下,原本封闭落后的达斡尔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愈渐频繁,于各个层面都发生着显性或隐性的变迁[9]。作为全国唯一的达斡尔族自治旗,该地区的发展与变迁能够代表性地反映达斡尔族族群文化发展的变迁。
达斡尔族最初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始于将风雨雷电等自然万物视为由神灵主宰。而人自身也有灵魂,死后会转生或漫游,以保护或加害于后人。因此,信仰活动以祭祀与占卜为主,来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和人之生死。因为对万物和灵魂的敬畏之心,达斡尔族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伦理和道德准则随处可见,禁忌和图腾就是这些约束的表现形式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原始族群的行为受复杂的一系列习俗和规范制约,也受禁律和特权支配[11]。禁忌和图腾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不断的面对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时,一方面无法对抗,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一些感性的思维判断。为了规避灾祸,民众约定在某些情况和场合下禁止某些言行,后逐渐发展为禁忌和图腾。例如,除夕之夜天黑前必须将门窗糊好,否则将被邪灵入侵;大年初一不许从门外叫人,否则会被群魔缠身,摄去心神;人死咽气前,家人不准入睡,否则死者灵魂会将睡者灵魂带走;外姓人死后,不得从门出,必须从窗户抬出,否则其魂魄会认门等等。而达斡尔族人之所以崇拜萨满,是因为萨满是与灵沟通的媒介,能够完成人、鬼、神之间的交流,对产生各种灾难、疾病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12]。达斡尔族人畏惧自然力的同时又期望借助自然力,通过萨满的祝祷进行祈福,在遇到困难时倚仗其指引方向。代代相传之下,萨满成为了族人们信念的最终集结,萨满仪式成为传承萨满文化的载体。
三、达斡尔族民间萨满仪式的变迁
民族仪式中包含的元素涉猎广泛,因此关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常以仪式为切入点。仅从仪式便能够将一个民族的音乐、舞蹈、语言、图腾、习俗等具象化。作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因素,仪式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建构作用,既包括个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生活方式,也包括社区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网络的互动方式[13]。学者彭兆荣将仪式描述成充满艺术色彩的实践、特定的宗教程序、心理诉求的形式、生活经验的记事、制度性功能的行为、政治场域内的谋略以及族群的族性认同等等[14]。可见民间仪式包罗多元的社会意象,可以视为是其所处社会系统的缩影。而民间仪式的变迁是参与和表现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仪式的变迁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当代达斡尔族群体文化变迁的路径以及不同时期该民族的不同诉求。
(一)早期以治疗为主的萨满仪式
以治疗为主的仪式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族人因疾病难以治愈寻求萨满帮助,按照礼仪,要携带礼品请萨满到家中治病或请萨满出山。萨满一般在夜晚请肩上的神鸟飞出了解求助者被何种鬼神缠身作祟,当神鸟飞回告知萨满前因后果后,方能出山治病。这种仪式的特点是:公开举行,不具神秘性;无需固定场所;时间较为随意。萨满作为仪式主导选定配合自己的二神,共同施法。诊病方式为唱神歌,诉求神灵附体,仪式完毕后,邀请参与者共享祭祀物。萨满最高的法术是“过阴追魂”,法力高超的萨满能够自由出入阴间,为挽救病重之人去往阴间询问,并口述所见所闻。对于昏迷不醒的病人,还需查生死簿,若患者未到死期需把魂找回。虽然在该族群的观念中阴间是对外部世界颠倒、虚幻的反映,但在萨满绘声绘色的描述当中,能够反衬出人间的生活,借用超人间的行为规范来维系群体感情,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后期以祭祀为主的萨满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萨满仪式的主题通常是祭祀以及祝祷。典型的有奥米南仪式和洁身祭。奥米南仪式的特点是程序化、正规化;需要特定地点;以祭祀为主导。仪式的前两天进行祷告、跳神,请神灵降临人间,祈求族众平安。第三天举行库热仪式,萨满用整张牛皮,剪成无接头的皮条,参与的族人从皮条下通过,以此得到神灵的庇佑,保万事顺意,结束时再举行献血仪式。洁身祭即每年正月时节,萨满在家中将所用的神器及灵物投入锅内烧开,用此水洗浴自身,并洒向前来膜拜的人。作为神灵赐给人间的圣物,神水被认为可以洁身驱邪。洁身祭是萨满进行自我净化的仪式,又寓意回到原点,洗掉往日的烦恼,摆脱负疚的罪恶感,一切重新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神灵的保佑[15]。
(三)现代化冲击下的民间仪式
文革时期萨满教备受打压,其文化被严重破坏,遭遇濒临灭绝的危机。在社会结构、生产力的转变下,达斡尔族萨满教经历了诸多变异在夹缝中得以发展下来。莫力达瓦现存的萨满仪式,削弱了浓厚的宗教仪式感和繁琐的祭祀流程,融入了更多民间元素。当地现存民间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看邪病”“叫魂”和占卜。“邪病”指诸如儿童高烧不退,老人久病不愈,或因不知名的疾病卧床不起。在仪式中,萨满首先会通过“过阴追魂”寻找疾病的起因,“邪病”的致病起因一般分为自身和他者。在达斡尔信仰中,往生之人若有某种诉求难以达到,便会让生者被疾病缠身,若自身冒犯过狐狸、黄鼠狼等生灵也会有些遭遇。驱除病症的方法是祭祀,达到为往生者还愿或为冒犯生灵赎罪;“叫魂”是将受到惊吓、神经衰弱或精神失常之人的魂魄叫回躯体。萨满依然使用“过阴追魂”与灵魂进行沟通,即萨满的灵魂进入地界以及去往地界的交界处寻找游荡的亡灵,带回人间放入魂魄丢失、涣散者的身体内,使其恢复正常。在仪式后,需要求助者亲自祭祀和供奉,其形式包括烧黄纸、烧“小人”和焚香祭祀等,以满足与求助者相关的往生之人的诉求。古时萨满的占卜仪式主要是预测战争,而现今的占卜主要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通过萨满占卜的结果,规避一些风险或制定重要事件如婚礼、丧礼当中的禁忌等。
此种现存在于莫力达瓦民间的仪式具有以下特点:祭祀场面不再宏大、流程简洁,逐渐私人化;萨满的身份无需权威认定,而是通过坊间对其能力的流传,在当地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求助者民族成分多元化,除达斡尔族人,当地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亦会求助于萨满;祭祀和供奉的实施者从萨满转移到求助者或双方共同进行。古时的宗教活动者包括萨满等神职依靠宗族供养,地位极高。现今的仪式活动与早期不同,萨满地位严重削弱后,自身可能会需要其他社会身份或工作来维持生计,因此在仪式中也会有经济成分的参与,萨满会收取求助者较低的经济报酬或礼物馈赠。
四、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达斡尔族民间仪式
仪式的存在必然有其目的性和功能性。从目的性来看,仪式是为了巩固和追逐信仰。社会学家特纳强调仪式的规范与信仰,关注仪式中正式的行为、规定的场合以及特定的技术手段等,而所有的规范都是为了接近信仰者所追求的神秘力量。从功能性来看,仪式能够整合和凝聚社会力量。人类学家格尔兹将仪式视为神圣化的行为,是产生“宗教观念是真实的”信念的基础,是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是参与者认识世界的大门[16]。社会学家涂尔干和人类学家布朗将仪式视为具有家族凝聚和社会整合作用的人类文化现象[17]。而功能主义认为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富含或积极或消极的功能,系统要生存则某些功能是必需满足或达到的。因此我们假设达斡尔族民间仪式得以存在和延续,得益于其某些功能的效用满足于既定环境中的需求,而需求普遍存在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因此可从这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宏观视角:达斡尔民间仪式功能的讨论
任何社会系统都是内部分工与相互依赖的整体[18]。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适应,即对环境的适应功能。包括对环境限制和压力的顺应,以及对环境的积极改造;二是目标达成,系统制定目标并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调动内部能量去实现目标;三是整合,即协调各组成部分,将各部分联系、协调一致;四是维模,又叫潜在模式的维持,即根据某些规范与原则维持自身延续的功能[19],如在系统运行中断时,系统拥有特定机制维护自身处于潜在状态的模式[20]。结合前人研究的描述以及现今存在的达斡尔族仪式的表象,萨满民间仪式的社会功能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更为和谐相处,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能够在社会建设发展之中对自然环境进行良性的改造。通过禁忌的约束,达斡尔族人对自然万物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达斡尔族萨满信仰者认为大自然里贮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是群体的共有财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行需要之外的捕杀、砍伐。在遭遇变故或疾病时,族人可能会将事故的缘由归结于对自然生灵的触犯。在现今的达斡尔族社会中,这种思想和观念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促进家庭、民族关系的稳定。仪式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其目的便是解决问题、恢复平静的生活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祈福。参与仪式的族人会逐渐意识到:作为族群中的成员,除了要对自我负责,也要肩负家庭和群体延续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因个体的行为可能会为家庭以及族群招致灾祸,从而在生活中族人会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重视各种社会关系的正向发展。另一方面,集体活动带来的群体归属感,是民族发展稳定性的重要保证[21]。而当家族形式逐渐被家庭单位取代后,仪式也同样在维护家庭关系中发挥作用。
第三,延续良好的民族价值观及道德观。大型仪式或祭祀活动使族人之间的契约公开化、传统标准化。也将典型的民族信念传播并延续下去,在萨满代表神明的倡导之下,全体族人均是道德的监督者和集体利益的维护者。价值观的表现一是“乐观”,达斡尔族人在面临困难时的反应普遍比较正面,因相信萨满的力量和自身的努力会使情况改善,萨满更像是整个民族的定心剂。价值观的又一表现是相信“善恶有报”,因为神明会祝福善良之人,惩罚有过之人。而道德观的表现便是“重孝”,族人中的年长者往往是权威的象征,因此达斡尔人形成了“长者在不分家的”家庭观念,长者逝世更要举办仪式悼念。达斡尔人祖先的灵魂被视为是无所不能的,对先祖尊敬与否对后世子孙的荣辱兴衰至关重要。尊老和慈孝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达斡尔族人家庭和家族关系的长期和睦与牢固。
第四,保持独立的民族性格,维护民族得以延续。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指沉淀于心灵底层、普遍共同的本能和经验遗存。萨满文化情结始于原始意象的表达,通过一代代仪式的反复强化,达到集体无意识的不断凝聚和升华[22]。进而,萨满信仰寄托成为了原始意象与集体无意识的切合点。仪式是集体无意识所隐含的文化意向最全面且恰到好处的表达。达斡尔族的萨满仪式产生于远古时代,传承至今甚至萨满本身都无法言说其最根本的意义及内涵,但仪式或直观或间接的表达千年发展而来的原始意象,在无形之中仍然给后代带来深刻影响。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无论仪式的形态如何随时代变迁,其传递的民族意象和精髓仍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也是在民族交融、文化冲击的时代下,达斡尔族仍然保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性格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达斡尔族民间仪式具有的保护和适应生态环境、促进民族社会价值观、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道德观形成以及保持独立的民族性格及推动民族的维护与延续的社会功能,与功能主义视角中社会系统为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的四种功能条件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以及维模基本吻合,从功能主义宏观的视角来看,达斡尔族的信仰仪式具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微观视角:达斡尔民间仪式功能的讨论
仪式作为一件事物的整体,其包含的每一部分都是不能脱离整体意象表达而单独构成有效意义的个体。在功能上满足整体的需要同时,还需维持个体组成部分的稳定。近年来仪式研究迈入更广阔的领域,其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了“仪式化”的境地[23]。目前已有学者根据心理学的记忆提取理论,探讨了萨满文化对满族后代思维和心理的作用[24];还有学者将萨满仪式类比为心理治疗,论述“跳神”的心理医疗功能[25]。该类研究突破了宏观视角的界限,但仍然忽视了萨满仪式逐渐由群体活动向个体治疗活动演变的过程中,仪式功能与受众群体中不同个体需求差异之间的交互关系。
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事物的功能包含“显功能”和“潜功能”两个层次。其中,显功能是指人们容易想到并且容易接受、认识的客观结果,而潜功能则更多的表现事物所不为人知的内在本质,它不易发现且难以理解,却决定了事物的内容、命脉与核心。通过研究事物的潜功能,能够增加对事物更深层次的理解,加深主体对事物与社会认知和辨识的能力[26]。不同的个体参与仪式的目的和诉求,必然在于对仪式的某些表面或本质功能的需要。因此透过“显功能”去追溯“潜功能”,更能够探究在微观层面萨满仪式存在的意义。
仪式的显功能是参与仪式者都能够感知并明白其能够满足自身某种需求的所在。涂尔干在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宗教与信仰时,提出宗教既有追寻超自然力量的超现世取向,又有文化事实上的现世性[27]。因信仰本身体现出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并非是刻意安排的后果,那么以这两种取向去衡量萨满仪式,现世性则是仪式隐功能的体现。在现代的萨满民间仪式中,无论是治病、占卜或是祭祀、祝祷,针对的都是为人们在遭遇困难、深陷迷茫时指引方向。然而这种显功能作用于个体之后,会转化出其他差异性的隐功能,可以概括为行为助推和精神治疗。具体而言,萨满仪式所做的指引未必是绝对正确,但能够在大方向上促进求助者将潜在的思维转化为行动。萨满通过求助者问题的表述,不断挖掘其内心的诉求,再与某种超自然的手段相结合,达成最终的因果分析和解决途径的指引。人们寻求萨满的帮助,很多时候是由于对某些人生抉择产生犹豫或恐惧。而此时,在仪式的祭祀、祝祷之后,求助者如同获得一副行动的助推剂,能够克服犹豫和恐惧去实践。另外,隐功能之所以是探讨仪式存在意义的重点,是因为其作用于个体上体现的的精神价值,在困境中反省自我以及获得正向的心理暗示。萨满在解决问题时,常会引导求助者思考是否有触犯过生灵或是犯下过罪孽,因此问题最终的解决便是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善行或善念来达到。而无论是“叫魂”的特殊方式和送往生者的既定民族语言,这些对于虔诚的求助者来说,便是萨满与自我的心身相互。此时,萨满所代表的权威和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所代表的权威类似,能够让疾病患者或是受惊吓者恢复心灵上的安定与平静。无论是对自我的反省还是正向暗示,均是精神治疗作用的体现。
结 语
反身思考萨满仪式,现代化使达斡尔萨满民间仪式融入了更多元的文化元素使之能够适应发展而留存。反过来,萨满仪式和信仰也同样是维系该群体的道德动力和精神活力。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萨满仪式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仪式中器物、语言、行为等符号与人的成长、家族的团结结合起来,通过将符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融入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借助仪式活动得以传承。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人口较少且文字消失的民族在文化变迁和冲突中已经陷入困境,当地传统的民间仪式面临被遗忘或被抵制的境遇,此种境遇需要多方的力量助其突围。
作为宗教文化的一种具现式,萨满仪式存在糟粕但也有其精华,仍然是中华历史文化宝库中不可复制的瑰宝。民间仪式中的超自然力量让人敬畏和神往,它在社会不同层次中发挥的功能和价值也值得更深入的探寻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