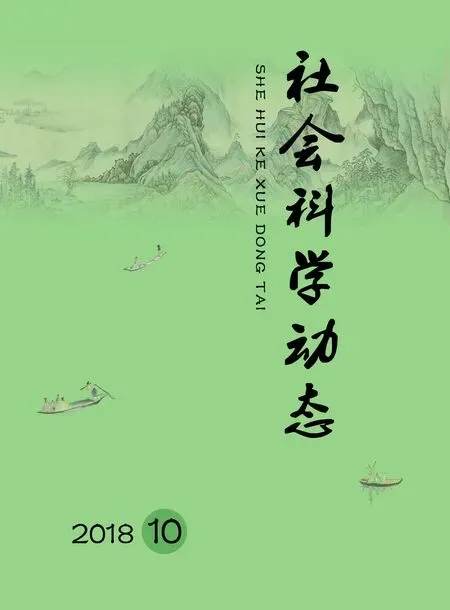论公共文化空间视界下民国湖北的城市公园
熊 霞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园林建设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新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公园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脱胎于传统园林的城市公园,在传承了古典园林的基本设计和构景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了民主、科学的发展成果,体现出迥异于传统园林的开放性、包容性或大众性特征。民国中期,在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科技知识的学者型官员的倡导下,湖北地区以汉口中山公园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公园相继诞生。这些公园见证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它们既是民众休闲游憩、修养身心的理想空间,也是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教育的重要课堂,还是为社会团体提供众多社会资源的场所。
一、传统私家园林到近代城市公园的演变
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没有专门向市民开放的公园,花园和园林完全归私人所有,不向社会开放。湖北地区的私家花园和园林建设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江夏(今武昌)、汉阳已有黄鹤楼、古琴台等园林实体。以后,各地的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开始建园亭以自娱,私家园林建设愈来愈盛。元明清时期,武汉的熊园、葵园、怡园、寸园、刘园;沙市的金粟园、平楚园、徐园、梅园、知足园、醒园、西园;樊城的习家池、杨吉六花园、米公祠;随县的夜光池、且园;光化县的简家花园、傅家花园、李家花园等湖北著名私家园林纷纷建立。①私家园林的造园活动以文人仕官为主流,园主大多选择在依山傍水之宝地,模仿江南园林的风格来兴宅造园,以求远离城市喧嚣、享受田园之乐。园林一般由园主亲自筹划、监造,注重园林的私密性,并以审美为主要旨趣,常通过借鉴诗词书画来表达“以画入园,观园如画”般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境界。
辛亥革命后,“天下为公”“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也逐渐反映在城市建设中。一批民主主义人士极力宣传“田园城市”的思想,倡导筹建公园。民国二三十年代的湖北,在私家宅园、府署庭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一批向公众开放的近代城市公园相继诞生。
湖北最早的近代城市公园是1923年武昌首义人士夏道南筹建的首义公园。此后,相继建立的有武汉的中山公园(1928)、府前公园(1929)、龙王庙花园(1933)、蠡园(1941) 和不完全对外开放的湖北水灾纪念公园(1933),以及襄樊的中山公园、沙市的中山公园、光化县的中山公园等。这些公园多是在原有自然风景区或私园的基础上整理改建而成,此外也有部分是参照欧洲公园的风格而扩建或新辟。
现代城市公园在传承了古典园林基本的设计思想、构景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民主、科学发展的成果。相比较传统和古典的私家园林,城市公园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经过专业的规划设计,具有一定设施和园林艺术布局,以供市民休憩、游览和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绿地。城市公园的特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的开放性、服务对象的大众性、功能的多样性,这些都有别于传统园林。古典园林以私人园林为主,在园林的设计上更注重园林的私密性,更多的是城市统治阶级审美意识的体现。现代城市公园则以广大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强调其开放性。这导致了二者设计理念的不同: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是审美导向型的,现代城市公园是社会文化功能导向型的。作为大众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现代城市公园规模一般较大,而且设计团队专业化,多由城市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为了适应各个年龄段的市民日常需要,城市公园内的设施不再是以修身养性为主的静态景观,而增加了各种各样游乐设施,以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这决定了它在规划和设计上更注重其社会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审美功能反而退居其次。
二、湖北城市公园的兴起和发展
公园作为普通百姓可以前往消遣和娱乐的场所,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引入的。近代城市公园最初兴起于19世纪初的英国,它的产生是为解决当时由于工业化及人口剧增而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工业革命崛起,工业文明带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无节制的掠夺开发也造成大范围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工业的相对集中,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引起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城市超负荷运转,形成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引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对应之策。1811年,伦敦建立了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园——摄政公园,欧美城市公园运动由此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辟设公园可以通过享受空间和美景,消解社会压力、改善城市环境,有助于创建社会、心理和政治秩序,以及塑造城市形态和景观。当时到欧美各国游历的官员和专家、中国留学生亲历了公园建设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福祉,其中就包括后来执掌汉口市政府的专家型官员。
20世纪初公园概念被引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开始蓬勃发展。在北京,由朱启钤倡导,1914年北京社稷坛被改为中央公园,传统的帝制空间秩序被打破。南方的广州,在市长孙科的领导下引入了科学规划思想,成为近代中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发源地。20年代,一系列城市公园相继设立,其中包括湖北的武昌首义公园、汉口中山公园、襄樊中山公园,30年代沙市的中山公园、光化县的中山公园等都已具相当规模。
湖北城市公园的兴建,既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城市运动紧密联系,同时也根植于当时国民革命时期的湖北社会背景。
自1911年以来,湖北武汉地区为北洋军阀统治,市政建设屡受战火、兵变破坏,发展缓慢。1912年到1927年间,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第二次兴办高潮。产业革命使城市化运动不断加快,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使城市迅速膨胀,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肮脏、嘈杂、拥挤、混乱、紧张构成了这一时期汉口城市的基本面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的汉口市政府发动了浩大的公共工程运动,其中包括筹划并开辟公园作为新式的公共文化空间。
1926年国民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汉口市政府,市政建设管理体制已开始初步形成,并迎来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和科技知识的学者型官员。1927年4月、1929年4月两度出任市长的刘文岛,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巴黎大学,具有现代意识,热衷城市建设。他认为“市政要务,首在建设,如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需求其安适,以谋市民之福利”②。面对当时落后的市政建设,刘文岛四处求贤,以求能人志士对于治理新市提出良策,并追加建设费至全市经费的十分之七,积极招聘市政类、工程类人才来建设汉口。1927年,著名市政专家董修甲受其邀请,先后担任武汉市政府秘书处秘书长、汉口市工务局局长、公用局局长以及汉口市政府干事。董修甲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市政经济学学士学位,而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市政硕士学位。董在留美期间,先后受到当时西方最著名的市政专家和教授指导,并深受影响,思想活跃。他于1921年回国,先后在吴淞、上海、杭州等市的市政府任职,也曾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教授过市政管理等课程,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市政专著。他在调查了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的市政现状后,汲取经验教训,并结合汉口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市政建设措施,影响深远。而1932年至1938年担任汉口市市长的吴国桢,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21年在美国爱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并兼修了市政方面的课程,之后继续取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担任汉口市市长期间,同样热心于市政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城市物质环境得到不少改善。
在以刘文岛、董修甲、吴国桢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型官员的倡导和影响下,汉口市政府逐渐确立现代城市体制和专家治市的局面。这些城市管理者上任伊始,便把市政建设包括公园的辟设作为迫在眉睫之事。1929年前,城市绿地作为公共娱乐场所,开始与博物馆、游戏场与戏院、运动场与游泳池一起列入规划。随着规划思想的发展,公园绿地逐渐从最初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项进行规划,以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自然环境及生活环境。1929年出版的《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案》,首次考虑将城市公园作为专项来进行系统规划。同年的《汉口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还写到“公园于都市中如沙漠之泉源,其重要可想而知”,并指出日益增多的市民,在长时间、高强度劳作的工厂和狭小拥挤嘈杂的居所之间,企盼着到大自然的轻松环境中去放松调整。通过设置公园,“市民能得健全之游戏,健全之消遣,其身体可以日强,精神可以日振”。③《新汉口》市政公报明确指出建立公园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犯罪率。此外,《新汉口》还刊载了一系列的文章,向汉口市民介绍纽约、伦敦、巴黎等地的城市公园。其中有一篇翻译了布偌克(Clarence L Brock) 的最新评论,详细论述了1909年至1930年间美国城市公园系统的发展及价值。可以说,政府大力宣传公园在生理、精神、道德、政治等方面的诸多益处,希望通过创建公园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来缓解汉口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努力营造出不同于旧政权时期的新气象。以中山公园为代表的湖北城市公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中山公园的筹划与兴建
无论从公园规模、设计水平,还是从知名度与影响力来看,在湖北的这些城市公园中,当属汉口中山公园为佼佼者。民国年间,除因1931年水灾和1938年沦陷的冲击而短暂关闭外,直到武汉解放,中山公园都是三镇市民举行娱乐休闲和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并成为本地的显著标记和名片。汉口中山公园是中国近代打造城市公共空间中非常成功的案例,其中西合璧的园林风景,淳朴隽永的人文景观,宽阔多功能的运动场地,可以说对后来的城市公园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山公园作为城市公园的一个缩影,其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公园的演变。中山公园在私家园林—西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来。其旧址西园,占地十余亩,是汉口华商、“地皮大王”刘歆生于20世纪初修建的两处私人花园之一,另一处为刘园。辛亥革命后,为笼络首义新贵“将军团”以自保,刘遂将此园赠予当时湖北军政府财政厅长、“将军团”的中坚分子李华堂。此后,李华堂将西园扩建,以太湖石和片黄石构筑大型假山,与周围的溪、岛、桥、亭等相互交融,风景更为秀丽。北伐胜利后,新成立的汉口市政府将西园没收,充作公产,暂且荒置。1928年初夏,留英归国的工程师吴国柄建议,在西园的基础上扩大兴建汉口市第一公园,并将该公园的面积由西园的0.16公顷扩大到12.5公顷,规划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园和“亚洲第一个综合公园”④。该工程由以董修甲为核心的汉口市工务局主持,吴国柄负责设计和修建。1929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并命名为“汉口中山公园”,以纪念“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
作为亚洲一流的综合性公园,汉口中山公园的规模和设计颇为瞩目,时任内政部长蒋作宾曾夸奖中山公园的设计水平说:“我到过欧洲、日本,还没有这么好的公园,回南京要通令全国到汉口考察,提倡建公园、修下水道,以汉口为榜样。”⑤蒋介石到汉巡视,也称赞中山公园的设计很好。中山公园享有如此之高的盛誉,离不开它的设计者吴国柄。
吴国柄,湖北建始人,自幼聪慧。1918年入上海交通大学,1920年考上湖北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英国皇家工程师头衔,并考察过欧美日本各国。⑥当时的英国伦敦市区有几个大公园,如肯斯顿公园、海德公园、绿园、皇宫公园、詹姆斯公园、摄政公园、巴特斯公园、科烈公地等,这些公园在伦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公园有益于当地居民精神畅快、身心健康,吴国柄对此感受颇深。1926年,吴国柄曾以翻译的身份陪同时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工兵上将的徐树铮赴美、英、法、瑞、卢、德、俄等国。在考察军事政治的同时,欧美各国的城市公园,特别是纽约中央公园中游人尽享自然、悠闲漫步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吴国柄回到武汉,惊诧于武汉三镇的落后状况:城市依然落后颓废,与他出国前毫无进步;市民孱弱、散漫而愚钝,他们以抽鸦片、打牌为主要娱乐,白天睡觉;城市里没有公园、树木,百姓甚至春、夏、秋、冬四季都不知晓。吴国柄因此毛遂自荐,向当时立志“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李宗仁提议采取措施改变市民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吴国柄认为武汉地方太大,短期建设和有限的资金并不能立竿见影,当务之急是先要百姓出来见天日,过有太阳的生活,建议“把在欧洲社会上看到的搬回中国”⑦,主张先修建一座公园,在公园里种树栽花,有运动场可以打球,游泳池也可以游泳,大湖可以划船,让人人都可以锻炼身体。这一建议得到时任汉口市长刘文岛等人的大力支持,汉口中山公园便是在此背景下酝酿建立的。
中山公园布局大体分为四部分:湖山景区、原西园景区、几何式花园区及运动场区。湖山景区、原西园景区、几何式花园区位于公园南部,是仿自然意趣的湖山景区以及几何规则的西式园林,而北部则是各式各样的运动场区。
公园正门位于南端,仿英国白金汉宫大门设计,湖山景区、原西园景区和几何式花园位于正门两侧。景区内的湖、山、桥、亭、溪层次分明,跌宕有致,与传统园林的诗情画意和追求视觉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传统园林明显不同的是,除了向公众开放外,中山公园还开辟了广阔的运动场地和健身设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及游戏设施逐渐成为城市公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公园已经从原来散步、闲逛及猎奇之地,转变为迎合积极运动和有组织休闲的场所。吴国柄效仿西方,将西方公园内公众运动场地“搬到”汉口中山公园中。
中山公园的运动场地位于几何式花园和湖山景区以北,辟有儿童运动场、溜冰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骑马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等,并配备了看台、休息室和男女西式中式厕所若干。1933年又在园东北的空地添建一足球场和一条400米的田径跑道,使园地面积增大近一倍。儿童运动场内布置了秋千、滑梯、跷跷板、木马、浪桥等器具,以提倡儿童运动。公园游泳池是当时湖北的第一座游泳池,采用自来水,并定期换水。泳池的西部设普通运动场,既可运动,也可作会场。1933年东部扩建后,该运动场改建成小型高尔夫球场,并在每个洞上面用钢筋水泥筑成著名建筑物的微缩模型,如巴黎的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伦敦的大桥、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等进行装饰,游客可以一边打球,一边欣赏这些建筑物。1932年,吴国柄还在公园维修时新建了“日晷”,不仅成为公园重要景点,也起到报时作用。
汉口中山公园内,规则与不规则元素相并置, 既营造了湖山风景和几何式园林,又配备了丰富多样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并且免费开放,让市民们有地方、有兴致来积极活动,为民众带了截然不同于传统园林的体验,吴国柄将自己对现代公园“公共”和“健身”含义的理解完全体现在中山公园的设计之中。
四、公共文化空间视野下的中山公园
“公园是城市之肺,可以清新空气;公园提供锻炼的场所,可以增强人们的体质;公园让人们与自然的亲密接触,精神焕发,可以取代酒馆成为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场所;公园面向社会的所有成员开放,不同阶层间可以相互接触,相互学习,因而社会张力也会有所消解。”公共步道特别委员会 1833年在其报告中科学总结了公园在生理、道德、精神、政治等方面的种种益处。⑧从公共文化空间的层面来看,由于现代城市公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山公园既是城市娱乐、政治、教育、文化和生活的多功能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各阶层各组织包括普通市民、政府当局、社会团体的重要活动舞台。
首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中山公园是休闲游憩、修养身心的理想空间。
中山公园在都市中创造了一个自然空间,除了怡人的风景和新鲜的空气使广大市民在繁忙都市生活中有了修养身心的好去处,公园设置的儿童运动场、体育设施以及动物园、茶社、照相馆等大众消费场所,也满足了市民对游览风光、体育运动和娱乐休闲的多重需求。中山公园功能的综合化和多元化,使其成为近代武汉三镇及周边湖北民众休闲游憩、愉悦身心的理想空间。
公园中有很多受人欢迎的休闲项目,如游划和品茗。还有参照当时欧美公园设计的溜冰场、网球场、游泳池和大型运动场,更是游客青睐之地,每到运动会时便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但由于体育运动尚未普及,平时来运动的游人大多为外侨或政府官员,本地民众较少。公园也是市民了解外界的绝佳窗口,不少百姓进公园就是为了看热闹、开眼界,比如公园里会放映免费电影或者表演街头剧等,或者去见识譬如“日晷”之类的当时罕见的设施,这些都足以让市民身心得到愉悦和满足。
中山公园能成为普通百姓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主要源于它的“公平性”和“开放性”。与其他公共空间明显不同的是,公园可以免费进入,城市居民,无论贫富,都“相对平等地使用”这一“公共空间”,从而使其迅速成为最受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各色人等特别是下层人民”欢迎的“日常生活之地”。⑨由于受众的广泛性,汉口公园成为改善受众身心健康和精神状态的主要场所。原来习惯于抽鸦片、打麻将的人们,逐渐改掉旧习,开始早起到公园散步、划船、游泳,市民的精神状态由此得以明显改变。在当时汉口市民的眼中,“公园有湖可以划船,陆地有足球、篮球、网球、跑道、动物园、骑马场、溜冰场、儿童游戏场,……设备齐全”;“有钱的人坐茶馆,身体好的到运动场运动,花没人摘,没人随地大小便了,人民接受日常生活教育,井井有条。”⑩
其次,对当局政府而言,中山公园是进行政治宣传的空间和民众教育的重要课堂。
作为大众文化空间,公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表达的场所,尤其是在当政者和设计者眼中,公园更应是培养市民政治情感和情操的平台。中山公园的命名、公园空间与建筑的设计部署及公园的官方公共活动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筹议时的“汉口市第一公园”最终定名为“汉口中山公园”,体现了国民政府通过公园灌输政治符号的意愿。其后在湖北其他地方建立的城市公园,多以“中山公园”命名,比如沙市中山公园、襄樊中山公园、老河口中山公园等,均有此政治意愿。园内设有中山纪念堂,内置总理遗像;还另建中山亭,并建有中山纪念碑,这些政治元素显著的建筑,是园内的“点睛之笔”。作为民国时期全国140多所中山公园中的一所,汉口中山公园的命名和园内建筑的名称,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另一方面则是意欲通过公园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向民众宣传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中华民国的国家观念,从而增强民众对新政府的认同感,强化新政府的合法性。此外,政府当局常利用国庆和总理生忌两日进行民众集会和政治宣教。典型的形式是数万市民到公园参加集会,聆听大人物的讲演。公园运动场“有演讲台,台之后面构成一大圆弧穹隆,使台上演讲或奏乐之声浪集中反射于听众之耳鼓,其功用犹如波音之喇叭”⑪。园内还建有受降堂,这一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园内建筑,记录了国民政府在公园内接受日本投降这一重历史事件。受降堂已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能有效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
汉口中山公园还是一个多功能的社会教育空间,政府在此设立图书馆,供民众普通阅读,以开启民智。社会部汉口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站设于园内,对流动的游人提供文化服务,以提高市民文化素养。作为市政府重要教育机构的汉口市立民众教育馆,积极利用公园的受众广泛性来推广社会教育,提升市民素养。如汉口市第十三民众补习学校也假公园之地办学,开展启蒙识字教育。1948年2月,汉口市立民教育馆在中山公园举办礼俗改良展览会,把民间习俗分为年节、生寿、婚嫁、丧葬、迷信五项分别绘表一张,加以注释并说明改良意见,陈列展览,以引导民众告别旧的生活习俗,采用文明的庆祝方式。后来,民教馆在中山公园图书室附设民教画廊,经常展览古今绘画、木刻、书法、雕塑,供市民欣赏以提高市民鉴赏能力,并实施艺术大众化。
公园的社会教育还体现在对市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和公共精神的养成,从而改良社会风气。为宣传禁食鸦片,以益于市民健康,汉口政府指令公园在醒目处悬挂禁烟挂图。为加强市民的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和运动参与意识的提高,公园经常举行各种运动会、溜冰比赛等公共体育竞赛活动。政府还将赈灾足球义赛放在公园举行,吸引市民前往观看并慷慨解囊,鼓励市民参与救济事务,养成社会责任感。另外,政府还假借公园公共礼堂,公开举行集团结婚典礼,提倡新式婚姻习俗,倡导节约,杜绝婚礼的浪费陋习,以引导社会新风尚。⑫
再次,对社会团体而言,中山公园是提供众多社会资源的活动场所。
公园作为一种价值丰富的社会资源,也成为一些社会机构进行与其功能或职业的相关活动的重要场所。比如驻汉军警常常打着运动、训练的旗帜,请求公园准许部队官兵免费入公园游泳池游泳。学校等教育机构也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如进行游泳比赛、免费参观动物园、采集标本、开展童军夏令营活动等。教会组织则借公园宣讲圣道、发展信徒。中华信义会豫中总会汉口分会每年“趁滠口神学院放暑假之便,特请学员数名短期帮忙布道工作”,在公园宣传圣道。正义力量常利用公园开展抗日宣传。抗日战争期间,汉口中山公园成为抗战宣传的强大阵地。如1938年4月8日,郭沫若、田汉等人在汉口中山公园召集万人歌咏日活动,由冼星海担任总指挥,歌声震撼三镇,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的战斗热情。
五、结语
城市公园对市民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市公园的建立拓展了人的交往活动空间,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社会文化思想的交融和发展,是城市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民国中期,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近代意识和科技知识的学者型官员,为改善湖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民众的精神状态,筹划并辟设城市公园。公园在改善城市外部环境的同时,更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以湖北汉口的中山公园为代表,它既是城市娱乐、政治、教育、文化和生活的多功能平台,另一方面也是各阶层各组织包括普通市民、政府当局、社会团体的重要活动舞台。城市公园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城市的变迁,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湖北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日益受到关注的当下,公园空间的辟设显得尤其重要。相比较时下大多数商业色彩浓厚的新式和传统空间,对市民免费使用的公园空间不仅能美化环境、愉悦身心,更能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对于塑造城市文化品格、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提升地方软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一层面来看,从公共文化空间的角度来考察湖北的城市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注释:
①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城乡建设(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② 《刘文岛之整理市政谈》,《汉口中西报》,1929年4月12日。
③ 汉口市政府工务局编:《汉口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1930年版,第13页。
④ 参见姚倩:《武汉市综合公园发展历程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 武汉园林局编:《武汉风景名胜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⑥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第八卷社会人物大事记》,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⑦⑩吴国柄:《江山万里行(九)——游学归国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外杂志》1979年第4期。
⑧ 参见张天洁、李泽:《从传统私家园林到近代城市公园——汉口中山公园(1928—1938年)》,《华中建筑》2006年第10期。
⑨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⑪⑫ 参见胡俊修、李勇军:《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为表述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