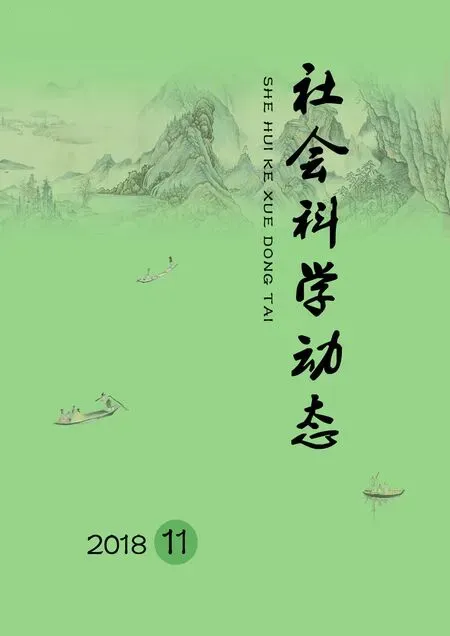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综论之儒家篇(一)
胡 静
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知,一般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念,一种是自然与人相亲的观念,另一种是自然与人对抗的观念。严格来说,这两种观念在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体现着人类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与自然万物万象之间必然存在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倾向,但是总体上,由农耕民族的特点所决定,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这一文化的基调。在本土文化当中,儒家与道家是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文化流派,这两大文化流派均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其思想蕴涵深切的人文关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乃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把握,亦即司马迁所谓的 “究天人之际”而得以展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主义的,自然是文化的价值根据,文化是自然的言说和开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文化必然需要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合理解说,以为其立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我们认为其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的理由。
本文着重揭示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及其特质,道家生态思想资源的阐明将另文撰述。
一、儒家生态思想资源的基本特点
儒学是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总括性称谓。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儒学的理论表达虽然几经调整,但实则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其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奉天承道、仁以施为。也就是说,天道、仁 (有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人是儒学的必备要素。因而,作为儒学基本组成部分,甚至是立论基础和价值根据的生态思想也必然会贯彻这一思想内核与文化精神,围绕天道、仁与人三要素展开论说。这一点也从学者们对儒家生态思想阐扬的角度上得到反映。例如,“天人合一”的角度、阴阳和合的角度、同胞物与的角度、成己成物的角度、顺天守时的角度、裁成辅相的角度、古代生态制度法规的角度,等等。由此我们总结认为,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坚持 《周易》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理念,二是通过 “仁”或 “理”理顺天人关系,三是规范人类活动实现天人和合,生生不息。
首先,就第一个特点来说。 《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其原初的功能是占断吉凶、预测人事。占筮是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构建起某种相对确定的相关性,以实现对人事发展趋势的预测。因此在 《易经》的卦爻辞中呈现了大量时人社会生活的情境,通过对这些经验情境进行想象和体贴,后人就可以较好地理解古人所谓吉凶的基本规定,理解他们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基本观念。 《易经》言简意赅,象意丰富,辞意深奥,给了后人广阔的解释空间,因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更有学者直接指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易文化传统,认为 《易经》确立了 “一个通过数和象奠定的宇宙万有统一于道的系统的认知结构”①,其为后来的文化思想的生发提供了包括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基本逻辑以及思维模式等在内的原始框架, 《易传》则是对这一认知结构与原始框架的集中概说②。 《易传》而后,《周易》经传合体,尊为儒家六经之首,凡欲究天人之际者皆由以阐发。因此可以说, 《周易》奠定了儒家生态思想的基调。
《周易》经传所体现的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基本理念包括: (1)自然与人异体同质、相感互通。(2)自然有着内在的规律性秩序性,人的活动受其规制。 (3)阴阳的动态平衡是实现自然与人持久发展 (生生不息)的根本之道。 (4)自然的运动与人的自主活动是影响人类命运的两大基本因素③。人的活动只有自觉与自然运动相配合,才能成己成物、共生共荣。大概地说,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在 (2) (4)方面多有阐述,强调人的活动要顺天应时,备天之养,全天之功,成天之德;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在 (1) (3)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强调天人相须互动以实现长治久安,并在 (2)与 (4)的基础上将天道秩序拓展到社会生活,确立起三纲五常的社会生态;宋明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对 《周易》思想的阐发,因此从四个方面均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发展出气本论、天人一体论等,使 “天人合一”观念得到进一步的穷究、充实和完善。理学更加突出人对自然之道,即自然运动规律、机制、本质等的认知,而心学更加突出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将天本论导向了人本论。整体来看,与儒学的精神品质相一致,儒家生态思想贯彻了 《周易》的 “天人合一”理念,在对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平衡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承认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又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对于整个世界的现实存在所起的作用不同。自然所行的是无为化育之功,而人所行的是有为参赞之功。没有自然,万物无以为生,没有人万物无以成其所是,因而从人的存在论立场来看,二者皆不可偏废。而对于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从儒家诸子对人性的考察来看,他们又非常重视人性当中存在的与天道相背反的倾向,并将之视为可能导致自然与人均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基于此种认识,儒家生态思想非常强调人的自觉反思和责任担当,这一方面是对人的精神品质的肯定和积极作为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的消极倾向的遏制。
其次,就第二个特点来说。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被贯彻到儒家思想的全部理论当中。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 “仁”有诸多解释,但主要都是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提出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 “仁”主要是就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提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爱是仁的本质,仁之爱并非墨家的兼爱,而是有差等的爱,这种差等主要不是指量上的区别,而是质上的差异,或者说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即先巩固亲亲关系,然后将亲亲关系的相爱模式推扩到其他关系当中。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推扩的机制,才有了将仁爱精神推扩至有关人类生存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当中的可能。 “仁”的范畴并不是从天而降或者孔子凭空想象出来的。孔子对于西周的礼乐制度非常倾慕,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虽然文献显示孔子似乎在晚年才开始重视对 《易》的文本研究,但是西周的文化与 《周易》的人文精神是贯通的,因此虽然仁的直接来源应该归于孔子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本质精神的体悟,但是其间接来源则可追溯到 《周易》的人文精神。事实上,从 《易传》中呈现的孔子对 《易经》的诠释已经可以看出其仁学思想的注入,以及其仁学思想与 《易经》基本理念的内在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主张的仁爱当然又不应仅仅理解为 “泛爱人”,也必然会反哺式地推扩于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达到泛爱天下苍生。诚如戴震所说:“仁者,生生之德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④儒家生态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的。
由于先秦儒家对于自然 (天)的理解具有某种神秘化倾向,视其为既具有自然性也具有人格性的复杂存在,因此由仁出发,人于功利目的上为了自爱 (自保),必须对自然保持敬畏与服从之心,如孔子说 “获罪于天无所祷” (《论语·八佾》)。这里的 “天”既有自然意,也有人格神意,这就相当于承认天命 (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天人关系设定为道之源与道之践行者的关系。为此,人要奉行自然生生之道 (德),不仅对人,而且对自然万物都要心存爱惜护生成全之意,即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宋明学者甚至直接对仁作实体性理解,将仁与植物的果核、种子联系起来,认为仁包含着生意,如周敦颐说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⑤,程颢说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⑥,程颐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⑦,朱熹说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⑧,罗汝芳说 “盖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无处无时,不是这个生机”⑨,诸如此类。由于儒家的仁学与礼学是紧密相关的,仁为礼之质,礼为仁之表。因此生态意义的仁也会通过礼制反映出来。比如祭祀之礼中体现的敬天承祖、慎终追远,实际上就是感激自然与祖先赐予的福祉和给予的护佑;乐礼崇尚的中正平和实则对自然界美好秩序与和谐关系的赞美,正所谓乐者,天地之合;传统婚礼的礼仪称之为 “拜天地”,夫妻双方第一拜就是拜天地,其次才是拜父母和夫妻对拜。这也能够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被赋予了生生之源的重要意义,诸如此类。在政策制度上礼制也要求克制人的不合理的欲望及其为满足欲望进行的不合理的活动,坚持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基本原则,以 “不枉杀”、 “以时禁发”、 “畜养”、 “驯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天人和谐、永续发展。先秦儒家的这种生态思想为后世儒家贯彻始终,秦汉以后自然与人的关系被进一步伦理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 “天子”。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从理论上论证, “天子”之所作所为只有顺从天意,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确保其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否则天就会降下自然灾难,以示惩戒,致使民怨沸腾、政治动荡。宋代张载进一步在形上层面将自然与人的关系界定为亲子关系,称乾父坤母,由此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则为民胞物与的关系。宋明理学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阐明仁的本质、生发机制、价值根据,进一步提出了 “理”这一范畴。他们通过对自然的本质及其运动机制的深入探讨,在为 “仁”提供本体与价值的形而上说明的同时,也清晰地呈现了天人关系的双向互动逻辑。因此可以说宋明儒学的生态思想是儒家生态思想最深刻的表达。
最后,就第三个特点来说。儒家是具有现实主义品质的学派,特别强调在现实生活当中安顿人的精神追求,因此,其理论充满了达则济世救民、穷则明哲保身的基本精神。而真正的儒者同样是彻底的实践派。由此不难想象,儒家生态思想绝对不会只是某种审美意义上的寄情或纯粹道德意义上的空谈。儒家生态思想与儒学其他组成部分是内在贯通的。儒学以仁为本的实践品格可以归结为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明确指出的为仁之方,其根本在于将具有仁之本质的礼作为行为基准,当与外界发生关系时,严守相应的礼,非礼不为。由此,在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也应当有礼可据,非礼不为。这种非礼不为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给人的行为确立底线。此外,义是克己,即规范人类行为的又一准绳,并且由义的界定来说,义更是一种由事物自身所形成的客观规定。 《中庸》说 “义者,宜也”,朱熹说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⑩。只有在行为上遵循礼的规定和受义的制约,儒家生态思想才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
现代人类学家明确指出,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其欲望不止于生理层面的自然限制,而会在人文层面得到无限的拓展和深化,也就是说,人类的欲求会随着自身社会活动 (人文活动)的开展与发展而不断丰富和精致化。人类学家称这种特征为 “非特定化”,实际上就是缺乏先天规定性或者说具有无 “止”性。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特性驱使人类不断创新突破,使得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发展,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种群;但从消极方面看,这一特性也是使得人类不断越出自然生态给定的终极界限,突破维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先秦儒家对人性的看法虽有善恶之分歧,但是他们都不否认现实的人性所呈现的 “恶”,这种 “恶”实质上就是人的这一特性的消极倾向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或许正因为看到了人的无 “止”性的善恶两分,儒家才特别强调不偏不倚,强调中庸。而中庸作为儒学推崇的至德和理想的行为标准,同样要落实到生态领域。所以在儒家生态思想中,既出于保障人类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强调人类应该正确认识、有效管理、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使物尽其用;又出于对人类缺乏先天规定性或者说无“止”性的消极倾向的防范,强调克己节用,推崇朴素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把人生的关注点放在内在精神的提升上,强调精神对欲望的调节和控制力,要求人为自己立法,自觉确立并坚守行为底线。
总体来说,儒家生态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贯彻了 《周易》的生态理念,遵循仁学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在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强调以仁爱之心关照万物,另一个是要求人自身克制欲望,谨慎行为,与万物保持相须以成、和谐共生关系。两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修养工夫,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在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的积极作为的同时,建立并坚守人类活动的底线,才能真正为自然万物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自然万物之间形成一种在资源上的相与,在情感上的相依,在道义上的相须的良性互动关系,恢复自然与人的动态平衡,实现二者生生不息的发展。
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重点方向
截止目前,查阅学界围绕儒家生态思想展开研究的主要对应文献或参考资料,可以发现,学者们通常关注的重点方向包括以下几类:
(一)六经类
《汉书·艺文志》说 “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可见六经乃儒家学者思想生发的园地。六经包括《易》、 《诗》、 《书》、 《礼》、 《乐》、 《春秋》,《礼记·经解》对 《六经》的社会教化功能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区分: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从这一段话即可体会到六经在涵养人的性情和精神面貌,矫正人的行为偏失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自然大美而不言,人才是真正的主导方。所以儒家坚持的先治其人,人治则其事必顺理成章的社会治理思路也被贯彻到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当中。
1.《周易》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具有特殊的文本形式和特点, 《易经》之象意蕴丰富、辞则言简意赅; 《易传》则提纲挈领、思想深邃。 《周易》经传合体,在中国古代,具有成为一切具体科学之指导思想的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当代学者们也从 《周易》中发掘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资源。对 《周易》生态思想的发掘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的:
(1)“生生”。 “生生之谓易”,生生是 《周易》经传所传达的最根本的理念。所谓生生,一方面是指自然万物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一种动态的存在性质。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已经是物自身经历了生发、生化、生物、生成过程之后的现实结果。”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其实可以理解为生生的状态⑪;另一方面指这种存在状态背后的自然机制,也就是《大戴礼记·本命》所说的 “化于阴阳,象形而发”,即源于道之动,先于万物之显形,使万物是其所是的内在机制。 《易传·系辞下》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生非为万物产生之一刹那,而是指 “常生”、 “恒生”,体现了自然万物在阴阳转易、屈伸往复中实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延续,即可持续发展。儒家的仁道本身就取源于天道,因此它也是与生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 “仁者,生生之德也”。所以古今儒家学者都将生生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和精神理念。 “生生”关乎自然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当然也包括人,反过来,人要从理论、从观念层面找到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由,就必然无法绕过 “生生”。由此逻辑, “生生”乃是儒家生态思想的核心资源之一。
(2)秩序与平衡。 《易经》的六十四卦卦象的变化包涵着明确的秩序与平衡观念。而 《系辞传》也已经表明,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创造与推演实源于对天道,即自然运动规律与机制的观察和领悟。秩序与平衡所反映的恰恰是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且也是万物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内在机理。生物界的食物链所体现的既是一种秩序,同时也包涵着平衡。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家独大、无限扩张,万物相须以成的相生关系内在地要通过相克来实现。这正是平衡机制的表现。对这种自然的秩序与平衡状态及其机制的尊重与服从反映在儒家生态思想当中,表现为强调顺天守时各安其位与曲成万物各正性命。顺天守时各安其位,就是尊重并服从自然生命成长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既存在于生物本身的成长过程与条件环境中,也存在于整个生态四时昼夜的交替循环与立体空间的高低层次中。正是在这种秩序性的时空环境下,万物才能获得应有的滋养,完成新陈代谢,实现生生不息的发展。人类也不例外。所以对这种秩序性的尊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一旦其秩序性遭到破坏,则必然带来一系列连锁性的恶果,正所谓“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曲成万物各正性命,就是尊重并成全自然万物的本性,使之各行其是、各得其宜。在自然生命的本性当中已经包涵了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潜质,这种潜质的自然发挥就能够产生平衡的效果,或者说,自然生命形态本身就是遵循平衡机制而产生的,因此恰恰需要使其本性自然地发挥出来,才能够实现平衡。为此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也必须确保万物本性的自然发挥。之所以说曲成,乃是由于人类不是自然,不是天,只能通过知天领悟天意,认识万物的本性,从而 “替天行道”,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使万物各行其是、各得其宜。顺天守时各安其位与曲成万物各正性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顺天守时各安其位已经内在地包涵了对万物包括非生命事物或现象之本性的尊重与成全,而曲成万物各正性命也内在地要求通过顺天守时居其所宜来实现。
(3)天人同源。 《周易》经传以阴阳爻为基本元素,呈现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揭示了宇宙及其自然万物生成的过程、机制、变化特征等等。由于《周易》古经乃为上古占筮卜辞的集成,其本身就是以改善和增进人的生存与发展之福祉为创作目的的,因此可以说, 《周易》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先哲对人之所从来与所将往进行的思考与推演,而其结论就是天人同源,即都是由阴阳交互作用而生成的。在天人同源的主旨观念下,自然万物与人之间在本质上就只可能是一种同根异形的平等关系。从卦象来理解,万物异形及其特质的产生是事物内部阴阳结构排列及其多寡差异造成的,但是由于经由相同的材料 (阴阳)、相同的机制 (阴阳互动)而生成,因此它们在根本上却属于同气连枝。所以董仲舒可以生发出天人感应说和人副天数说,而宋明儒者则可以借由对 《周易》的诠释建立起儒学本体论思想体系。这些都被学者们视为重要的儒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根据。
(4)三才之道。 “三才之道”确切地说是 《易传》对 《易经》所作的诠释。虽然讲三才,实则主要突显的是人的价值。因为天地作为生养万物的基础源泉,对万物包括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而在万物当中,唯有人凸显出来。由于人通过其灵智性与能动性而能够对万物施加非自然的影响,使世界为之改变,其功确实有如天地造物成物,所以人自贵其能,许与天地并列,参赞天地生生之功德。在 《周易》中,人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圣人君子来体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系辞下》)另一面则通过人能够自觉地根据天时地利的条件状况,调整自身的行动,以增进福祉或减少灾难来体现。前者主要在 《易传》中得到强调,后者则可以从 《易经》的卦爻辞获得线索。儒学一直保持着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人的主动作为的积极意义,儒家生态思想也不例外。由三才之道切入,可以很好地阐发在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处理中人类充分发挥其自觉能动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意义。比如荀子的 “明于天人之分”,实质上就是对天人在决定人事发展状态与趋势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加以区别,从而对人及其作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先修其身以仁,涵养自身素质、形成自我约束,再施其为于物。在施为于物的过程中,则要礼法兼备,以确保克制消极作为、发挥积极作用。
2.除 《周易》外,三礼也是儒家生态思想的重要来源。
礼在儒家是一种现实的规制,其本质为仁,是对仁的践履和体现。因此如果说仁道本身源于并且贯彻了天道的话,那么礼也就当然是对天道的贯彻。如上所述,从 《周易》开始,中华文化就展现了对人及其活动的重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结构中,人是最大的变数。所以儒家三礼, 《周礼》从制度层面, 《仪礼》从规范层面, 《礼记》从义理层面分别对人的社会活动及其社会生活进行规制,使人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涵养性情,学以成人——成为能够合理发挥自身潜质,成就人 “才”之质,参赞天地化育之功的人。
例如, 《周礼·天官冢宰上》中十分重视对与人生存相关的生态进行有效管理,包括驯化动物,培育植物,营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等。 《地官司徒》则明确以 “仁者,仁爱之及物也”作为制度制定的依据。所谓司徒 “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众徒。地者载养万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扰万民” (《周礼·地官司徒·郑目录》),简单地说,司徒这个官职的职责就是教育国民在生产生活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包括 “认知地貌生态地理,以教民生产”和 “认知气候生态地理,以建居民居住地”⑩。这些教化活动本身也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教民掌握利用自然事物、现象特点从事生产生活的知识,另一方面对自然事物、现象的特点加以人文转化,使之成为礼的根据和基础,达到移风化俗、涵养民性的效果。这其中包涵的自然与人文相长的生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周礼》中有大量关于生态环境职官的设置,比如 “地官”、 “稻人”、“土训”、 “山虞”、 “林衡”、 “川衡”、 “泽虞”、“迹人”、 “丱人”、 “掌畜”、 “土方氏”、 “雍氏”、“萍氏”、 “秋官”、 “祚氏”、 “薙氏”等等⑪。 这些官职的设立分门别类极尽详备,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自然与人关系及其管理的重视,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礼中的 《礼记》由于以义理为主,因此思想性最强,其中对生态问题有明确而深刻的阐发。如《礼记·祭义》将取物以时提高到伦理层面,指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 “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礼运》中既指出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具有特殊的才性与可贵的价值,又强调要克服人的主观片面,在尊重万物本性与存在事实的前提下施以作为: “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中庸》将天人关系阐释得极为深刻而鲜明,一直成为学者们研究儒家生态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不仅对天道至善生物的状态进行了描述: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且对人如何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之功,成己成物进行了描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月令》则可以说就是在儒家生态观的指导下制定的一系列全年性生态保护规划,其中可见古人生态保护法度的细致,自然也由以得见其所秉持的指导思想。此外,《大戴礼记·易本命》中有强烈的天人感应思想:“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天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甚至还有将人的外表性格等与其世代生活的土地的性质进行联系的奇妙思想: “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虽然缺乏科学道理,但是也并非没有启发意义。这与董仲舒的 “人副天数”的思想极为类似,可以说明汉代对天人关系认知上的共同特点。
3.目前来看,学者对 《诗》 《书》 《乐》 《春秋》四经中的生态思想有一定阐发,但是研究力度和深度尚不够。
《诗经》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古时不同阶层的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在古代人们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极为亲和的关系,人们生产生活于自然山水之间,抒情于生产生活过程之中,因此其中必然包涵了自然与人的互动。如 《诗经·大雅·旱麓》描绘了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色。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对于景色的感受与其社会生活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难想象能够感受到这种景色,并以诗歌的方式抒发情怀的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诗经》中不少诗歌都反映了人与自然愉悦相处、相映成趣的情境,人类寄情于山水之间,不仅能够带来美好的生存感受,而且能够涵养单纯无邪的品格和志趣。诗意的自然是人文化的自然,诗意的人是自然美的人。这其中的生态意义值得我们品味。
《尚书》的主要内容是 “教、典、谟、训、诰、誓、命”,简单地说就是上古时期的政治性纲领、宣言,以及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等,其形式上 “举其宏纲、撮其机要”,目的在于 “以垂世立”, “以恢弘正道示人主,以轨范也”⑬,也就是说主要是为帝王治理国家建立一种典范。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因此在治国理政中必然要涉及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界定。例如 《尚书·泰誓上》说,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句话中就已经包涵了几个层次的生态思想,其一,对 “天”的自然主义立场的理解,即将天地 (自然)作为万物及人产生的源头;其二,从伦理意义上赋予天地 (自然)以父母的地位,使万物包括人具有了本质上的平等基础;其三,凸显了人在自然生态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除此之外, 《尚书》中所反映的周人对 “天”的人格化理解、对天意无情的敬畏意识,以及相应形成的政治思想与政令规范等也具有生态意义,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发掘。
《乐》经虽佚失,但是从其他典籍的记述当中可以知道,儒家所推崇的 “乐”是具有涵养教化功能的,其与礼并称同治,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美好的 “乐”之所以能够涵养性情、教化人心,是因为其具有中正平和的内在精神。正如 《中庸》所说, “中和”乃是天地之所以存在并且能够化育万物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宇宙运动的理想状态。音乐的创造灵感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界美好生态的愉悦感受和各种和谐声音的心理反应与人性解读,反过来,音乐也就能够对人的心理和性情产生影响。而儒家 《乐》教所使用的就是源于对自然精神中正平和之解读的音乐,所以它被认为能够使人洗尽铅华、摒除杂念、返朴归真,获得敏锐的感知力,从而更好地领略宇宙之大美,感受万物之生机。显然,由此切入不难生发出儒家生态美学思想。
《春秋》的内容主要是当时鲁国上层的政治活动及其人物言行。但由于文体为史录,因此其中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还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如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孔子虽然对于自然现象与人的作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联持谨慎的态度,所谓 “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但是考虑到 《春秋》经过孔子的删节和修改,文字精炼,用字意旨深远,具有强烈的褒贬倾向,我们认为不能单纯地去看这些自然现象的记载,而应将其作为与人事相关的自然背景、条件或结果加以理解。由此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梳理出 《春秋》经传中孔子及其儒家的生态思想意识。 (待续)
(本文参阅了大量的文献,是在对比与综合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完成的综论,基本上没有直接选择某位作者的具体观点,如有引用也标明了出处。限于篇幅不另作注释说明具体参考文献。在此对这些在儒家生态思想领域不断耕耘并为本文提供了智力支撑的学者一并表示感谢和敬意。)
注释:
①罗炽:《中国的〈易〉文化传统——关于〈周易〉与中国文化的几点思考》, 《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易传》被指认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可以视之为先秦时期 《易》学思想的集之大成。也就是说,尽管 《易传》晚出,但人们对于 《易经》的运用已经颇为广泛,对其中所揭示的 “易”的本质与精神已经有所领悟。这一点可以从先秦史料及其各家所得出的观点得到验证。学者于此多有论说,此非本文重点,因此不作赘述。
③ 三才中的天地统为自然,因此实际上就是自然与人两大因素。
④ [清]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何文光整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页。
⑤ 《周子通书·顺化第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⑥ 《二程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⑦ 《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⑧ 《晦庵集》卷40, 《四库全书》第1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⑨ 方祖猷等编校: 《罗汝芳集》 (上),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⑩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1页。
⑪ 余治平: 《“生生”与 “生态”的哲学追问》,《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3年01期。
⑫ 参见吉恩煦: 《从 〈周礼·地官司徒〉中观儒家人本生态思想》,载张立文主编: 《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⑬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疏: 《尚书正义·卷第一·尚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