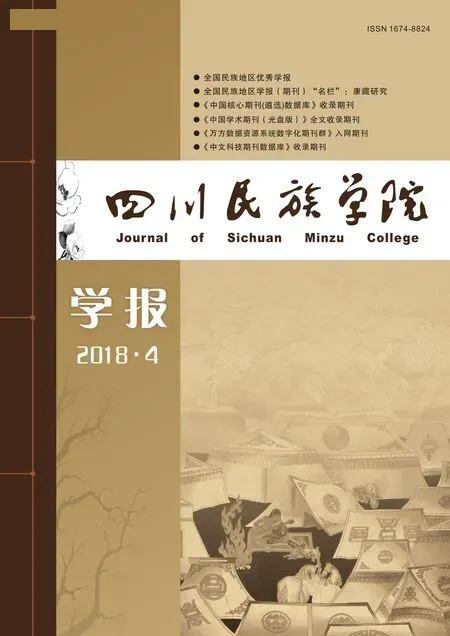根敦群培的斯里兰卡之旅及其记述
增宝当周
引 言
根敦群培以其独特思想、叛逆性格、批判精神及传奇人生成为了近代历史上藏族知识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纵观根敦群培的一生,游学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番经历,尤其是前往南亚游学的经历对他自身的文化视野和思想观念及人格特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南亚游学期间,根敦群培曾一度到过锡兰(即今日斯里兰卡),虽只停留了一年四个月[1],却对他产生了不小影响。
根敦群培域外行游十二年,目的在于考察古代佛教文化,他大部分时间居住于印度。但由于当时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衰落,所以在印度根敦群培虽考察了佛教名胜古迹、印度民俗文化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真切地体验到佛教。与之相比,斯里兰卡自始至终作为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国家,这里的社会制度、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都深受佛教文化浸染。因此,斯里兰卡之旅不仅为作为佛教徒的根敦群培提供了一番与旅居印度时的不同感受,更为他了解小乘佛教、了解佛教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而他本人也在当地学习小乘佛教传统并记述了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事项,为后人了解斯里兰卡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根敦群培有关斯里兰卡的记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和佛教传统,也能看到作为书写者的根敦群培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思想转变。
一
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佛教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小乘佛教传统。自公元前3世纪左右印度阿育王之子来此传教直到今日,佛教一直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宗教受当地人的拥护和膜拜,佛教文化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并与当地人文地理互为融合构成了其独特风格。然而,佛教同样兴盛的西藏却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斯里兰卡是缺乏了解的,在二十世纪前的藏文历史文本中涉及斯里兰卡的记录寥寥无几。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印度学者罗睺罗迎请到印度的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在域外游学期间,为学习梵文、巴利文,了解佛教传统曾前往斯里兰卡并在此居住了一年四个月之久,根敦群培的短暂停留却为两个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开启了一扇窗。在斯里兰卡,根敦群培感受到了浓郁的佛教气息,更触发了他的许多兴趣和感触,致使他以居士身份几乎游历了整座岛屿、朝拜了这里的所有主要佛教胜迹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将个人感悟与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根敦群培对斯里兰卡是有着自己独特情感关注的,而这些体验则集中体现在了《智游佛国漫记》之“斯里兰卡的历史”一章中。
尚未前往斯里兰卡之前,根敦群培一直在印度考察佛教胜迹、学习梵文、了解印度文化并在同伴罗睺罗的推荐下加入了当地的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据唐纳德·小洛佩兹介绍,“1920年代,罗睺罗在摩诃菩提会的资助下在斯里兰卡学习了八个月的巴利文。在印度居住四年后,即1938年罗睺罗邀请根敦群培去西藏西部考察梵文贝叶经返回印度后,他可能强烈建议根敦群培去南部旅行,这或许是1940年或1941年,而他们用的旅行证件由锡金王提供,后者是摩诃菩提会的常任主席。”[2]对此,李有义则说,根敦群培“从加尔各答访问锡兰,是锡金大公的私人秘书若乙巴都给他弄的护照。”[3]无论如何,摩诃菩提会对根敦群培游访斯里兰卡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同样也体现在了根敦群培的思想层面,换句话说,摩诃菩提会的思想宗旨对根敦群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摩诃菩提会的产生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亚洲民族文化觉醒的历史语境分不开,当时“在亚洲发生过一场泛佛教运动……摩诃菩提教会的组织者就是该运动的组织成员。”[4]而“大菩提会和其创建者达摩菩提所倡导的,正是宗教宽容精神,该组织力图通过宽容精神来整合各派佛教势力,凝聚共同力量,以实现佛教的振兴”[5],以便对抗外来文化。根敦群培在《印度诸圣地旅游纪实》的后记中介绍了摩诃菩提会的宗旨,他说:“众佛教徒应当不顾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弘扬佛法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暂由这里的摩诃菩提不断派出精通佛学的比丘,作为佛教使者,前往世界各国讲说法旨,辩论经义和著书立说……同一教派与教主的教友们,敬请参加这里的佛教团体,并竭尽所能,赐与帮助为谢!”[6]他在一首诗歌中同样写到:“斯里兰卡之上座部与雪山中的说一切有部,乃为同一导师之学子,也为十八部派之剩余,而具有四手印之佛陀语,流传于上座部之经典中,故此,我将犹如珍珠藤蔓之信件,寄往雪山中。”[7]由此可见,宗教认同在根敦群培眼里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斯里兰卡的书写中,佛教与历史之间的特殊张力更是构成了他书写斯里兰卡的主体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根敦群培的宗教观。
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只居住了一年四个月,这对他十二年的域外行游而言时间显然并不长,但在这一时段他完成了许多工作,也接触到了之前未能接触到的较多的新颖事物。对此,他自己也说:“在印度逗留十三年,在斯里兰卡逗留一年四个月,在此期间没有休闲地度过一天,那时我以强烈的责任感,希望为西藏做点贡献。”[8]*文中虽提到在根敦群培在印度居住十三年,但事实上根敦群培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地总共居住十二年。在寄往家乡的一封信中他同样提到了自己在斯里兰卡学习的情况[9]。根敦群培游历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时,为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和佛教文化传统他时刻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刻苦学习,而比起印度,斯里兰卡之行对根敦群培而言是一次切身体验异域佛教传统的重要时机,在《智游佛国漫记》中他也多次提到自己在斯里兰卡学会游泳,模仿当地人食用海生动物等的情状,以此突出了他自身以生活方式为主的在文化习性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根敦群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述写了自己游历斯里兰卡时的所见所闻,其大体上从地理、历史、民俗三个层面展开。游记中,根敦群培首先对这个地域的地理空间进行了简约描述,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了他不同的感受。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看到了之前没有见过的许多自然事物,对这里的动植物他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据说他还绘制了一些该岛优美的自然环境、树木、鸟类、寺院、岛上居住的原始民族的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十分引人入胜的生动的图画。”[10]“不少藏人曾见到过一本用藏文撰写、附有大量插图的书,插图绘有锡兰的民俗和生活、‘上座部’(theravadin)僧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各种宗教仪式和戒律(Vinaya)修习。他们简朴的生活,令这位还俗的藏族僧人感到震惊。”[11]而其中有些在根敦群培的图画中是可以看到的[12]。此外,在地理书写时,根敦群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多次提到了义净、法显等高僧的记述并表示十分欣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法显游记中的相关记述和记述方式影响了根敦群培的情感体验和书写内容及其行游心态。
二
如前所述,斯里兰卡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这里有着悠久的小乘佛教历史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斯里兰卡的文化虽经历过一些重大的变革时期,但佛教始终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为斯里兰卡提供了文化上的一脉相承性。对此,根敦群培谈到,自佛陀圆寂不久佛教传入该地,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佛教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特点并保留了许多早期传统[7]。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斯里兰卡之旅不仅使根敦群培体验到了佛教传统,更是让他体验到了一种古朴的、原始的、不同于自身佛教的传统,而这一点恰恰使他倍感高兴。根敦群培说:“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徒的圣地,律藏教义在那里广为传播。每当黎明时刻,寺院仍然像当年佛在世一样,就已有人喊话督促众僧侣:‘死殁无常,即刻到此!’于是人们便都恐惧地从睡梦中醒来,个个都去忙碌佛事。斯里兰卡的世俗人中还有不少居士。不论是比丘、沙弥还是居士,都有各自的修持庙宇。那里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国度,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形成大小不等的礁石上,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凉亭。这些凉亭,如同西藏的修行山洞一样,是佛家的修行之地。”[13]他还说,斯里兰卡所持有的信仰和保存的经典、沿续的传承及佛教寺塔等宗教建筑使这一地区成为了上座部教法的中心。
在斯里兰卡的历史记述中根敦群培突出了这里的宗教性文化,这自然体现着外在社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根敦群培亲眼目睹了佛教对该地域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根敦群培通过当地孩童入学、僧人化缘等场景勾画了佛教在斯里兰卡民间场域中的传承。同样,斯里兰卡民众欢庆宗教性节日和举行佛教供奉仪式的细节也构成了他书写的主要内容,他尤其描绘了斯里兰卡民众于四月庆祝佛陀诞生日的习俗和僧侣结束夏安居时的庆典仪式。“四月十五欢庆佛陀诞生日乃一年中最为重大的日子。此时,孩童们准备好一个小鼓并数着日子盼待时节的到来。黎明时,整个村落歌声、鼓声及问候声遍地,一位孩童被装扮成勋努顿珠的样子,由家人供奉。所有人身着白色服饰,探亲访友。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一座雕像并挂有五彩旗。在房屋前,四五层高的亭院中,通过仪器展示佛陀从天而降的诞生传记……”[7]“当夏安居解制后,临近的俗人们聚在一起,举办袈裟节。那时,男女老少们都半夜起床,整齐排列,手持油灯,每个人头顶一个较大的盆器,里面装有用作袈裟的白色布料,他们唱着各种声乐围绕当地的佛塔转圈朝拜,最后来到寺院向每位僧侣进献……总之,袈裟节对小乘佛教而言,是一年中最隆重盛大的仪式。此后直至晌午,所有人一起缝制袈裟、染色,后献给僧伽,再献给比丘。此仪式极为动人,我感触颇深,故此记录。”[7]关于斯里兰卡寺院及僧侣生活方面,根敦群培记录了佛堂内佛像的陈列,以及当地比丘们的洗漱、饮食等日常生活细节,在一种田野民俗志式的记录中为我们了解斯里兰卡佛教民俗提供了一幅可观可感的图景,从中我们能窥见当地民众的知识和社会文化。
斯里兰卡佛教中巴利文文献构成了其独特的经典系统,保存了较多的佛教的原始教义。根敦群培在游记中叙说了小乘佛教经典的大致内容并将其与大乘佛教经典进行对比指出了一些看法上的差别。根敦群培进一步说,“一般而言,小乘佛教的历史以一般性论述展开,在谈及佛陀的功绩等时是极其动人的,然而,大乘佛教所言由于深广宏大,因此,除极其聪明或极为愚昧者,而非一般人所能理解。”[7]根敦群培还说,小乘佛教的经典书写于佛陀圆寂五百多年之后出现,对于佛教史小乘佛教说法不可或缺,而由于佛教有不立文字之传统,小乘佛教当中的许多教派因此也就销声匿迹了。此外,根敦群培极度赞同小乘佛教的纪年历法,说此前藏族历史上萨迦班智达等人对小乘佛教历算的批判不符合事实。
斯里兰卡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派别,历史上在斯里兰卡也兴起过大乘佛教。对此,根敦群培说,“在斯里兰卡喜好大乘佛教者也比较多,历史上这里也确实兴起过大乘佛教,然而,众多僧侣对于金刚乘或密宗佛教表示不满。”[7]通过这些记述我们不仅能看到斯里兰卡的佛教叙事传统与历史沿革,也能发现根敦群培面对差异时的反映,尽管在小乘佛教难以接受大乘佛教方面根敦群培表现出了些许悲伤,但总体而言,斯里兰卡佛教使他倍感喜悦,为他留下了深刻影响[14]。总之,比起在印度,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感受到了异域佛教,尤其学习并体验到了小乘佛教传统,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使根敦群培找回了佛教信念[2]。在游记中根敦群培写到,自己虽早已不是僧侣,却有缘来此地记述[7]。由此可见,根敦群培对斯里兰卡佛教进行观照是一种在佛教文化内部进行文化双重确认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激发了他对佛教文化的再度认同和对其进行探寻的思想。
根敦群培记述斯里兰卡是想为西藏读者提供一种理解斯里兰卡及其佛教传统的途径,也是在两者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策略。在游记中根敦群培以反语式的言语表达了佛教内部应该相互理解、团结的看法。他说:“一方面手持黑色托钵者(斯里兰卡佛教)对万事充满猜忌,而另一方手持骨号者(西藏佛教)总是仗势欺人,因两者都顽固不化,故暂时只在各自地方处事,不忘佛陀与教法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7]同样,在斯里兰卡期间翻译的《法句经》后记中他也谈到了这一意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根敦群培十分强调佛教宗派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内部对话。此外,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遇到了欧洲佛教僧人并说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情况。是以,根敦群培不仅强调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与宗派之间的平和,更是对狭隘的地方主义、排外思想和妄自尊大的优越心态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反帝反殖民运动的文化浪潮中,根敦群培对摩诃菩提会的宗旨,即佛教不同派系之间的互补和关联是有着深刻体会的。他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分析,就是一种对佛教传统的再度认同过程。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不仅凸显了根敦群培的佛教认同,更体现了他在遭遇殖民帝国时,反思传统并希望从传统中汲取滋养的态度。
三
记述斯里兰卡历史时,根敦群培参考了当地的口头历史及《大史》《岛史》《王史》等历史文献,并通过田野考察历史遗迹,以佛历时间勾勒了斯里兰卡历代主要帝王的历史[7]。在此类历史叙事中,根敦群培较为简略地论述了斯里兰卡的一些主要国王及其政绩,突出了王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斯里兰卡的民族起源,根据巴利文史书《大史》记载:印度孟加拉一位美貌的公主与狮子结合生下王子与公主,王子从母亲口中听闻人间的繁华后便带母亲和妹妹来到一个叫做剌拉的地方,成了这里国王。他有很多王子,其中一位因违抗父旨流放边地,于是乘船来到了兰卡岛,成了这里的第一个国王,建立了狮子国[15]。佛陀圆寂二百七十一年后印度阿育王登基,此时阿育王派人向周边传播佛教,国王将受具足戒已有12年的王子摩哂陀派到今日斯里兰卡之地传播佛教。在这里王子摩哂陀得到了斯里兰卡第七代国王噶尔杰的支持,王室中出现了第一个比丘僧并修建了佛塔。此后公主听闻佛法,欲出家为比丘尼,便从印度迎请了摩哂陀的妹妹来此受戒,由此斯里兰卡出现了第一个比丘尼。在历代国王的扶持下,佛法在这里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先后从印度获得了菩提树枝和佛牙,与邻国印度也建立了密切关系,佛教慢慢变成了斯里兰卡最主要的宗教。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除了个别国王推崇婆罗门教外,佛教的主导地位几乎得到了政治上的保障,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由于斯里兰卡佛教的兴盛与王室政权的支持息息相关,因此,佛教与斯里兰卡的政权相辅相成,宗教为统治提供了方便,也由此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尤其印度佛教没落后,斯里兰卡成为了佛教的重阵地。根敦群培说:“自佛陀圆寂后不久此地出现佛教直到变成这样一个现代国家,僧侣们一直讲修三藏,俗家人也秉承着佛教传统,因此,该地在佛教国家中如金冠般夺人耳目。”[7]“当作为我们父辈家园的摩揭陀被外道之妻与欧洲之夫所占领,变得破败不堪时,我们现需要将以南方海洋岛国斯里兰卡来替代它们的位置。”[7]
随着斯里兰卡各历史阶段政权的跌宕起伏,佛教也经历了一个坎坷发展的过程,尤其在十六世纪后,斯里兰卡相继受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的统治,此时由于殖民者企图使当地人接受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殖民者在当地开办西方学校、推广基督教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为抵制这一举止,十九世纪在斯里兰卡发生了一场保护佛教、复兴民族文化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事件是当地佛教徒古那热那与基督教徒之间的一场辩论,结果是古那然那战胜基督教徒,使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斯里兰卡人改信佛教,很多佛教徒恢复了自己的宗教信心,这一事件激发了斯里兰卡民族文化复兴的觉醒意识,推动了当地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根敦群培从自己的老师确吉嘎瓦那里听说过这一人物,也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在游记中阐述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时,根敦群培就例举这一人物,以此批判了西藏当时的愚昧,认为斯里兰卡虽提倡佛教,但并没有拒绝科学[7]。由此而言,根敦群培所具备的南亚尤其是斯里兰卡体验佛教的经验,对他关注佛教和振兴佛教有着深刻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根敦群培关于科学的论述实则是为了振兴佛教,为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探寻出路,努力扩大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的一种实践。因此,这不仅是根敦群培信仰佛教、维护佛教的表现,更是对当时所处时代价值观的一种积极回应。可以说,根敦群培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关注是一种对当时世界社会剧烈变革的积极回应,而他也希望通过这种回应来探索西藏佛教的出路,所以在《智游佛国漫记》的结尾他再度强调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借鉴意义。故此,学习并书写斯里兰卡历史使根敦群培对该地区的体认更为强烈,对佛教历史发展有着以个人丰富情感为依托的洞察及其价值关怀,而根敦群培的此类书写恰恰包含了他对当时西藏本土佛教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本民族的、自身身份的深切认同和在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忧患意识。
概言之,根敦群培对斯里兰卡历史的叙述不仅依托于当地巴利文史料的运用和个人田野考察与发现,更有着自己对异域历史的感悟理解与理想寄托,因而,在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能发现作为历史学家的根敦群培的历史思考和历史认知的情感维度。
结 语
斯里兰卡之旅是根敦群培域外行游时期的一个重要时段,在此他不仅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翻译了佛教典籍《法句经》,查阅了巴利文《大史》《岛史》等历史典籍,更以切身体验感受了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因此,斯里兰卡之旅是根敦群培游学过程中一次感受佛教文化传统、反观自身文化的重要阶段。当然,在二十世纪初亚洲反殖民运动高涨,现代性冲击十分突出的变化巨大的时代,身处不同地理空间不仅使根敦群培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也促使他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这个层面上,斯里兰卡之旅,深刻地影响了根敦群培对佛教历史文化和当时现实处境的观照方式与文化态度,也为他在历史与他者中理解本土传统、理解佛教、感受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