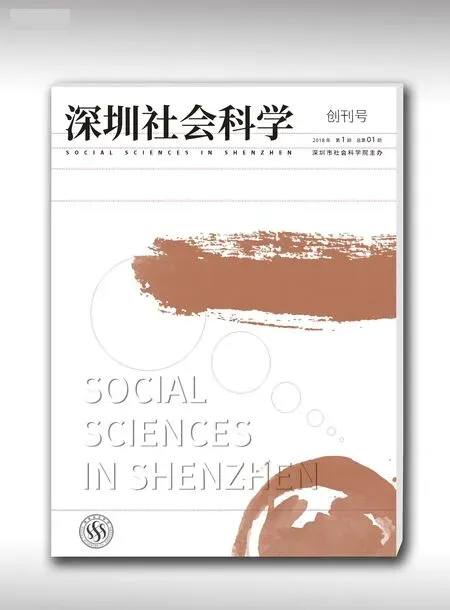“慎独”“自反”与“目光”*—儒家修身学中的自我反省向度
陈立胜
在《荀子·不苟》《庄子·大宗师》《管子·心术》《文子·精诚》与《礼记》之《中庸》《大学》《礼器》三篇等传世经典以及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与郭店竹简《五行》中,都出现了“慎其独”或“见独”一类的“独”文本,这无疑表明“独”的观念乃是先秦儒道二家工夫论之共同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岛森哲男就指出,在先秦儒家的慎独文字之中,“独”字提出的背景通常是设定了除了自己以外、无他人在看这一场景。为何慎独的要求通常是在这种场景下提出来呢?这是缘于“对人性的洞察或危惧而来”,因为“人类会因为他者的在或不在而改变态度,尤其他者不在时,人性有容易偏向恶的倾向”,故在慎其独的文本之中,“潜虽伏矣,亦孔之昭”的说法便格外抢眼,这是一种“从外部而来的锐利的视线”,是“鬼神的视线”,慎独文本之中浓厚的他者的目光这一思想氛围,“显示了他者的视线对自己渗透的深度,以及人生活在共同体中彼此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对社会归属感稀薄的我们,有时也不得不感受到这样的视线,更何况对于紧密生活在共同体的古代人来说,必定更强烈感受到视线的威力。”①岛森哲男:《慎独思想》,梁涛、斯云龙编:《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慎独问题讨论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笔者认为,岛森哲男对慎独文本之中的他者目光的阐述,对于我们理解儒家的省身工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实际上,在儒家修身学中,无论在慎独要求抑或在“三自反”的主张之中,都设定了一种“他者的目光”,这个他者的目光首先表现为“鬼神的目光”与“他人的目光”,而随着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勃兴,他者的目光渐被每个人内在的“心目之光”“良知之光”所替代。在儒家修身工夫的“反省”向度之中,“鬼神的目光”“他者的目光”与“良知之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一、“鬼神的目光”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之两面性:在众目睽睽的“前台”,自我容易配合观众目光的“角色期待”,而表现出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之一面,及至退至“后台”,则容易暴露原形,显示出私小之面目。《慎子》有句话就生动地描述这种人性的“双面”:“能辞万钟之禄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无人之地;能谨百节之礼于庙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独居之余。盖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因“朝陛”与“无人之地”、“庙宇”与“独居之余”场景之转换,人之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反差:在权力之大庭与神圣之空间表现光鲜动人,在隐秘与私己之场所则寸利必得、放肆无忌。《慎子》这里所描述的人性现象属于典型的“人莫不自为”、“每狎于所私”这一人性丑陋的一面,同样的观察也见于《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如何克服此人性之有限性?一个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让行动者始终保持活动于“前台”、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之感受。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这强烈地暗示出一种通过公共的目光审视自家之“过”的省思模式,就如同在都市行走的今人无时不感受到既高清又无死角的全程监控一样。于是,老子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是的,今天大陆都市的监控系统就叫天网工程。不过古人的天网工程的主角不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而是比摄像头更加神奇的“鬼神”:《诗·大雅·抑》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的临在不可揣度,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亦描述出古人对这种“目光”的敬畏、忌惮之感受。《墨子·天志上》指出,处家、处国虽“共相儆戒”“不可不戒”“不可不慎”,但得罪于家长,犹可逃往邻家,躲避家长之惩罚;得罪于国君,犹可逃往邻国,躲避国君之惩罚;而得罪于天,则无所逃避:“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逃避之者矣。”(《天志下》)因为“鬼神的目光”无处不在(《明鬼下》):“子墨子言曰: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毋(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堇),见有鬼神视之。”②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大盛,人之罪行,天必知之、感之而诛伐之。《淮南子·览冥训》云:“上天之诛也,虽在圹虚幽闲,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新书·耳痹》亦有类似的说法:“故天之诛伐,不可为虚幽间,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庄子·庚桑楚》也说:“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显明”处人之目光与“幽闲”处“鬼神的目光”共同交织成为无处、无时不在的“他者的目光”,让人在行动的每一刻都有被人神共同关注(“明乎人、明乎鬼”)的感受,惟如此方能做到郭象注中所说“幽显无愧于心,则独行而不惧”。显然,《庚桑楚》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庸》的说法,林希逸就说:“如此之人,所为既不善矣,非有人诛,则有鬼责,言幽明之间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则能谨独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后能独行。此即‘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独也’。独行,即慎独也。似此数语,入之经书亦得。”①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口义校注》卷23,中华书局,1997年,第360页。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后(一作‘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中透露出“人的目光”的有限性,理学家张履祥就撰诗驳正曰:“周公自有周公志,王莽终怀王莽情。勿谓隐微人不见,千秋公论日星明。”②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题王介甫诗后》,《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9页。此白居易诗自明代即被误传为王安石所作。“他者的目光”成为超越时代的目光,换言之,“隐微”之事纵一世不为人知,却最终也难逃“千秋公论”这一“历史目光”的审视。
在这样一种“他者的目光”的浓厚文化心理氛围下,《大学》之“慎其独”的郑玄之注也就不难理解了:“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可以肯定的是,郑玄将“独”训为“闲居之所为”,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看来还是与这种无处不在的“他者的目光”相关。实际上,如果我们浏览以下郑玄前后的思想家对“慎其独”文本的理解,都可以看到它们都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情之所忽”有高度的警惕:
刘向《说苑·敬慎》: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隠,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诚无诟,思无辱。”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③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240页。
《后汉书·杨震列传》:(王密)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④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7册,中华书局,1965,第1760页。
徐干《中论·法象》: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夫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胡可简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蔽,鬼神不得见其隙也。《诗》云:“肃肃兎罝,施于中林。”处独之谓也。⑤徐干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第25页。
“隐微”、“幽微”、“孤独”之处是常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能够在此处“敬慎”,方可称为君子。杨震暮夜却金故事明确指出,夜晚所发生之事除了当事人知道之外,还有“天知”与“神知”这一无处不在的超越性的“知”之向度。徐干则将君子敬孤独慎幽微与“鬼神不得见其隙”相提并论,再次展现“他者的目光”之无所不在性。其后,《刘子·慎独》更是尽畅此鬼神目光之旨趣:“居室如见宾,入虚如有人。……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显;昏惑之行,无有隐而不彰。修操于明,行悖于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则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则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盗钟掩耳之智也。”这里的着眼点仍然还是幽暗之处的举止(“行悖于幽”)。郑玄着重从闲居之所为训“独”良有以也。
能够在“幽闲”处、“屋漏处”、孤独幽微处贞定其心志的人格称为“君子”,《淮南子·说山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这种独立不改、表里如一的君子人格也正是儒家“慎其独”工夫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一语早见于《晏子春秋》,及至《文子·精诚》,则将“不惭于影”直接与“君子慎其独”联系在一起:“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违其难也。君子之憯怛,非正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圣人不惭于景,君子慎其独也,舍近期远塞矣。”章太炎将儒家的慎独观念追溯至晏婴,不亦宜乎!①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79~980页。实际上,《论语·乡党》对夫子行为之描述,无论在乡党抑或在朝廷夫子之行为表现出修己以敬的高度一致性,无疑是慎独工夫之典范。
《中庸》之中浓墨重彩的“鬼神的目光”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殷周鬼神文化的遗留。“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昭,见也。文王见于天,且在帝左右,文王显现于天、与帝同在的画面无疑折射出的是先民对祖灵与上天的仰视与敬畏之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管四方,求民之莫”(《诗经·大雅·皇矣》),“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诗经·大雅·大明》),“敬天之怒,无敢豫戏”(《诗经·大雅·板》),由《诗经》中的这些篇章可以管窥先民对一种自上而下的、威慑性的、监视性的鬼神目光之感受。只是这种宗教性的“他者的目光”在文明的轴心期突破的过程之中,经过儒家人文主义的洗礼,而逐渐内化为一种“天命意识”、一种“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德性生命意识。故儒家“慎其独”之“独”在本质上乃是天所赋予的内在的“德性”及其栖息之所(“内心”),用孟子的话说是“天爵”“良贵”。诚如岛森哲男所指出的,这种指向内在良心的目光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独’”,它有别于“他者的目光”这一消极意义上的“独”,“积极意义上的独”则表现为“自己本身成为视线的主人,用内省的视线来规律自己。也就是所谓‘毋自欺’(《大学》)、‘自谦’(《大学》)、‘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中庸》)的立场。”②岛森哲男:《慎独思想》,梁涛、斯云龙编:《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慎独问题讨论集》,第16~17页。而这种“内省的视线”与孟子反身而诚、求其放心的工夫取向紧密相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基于内在的存养之功所呈现的“恒心”自是一浩然之气之道德场域,美、大、圣、神则是其华彩流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儒家对“独处”行为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后来的理学修身工夫实践之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最隐秘的夫妻生活、床第生活也成了“鬼神的目光”的场所。颜元有“闺门之内,肃若朝廷”之说,李二曲更是称:“闺门床第之际,莫非上天昭鉴之所,处闺门如处大庭,心思言动,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③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96年,第420页。吕妙芬《成圣与家庭人伦:宗教对话脉络下的明清之际儒学》一书(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六章第二节(“广嗣与寡欲的夫妇生活”)对此有生动描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对“独处”这一严格要求仅限于“修己”这一自我关涉面向(用孔子的话说是“躬自厚”),它绝不意味着对他人隐私的干涉,相反《礼记》之中不乏对他人隐私保护之礼仪,如“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礼记·曲礼》中的这一行为准则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而《韩诗外传》所记孟子与孟母之对话则表明《礼记·曲礼》的这一规定由来已久: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①韩婴:《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七章,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322页。
君子必须对他人独处之隐私保持足够的尊重,“箕踞”本是一非常不雅之坐姿(古人上衣下裳,箕踞极易露出私处),孔子老友原壤箕踞以待,就被夫子斥为无礼并以杖击其小腿(《论语·宪问》)。
二、“他人的目光”
在儒家的省身传统之中尚有另一种“他者的目光”,这种“他者的目光”乃是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之中、在人际的互动之中所遭遇到的“他人的目光”。这种“他人的目光”虽然也往往让我感受到不适、不安,但它有别于“鬼神的目光”,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视性的、威慑性的目光,而是与我的目光平行的、向我表达某种不满的目光,是让我感到受冷漠、怀疑、蔑视、鄙夷等等的目光。在先秦的政治哲学之中,人们往往把这种“他人的目光”视为君主、为政者获得清醒的自我认识之不可或缺的借镜,《墨子·非攻上》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国语·吴语》亦有“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之说,这些说法的意思不外是在他者的反应(目光、表情、举止)那里认清自己的“欠缺”与“亏欠”。而在儒家这里,这种日常的“他人的目光”则应成为君子“反身而诚”的一个契机,这是先秦儒家“自反”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又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离娄下》)《荀子·荣辱》也有类似的说法:“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而《荀子·法行》则明确引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显然孟子的三自反思想出自曾子,实际上,曾子三省工夫(《论语·学而》)未尝不可视为是一种自反工夫,这是一种事后的自我省思②《大戴礼记》有两处文字暗示三省的工夫乃是在晚上进行的:《曾子立事》记曾子语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又《曾子制言中》:“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国语·鲁语下》对“士”一天修身内容所做的以下描述:“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则可以断定曾子三省工夫即属于“夜而计过无憾”一类的士之修身活动。,而三省之对象均牵涉到对待他者的态度。这些看法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及颜子“犯而不校”这一要求上面。可以说“自反”乃是先秦儒家修身工夫的共法。实际上墨子亦分享儒家这一自反的修身理念,其“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墨子·亲士》)即是夫子恭厚薄责之义,而《墨子·修身》更是指出,君子如见不修行、见毁则应“反之身”。“仁义忠信”这些德目所涉及他人的态度最终都是由内在的心性向度发出的,需要省思的是这个“内”之向度是否是由衷的、真诚不妄的,如是,则是“动以天”,用孟子的话就是“诚者天之道”;如否,则是“动以人”,则须反身而诚,此为“思诚者人之道”,《荀子·不苟》中以“诚心守仁”、“诚心行义”来指点“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之工夫,跟孟子“反身而诚”的工夫也是高度一致的,学界在追溯孟子诚身工夫时往往指出子思的影响,此诚然不错,但论起源头当应进一步上溯至曾子之自反的工夫论这里。
人之生存于世,其目光通常是向外的,寻视于周遭世界之人与物:“行路”寻视着远方与脚下,“生产”寻视着工具与活动所关涉之对象,“交往”则寻视着各色人等,诸如此类。而在交往活动之中,眼神的交流通常或是向对方表达我们的意图、诉求、情感,或是透过对方的眼神而力抵其内心世界。在我们遭遇到对方不屑、不满、愤怒的表情、目光之际,或是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甚或加倍奉还,或是躲避,惹不起,躲得起。惟在儒家“自反”的要求之中,我们则顺着他人向我表达不屑、不满、愤怒的表情、目光而关注到“自我”,“他人的目光”成为我心灵生活的一面明镜,他人的眼睛成了我自己心灵生活的窗户:我藉着这个窗户看到自家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这种“内视”乃是一种“审视”:我对他者的关爱是否是真诚的?我对他者尊敬是否是自然的?一言以蔽之,我内在的德性世界究竟有无欠缺以及有何欠缺?
孟子的三自反要求本是极高的道德自省要求,但后儒有不若颜子“犯而不校”之高明之疑问(杨时即有此疑问,见朱子《论语或问》卷八),对此冯少墟辩解说:“曾子说‘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学者泥其词,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说。若是果能自反,则横逆之来,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别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处。昔人谓孟子三自反不如颜子之犯而不校,误矣。”①冯从吾撰:《少墟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9页。少墟对“犯而不校”与“自反”之关系辨析甚精:“世之犯而必校者无论,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样: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颜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横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兽也,何足与之校!如此,若与颜子不校一样,不知这样不校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把人都当禽兽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颜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后之说,是又以不校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说,正在精微处辨毫厘千里之异耳,犯而不校谈何容易!”同上书,第90页。不过孟子“比妄人为禽兽”的说法还是遭到后儒的批评,认为“英气太露”,王阳明说:“孟子三自反后比妄人为禽兽,此处似尚欠细。盖横逆之来,自谤讪怒骂以至于不道之甚,无非是我实受用得力处,初不见其可憎。所谓‘山河大地尽是黄金,满世界皆药物’者也。”②王阳明撰,吴光、钱明等编校:《新编王阳明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00页。
当然阳明后学之中也有不认同阳明之批评者,如面对门人对孟子三反之后比妄人为禽兽之如下质疑:“孔子于君子既断谓之‘无争’,孟子亦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大率修身为本故,是洙泗相传之家法也。决无有向人分上校计之理。何三反之后,乃曰:‘如此,则于禽兽奚择焉?又何难焉?’此其绝人也得无已甚,而自反之道尚为未至耶……”,李见罗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给出了以下回应:“经创知惩,遇跌长智。自非身履其境,亦谁识孟子立言之意于自反乃最深切乎?偶记二十载前,曾同从兄迪菴看山。抵山落步,为骡所踶。予时负痛之甚,手自拊摩。迪菴兄亦就摩之。乃直悔其落脚之失支持,而曾不以一语责及于骡也。予因嘻笑曰:‘予乃今知禽兽何难,孟子之非轻绝人也。至于自反而忠而曾莫之省焉,是真犹木石禽虫之蠢然无知识者矣,而尚可责乎?是正教人以自反之至,到底不以纤毫之意气涉向人边也。’”①李材:《教学录》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1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52页。毫无疑问,围绕孟子三自反工夫所展开的讨论,反映了理学自反工夫日趋细腻与严格之趋势。
三、“良知的目光”
在儒家的反省工夫之中,还有一种“目光现象”值得留意,这是由“三自反”而推衍出一种自我审视的目光,曾子的三省、孟子的三自反实际上有一理论上的预设,即有一反省内视的主体可对其内在的心灵生活加以审视、检查。罗近溪即揭示了这一现象:
诸友静坐,寂然无哗,良久有将欲为问难者。罗子乃止令复坐,徐徐语之曰:“诸君当此静默之境,能澄虑反求,如平时躁动,今觉凝定;平时昏昧,今觉虚朗;平时怠散,今觉整肃。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彻,则人人坐间,各抱一明镜在于怀中,却请诸君将自己头面,对镜观照,若心事端庄,则如冠裳济楚,意态自然精明;若念头不免尘俗,则蓬头垢面,不待旁观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顷刻安耶?”或问:“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镜否?”罗子曰:“此个镜子,原得于造化炉中,与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纤毫瞒他不过。故不忠不仁,亦是当初自己放过。故自反者,反其不应放过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后因反己乃知也。”②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页。在罗近溪的描述之中,让我们照见自己的镜子不再是“他人的目光”与“他人的面容”,而是每个人抱于怀中的“明镜”,这面镜子“与生俱生”,故是先天本具的;“不待人照而常自照”;故是独立的、无待的;“人纤毫瞒他不过”(“心目醒然”),故是不可欺的。它所照出的乃是内外一如的自家面目:“心事端庄”则“意态自然精明”,“念头尘俗”则“蓬头垢面”。而“自反者,反其不应放过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后因反己乃知也”表明:“念头尘俗”、“不忠不仁”,则是自我放纵之结果,用王阳明的话说,不忠、不仁之念起处,“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自反”即是返回到这一“不应放过”的“自知”向度。近溪的“明镜说”充分显明,良知乃是内在的、先天本具的、恒常的,完全超越了人己、共处独处之对待的“光之体”。近溪“良知光照”说可溯源至阳明处,昔南大吉向阳明问学,自述临政多过,为何阳明无一言及之,阳明答曰:“吾言之矣”。大吉不解。阳明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始恍然有悟“良知自知之”之说。其后,大吉屡屡向阳明坦诚其过,并有“身过可勉,心过奈何?”之请益,王阳明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③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2006年修订版,第415~416页。
而在刘蕺山的静坐讼过法之中,这种自我审视的“良知的目光”与“鬼神的目光”、“他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道“内在而超越”的强光,具有照彻心灵整体的透视力: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鉴临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尔固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兽乃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应曰:“唯唯。”复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视,皆作如是言,应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发颊,若身亲三木者。已乃跃然而奋曰:“是予之罪也夫。”则又敕之曰:“莫得姑且供认。”又应曰:“否否。”顷之,一线清明之气徐徐来,若向太虚然,此心便与太虚同体。乃知从前都是妄缘,妄则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无来,随之无去,却是本来真面目也。此时正好与之葆任,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如此数番,勿忘勿助,勿问效验如何。一霍间,整身而起,闭合终日。①刘宗周:《人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6页。
这里,“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乃是要营造一种静谧的宗教氛围,“平旦”这一时间点的选择是考虑到孟子“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告子上》)这一说法,这是最适合省察与涵养的时机。“鉴临有赫”无疑四字衍自《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乃是指是指“鬼神的目光”,而“十目十手”则又系“他人的目光”与指点,显然这是“鬼神的目光”与“他人的目光”共同交织而成的“良知之光”,其实质是要达到“通身是眼”②“通身是眼”一说出自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4,中华书局,1996年,第37页。之效果,良知之为高悬的明镜,如洋洋在上的目光,如十目十手之所睽、所指,我全幅的心灵生活完全暴露在良知的强光聚焦之下。在刘蕺山的静坐讼过仪式之中,儒家的反省的理论结构已经昭然若揭:
(1)“超越于我”的目光之永恒在场(鉴临有赫、十目十指),在此威慑性氛围下,“良知的呼声”乃是类似于审判官的严厉的声音。
(2)“鉴临有赫”的目光虽超越于有待审判的习染之我(客我),但又不是一完全的“外在之超越”,究其实,它不过是“内在”于我的“独体”“良知”之光照。质言之,在这一虚拟的审判法庭之中,诉讼者与应讼者是同一个当事人。
(3)在严格而逼真的审判氛围下,意识生活之中各种疾病,特别是积淀、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宿疚”成为反省、省察之对象。
(4)反省、省察乃一种道德上的审判、一种心灵的拷问(“若身亲三木”),作为“良知呼声”的被呼唤者成了一位“有罪者”、一位“被审判者”。
(5)反省、省察过程本身既是一“审判过程”又是一当下“执行过程”,是一“治疗过程”、一“涵养过程”,朱子那里省察与涵养工夫在此融为即省察即涵养的工夫:一边省察(“痛汗微星,赤光发颊”),一边涵养、“葆任”(“一线清明之气徐徐来”、“一真自若,湛湛澄澄”)。
论者(牟宗三、王汎森等)或将刘蕺山的这种静坐讼过法追溯至佛教的《法华忏仪》,或认为它跟西方式灵魂审判(the soul on trial)有相近之处③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31页。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4页。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4.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5~346页。,确实,旨在转化自我的反省法在世界各大宗教传统之中本是一“共法”。其实在儒家传统自孔子提出“内自讼”的要求后,这种自我审判的反省方法就一直是儒者修身一个重要工夫,王阳明“倒巢搜贼”式的省察之功已经为刘蕺山静坐讼过法的出场做足了铺垫工作: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①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2006年修订版,第75页。在这里,良知之光照(“一眼看着,一耳听着”)被拟为捉贼的捕头、捕鼠的猫之锐利的目光,而潜藏在意识生活之中的“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则被拟为贼与鼠,于是,自我省察与反省成了一场捕头捉贼、猫捕老鼠的游戏。在良知“知是知非”的光照下,如贼、鼠一样潜伏在暗处的私心杂念遂暴露目标(“一念萌动”)而自投罗网(“即与克去”)。
而早在程子那里,心灵生活自我澄澈的工夫就与鬼神的目光、上帝的目光的绾结在一起:
“忠信所以进徳”,“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②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终日对越在天”“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说明君子进德修身的实践活动始终是在一“上帝临在”(“上帝临女”)的场域之中展开的,而“敬”(“毋不敬”)之工夫最能保持此心灵生活的肃穆、严谨与神圣性。毫无疑问,在程子那里,“对越在天”首先是在心灵的自我澄澈之中敞开的,朱子就说“人心苟正,表里洞达,无纤豪私意,可以对越上帝,则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又告诫门人“今且未要理会到鬼神处。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则万理毕见……”③《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84页。朱子鬼神观研究可参吾妻重二:《朱熹的鬼神论和气的逻辑》,吾妻重二著、付锡洪等译:《朱子学的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1~155页;吴展良:《朱子之鬼神论述义》,《汉学研究》31卷第4期,2013年,第111~144页。这种重在心地上用功的路径跟道家中“神明来舍”的观念是相通的:“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管子·心术》)“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庄子·知北游》)理学家所说的敬的工夫与庄子所谓的“心斋”工夫确实有某种对应性,吴与弼“精白一心,对越神明”④吴与弼:《康斋集》,《四库全书》,第12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575页。的说法更是与庄子“虚室生白”、“鬼神将来舍”的说法(《庄子·人间世》)如出一辙。不过在理学家的对越上帝的论述之中,“对越”一词逐渐具有了“面见”“直面”“面对”的意思⑤翟奎凤:《“对越上帝”与儒学的宗教性》,《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中晚明省过工夫之中“上帝的目光”(天之灵光)与“心灵的目光”(心之灵光)的交织就折射出这一现象,而刘蕺山的静坐讼过法无疑是其经典案例。牟宗三先生在论程子“对越在天”的观念时指出,“对越在天”有“原始之超越地对”与“经过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性而为内在地对”两义:
凡《诗》《书》中说及帝、天,皆是超越地对,帝天皆有人格神之意。但经过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性,则渐转成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义,超越的帝天与内在的心性打成一片,无论帝天或心性皆变成能起宇宙生化或道德创造之寂感真几,就此而言“对越在天”便为内在地对,此即所谓“觌体承当”也。面对既超越而又内在之道德实体而承当下来,以清澈光畅吾人之生命,便是内在地对,此是进德修业之更为内在化与深邃化。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6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5~26页。
就刘蕺山静坐讼过法而看,牟先生的观察还是很精准的,一方面,“鉴临有赫”、“十目十指”的说法确实强烈地营造出“鬼神的目光”与“他者的目光”于我个己心灵生活的“超越性”,在此“超越于我”的他者目光注视下,“我”成了一个被审判者,然而另一方面,这一“目光”又出自“我”的“良知独体”,这并不是一种完全异在的目光。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出于我”(此为“内在”)而又“高于我”(此为“超越”)的目光。这种“出于我”而又“高于我”的结构,倒颇有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中对“此在”(Dasein)的良知呼唤现象的描述:“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此在”既是呼唤者,又是被召唤者,良知的呼声“出于我而又逾越我”,由于良知所呼唤的乃是“此在”“本己的能在自身”,而这种本己的能在自身在“常人”状态下被遮蔽、被压抑已久,故良知的呼声于此在听来竟然像是一种“陌生的声音”,“呼声不是明确地由我呼出的,倒不如说‘有声呼唤’”。刘蕺山“鉴临有赫”“十目十指”的说法也是在营造一种“陌生的”“超越”于我的效果,但这个“逾越”的光照实际上是出于我的良知独体,所谓“造化鬼神不必事,吾心之鬼神不可不事”②刘蕺山:《答履思二》,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第310页。,吾心之鬼神即此“鉴临有赫”之谓也。在此良知独体的自我透视下,遮蔽我、扭曲我的“常人”格套被彻底剥落,最终我认出了我的“本己的能在本身”(“本来真面目”)。
不过,在明清之际省过思潮愈演愈烈的局势下,儒学阵营之中确实不乏将“对越上帝”观念重新恢复“原始之超越地对”之尝试。李二曲说:“知鬼神体物不遗,则知无处无鬼神,无时无鬼神。人心甫动,鬼神即觉,存心之功,真无一时一刻而可忽,故必质诸鬼神而无疑,方可言学。”他还批评后儒淡化鬼神的观念:“夫子赞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说体物而不遗;乃后儒动言无鬼神,启人无忌惮之心,而为不善于幽独者,必此之言夫。”③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30,第421页。
结 论
1.“鬼神的目光”是无人之际、独处之时一种超越的监视目光,“我”是这个目光聚焦下的“行动者”,“我”之举止与众人共处之时完全一样,不欺暗室,因为“暗室”本不暗,“鬼神的目光”在严厉地盯着“我”(“举头三尺有神明”),故在“鬼神的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必须……”(I must)这一当下的行为期待,伴随这种期待而来的是“我”当下小心翼翼的举止。
2.“三自反”处境下所遭遇的“他人的目光”是一种责备的目光、令“我”不安的目光,“我”顺着这个目光返观内视,“我”是对某一行为(“横逆”)的“负责者”,“我”对自己适才对待他人的行动加以省察,它所省察的对象是“我”之内心世界对他人不满、愤怒一类的负面的目光与表情究竟负何种责任、“我”在哪些方面本应做得更好而未能做好,故在三自反的“内视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本应该……”(I should have)这一对适才发生的行动之反省,伴随这种反省而来的是愧疚感(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3.静坐讼过之中自我审视的“良知的目光”(“通身是眼”)是一种审判的目光,“我”是这一目光下的“有罪者”“被审判者”,面对这一鉴临赫然之光,“我”全盘交待出自己心灵之隐情(以往的不当行为、宿疚、各种各样潜存的私心杂念),“我”是聚光灯下的被审判者,当然“我”又是审判者:“两造当庭,抵死雠对”,故在自我审视的“良知的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认罪……”(I confess)这一对心灵生活负责的忏悔态度,伴随着这种忏悔而来的是精神生命的重生。
4.这三种自我省思的模式各有侧重,“鬼神的目光”让“我”在独居、暗室之中的行动与在大庭广众下的行动一样保持一种连续性;藉着“他人的目光”“反观内视”,则旨在对自己行动背后的情感、态度、动机加以检讨,让“我”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真诚的道德行动者;出于良知的目光的自我审判则是一种专题化的荡涤心灵染污“心理治疗术”。三者之共同的旨趣均是通过省思而培育一德性人格,一无计顺境(“得志”“达”)与逆境(“不得志”“穷”)、独处(“幽闲”)与共处(“显明”)始终如一、表里如一的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