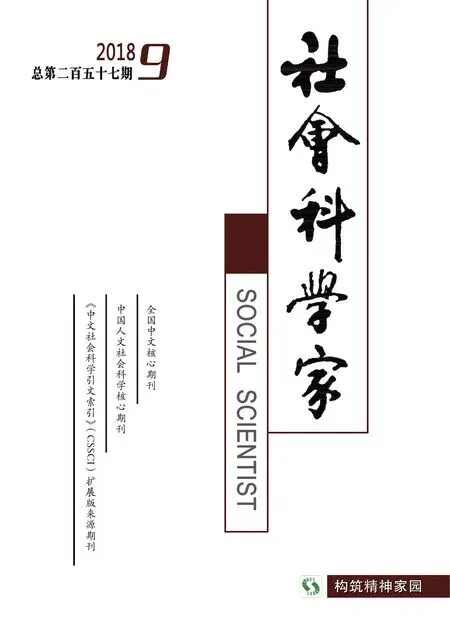党项民族的法律演进:西夏法律历史沿革与多元文化属性形成
于 熠
(1.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上海 730070;2.湖南师范大学 法治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6)
党项最初是以唐所属藩镇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然而由于唐末田制的崩坏,社会呈现纷扰的乱象。五代时,各路诸侯粉墨登场逐鹿中原,无暇西固,这为党项的生存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党项的首领正是能够抓住时机,在这种复杂的周边大国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立国途径,最终得以建国。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西夏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元昊既“慕中原文化”,同时自诩党项拓跋氏本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故更具正统性。因此,在西夏建国后,执政者:一方面,以吸收汉族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法律改革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注重对党项民族的习惯法律的传承和改进。通过法律、军事、官制、风俗、宗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得西夏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体现了“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理念。
陈景良教授曾经讲过:中国古代地方法制假如客观存在,应当以何种视角进行切入,研究的范围如何确定,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中国古代各民族不仅有自己的传统、风俗、法律习惯,且文字也不相同,把他们纳入研究的范围,固然丰富了研究视野,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问题。这些少数民族法制无论是法律表现形式,还是司法的运行等问题都无法完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该成果的理论解释力,也使该成果虽具有系统专题之名,实缺独到之实。本文试从西夏王朝法律历史沿革出发,梳理各时期立法特征与王朝盛衰的关系,总结党项民族法律演进的特征,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夏法律文化和规律奠定基础。
一、王朝奠基与法律依从习惯、制度简约(公元881年-公元1032年)
公元756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在这一动乱时期,党项人在河西地区开始乘机向周边扩张,并一度联合与其有着罅隙致其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吐蕃。拓跋思恭在从长安回夏州的路上路过了一个名叫统万城的废城,引发了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政治设想,于是将统万城修葺一新,并以之为中心发展夏州,任命管理、征收租税,开始了立国的最早实验。如果从此时(公元881年)拓跋氏“王其土”开始计算,整个大夏国长达347年(公元881年-公元1227年)。
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西夏的党项民族与同时期的汉族相较,无论是经济、文化,抑或是社会生活方面都比公认的“中原文明”诸方面均“落后”一些。如史书记载党项人: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其俗淫秽蒸報,于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①(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0;(唐)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8.5169;(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七[C].北京:中华书局,2000.286;(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八[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1755.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②《北史》,“大”作“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1]这种落后的印象是建筑在共识性的“中心论”和“正统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受到外族叛乱及欺凌的刺激和因科举制度发展后,“中华”逐渐形成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对传统文化热爱以及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体系的建立。
公元1004年,李继迁率军攻打潘罗支误中弩箭,伤重不治。在弥留之际,李继迁将其子李德明叫到身边,提出了立国策略:“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2]同时还对多年来竭力辅佐自己的张浦等人进行了叮嘱:“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2]可见“倾心内属”为韬光养晦之计,“负荷旧业,为前人光”才是此后两百年的根本任务。李继迁撒手人寰后,其子李德明谨记此两条,使其父辛苦打下的江山不至于丧失殆尽,且能够“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夺凉州、攻甘州、收瓜州,“经谋不息”,统一河西地区。一种以党项为中心的“西夏意识”在拓跋氏的心中开始酝酿、发展。与唐末五代时期的“向背不常”不同,此时的党项民族意识核心不断凝聚,独立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二、西夏建国与法律“尚武重法”、“礼从汉制”(公元1032年-公元1086年)
公元1004年,李继迁去世了,但党项拓跋氏未竞的事业还需要继续。与李继迁的强硬不同,李德明在遵从父亲教诲积极向中原“倾心内属”的过程中打破了赵宋统治者的戒心,双方大量的贸易往来过程中也使李德明强烈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在要求其子元昊认真学习党项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掌握中原文化,识广且博。这种教育思想使得元昊自幼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常携《野战歌》(军事书籍)、《太乙金鉴诀》(占卜书籍)。”[3]为其此后成长为一位文化上的通才、政治上的奇才、治国上的异才、军事上的天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元昊在战争岁月中逐渐成长,“圆面高准,身高五尺余,性沉勇刚毅,多谋略”,屡立战功。然而就在公元1032年10月元昊攻下凉州城后,李德明竟然兴奋过度而一命呜呼。史载,李德明薨,“皇太后至幕殿,释常服,白罗大袖、白罗大带,举哀如皇帝仪。”[4]作为鹰派领军人物的元昊,终于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同年11月,元昊继位,宋朝降诏,“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5]受封后,元昊对属下说:“我的父亲错了,现如今我们已经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和军事战力,为什么还要臣服于宋呢?”根据外交惯例,由于大夏国此时仍为宋的地方政权,因此,宋国的使臣应当代表中央朝廷居中而坐。元昊对此甚为不满,想要独坐主位。经使臣杨告再三劝阻,元昊才没有“违礼”。但此时,雪耻的信念已经在元昊的心中膨胀,于是“更祖宗之成规,藐中朝之建置”,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通过“尚武重法”,以期达到两个功效:一是移风易尚,改革党项不适宜的民族习惯,形成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整合各部,愿意效忠自己的,便笼络重用,离心离德的,就借助法律大开杀戒;三是巩固根基,妥善处理疆域内“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的复杂民族矛盾。在典章制度方面,元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第一,改姓正名。尽管公元991年,宋王朝曾赐李继迁姓赵,但基于各方考虑,无论是党项内部,还是契丹人,对于李继迁一族仍沿用“李”姓①尽管经历了五代十国,且赵宋已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在北方少数民族心目中,李唐仍为正统,沿用“李”姓更利于党项拓跋氏聚拢外来者。此外,在李继迁的心中,并没有真正承认过宋朝的宗主国地位。。元昊耻于宋所赐的“赵”姓,而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立地位,也断不能沿用“李”姓,因此下令将党项皇室姓氏改为“嵬名”,元昊自称“兀卒”。
第二,建章立制。元昊固然对宋没有好感,但因其自幼学习中原文化,使其真切感受到中原制度的先进性,故仿宋制,推行职官改革,为了表现出该制度的西夏属性,元昊将所有名称都匹配了一个党项称呼。
第三,颁“秃法令”。元昊要求党项族恢复在青藏高原时与鲜卑先民融合后的发型——秃发,达到区别于其他草原部族的鲜明标志的作用,三日后不听从命令的,允许众人将其杀死。
第四,区分衣冠。将蕃、汉人员服饰给予区分,要求汉人官吏必须戴汉式头巾,否则要给予重罚。②官员罚马一匹,平民打十三杖,参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第五,皇帝装束。冠用金缕帖间起云,银纸帖绯衣,金涂银带,佩带蹀躞解锥、短刀,弓衣穿(革华)耳,重环紫旋襕,六袭。
第六,皇帝出行。出入乘车马,张设青色伞盖,以二旗在前引导,有百余名骑兵跟随。
第七,重定兵制。民众年满十五岁为壮丁,每家有壮丁二人的“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其余的人仍然得为“丁”做杂役,学习作战技巧。“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只要成为正军,均给长生马、驼各一匹,“死则偿之”。团练使以上,帐、弓各一副,箭五百支、马一匹、橐驼五匹,旗,鼓、枪、剑、棍、棒、沙袋、雨毡、浑脱、背索、锹钁、斤斧、箭牌、铁笊篱各一。(《隆平集》载:凡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这里与《宋史》‘夏国传’有出入)。[6]此外,刺史以下军官,“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匹、箭三百支、幕梁一。兵士则三人共用一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之。)有炮手二百人,号称“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汉人中勇敢健壮的为前军,号称“撞令郎”。倘若胆怯且没有其他的技能,则令其到肃州去驻守,或迁到“河外”耕作。合国内诸州计之,总兵五十余万。(《隆平集》载:赵德明时兵十万而已,元昊遂逾十五万。自以地广兵劲,敢行叛逆。)”“别立擒生军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担。另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蕃宿卫,月给米二石。”“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经常用疑兵之计,“遇敌则虚设寨帐”,将伏兵埋伏在敌人的身后,以“铁骑”为先锋,驾驭良马,用钩索绞联起来,“虽死不坠”,身披重甲,可以保护身体“斫刺不入”。“其兵凡三千,分十部,战则先出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发兵则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白天则举烟扬尘,夜晚则以篝火来进行传递信号。出兵的日期一律选在单日,回避晦日③以十日当中的五个单数日为阳日、刚日、奇日,单日吉利;五个双数日为阴日、晦日,不吉利。。供给的军粮不超过十天的用度。如果有战事则大将居后,或据高险。“弓,皮弦;矢,柳簳;中之必贯甲。”[7]由于兵多将广,为了便于管理,元昊还设立了左右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驻天都山);曰“石州祥祐”(驻石州);曰“宥州嘉宁”(驻宥州);曰“韦州静塞”(驻韦州);曰“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曰“卓罗和南”(驻黄河北岸);曰“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曰“甘州甘肃”(驻唐删丹县故地);曰“瓜州西平”(驻瓜州);曰“黑水镇燕”(驻兀剌海城);曰“白马强镇”(驻盐州);曰“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东北限大泽,西北接沙碛)。每一监军司设立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各一人,“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8]
第八,更定礼乐。夏州建立时,党项族一直沿用其传统习俗来进行祭拜。从拓跋赤辞降唐开始,学习唐王朝各项尊卑祭拜的礼仪,直到北宋建立时,党项的祭祀音乐还留有唐代遗风。李德明秉承李继迁的策略内附宋朝后,开始“遵依宋制”。元昊认为中原的仪式不足以效法,因此对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我断没有学习的必要。于是,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亨的礼仪进行了改革,把需要九拜的礼改为三拜。(这种仪式就是《梦溪笔谈》中所讲的“元昊令国中悉用胡礼”。)此外,元昊还“革五音为一音”。此后,西夏的礼乐就一直沿用这种标准。为了使这种礼仪得以贯彻执行,“令于国中,有不尊者,族。”[9]
第九,创制文字。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帝国的雏形日渐显露。然而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土地上,文化的发展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走向。元昊正是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与其他国家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自己的文化载体——政令的下达需要文字,党项族数千年所奉行的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族群的优秀传统无法流传,未来的发展壮大同样需要依靠文字来记录。于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奔赴宋进行考察。野利仁荣回到西夏后汇报:我们正在以及将来做的事都是我们的祖先所没有做过的,这一切都是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创制自己的文字?在这样一种思考下,元昊下令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文字定位“国字”,要求国内所有的文字诰牒都要使用这种文字。为了规范这种文字,元昊专门设立了“蕃字院”和“汉字院”,将西夏文演绎成为篆书和隶书。“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6]
公元1038年10月,元昊南面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三足鼎立的局面自此开始。然而,从第二代皇帝夏毅宗嵬名谅祚开始,西夏便陷入“母党”与“后族”轮流掌权,同皇族争夺利益的政治漩涡中。在这一时期,掌权的女人将鲜血和长刀作为至爱,而皇帝则胸怀仁爱谋求和平,推崇中原文化。一时间,“诸梁(两任梁太后)恣横,国中皆危之。”但这并没有拖垮刚刚起航的西夏巨轮,究其原因乃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目标一致——务实改革,锐意创新——皇族短暂强盛时期进行制度的改革,如改蕃礼为汉礼,大量任用汉人官员,划分地界,恢复榷场交易等,为以后的鼎盛奠定政治和经济基础。更注重军事战斗力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保留马背民族的能征善战的传统。
三、王朝鼎盛与法律“尚文重法”“内兴改革”(公元1086年-公元1193年)
公元1086年,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嵬名乾顺继位。然而,实权仍由毅宗秉常的寡妻——西夏历史上的第二位梁太后把持。梁太后崇武,乾顺尚文,治国之道南辕北辙。根据西夏的法律规定,男子年满15岁就认定为成年人,但直到公元1099年,嵬名乾顺仍无法从其母梁太后手中接过皇权。此时表示出强烈不满的力量主要来自辽国,由于辽道宗对于梁太后的专权以及好战十分厌恶,恰逢梁太后在向辽国上书中言辞颇为不恭敬,成为了辽道宗对梁太后起杀机的导火索。辽道宗派人在梁太后的酒中下毒,结果一杯毒酒结束了西夏第二位梁太后把持朝纲的局面。16岁的嵬名乾顺终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看上去温顺的皇帝,骨子里充满了智慧,一路在宋、辽、金、吐蕃四方势力之间游走,在地理版图上,(从蒙古戈壁到青藏高原,贺兰山、祁连山和六盘山交织成了西夏独特的地理风景)西夏走上了巅峰时期。梁太后当政时期,由于常年对宋用兵,导致两国罅隙加大。乾顺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弥合这种裂痕。北宋元符(哲宗年号)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西夏崇宗向北宋修和,哲宗敕夏国主乾顺:省上所表,具悉。尔国常乱,历年于此,迨尔母氏,复听奸谋,屡兴甲兵,扰我疆场。天讨有罪,义何可容!今凶党翦除,尔既亲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尔改图,故从矜贷。已指挥诸路经略司,令各据巡绰所至处,明立界至。并约束城寨兵将官:“如西人不来侵犯,即不得出兵过界。”尔当严戒缘边首领,毋得侵犯边境。候施行讫,遣使进纳誓表,当议许令收接。[10]宋提出了条件,即处死屡次侵犯宋朝边境的西夏大将嵬名保没和结讹遇。嵬名乾顺思虑再三,随着这两个长期对宋主战派的将领被处死,西夏进入到了新的治国策略时期。
1.“尚文”而不废“武备”
崇宗时期,嵬名乾顺注重对党项民族精神上的改造,废除了元昊设定的“尚武重法”的“武法”治国策略,转而走向了“尚文重法”,“国中建学养贤,不复尚武”的“文法”治国策略上。对于这一策略的改变,西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曾上书提出过异议,主张“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显然,在长期受到梁氏集团的压抑下,充满逆反心理的嵬名乾顺很难再认可“尚武”的观点,史书记载“乾顺善之,不能用。”然而,嵬名乾顺此时的“尚文”并非不要武备,时任都统军镇衙头的乾顺庶弟察哥曾建议言:“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11]察哥的建议得到了嵬名乾顺的认同,于是封其为晋王,掌握军政大权,不止吸收中原王朝的文化,更吸收赵宋的军事技法,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尚文”方面主要表现在始建国学。由于在元昊时期,统治者大力倡导党项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下,西夏在中央机构中创建了“蕃学”,导致“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12]对此,嵬名乾顺深感忧虑。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道:“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遵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士人,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13]在薛元礼的力荐下,嵬名乾顺创建“国学”,尊崇儒家学说,储备高等人才。“较谅祚之用汉礼、求赐书,不更有进耶?”[14]尽管嵬名乾顺奉行“尚文重法”的策略,但其始终没有放弃“武备”,使党项族内部“尚武”之风得以保留,在位的50余年间,西夏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扩张。应该说此时的西夏,文武兼备,面对虎狼近邻的觊觎下仍能够游刃于夹缝中。特别是在处理“国学”与“蕃学”的问题上能够做到吸收中原文化但又不失民族的根本,西夏终于迎来了其辉煌的顶峰。然而,西夏被后人颇为诟病的“朝秦暮楚”外交政策也始于此时。在不断变换“臣宋”和“臣辽”过程中西夏虽然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但也给其他政权以无法信任之感,且在获得广大疆域之后仍然要找“靠山”——“臣金”,而始终没有以自立自强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元昊时的独立外交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异。无怪乎清代学者吴广成评论道:“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然受辽国百余年卵覆之恩,宜水一败,遽尔反颜。则前之问起居,请临幸,诚耶伪耶?当是时,地界扼阴山以北,马足遍关陕之西。方谓借兹新盟,大启尔宇,而难生天德,兵聚云中。向之,臣宋、臣辽,惟吾披猖者;至金,而故技莫施焉。四川之使,悔亦晚矣!惟是元昊制蕃书,立蕃学,久绝风华;乾顺建国学,置养贤务。他时仁孝重圣亲贤,贻谋有自。亶其然乎?”[14]
2.“文法”改革
公元1140年,嵬名乾顺驾崩,享年56岁,夏仁宗嵬名仁孝继位,此时已年满16周岁。嵬名仁孝与其祖父、父亲幼年继位的情形有着显著差异,此时没有了“后党”专政,一开始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施政。为了吸取前朝的教训,刚办完国丧嵬名仁孝就颁旨“两母并尊,奉养礼秩如一。”[14]但坚决不允许她们干政。嵬名仁孝刚继位时,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中国的版图呈现了西夏苦心经营百年后所迎来的南宋、金以及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这其中又有着微妙的外交关系。迅速崛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横亘在西夏与南宋之间,看似三足鼎立,但实际上西夏与南宋进行马匹交易换取必需品的道路被金截断,而西夏亦在金的包围之中。为求自保,仁孝选择了“附金”和“附宋”的国策,在实际的执行上,这一国策贯穿于其执政的54年中。在经历了两代梁太后专权之苦后,嵬名仁孝决定进行改革,以求“革故鼎新”。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嵬名仁孝,认为暴民的出现乃党项族传统的陋习所致。为了革西夏一时之风气,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尚文重法”推行到了极致,吸收中原文化在嵬名仁孝看来是首要任务。西夏人庆(仁宗仁孝年号)二年(公元1145年)七月,西夏仁宗下诏“初立大汉太学。仁孝亲视奠,赐予有差。”[15]“初立”说明了这种设置始于仁孝,“亲视”在表明了君主的诚心。次年(公元1146年)三月,(嵬名仁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15]尊孔子为文宣帝,“为世教振颓风,以圣学维国本,乃偏霸中罕觏者”。[16]嵬名仁孝的这一举动就连南宋王朝的儒学知识分子也颇为吃惊,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孔子尊崇到皇帝的位置。从西夏君主到地方官吏,乃至平民百姓,都对孔子进行祭祀并顶礼膜拜,标志着西夏吸收中原文化的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这一活动也使得身为游牧民族的党项人身上所具有的肃杀之气被渐渐从民族文化中清出,取而代之的是彬彬有儒者之礼。公元1148年3月,嵬名仁孝又下令设立内学,并亲自挑选儒学名士承担授课任务。由于从夏至宋需经过金国领土,公元1154年9月,夏仁宗又派人到金国,请求在夏、金交界处设立书事,用以出售西夏翻印的儒学方面的书籍。公元1161年1月,西夏的最高学府——翰林学士院在仁孝的授意下设立,这一机构不但成了统治者的智库,更为随时选拔官员提供人才储备。
为了广开言路,嵬名仁孝十分赞赏北宋开国君主所定下的直谏文官的举措,且身体力行的去付诸实践。公元1162年,夏仁宗为了“上无匆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移中书、枢密院与内门外”,[15]以便顾问。时任中书令的斡道冲就是这一时期文官直言劝谏的范本。史载斡道冲“先世灵州人,祖从德明迁兴州,世掌夏国史职。道冲年五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17]被封为蕃、汉教授,更晋升为夏国相。直到元代,斡道冲仍被尊为一代儒学大师。以国相斡道冲、中书令嵬名仁忠、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御史中丞贺义忠等位代表的文官集团为西夏开创了开明的政治风气。嵬名仁孝采用“以儒治国”为“尚文重法”的核心,倡导以仁孝治天下。著名的传世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是在这一时期制定颁布实行的。通过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带有鲜明儒家色彩的“十恶”重罪、“八议”、“官当”的特权规定、《节亲门》中的“丧服制”乃至婚姻关系中的“七出”与“三不去”都被党项人吸收内化在其本民族的法典当中。笔者之所以用“吸收”与“内化”来表现西夏法律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乃源于党项人的立法仍是在立足于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习惯的基础上。此外,在嵬名仁孝时期,“崇佛”的观念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也得到了罕见的广布流传。著名的“帝师”制度就是在这一阶段首创的,宗教对于西夏法律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大大加深,无论是在民众间的信仰传播,还是法典中的宗教规定,都为西夏打上了佛的烙印。
应该说从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中原文化来看,嵬名仁孝的这一文化和制度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之处就是成功将一个“蛮夷”民族驯化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准谦谦君子”。然而,这种改革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对内,这种“以儒治国”仁孝行天下的文化倡导使得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臣属也会惯性的讲“君臣之义”,在不断忍辱退让中导致内乱丛生,险些中期亡国。期间,嵬名仁孝的岳丈任得敬阴谋分裂夏国所带来的危害就是最好的诠释。对外,长期过分的“尚文”使得党项民族“军政日弛”。以武立国的马背民族党项族,在文化的改革中蜕变为了一个文弱的民族。“可怜无定河边骨”既是宋人的一曲哀歌,更是党项族的彪悍、粗犷的写照。但之后的西夏抵御外敌的侵略能力被严重损毁,在外交政策的失误下,使其丧失了鼎足三方的局势,更在蒙古铁蹄的踩踏下显得几乎全无还手之力,最终在蒙古人的屠城中灭亡了。西夏这艘万吨巨轮行至夏仁宗时期,在新一轮的改革中,迎来了一个文官政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但同时也泯灭了党项族人的原始血性,更掘掉了西夏帝国的英武之魂。
四、王朝衰败与西夏法制消亡(公元1193年-公元1227年)
如果说西夏这辆战车的创制始于李继迁、李德明,则将这辆战车推到历史前台的则是元昊。在百年的发展中行至乾顺时期终于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仁孝在位时为其进行了文化改造,行至巅峰靠刀剑,成就辉煌靠文化。元昊的谋臣野利仁荣曾论及兴(兴庆府)、灵(灵州)立国之大势:“一王之兴,必有一带之制。议者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义可敌哉?”[18]他早在西夏建国之初已为西夏开出了兴国之良策,然而,行至仁宗时期,这一策略被完全打破。西夏中期的文化改造为西夏埋下了衰弱的隐患,以至于温良恭俭的纯祐皇帝被其生母为了试图恢复祖先的血性而狠心拿下。但一切都已经太晚,来自北方的蒙古已经将刀口对准了党项民族。从公元1193至1205年的12年间,西夏桓宗嵬名纯祐坚定不移地奉行着仁宗的“尚文”方针,对内安养民生,对外附和宋、金。然而,北边不时有蒙古的骚扰,国内在吸收了中原文弱之气的同时更弥漫着奢靡贪腐之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大量人才的流失,种种困扰使得西夏的经济、文化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夏襄宗嵬名安全的附蒙侵金的错误路线使得原本已衰落的军队战力“精锐皆尽,两国俱败。”公元1207年,夏襄宗嵬名安全思考着如何防御蒙古,而成吉思汗却在考虑着怎样攻打西夏。无奈,西夏的“铁鹞军”已不复往日的辉煌,而蒙古军队却学会了“铁鹞军”的战法。此后的数十年间,西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噩梦就伴随着西夏走进了坟墓。接下来的21年间,西夏皇位更换频繁,襄宗嵬名安全在位5年、神宗嵬名遵顼在位13年、献宗嵬名德旺在位4年、末主嵬名睍在位1年。《左传》云“欲亡其国先去其史”,在蒙古的一次次屠城中,西夏的历史印记一点点的被抹去。伴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盛极一时的西夏文字因蒙元的文化灭绝政策以及本身的难以辨认,在岁月的流逝中很少有人能够识读,成为著名的“死文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匆焉。“夏叶中衰,于是乎始”,在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西夏,我们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先后臣吐谷浑、隋、唐、宋的党项,能够在1038年建立西夏政权且前后历190年,传十代皇帝,与北宋、辽和南宋、金呈对峙之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概其原因,皆在于早期党项人所拥有的尚武精神,这在动乱的年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蛮族”法,到“武法”,再到“文法”,西夏完成了从弱小到强大,再到备受重视的华丽转身。应该说党项从“酋邦政治”转向“地缘政治”,向中原学习先进文化当为正确之举,但是由于儒家强调以理服人,反对以暴制暴,既与党项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也与当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协调。而西夏统治者为了尽快以文明人的姿态出现,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民族特性,被儒家思想削弱了尚武精神。从法律上,不仅是对中原儒法中“十恶”、“八议”内容的引入,即便是立法的精神也是“欲全先圣灵略,用正大法文义”①参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我们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痕迹。如果说西夏初期尚武精神在党项人信仰原始宗教中“招魂杀鬼”的巫术中得到强化,则西夏中期后精神孱弱就与佛教与西夏法律的融合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党项人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演化,原本崇敬“鬼神”与施用“巫术”的宗教观念与河西信仰佛教的现状已不能相适应。为了加强对西夏境内百姓思想的控制,自元昊开始,西夏统治者开始推崇佛教,不仅广修庙宇、开凿石窟,开展佛事活动,更自诩为“佛天子”,到了中期的法律改革,西夏法典俨然成了一部宗教教义。一方面,统治者对于百姓的思想钳制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佛教中“尚和”的思想也削弱了党项人崇尚武力、血亲复仇的观念。党项人的“血性”被逐步淡化。虽然国家的财富得到了积累,但农业生产中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也渗入到西夏人的文化精神中。农业固然使得西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自给自足,但党项人也开始追求安定与享乐,不再有开疆破土的雄心壮志。尽管西夏也曾有有识之士提出党项人以武立国,理应保持传统的民族习惯,[19]重兴节俭之风,[20]但毕竟农耕文明已经深入党项人的骨髓,其优势与劣势均在西夏得以呈现。在统治者自身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下,西夏经历了由“武法”向“文法”治国方针的转变。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丰衣足食后追逐享乐,崇尚儒家思想,推行“文治”,倡导佛教信仰,慎杀“尚和”,随着“文法”的改革,削弱的党项人的战斗力、贪生怕死、转攻为守,最终走向了衰亡。
西夏法律多元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如党项、鲜卑、吐蕃、吐谷浑、契丹、女真等民族习惯皆融入西夏法律系统中;对“儒教”的学习使西夏法典体现儒家的文化内容;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又使西夏法律呈现宗教法特征。这种多元文化属性在西夏法律体系中起到精神主导作用。通过梳理党项法律文化的演进阶段,使我们更加清晰了解到这种多元文化对于西夏盛衰所起到的功与过。在得出西夏法律具有多元文化属性后,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西夏法律的特殊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