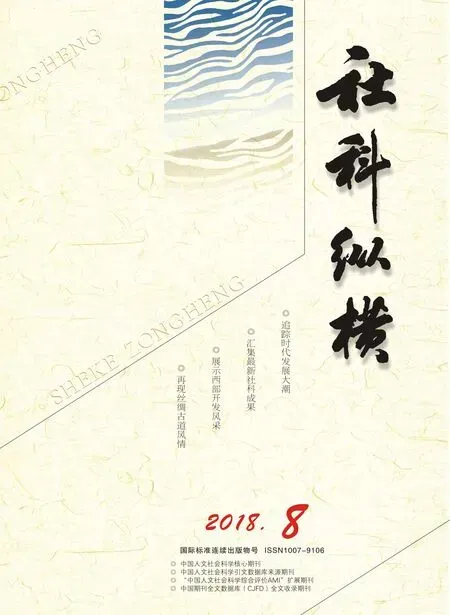祠堂
——《白鹿原》空间意象的文化意蕴
祁小绒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庞德认为,“一个意象就是在瞬间呈现的一个物性,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是诗人主体的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和精确完整的物象的结合。”[1]空间意象既是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又是象征其社会关系和精神领域的意义空间,空间意象对作者的文化立场、生命体验的表达产生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祠堂意象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祠堂不仅是白鹿村人祭祀祖先的宗祠,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公共场所,祠堂所代表的文化承载着白、鹿两姓族人的祖先崇拜和集体无意识,对人物的心灵和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传统祠堂文化释义
中国古代祠堂兴起于汉代,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祠堂文化。祠堂是宗族祭祀祖宗先贤的场所,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物质形态。祠堂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2],与宗族有关的事务大都在祠堂里商议或实施。祠堂既有为祭祀祖先的宗祠,也有敬奉先贤和有德之人的祠庙,朱熹在《家礼》中写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3]
祠堂是家族文化的象征,家族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整个宗族成员,祠堂“通过匾额、楹联、碑记、家训、族规、乡约等形式弘扬了爱国、孝悌、诚信、互助、友善,勤劳、节俭等传统美德,形成了诸如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礼让宽容”[4]等道德风尚。这些祖训族规世代相传,起到了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祭祀祖先也是儒家礼仪的表现形态,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5](P609),因此祠堂是落实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化为乡约、家法、族规等形式,形成礼仪风尚、社会风俗,沉淀在国人的意识深层。祠堂将祭祀文化、家族文化、宗法制度,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乡土中国子民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结构,折射出人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祠堂包含着供奉先祖、祈求祖先庇佑后代繁荣昌盛的特殊含义,寄托着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象征着家族命运的兴衰变化。祠堂也成为陈忠实思考民族秘史本质特征的切入点。
二、《白鹿原》祠堂空间意象文化意蕴
(一)传统祠堂文化精神的体现
祠堂是陈忠实在《白鹿原》重点书写的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空间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了近180次,小说中关于祠堂的介绍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它对白鹿村人的精神和行为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祠堂凝聚着一个宗族世代人的情感,没有或失去了祠堂,对一个家族意味着失去了精神家园。首先,小说讲述白鹿村人失根、寻根的历史记忆:“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搞不清这里从何年起始有人迹,说不清第一位来到这原坡挖凿头一孔窑洞或搭置第一座茅屋的始祖是谁……祠堂里那幅记载着列祖列宗显考显姚的宽大的神轴和椽子擦条,一齐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村庄的历史便形成断裂。传说又一年三伏天降火……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凛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6](P61-62)。于是才有了后人挖空心思改村名、建祠堂的举措。白鹿村过去叫胡家村或侯家村,因为白鹿传说改为白鹿村。“这个村庄后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6](P62)祠堂成为维系着白、鹿两姓族人的血缘关系的纽带,暗含着白鹿村人的祖先崇拜心理。
其次,作者通过人物活动对祠堂多重功能予以展现,祠堂是白鹿村公众活动中心,白鹿村的重要事件或决议都在这里发生或实施。在公共议事方面,当瘟疫蔓延至白鹿原时,几个村民找到白嘉轩吵嚷着要给田小娥修庙以消灾辟邪,“白嘉轩扬起脸说咱们不要在我屋里说……这是本族本村的大事,该当搁到祠堂去议,跟本族本村的男女一块议。”[6](P469)为防范白狼伤人,“白嘉轩提着大锣,从白鹿村自东至西由南到北敲过去,喊过去,宣告修补村庄围墙的事。人们丢下活计,扔下饭碗就集中到祠堂院子里。”[6](P84)祠堂也是白、鹿两姓族人婚宴场地,白孝文结婚时,“白嘉轩以族长的名义主持了儿子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6](P147)。鹿兆鹏婚后“第三天进祠堂拜祖宗,兆鹏又不愿意去,还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煽到祠堂里去了。”[6](P147)祠堂又是惩罚触犯族规者的重要场所,如惩罚淫荡男女狗蛋、田小娥和白孝文,惩处赌徒和大烟鬼等,祠堂使村规民约真正发挥了作用。
祠堂的也是族人供奉祖先、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过年祭祖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后代幸福安康;新娶的媳妇也要到祠堂祭祖才算被承认,田小娥虽然留在了白鹿村,却被白嘉轩坚决地挡在祠堂门外,她因而失去了在白鹿村生存的合法性;浪子黑娃、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也是被族人认可、接纳的形式。白嘉轩告诉儿子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6](P588)这些祭祖活动,强化了族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祠堂还是白鹿两姓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地方,白嘉轩和鹿子霖出面把破败的祠堂进行了彻底翻修,在这里创办起本村的学堂。祠堂不仅是子弟读书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族人的教化功能。祠堂与学堂两个空间意象的重合,预示了祠堂命运的兴衰与以黑娃、鹿兆鹏、白灵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的冲突关系。
最后,祠堂是维护家族制度、传统社会秩序的圣地,是族长行使权力的舞台。族长白嘉轩一生的作为几乎与祠堂关联,他翻修祠堂、建立学堂、实施《乡约》条文、惩罚不肖族人,自觉捍卫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性、合法性,建立起白鹿原理想的道德秩序,白嘉轩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代言人,祠堂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
《白鹿原》中的祠堂是中国民间祠堂的典型代表,祠堂既是物理学、建筑学意义的一种物质形态,又折射出着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方式,揭示出文化制约中人的生命形态。作者通过人物命运与祠堂的关系诠释了祠堂文化的丰富含义,祠堂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传统文化的场域,为族人接受儒家思想奠定了基础。祠堂与学堂两个空间意象的关联,凸显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信条对白鹿村人后世子孙心灵的深刻影响。
(二)《乡约》精神的物质载体
陈忠实力图在《白鹿原》中揭示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及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突出祠堂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对白鹿村人精神心理所构成的威慑作用。小说中的《乡约》是与祠堂意义联系密切的意象,《乡约》是儒家道德伦理的集大成者,朱先生亲书的《乡约》被放置在祠堂最显眼的位置,与祠堂构成了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乡约》是祠堂精神的集中体现,祠堂则是《乡约》的物质载体,是村民接受儒家思想的重要空间。
乡约即村规民约,是传统社会治理乡村条文的总称。北宋神宗年间,由陕西蓝田乡贤吕大忠、吕大钧等兄弟撰写的《吕氏乡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范式,集中体现了儒家以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和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管理思想,涵盖了传统村规民约的基本内容。《白鹿原》中朱先生亲书的《乡约》是以《吕氏乡约》为蓝本,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乡约》使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在祠堂这一空间得到具体实施,它将儒家思想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根植于每一个族人的内心;《乡约》也是白鹿两姓宗族的家法族规,它强化了儒家孝、悌、忠、信对族人精神、行为的约束作用。
《乡约》在《白鹿原》中一出现就与祠堂关联。“白嘉轩接着又约鹿子霖到祠堂议事……三人当即商量拿出一个在白鹿村实践《乡约》的方案,由族长白嘉轩负责实施,当晚,徐先生把《乡约》全文用黄纸抄写出来,第二天一早张贴在祠堂门楼外的墙壁上,晚上,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规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6](P93)
小说第六章结尾处有一段文字记述:“白嘉轩又请来两位石匠,凿下两方青石板碑,把《乡约》全文镌刻下来,镶在祠堂正门的两边,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竖碑互为映照。”[6](P94)《乡约》经过白嘉轩、朱先生等乡贤的宣传实施,白鹿村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这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7](P94)《乡约》对规范白鹿村乡民行为、教化民众思想,调和邻里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百姓通过《乡约》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仁义礼智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7]形成了超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乡约》条文的具体实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祠堂的神圣性、庄严性与《乡约》内容的严肃性相得益彰,对村民的精神、心理起到震慑、规范、引领的作用,强化了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功能。
祠堂翻修使白鹿村人脱离了失根的历史,朱先生、白嘉轩等乡贤制定的《乡约》使乡民的精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形成了良好的礼仪规范和道德风尚,祠堂与《乡约》意象的关联,表明了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营造出具有关中地域文化特征的儒家文化场域,它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与向心力,使祠堂成为白鹿原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
三、祠堂精神的衰落
《白鹿原》以20世纪末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心态为坐标,将浓缩了儒家文化特质的祠堂与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相联系,展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层演变历程。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现代文明(包括政治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瓦解,走向了必然没落的命运。《白鹿原》中朱先生亲书的《乡约》已被叛逆者的年轻的一代摒弃,祠堂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神土崩瓦解,祠堂所固有的调解争端、消弭危机、增进乡情、敦厚民风的功能在政治力量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祠堂业已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舞台,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它又顽强地存留在人们的意识深层。作者以祠堂兴衰与人物命运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出儒家文化遭遇现代文明后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表达了陈忠实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命运走向的矛盾和困惑。
《白鹿原》中祠堂的兴衰可用“翻修—毁坏—重修”三个阶段来概括,成为时代潮流冲击下家族命运变迁史的象征,也折射出现代中国新旧文化冲突的历史语境。民国初期,白嘉轩、朱先生等人通过翻修祠堂、建立学堂、践行《乡约》等行为方式对村民实施道德教化,在翻修祠堂的整个过程中,白鹿村“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6](P65),充分体现了“仁义白鹿村”的宗旨。但是祠堂却无法抵御外来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的冲击。“交农”事件后,乌鸦兵在祠堂前强夺粮食;以白灵、鹿兆鹏、黑娃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对祠堂的破坏,在风搅雪式的农民革命运动风潮中,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兄弟,冲进祠堂,砸烂祖宗牌位,捣毁刻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砸碎了《乡约》石刻,祠堂和它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革命力量地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但是,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8]农运会失败后。白嘉轩又一次率领众人修复祠堂,并遵照朱先生的指示,将破损的《乡约》碑文石板重新拼凑接到一起。“白鹿村的祠堂完全按照原来的格局复原过来,农协留在祠堂里的一条标语一块纸头都被彻底清除干净,正殿里铺地的方砖也用水洗刷一遍,把那些亵读祖宗的肮脏的脚印也洗掉了。白鹿两姓的宗族神谱重新绘制,凭借各个门族的嫡系子孙的记忆填写下来……白鹿两姓的族人拥进祠堂大门,首先映人眼帘的是断裂的碑石,都大声慨叹起来,慨叹中表现出一场梦醒后的大彻大悟,白嘉轩现在才领会姐夫朱先生阻止他换用新石板重刻的深意了。”[6](P235-235)白嘉轩修复祠堂的举措以及村人对此的虔诚态度勾勒出20世纪新旧文化冲突的复杂面貌,彰显出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普通百姓精神心理的引领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虽然在新文化的冲击下走向式微,但它早已沉淀到国人的意识深层,化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相宜的环境中,依然会重新浮现出历史的表层,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走向、对个体生命的行为方式继续产生影响。学者雷达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9]《白鹿原》祠堂空间意象的书写,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祠堂空间内容的不断转换,构成了一部人物及家族命运的变迁史,形成了小说纵向的时间流程。
结语
学者曹文轩认为:“现代小说理论最苍白的部分也是有关空间的部分,而最发达、最有系统的部分是与现代形态的小说实践相一致的时间部分。”[10](P192)但是,“作为小说材料的一切故事,都只能发生于空间之中——是空间才使得这些故事得以发生”[10](P176)。没有离开时间的空间,亦没有离开空间的时间,空间意象内容的转换体现了小说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统一,它不仅是环境的烘托、场景的展示,也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和深层的文化意义。《白鹿原》以祠堂意象为切入点,从空间维度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历史进行高度地概括和总结,表明了作家重视空间描写对小说主题表达的重要性。《白鹿原》祠堂空间意象的文化意蕴寄托着作者对历史文化、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它与小说中的“白鹿”意象彼此呼应,合力聚焦民族秘史的本质特征。另外,祠堂作为传统中国人的心灵圣殿,凝结着国人无法忘怀的乡土记忆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祠堂所蕴含的丰富意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陈忠实在《白鹿原》对祠堂空间意象文化意蕴的文学表达,客观上对当代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