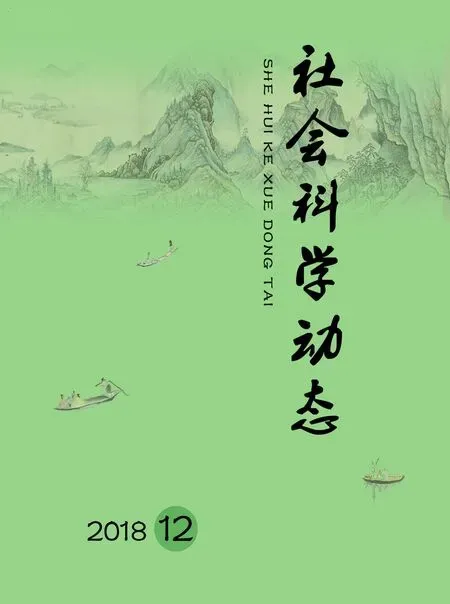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
——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献研究
刘玉杰
随着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成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以及曾大兴、杨义、陶礼天、邹建军、刘川鄂、梅新林等学者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的大量问世,文学地理学的中国话语属性日渐彰显。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二届硕博论坛于201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青海西宁青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17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近150篇,更是集中展现了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刘庆华在《从文学地理学看中国学的构建》中,从中国学术体系构建的角度如此肯定文学地理学的贡献:“在建构中国学术体系的艰难历程中,文学地理学学科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率先垂范,为构建中国学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①
一、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
言说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强调文学地理学的中国性,并非盲目的民族主义自信,而是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学理依据:
首先,长久以来中国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失语症困境,这是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诞生的学术生态背景,也凸显出文学地理学的中国话语属性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中国近现代以来长期遭受西方话语的压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现象学与阐释学、精神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迅速更迭、接踵而来;反观中国,新时期以来我们忙于目不暇接地被动接受各种西方批评话语,却疏于主动挖掘原生性的批评话语。曹顺庆在1996年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话语的缺失:“长期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 、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②
其次,何种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才能称为中国话语?一方面,从时间维度考量,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已有2560年的历史。”并将文学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划分为片段言说阶段(前544—1905)、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学科建设阶段(2011—今)等三阶段。③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同样具有2500多年或者110多年的历史吗?答案是不能也没有必要。中国话语是一个参照性观念,只有与西方话语相参照才有实际意义。具体到文学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焦虑,大体上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与文学地理学的渐成显学的时间大致一致。另一方面,从文学地理学性质定位考量,无论是作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作为学术研究方法还是作为文学史的补充,均面临着或者中外皆有或者中国源自外国的合法性质疑,无法被看作是中国话语。
综合以上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自2011年始的学科建设阶段才为中国所独有,也才可以被称为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曾大兴正是从学科史的视角考察,发现了中西对待文学地理学的态度差异:“为什么文学地理学在国外不受重视,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而在中国却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并且正在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呢?”④并详尽阐述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诞生的五大原因。具有学科自觉意识的研究同仁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文学地理学的中国属性,如曾大兴2012年明确地表示:“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学是‘舶来品’,文学批评学是‘舶来品’,文艺理论学也是‘舶来品’,只有文学地理学才属于‘中国创造’。”⑤再如陶礼天2016年指出,“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地理学不要也不可能只依靠外国的理论”,应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归纳出许多有创新性的命题,乃至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派,从而推动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思想’研究和‘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⑥
再次,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 (2017)的出版,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新收获,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崛起的又一有力例证和巨大推力。杜华平将该著看作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⑦;李仲凡认为该著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的早日建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⑧;刘川鄂与黄盼盼认为“此书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做通盘考虑的第一书,这对于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学科具有突破性意义”⑨。从以上诸位学者的评价中,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静态地看,《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作为学术话语的崛起;另一方面,动态地看,这种崛起不仅不意味着学科发展的停滞,反而是对学科更系统、更深入发展的一种助推。
最后,我们可以从研究者有无话语自觉意识来检验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是否真的崛起,事实上中国学者的确在自觉地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多领域研究。在此仅举一例,曾大兴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就系统地提出文学地理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并强调与文学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使用‘空间分析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时空并重’的原则”⑩。以下诸文无不在突出地理空间的前提下,兼而做到时空并重。刘介民的《文学地理之时空维度——唐诗绝句的时空意识》,从人文性、精神性、想像性、跨学科性等层面讨论文学地理的时空维度。左洪涛的《论唐代前后期女性审美观的演变与胡汉关系变化的关系》,使用曾大兴提出的“区域分异法”考察唐代女性审美观,认为初、盛唐以壮硕为美是黄河流域的胡人和北方汉族人的审美观,中、晚唐以劲瘦轻巧为美则是长江流域南方汉族人的审美观。颜红菲的《前文本·嵌文本·潜文本——论〈我们中的一个〉的景观叙事》指出叙事文本中的地理景观不仅展示故事背景,也发挥着时间叙事的功能。陈桐生的《从地理名称看〈诗经〉中的西周风诗》从地名推测《诗经》风诗的创作年代。彭民权的《从自然到文化:先秦地域观念的演变——以“夷狄”“蛮夷”“荆楚”为例》,强调对地域观念认识的时间维度,早期指中原以外自然区域的夷狄等,其后逐渐演变为对非中原区域的文化贬斥。陈丽丽的《论中国古代诗歌总集编纂中的地域意识》以地域与诗歌总集为切入点,对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窥见中国诗歌发展的地域轨迹。
探索学科建设的还有,杨波的《大数据时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通过大数据分析,把脉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绩、问题及方向。一方面,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绩体现在研究队伍逐渐增大、研究成果持续推出、跨学科研究课题数量激增、相关研究取得了阶段性共识等多个层面。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研究领域亟待开掘、创新成果突破较少、个体研究低水平重复较多等。文学地理学研究者“要尽量做到以战略眼光把握研究态势、以积极态度求取理论认同、以创新思维拓宽研究视野、以长远眼光推进深度研究,推动文学地理学研究从历史的深处走向现实的舞台,从书斋研究走向社会普及,持续深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⑪。王朝朝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多重价值》论析了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化产业的多重价值。李欣的《从时间纬度到空间纬度的转向——论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探讨空间转向与文学地理学兴起的因果关系。虽然空间转向对整个人文社科研究影响甚重,但它与文学地理学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存在何种程度的因果关系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在此给出一种相反意见供参考,曾大兴从中西两方面提出了否定性观点:“中国有个别学者认为‘当代西方的文学地理学是在空间转向和后现代语境下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一种误解和误判”,“有人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得益于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的‘空间转向’。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⑫
二、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1.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新探索
曾大兴的《“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区分了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指出不能仅仅依据作家的籍贯来判定其是否属于某一地域文学,而应按照籍贯、作品的产生地和作品的题材等三个要素来综合判断;针对以往地域文学研究使用单一文学史方法的缺陷,提出文学史方法和文学地理学方法并用的方法论。
与曾大兴侧重于探讨地域文学研究不同,刘川鄂的《当代中国区域文学研究的尝试与思考——〈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主编感言》主要探讨区域文学研究。刘川鄂将《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称之为区域文学研究,因“湖北的文化品性是庞杂的,其文学也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当代湖北作家群这个概念其行政区域意义大于文学风格含义”,即湖北是一个地理界限明晰的行政区域,这正好印证了曾大兴的观点。另一方面,他还提醒在行政区域打造的“地域牌”热潮中应该清醒认识到:“只用地域的视角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审美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文化,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⑬
陶礼天的《〈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研究(上篇)》根据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论,提出《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内容研究的范式:第一,《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的问题,即基于《原道》篇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理论纲领而立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与文化视野;第二,作家与地理的关系问题,主要指作家创作个性(才性)、风格与文学地域等;第三,作品与地理的关系问题, 主要指风景论、乐府论、语言声韵论、文学传统与文学史的通变论等;第四,读者与地理的关系问题。
邹建军的《地方文献与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探讨了地方文献与文学地理学的关系问题,认为地方文献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内容。地方文献由以下四方面构成:国家层面,方志层面,家族层面的历史文献以及回忆录,口述史层面的历史文献以及作家个人的日记、游记等。针对如何整理地方文献中的“地理”这一问题,认为首先是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学思想,其次是在地方志中寻求文学地理学相关内容,再次是在家谱与族谱中研究文学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后是实地考察地方民歌民谣。⑭
周文业的《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构建中国文学地理开放交互信息平台》,介绍了中国文学地理开放交互信息平台的设计思想和总体设计方案,指出将地理信息系统 GIS应用于中国文学地理,是以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平台为基础,构建中国文学地理学信息平台,应用于中国文学地理的教学和科研,从作家、作品、地点等三方面展示中国文学史。
龙其林、钟丽美的《地理图像史料、文学地理学科背景与专业精神——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地理图像史料问题及反思》指出目前研究者对于地理图像史料的使用存在三大方面的缺陷:地理图像史料的穿越化(史料与历史语境不符)与雷同化;文学地理学科背景(跨学科素养、必要的知识积累)与生命、审美体验的双重匮乏;持之以恒的专业精神,以及博物学、田野调查的意识的缺乏。
2.文学地理学核心概念辨析
在中心—边缘所构成的权力关系话语中,中心往往对边缘产生压迫,而边缘则总是对中心具有反抗意志,两者之间的张力、动态变化成为文学地理研究的关注所在。陈一军的《文学的“中心与边缘”义理考究》认为,中心与边缘发端于地理空间,继而上升为关乎人类普遍思维结构的认识论。“文学的中心与边缘即是在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复杂场域中形成的,渗透着情感、态度、立场、权力、利益等诸多因素,充分体现着话语权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分配关系”⑮,因而研究者应注重其在文化层面上的综合性、批判性阐释功能。杜国景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及:一是区域与地域之间的区别和矛盾,比如少数民族作家的地域文化认同在实际上被区域所分割;二是文学的中心与边缘之别,应打破将口头文学作为边缘文学、将书面文学作为中心文学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
地方性与非地方性的辩证关系。人们对地方的态度必然是丰富多变的,对地方性的认同已经得到文学地理学的广泛关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地方性。刘玉杰的《全球化中的地方性与非地方性——以湖北籍海外华人作家的地方书写为考察中心》认为全球化语境中人们对地方性的态度、书写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古典式恋地情结的地方性(Placeness)与现代性语境中的非地方性(Placelessness)。前者是求定意志的结果,反映出人归于自然的情感态度,而后者则是求知意志的产物,反映出人的认知自主性,认为“非地方性不是对地方性的无视、忽略,而是地方性的一种特殊形态”⑯。周爱勇的《故乡·民族·风景——毛南族作家孟学祥风景叙事研究》提出坚守型恋地、游移型恋地、离乡型恋地等三种恋地情结,后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彰显出非地方性。
此外,王东的《自由情结与气象美学研究》具体分析了三位学者的气象美学理论:梅尔斯·洛斯顿以“野性”赋予气象审美的反秩序性和颠覆性;马达丽娜·代克努以审美超验性赋予气象审美的终极无功利性;斋藤百合子以日常的无边界性赋予气象审美的融合沉浸性。借此指出气象美学建构的一种内在动力是自由情结,具有平民性、自由性、反科技控制等意识形态价值。
三、地理分布与文学区研究
按照《人文地理学词典》的解释,地理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据地理差异进行区域划分。以此观之,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与文学区研究,均源自这一地理学基本特点和内在思维结构,可将之称为文学的外部地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对新批评提倡文学内部研究的观点保持客观、冷静,打破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因为外部与内部实为二元互补的关系,偏废其一而不可。
1.地理分布研究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探讨静态分布的如李精耕的《明代江西状元作家的地域分布与诗歌创作》、俞晓红的《明清徽州才媛的地理分布与文化教育》、唐星的《北周鲜卑宇文家族诗人的地理分布与空间书写》、王成芳的《文化中心南移后的西北文学——以明代陕西作家的时空分布为路径的考察》、莫其康的《兴化李氏家族名士显宦考述》等;探讨动态分布的如李剑清的《汉末三国:北方文士的迁徙》,对汉末北方文士的迁徙分三方面来探讨,即汉末文士南徙的离心避难、曹操主导的建安文士的向心回聚以及蜀吴崛起中流徙文士的离中分向。其他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有两篇论文论及译者地理分布研究,如贺爱军的《唐代佛经译者地域分布的时空透视》、任小玲与郭闯的《明末至晚清译者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其缘由探源》;宋健的《〈荀子·成相〉地域文化归属考辨——兼及战国末期儒家分布》则关涉到思想家的地理分布;黄晔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域风情和民俗文化的生动展现——浅论〈古谣谚〉中辑录的少数民族类谣谚》涉及少数民族谣谚的地理分布。
2.文学区研究
曾大兴在《论文学区》中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区既不是诸如江苏文学区、陕西文学区等功能文学区,也不是诸如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等感觉文学区,而是根据地理依据、历史依据、文学依据等界定的形式文学区,并将中国具体划分为“东北、燕赵、齐鲁、中原、三晋、秦陇、新疆、青藏、巴蜀、滇黔、荆楚、吴越、闽台、岭南等14个文学区”⑰。
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年会是一个行走的研究共同体,具有带动效应,所到之处则催发出当地文学区研究的热潮。可明显归于青藏文学区、新疆文学区、秦陇文学区等地域的论文有13篇。青藏文学区研究,有栗军的《青藏高原的文学地理世界——以次仁罗布、万玛才旦、格绒追美文学创作为例》、刘大伟的《从“小桥流水”到“贵德地带”——元业诗歌创作特征解析》、杨柳的《双重视域下的非规约性书写——论藏族汉语作家的多维化叙事》、孔占芳的《边缘地域下边缘文化的张力:阿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特征探析》、李生滨与周蕾的《审美的决绝情态及其诗歌意象——谈谈昌耀与西部文学及现代诗歌》等五文均探析了青藏高原与现当代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李玲珑的《论青海民族民间戏剧的多样性及其成因》从民族、地域、社会三个方面阐述青海戏剧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成因。新疆文学区研究,有张凡与董新颖的《文化地理视域下的乡愁母题与生命景观——以新世纪以来的艾克拜尔·米吉提散文创作为考察中心》、祁晓冰与赵全伟的《帕蒂古丽创作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于京一的《他乡即故乡:作为文学地理的新疆之于红柯的意义》等三文均探析了新疆地理与现当代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史国强的《清代新疆交通与文学繁荣研究》指出清代统一新疆后以伊犁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激发了以行程游记诗文为代表的新疆地域文学的繁荣。此外,王伟的《唐代长安传奇小说创作嬗变之空间解读与群体分析》、韩玉蓉的《“商州”与“老西安”——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世界》、梁祖萍与张星星的《隋唐宁夏墓碑文叙录》等三文均属秦陇文学区研究。
另一方面,其他文学区研究也呈百花齐放的态势。东北文学区研究,有王丽君的《原始、自然、感性的神秘世界——评迟子建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张祖立的《地域文化与新时期以来大连小说创作》分别论述迟子建小说创作、大连小说创作。中原文学区研究,有吕东亮的《女性作家的崛起与当代文学的“中原经验”》、杨恂骅的《从王梵志诗看初唐中原地区民俗活动的多样性》等;杜玉俭的《盘古神话产生地域的重新考察》通过盘古神话所解释的地理现象(尤其是中国北方大山的形成)说明其起源于中原地区。三晋文学区研究,如王青峰的《古代山西的气候地理变迁与唐诗的繁荣》、王小芳的《文学地理视角下的运城盐池研究》、赵树婷的《从山西民间歌谣的特点看山西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巴蜀文学区研究,如李懿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陆游巴蜀诗及其意义》、张红波的《清代竹枝词中的重庆生活图谱》。滇黔文学区研究,如马志英的《清代回族诗人孙鹏咏史怀古诗的地域文化特征》、蒲日材与付煜的《从文学视角考察西南地区端公跳神习俗——以〈啖影集·跳神〉为例》、马兰州的《安南地区对汉诗“正音”的选择及对杜诗的接受》等。荆楚文学区研究,如刘海军的《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寓言化书写》认为陈应松对神农架的寓言化书写,凸显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刘学云的《〈湘行散记〉:自然与文化背景下湘西人生的书写》、伍志恒的《土家族作家孙健忠长篇小说〈醉乡〉探微》等均聚焦于湘西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岭南文学区研究,如宋秋敏的《宋南渡后岭南词学的兴起及其地域特征》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吴越文学区与燕赵文学区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城市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吴越文学区研究有聚焦于上海的,如冯仰操的《民国游记中的上海印象》、余梦林的《〈长恨歌〉与上海书写》、张双的《个体与日常的上海烙印——论王安忆〈乡关处处〉的上海书写》等;也有关注南京的,如赵步阳的《民国时期南京文学景观的变迁与意象转换——以地域性文学选本为考察对象》、王建国的《〈西洲曲〉产生的地理环境考释》、杨剑兵的《秦淮风月中的南都记忆——试论〈板桥杂记〉的地域特色》等。燕赵文学区研究均聚焦于北京,如于润琦的《〈儿女英雄传〉的文学地理特征》、吴蔚的《清代京都文学发展的地域特征》。除此之外,夏明宇的《双城映像: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书写》、敖翔的《“大”时代的都市“小”记趣:张爱玲<流言>的都市书写》等文则不局限于一城,而是涉及多城市的文学地理研究。
当然,任何体系划分都不可能涵括所有的现象。有些论文所论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文学区的归类,一者如高人雄的《汉唐高昌文学的地缘文化》并不拘泥于高昌文学属于新疆文学区,认为高昌文学具有典型的中国西北地域文学特征;任红敏的《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考察的亦是元代文学中的西北民族作家群;高忱忱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北魏太和文风》将北魏文学归于北方文学。二者如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的汉水流域文学研究,如王建科的《汉水流域历史剧剧目初探》、姚秋霞与荣丹的《论“汉调桄桄”对“包公戏”的传承与发展》、费团结与陈曦的《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母题及其当代重构》等论文。三者如韩鲁华的《贾平凹、莫言乡土叙事比较——以地域生态文化为视角》涉及两种文学区的比较研究。
四、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意象研究
曾大兴如此厘定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意象的关系:“多数的地理意象是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要素,少数的地理意象是文学景观。在我们从事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研究和文学景观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就包含了大量的地理意象研究。”⑱虚拟性文学景观(文学内部景观)、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和文学地理意象显然都处于文学文本内部;实体性文学景观(文学外部景观)虽处文学文本外部,但可与虚拟文学景观互相转换。有鉴于三者有别而又重叠的复杂关系,也为论述方便起见,暂且笼统地将三者合称为文学的内部地理研究。
1.文学景观研究
衣若芬、王姮等文可归于实体性文学景观研究。衣若芬的《东亚文明精神与潇湘八景文化意象》探讨了地理景观的跨国迁徙、移植与再生,认为“潇湘八景诗画源于中国宋代,传播至韩国、日本和越南等邻国,形成不同的本地化结果,可视为东亚国家交流互动,共享文化资产,缔造文化新生命的范例”⑲。王姮的《被制造的景区与被控制的观看——从“水浒城”“聊斋园”说起》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着手,以东平水浒城、淄川聊斋园等人工文学景区为例,批判了其内在的消费逻辑,强调文学景观建设应重视文学审美属性。
虚拟性文学景观研究仍占景观研究的大多数。人文景观明显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陈恩维的《文学空间、记忆之场与地域诗派——以“南园”与岭南诗派为例》,综合采用空间分析法与时间分析法,认为南园作为文学空间和记忆空间,与作为空间文本的南园诗一起,对岭南诗派的传承发挥了巨大作用。高建新的《唐诗中的烽火及其文化景观价值》论析了烽火在唐诗中的英雄主义豪情、祈望和平、思乡之情三种表意功能,是展现边疆地理、民族风情的文化景观。李世忠的《唐昭陵的诗歌书写及其史学价值》考察了昭陵诗对唐昭陵这一景观的文学书写。熊海英、俞乐的《元代中期江南地区宗教景观与文人的宗教活动浅论——以郭畀〈云山日记〉为中心》着眼于寺观宗教景观,探讨元代中期江南地区普通文人儒士宗教信仰多元化、注重实效的功利性特征。刘洁的《民间传说中昭君出塞的文学景观及其内涵》认为昭君民间传说较之作为书面文学的昭君诗词曲内容更为丰富,并详细研究了其中的青冢、昭君桥等文学景观。自然景观如薛展鸿的《崖山文学景观研究》探讨了崖山文学景观蕴含的山河破碎之痛、哀古警今之思、华夏之象征等多重意义,进而认为崖山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张福清、张曼洁的《论苏轼寓惠诗之自然、人文景观及其审美情感》从自然人文景观切入,探讨苏轼寓惠诗中愤懑、渴望北归、凄婉与旷达交加等审美情感。现时代的城乡区分造就了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的独特文学景观类别。张之帆的《论〈生死疲劳〉中的乡村景观书写》解读西门屯乡村景观对莫言思想的再现。赵步阳的《民国时期南京文学景观的变迁与意象转换》分析了民国时期南京文学景观的变迁与意象转换。杨章辉的《威廉斯长诗〈帕特森〉中的景观想象研究》探讨了威廉·威廉斯对城市地理景观、公园与图书馆景观等多重景观的建构。
2.文学的地理空间研究
陈富瑞的《论汤亭亭小说中的地理故乡》,从华裔作家如何借助“口述之中国”切入,揭示地理故乡的三重书写意义,即边缘人的心灵寄托、美国华裔青年与父母沟通的方式以及作家抒发家国情感的有效途径。李美芹的《论赖特〈土生子〉的空间政治书写》,将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和福柯的“空间权力论”贯通,认为小说中的“黑带区”反映了白人主流社会所规划的空间表征,而别格母亲、别格通过各自的空间实践表达出阐释性的表征空间与逾越性的表征空间。王海燕的《地理空间的流动与人物心理状态的关系研究——以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克里斯默斯为例》认为地理空间在不断的流动性中呈现出的差异性建构,表现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敏锐的地理感知及其悲剧意识。余一力的《〈英国情人〉中的地理空间建构与价值重估——来自读者的体验、创造与反抗》认为虹影《英国情人》中的东方地理空间,本质上体现了作者对于威权和“西方中心”话语的反抗意识。段亚鑫的《〈青年的污名〉的文学地理空间解读——以“荒若岛”为中心》探讨大江健三郎借助荒若岛这一特殊文学地理空间所体现的日本当代社会问题与拯救出路。李萌羽的《试论福克纳影响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地理世界的建构》考察福克纳建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对中国新时期小说诸多文学地理世界的激发作用。
3.文学的地理意象研究
中国山水文学传统悠久,山水意象也因此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除许外芳的《元代山川铭论略》兼论山水意象之外,专论水意象的论文还有朱育颖的《与水共舞: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河流意象》、孙胜杰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河流”书写及其隐喻意义——以黄佩华、叶梅、李进祥为例》、涂慧琴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湖泊意象》,分别探讨河流与女性、河流与民族、湖泊与人生抉择等之间的关联;专论山意象的论文有殷学国的《从语词到主题的话语分析:以〈渔歌子〉西塞山为中心》、安丽霞的《苏轼晚年诗歌中的罗浮山情结》、熊悦的《浅谈〈山海经〉中“昆仑山”的文学地理空间》等,分别探析作为中国诗学和江南意境表现符号的西塞山意象、苏轼诗歌中承载道教文化的罗浮山意象、《山海经》中具有三重空间意涵的昆仑山意象。动植物意象如路成文的《北宋牡丹审美文化新论》、杨宗红的《精怪母题与自然地理: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为例》分别论及牡丹植物意象、动物意象。其他地理意象如曾小月的《浅议余光中诗歌中的地理意象》论析了自然景物、自然节气、中国地理、离散地理等四种地理意象。王晓平的《论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几个意象》、薛玉坤的《盛世想象与文学地理意象的建构——论民国逊清遗民文人的江亭书写》、尹蓉与朱洁的《论汤显祖传奇中的边塞风情》分别论及断壁残垣与高墙意象、江亭意象、想象中的边塞意象等。
五、文学地理研究新拓展
1.地理迁徙与文学书写
作家的地理迁徙,使得“一”的地理认同模式被打破,造成了生命体验、文学书写中同时存在两个甚至多个地理核心,进而引发出文化认同、国族认同等深层而复杂的问题。出使文学如方丽萍的《论北宋出使文学中的文学地理问题》,通过考察北宋出使文学对辽国风土人情的反映以及对疆域、民族观念的认知,指出文学地理折射出的北宋士人骄傲、屈辱并存的复杂文化心态。李惠玲、陈奕奕的《相逢笔墨便相亲——越南使臣李文馥在闽地的交游与唱和》认为《闽行杂咏》见证了李文馥与来子庚等中国士大夫的情谊,以及对中越两国文化同源的强调。梁钊的《异域与西域:燕行使对回回国的认知》从地理、方物等方面探讨了域外汉籍《燕行录》中的回回国形象。其他迁徙文学如(美)韩小敏的《乾隆皇帝南巡给吴越归隐官员诗作之评析和英译》探讨了乾隆皇帝的南巡与御制诗间的关系。胡蓉的《地域视野下的元末西夏遗民诗人王翰诗歌创作》认为河西党项族民族性格与福建东南理学传统、山水文化,对王翰诗歌产生了双重地理影响。
2.地理交通与文学的内在双向关联
存在两种阐释路径:其一,由地理而至文学。或探讨地理交通对文学的影响,或探讨地理交通如何在文学中参与人的情感与审美。李文胜的《论元代馆阁文风》认为元代南北统一后的交通,为馆阁文风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空间支持。王忠禄的《丝绸之路上的五凉文学》认为五凉文学发生于丝路上的河西走廊,属于丝路文学。由陆路交通转向水路运输,如史悦的《汴水与北宋诗词创作探析》与王勇的《明代诗歌所见运河景象及其文学意蕴》均关注大运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者探讨汴水所承载的恋京、离别等主题,后者凸显大运河作为“明诗之路”的文学史意义。其二,由文学而地理。(韩)郑羽洛的《韩国洛东江及其沿岸的空间感性与文学疏通》以文学的角度诠释洛东江的疏通性,将其空间感性归纳为浪漫感性、道学感性与社会感性。这两种阐释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阐释闭环,将地理交通与文学的双向关联揭示出来。
3.文学的语言地理研究
高光新的《〈红楼梦〉与清代玉田方言词的关系》,通过对比《玉田县志》与《红楼梦》25个方言词的异同,认为曹雪芹对玉田方言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掌握与熟练运用。唐旭东的《〈诗·齐风〉语言地域性浅探》通过方音、方言词、句式等来探析《诗·齐风》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张向东、陈浩然的《乌热尔图小说的语言地理》分析了鄂温克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小说语言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不难看出,此类研究并非纯粹的语言地理研究,而是将语言作为文学的要素,旨在通过语言的地域性更好理解文学作品。
4.其他方面的文学地理研究
纳秀艳的《王夫之〈诗经〉学的湘学特质》论述了船山《诗经》学中忧怀家国的情感指向、重视人格的精神取向与重建秩序的美政理想等三种向度的湘学特质。张蓉的《王士禛诗学“江山之助”论》论述了王士禛“江山之助”的文学地理诗学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俞兆良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归隐词探究》探析了苏轼归隐词与归隐地理的关系。许振东的《〈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研究述论》梳理了《金瓶梅》创作地理背景的北京说、临清说、徐淮扬说、绍兴说等之后,认为北京说的可能性较大。上官文洁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文化性格研究——论文学地理学内在机制中的深层心理结构》分国别研究了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民族的文化性格。
六、问题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论文集中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具有高度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自觉意识,能够紧紧围绕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来立论、研究。但也存在极个别学科自觉意识淡薄的研究者,他们的论文并无鲜明的文学地理意识,这说明他们尚未完全进入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域,也并不清楚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更别说文学地理学的原理、研究方法和术语体系了。
相比前者,文学与地理的深度融合是更为普遍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追溯至另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文学与地理可能深度融合吗?这是所有的跨学科研究都面临的担心与质疑:研究者具有双学科或多学科专业背景吗?如果没有,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这种质疑带有强烈的不可认知论色彩。试问,何以文学可称之为一、地理可称之为一,而文学地理就不可称之为一?并非所有的地理空间都会进入文学,进入文学的地理经验几乎都是大众性体验,是人人皆会遭遇也皆可感受、理解的地理空间。曾大兴在大会总结发言中强调,文学地理学应该特别注重对两种地理空间的区分,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抽象空间,另一种是切实可感的具体地理。文学地理学关注的是后者,是获得作家主体审美润泽的感性地理,而非枯燥乏味的理论理性的地理。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是文学地理,不能等同于地理学地理。在此意义上讲,“文学地理学”一词可以有两种合理理解:在文学与地理分属两个学科的背景之下,是文学与地理的交叉学科;将文学地理看作一个整体,是关于文学地理的科学与学科。
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已然崛起,但是我们的话语声音还不够大,国际影响力也还有限,作为中国学派显然还未成气候,仍需假以时日,这是由文学地理学学科尚未真正建成、成熟这一学科现状所决定的。中国话语应具有世界眼光与胸怀,并不排斥域外精华思想,文学地理学历来注重汲取域外有益思想,诚如曾大兴所言:“由于这个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因此它的学术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等既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中国局限。因此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走出去,广泛听取国际学术界的意见,认真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相关成果。”⑳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应在坚持中国话语属性的基础上,积极与域外相关思想展开交流与对话,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更加完善、精深。
注释:
①⑧⑨⑪⑬⑭⑮⑯⑲ 参见 《中国文学 地理 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二届硕博论坛论文集》 (现当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卷),2017年7月,第140、111、482、279、121—123、439—452、16、502、302 页。
②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③④⑫⑱⑳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 367—413、457—462、436—458、324、412页。
⑤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⑥ 陶礼天:《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简要回顾和点滴思考》,《世界文学评论》 (高教版)2016年第2期。
⑦杜华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读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世界文学评论》 (高教版) 2018年第1期。
⑩ 曾大兴:《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诗词的时空结构》,《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1期。
⑰ 曾大兴:《论文学区》,《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