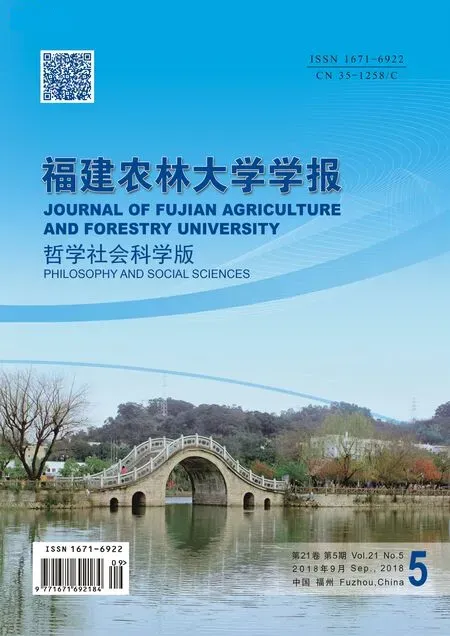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马 佳 林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1)
乡村的成功治理,对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深入发展,乡村的传统文化、规范秩序与社会关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乡村固有的规范秩序和群体结构被打破,村民从传统中脱离出来,村民个体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村民的流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个体化催生了强烈的个人利益诉求。在乡村社会发生的这些转变,使乡村在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新的治理困境:个体过于关注自身利益,乡村主体不断流失,公共事务被搁置,乡村发展鲜有人关注,村民自治运行艰难。面对这样的局面,应尽快整合个体化的乡村,解决乡村当下所面临的治理困境,推动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特点
在我国,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政策的转变,村民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乡村社会的个体化现象日渐突出。
目前,学术界还未对“个体化”的概念达成共识。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一种个体和社会间的‘变形’或者‘范畴转型’”[1],这个概念阐释的是社会制度、个人与社会关系发生的结构性转变,促使人从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中获得解放,以实现个体化;亨利·梅因认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契约主义的兴起割裂了个人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被引入一种以陌生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个体化日渐深入[2];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个体化就是把社会中成员转化为个体的过程,其动力来自于社会的‘分化’活动”[3];诺贝特·埃利亚认为,个体化是随着国家集体高度的集体化与城市化而发生的,受单个人流动强度的影响,其表现是单个的人脱离传统的血缘、地缘集体组织并实现自立自足[4]。根据以上观点,笔者将个体化界定为:在社会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个体逐渐从原来隶属的传统文化、社会规范和各类群体(家庭、社区、工作单位、阶级或阶层)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程度日益深入,乡村社会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1.传统习俗、社会规范和各类群体的作用不断弱化。从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来看,西方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即去传统化。去传统化要求个体从传统的关系链接中解放出来,宗族、家庭、邻里等的约束力日趋弱化,社会成员不断地从传统的义务与规范中脱离出来[5]。我国也不例外,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乡村的传统习俗、规范和制度对村民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弱;村民的交往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固定性、深入性不断地向流变性转变;家庭、亲属、社区、工作单位、阶级、阶层对个体的约束力不断弱化。
2.个体更自由但也更脆弱。一方面,在个体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个体与其归属的传统规范、秩序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越加重视和关注自我的权利、利益和个性,并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更有能力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追求自我快乐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个体在变得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原有社会共同体的庇护,必须“脱离宗族、宗教、出身和阶级这些旧有的纽带,过上自己的独立生活,还必须在国家、就业市场和科层机构等制定的各项新方针和规则下做到这一点”[6],但由于自身素质不高,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使得个体更脆弱。
3.乡村社会具有高流动性。乡村社会高流动性的结果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导致的。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生产模式,使农民从家庭、亲缘和社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和身份证的发行,以及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断地提高了村民的自由度,使下海经商、进城务工的浪潮一浪胜过一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还会被进一步激化。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61亿人,占总人口的19.5%,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1.17亿人,增长了81%,人口流动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且在这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中约有75%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7]。
4.人们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非农业化和打工浪潮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个体化程度日渐深化,村民的家庭、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个人的利益诉求得到了重视和关注,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再依托血缘、地缘关系,而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得到实现。随着人们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在生产生活、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实现和满足个人的利益和生活欲求成为人们的目标。个体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模式的指引下,践行“为自己而活”的人生哲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二、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
在国家、市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村民个体从传统的归属和社会规范秩序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对自身利益的重视和维护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一方面,个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乡村社会流动性增强;另一方面,传统的秩序规范被破坏后,新的秩序规范尚未确立,村民的思想行动缺乏必要的约束力。这些现实情况致使乡村社会个体化之后,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乡村公共事务废弛。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导致村民对集体事务与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逐渐减少,对于公共事务的建设和管理缺乏积极性。个体化了的村民,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普遍将精力投入自身事务的管理中,不愿意去理会公共事务,“各扫门前雪”成为村民心中的公理。个体化使村民养成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使他们同邻里乡亲隔离,同亲属朋友疏远;个体化的村民热心于为自己创建的小社会,对大社会则不管不问,任其自行发展[8];而公共事务的建设和管理需要财力支持,但是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乡村几乎没有可利用的集体资源,所以,村民要建设公共事务必然要自己注入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村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大多离开了村庄,到城市去打工或经商,村里只留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使得村中的公共建设和管理缺少人力资源,乡村公共事务废弛。
总的来说,由于村民个体化,导致村民过于关心自身利益,忽视公共事务,使乡村社会出现了“发展悖论”的现象。目前乡村社会中村民的收入明显增加,村民个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维护村容村貌、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普遍呈现衰败的现象[9]。
2.短期内乡村发展前景不太明朗。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发展的出路是要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0]。目前,我国实现了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并因此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我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并间接地威胁到了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发展。短期内乡村发展前景不太明朗主要原因是乡村缺乏足够支撑其发展的人才、知识、技术、资源等。乡村农业产业单一、基本产业稀缺、就业吸纳力低、生产效率低、务农收入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如果村民继续留在乡村劳作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收入,难以满足各项生活开支与日益增长的多元物质文化需求,迫于生计不得不向外去寻求谋生之路,个体化则使这个动机得以实现。个体化使村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大量流向城市务工或经商,且基于个体自身利益的诉求,大多数村民更愿意留在城市,而不愿意回归乡村,建设乡村。
一直以来,国家都高度重视乡村的发展,如改革开放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都旨在支持乡村建设、挽留乡村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这些举措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乡村社会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资源向城市集中的洪流难以阻挡,把资源留在乡村或将资源引向乡村存在较大的困难。在短期内乡村发展仍将面临人才、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这将导致乡村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乡村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加大。
3.村民自治运行艰难。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使村民自治运行艰难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1)乡村社会和村民缺乏思想行动约束力。在乡村社会,建立在乡土认同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传统规范等传统约束力在村民摆脱原有社会结构、群体实现个体化的过程中被破坏,致使传统的乡村内生秩序肢解,但乡村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尚未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乡村社会和村民个体的思想缺乏约束,增加了村民自治的难度。(2)村民自治缺乏治理的主体。乡村社会个体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村庄去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据调查:农村家庭中有外出打工人员的占70%以上,其中长期外出打工者占打工人数的一半以上[11],可见村民外流事态相当严峻,乡村缺乏治理主体。(3)乡村基层组织权力弱化,组织动员能力下降。一方面,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组织无法将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使村民更分散、更不关心公共事务,组织动员村民更加困难,增加了村民自治的难度。
三、乡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乡村社会个体化,在乡村引发一些伴生性的治理问题,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如何破解社会个体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了4点建议。
1.重拾乡村社会认同感,增强公民的公共责任感。昔日,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主要来自于共同的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以及稳固的乡村熟人社会;如今,仍应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筑乡村的社会认同。首先,应当重视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吸引村民共同传承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次,应当在继承乡村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制定新的村规民约,创建共同的行为规范。最后,加强宣传引导,弘扬公德心、公共责任意识,教育引导村民避免功利化的人际交往,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只有乡村社会认同得以建立,才能形成村民新的思想行为约束力,防止村民为了个体利益而损坏集体利益;才能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的再次确立,让村民自觉地接受公共规则的约束,自觉地按照共同规范行事;才能增强村民的乡村主体性认知与意识,自觉主动地关心村庄、经营村中事务,以改变乡村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的窘境。
2.维护村民利益,健全村民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使村民更加注重自己利益的获得和保护,因此维护村民利益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在乡村社会个体化过程中,村民不断地与传统秩序和共同体脱离,日益丧失原有共同体的保护,在高流动性的情况下,又欠缺必需的社会制度保障,村民个体变得更加渺小脆弱,因此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也要注重维护村民利益。另外,还应健全村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增加村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即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求助于谁,也不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程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个体化更是使村民的利益维护能力弱化,因此建立健全村民利益表达和维护的渠道与机制十分必要。只有村民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表达和保护,他们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强的意愿去参与村务管理,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
3.保障国家对乡村的各项支持得到有效落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国家对乡村的支持能否真正落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政府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国家为了推动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政策取向、资源配置和规划布局等多方面向乡村倾斜。在国家的这些支持政策得以落实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是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地方政府应当更理性地与乡村干部和百姓增进沟通;国家应当完善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才能有力地保障国家对乡村的各项支持得到充分落实,真正惠及百姓。要实现乡村的发展,要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只依靠国家的支持是不够,乡村还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自主发展。
4.坚持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注重村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其重要的内容,经过40年的实践,被证明是合理的,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我国基层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在我国仍应继续推行。在乡村社会,随着个体化的深度发展,村民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利益,村民的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不断加强,更有必要依法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且更有长久施行下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过程中,应当继续广泛地向村民宣传普及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运作模式,进一步加强对村民的自治意识、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的培养。通过以往的宣传教育,村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自治意识已有显著提高,但是其参与能力和自治能力还亟待提高,可以通过政务公开向村民征求乡村管理的意见建议,落实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自治形式,以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