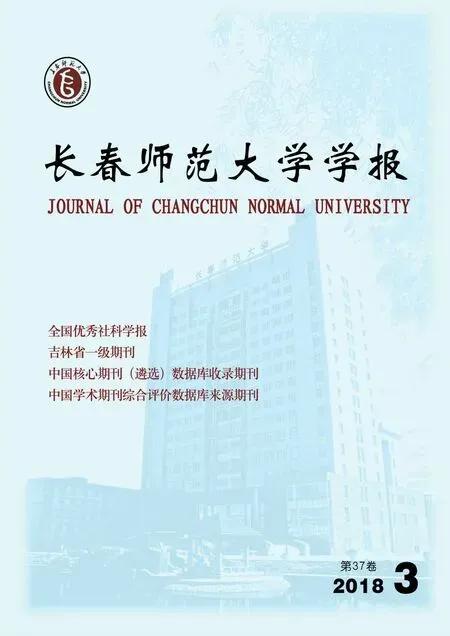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人的污点》中美国民族认同主题解析
徐雯雯
(龙岩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其公民身份具有双重性:一个是民族身份(族群身份);一个是国家身份(美国民族身份)。因此,标示美国人身份的完整称谓应当是“民族+国家”形式(如欧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印第安裔美国人等)。历史上,美国民族身份一度为欧裔美国人所垄断,而非裔、亚裔、印第安裔等有色人种则遭受歧视和排斥,无法拥有真正的美国民族身份。正如奥托·纽曼坦言,“多年来,代表美国人标识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新教派和共和政体都是以排斥其他人为基础的”[1]209。为了践行《独立宣言》宣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信条,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从来没有停止为获得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少数族裔努力获取美国民族身份、“成为”美国人的历史。
《人的污点》(TheHumanStain,2000)是美国当代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lip Roth)迟暮之年创作的“美国三部曲”(American Trilogy)中的最后一部①。该小说采用新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2],通过对雅典娜学院负责教务的前院长、古典文学系资深教授科尔曼·西尔克谜一般生命历程的艺术重构,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权力矛盾和话语张力。自《人的污点》问世以来,国内外学界在评述这部作品时往往止步于探讨其中的族裔(族群)身份问题,极少有人深入关切蕴含其中的国家认同(即主要人物努力获取美国民族身份,“成为”美国人)主题。鉴于此,本文拟从分析该小说的典型叙事特征入手,揭示其故事叙述背后隐含的美国民族认同主题。
一
新现实主义小说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叙事的非线性特征,《人的污点》亦不例外。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时,就好比步入一座故事迷宫,唯有留心隐含其中的时间线索,方能厘清纵横其间的情节脉络。论者往往误将该小说别出心裁的情节安排简单划为一种标新立异的写作游戏,忽略了菲利普·罗斯颇具匠心的情节编排背后意欲表达的深刻主题。《人的污点》的情节设置最使读者惊愕的莫过于它开篇即言“性”事。小说主人公科尔曼一出场,就向小说叙述者内森透露自己(七十一岁)正在和一个无论年龄还是地位都跟自己悬殊很大的中年女性福妮雅(三十四岁的清洁工)维系着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性”关系。“性”主题在美国现当代文坛颇为流行,身为小说家的菲利普·罗斯一向“‘性’趣盎然”[3],他的小说作品里多涉及赤裸裸的“性”事。有观点认为,《人的污点》以“性”开篇实乃娱乐化时代的作家取悦读者的惯用噱头。然而,考虑到菲利普·罗斯毕竟不是流行作家,而是公认的“当今美国的文学时代”的代言人[4]1,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人的污点》开篇情节的“密码”就隐含在它的时间设置上。菲利普·罗斯把科尔曼与内森畅谈“性”事的时间设定在一九九八年可谓意味深长。故事刚开头,内森便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交代了这个貌似平凡的年份所承载的特殊意蕴:这一年,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轰动了整个美国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菲利普·罗斯在陈述整个事件时特意采用细描手法,生动地勾勒出一幅众声喧哗的狂欢场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4]2。狂欢总意味着差异的消解和民主的张扬。小说中,不分族群的美国民众不仅有权利自由喧哗,竟然还嚷嚷着要对美国最高权力象征——总统先生实施阉割惩戒,狂欢的民主特性尽显无遗。在这里,个体观点得到了充分表达,私人情绪得到了充分宣泄;在这里,不管你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是盎格鲁-萨克逊子孙还是非洲黑奴后代,是清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一律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这里,族群身份彻底消失,剩下的惟有美国民族身份,即美国民众的族群身份(子身份)完全融入到美国民族身份(大身份)之中。概言之,菲利普·罗斯笔下(即内森的叙述中)的狂欢场景在身份注明上删除了个体的族群特性,赫然成为多元文化平等共生的时代表征,无形之中凸显了当代美国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烈意识。
在这种文本语境之下,“性”自然不仅是人类个体自然属性的物理标识,还是折射美国多元族群共生状态的文化“棱镜”。通过“一九九八”这一特定时间,菲利普·罗斯把有关科尔曼的故事叙述不着痕迹地嵌入到克林顿执政时代的美国书写之中,让象征普通民众的科尔曼和象征美国民族的克林顿在“性”的主题上并置起来,使读者根本无法辨识二者(作为美国人)除却职业之外的任何差异。在这场20世纪末的全美大狂欢中,“性”显然被菲利普·罗斯赋予一种超越族群界限的文化使命,神奇地给予每个普通民众以平等的美国民族身份。小说中,科尔曼与福妮雅之间超越职位、年龄和种族的亲密关系着实强化了“性”的这一文本特征。在小说结尾部分,科尔曼的妹妹欧内斯廷对美国社会非裔族群生存现状的口头描述为当今美国社会族群身份与美国民族身份的融合状态提供了确凿的文本证据。
与此同时,菲利普·罗斯不忘提醒读者,“性”从来都不是新兴的现代意识产物,而是有着悠久传统的美国古老话题。从霍桑时代的性压制到“美国小姐”时代的性放纵,再到当今时代的性狂欢,“性”早已幻化成为标注美国民族身份历史建构特质的时代符码。在小说叙述者内森精心建构的文学空间里,“性”戏虐性地具备了与美国历史上的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相同的特征,成为激发“美国最古老公众激情”的“兴奋剂”,成为“曝光”美国族群身份与美国民族身份关系状态的“指示器”。“性”的这一角色贯穿于《人的污点》文本始末。科尔曼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因黑人身份而被白人妓女狼狈地赶出了门;参加工作后,与他一直维系着和谐“性”爱关系的女朋友在拜访他的家人时发现了他隐藏在浅色皮肤下的非裔血统,于是乎果断与之诀别。这些有关“性”的情节设置无不客观折射出那个时代非裔族群游离于美国民族身份之外的真实社会状况。
由此看来,《人的污点》以“性”开篇完全是基于小说主题表达的需要:一方面,透过“性”,菲利普·罗斯旨在呈现当今美国社会族群身份和美国民族身份彼此相容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通过“性”,菲利普·罗斯意在暗示美国民族身份的生成性,即历史建构性特质,为小说故事的全面展开(历时地再现科尔曼通过隐匿/背叛自我种族身份努力“成为”美国人的生命历程)埋下伏笔。
二
新现实主义叙事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事实与虚构的融合”[2],《人的污点》在这一点上同样堪称典范。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与想像、写实与虚拟的界限完全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对此,国内外学者均作过相关阐释。其中,德里克·帕克·罗佑(Derek Parker Royal)[5]的论述最为深刻。他在详细论证《人的污点》文本虚构性(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the text,即小说围绕科尔曼展开的故事绝大部分缺乏可靠信息来源,完全凭依叙述者内森的自我想像虚构而成)的同时,颇有见地指出该小说的文本虚构性与科尔曼的身份虚构性(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identity,即科尔曼通过隐匿/背叛非裔身份获得美国民族身份)相映成趣,两者之间暗含着某种隐喻性关联(a metaphorical link)。罗佑的论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人的污点》外表新潮的叙述策略(“非线性叙事”“事实与想像相融合”等)与其内在蕴含的叙事主题(族群身份与美国/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关系及后者的生成性特质”)高度契合的文本特征(即形式与内容的同一性)。
小说中科尔曼身份的虚构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促使内森(抑或内森的创造者菲利普·罗斯)最终决定叙述/虚构科尔曼故事的关键动因。对于内森而言,科尔曼当前的身份状态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获得现在的身份,即如何“成为”现在的他自己。科尔曼原是一位浅肤色的非裔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隐匿/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族群)身份,伪装成一位犹太人并取得了成功。代价则是他不得不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终身隐瞒有关自我身份的秘密。若不是“幽灵”事件,若不是意外车祸,若不是科尔曼妹妹欧内斯廷的陈述,小说的叙述者内森根本无从了解有关科尔曼身份的虚构性本质。小说文本交代,科尔曼甚至以“一名犹太人的身份入葬”。其实,作为小说家的内森一开始对科尔曼的故事并不感兴趣,一度拒绝为科尔曼著书立传。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入发展,内森渐渐对科尔曼的一切充满好感和好奇。内森真正着手讲述/虚构科尔曼的故事(“写这本书”[4]348)是在欧内斯廷向他陈述有关科尔曼的身份秘密之后开始。内森回忆说,送走欧内斯廷之后,自己驾车独自来到科尔曼的墓地,“对正在发生的事茫然无知,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伫立在科尔曼棺木上所覆盖的高低不平的土丘边,我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开始,它的结尾,于是我当场写这本书”[4]348。这段文字明确显示,吸引和打动内森(抑或内森背后的菲利普·罗斯)并驱使他最终下决心叙述/虚构科尔曼故事的原因是科尔曼美国民族身份的“生成”过程(从它开始,到它结束)。简言之,科尔曼由一名处处受挫的非裔青年“蜕变”成为一名近乎功成名就的犹太学者(犹太裔族群在美国也属于少数族群,但远比非裔族群更接近欧裔白人,科尔曼的外貌特征决定了他更适合伪装成犹太人而不是欧裔白人),最终走向毁灭的生命历程才是内森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或许,正是为了充分展现小说主人公科尔曼美国民族身份的“虚构”性特质,《人的污点》才最终选择了“虚构”文本事实的叙述策略。
问题是,科尔曼的身份秘密(科尔曼美国民族身份的生成过程)缘何会给小说家内森带来如此巨大的心灵震撼,以至于他热切地想要叙述/虚构他的故事?根据罗佑的剖析,原因有二:科尔曼的故事极具文学潜质;科尔曼的故事符合菲利普·罗斯一贯秉持的小说务必体现社会关切的创作理念。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罗佑没有深入探究科尔曼故事的文学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也没有继续追问身为犹太作家的菲利普·罗思究竟为什么偏偏执意叙述/虚构一个非裔学者的故事。为更加精准地甄别隐含在小说叙事背后的文本主题,笔者拟对罗佑的上述论点做适当拓展。
首先,分析内森执着叙述/虚构一个非裔学者故事的缘由。如罗佑所论,科尔曼的故事充盈着社会普遍性(socially charged),为步入暮年的犹太作者内森(菲利普·罗斯的文本化身)突破道德伦理藩篱,探究、发现自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文本参照。菲利普·罗斯作为一名犹太作家执意叙述/虚构一个非裔青年的人生故事显然另有原因。一方面,菲利普·罗斯坚决反对别人为自己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超越自我族群的文学叙事始终是他坚持的文学追寻。他曾经严肃宣告世界:“我不是犹太作家,我只是一个身为犹太人的作家,一生最关心的事和最大的热情就是写小说,而不是做个犹太人”[6]1907。另一方面,美国民族身份认同(少数族群的美国/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历史构建)构成《人的污点》的核心主题,小说有限的叙事空间却不允许作者“染指”全部族群,选择某个族群作为代表成为唯一可行的写作方案。非裔族群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少数族裔的典型个案,非裔题材故事不失为菲利普·罗斯写作素材的最佳选项。细心读者不难发现,《人的污点》第二章毫不避讳地讲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仍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事实。
其次,分析科尔曼故事的文学价值。美国文学史上探讨美国民族身份生成机制的作品并不少见,主要有两种模式:容忍(如斯托夫人《汤姆叔叔小屋》中的汤姆叔叔);抗争(如怀特《土生子》中的比格)。科尔曼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即隐匿/背叛。科尔曼的“隐匿/背叛”模式同样属于时代产物,属于非个体现象,然而《人的污点》问世之前鲜有作品深刻揭示之。小说中,小说家内森凭借职业敏感,通过之前与科尔曼“亲密”接触,之后又从欧内斯廷那里打探到关于科尔曼美国民族身份的生成秘密,迅速捕捉到了科尔曼故事的独特价值,于是决心把科尔曼塑造(抑或虚构)成一位通过隐匿/背叛非裔身份成功获取美国民族身份,最后却走向毁灭的希腊悲剧式人物形象。实际上,现实中的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才是发掘美国民族身份生成机制第三模式的第一人。
三
随着小说叙述徐徐展开,围绕科尔曼的身份秘密缓缓揭晓。读者渐渐明白,位于小说开篇的狂欢场景所彰显的统一的当代美国民族身份的背后隐含着沉重的历史叙事:美国民族身份原来一直都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自建国以来,美国民族身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变化、逐步建构的过程。一直以来,为了赢得美国公民平等权利,为了“成为”美国人,处于边缘的少数族裔群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科尔曼的悲剧人生不过是美国旧时代的一抹剪影。科尔曼身份之谜就好比小说结尾处内森与莱斯相遇之地厚厚冰面下漆黑的源流(“真正的黑暗”[4]370),映射出深埋于美国现时代政治文明外壳之下的历史沉痛。小说以《人的污点》为题,或许正是为了暗示并提请读者铭记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经历的这段有“污点”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尔曼的故事仿佛弗莱斯透过厚厚的冰层探入湖中的熠熠发光、微微震颤、坠着诱饵的长长引线。阅读《人的污点》,读者便好比穿过冰封的岁月,重新经历了一次美国“黑暗”历史的精神洗礼。
[注释]
①另外两部分别为:《美国牧歌》(1997),《嫁给一个共产党人》(1998)。
②有的学者据此指出,《人的污点》极有可能是部政治讽喻小说。倘若如此,小说行文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克林顿的同情倒是值得读者仔细回味、认真体悟一番。
[1]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M].南京:南江大学出版社,2008.
[2]姜涛.当代美国小说的新现实主义视域[J].当代外国文学,2007(4):115-121.
[3]黄铁池.不断翻转的万花筒—菲利普·罗斯创作手法流变初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1):56-63.
[4]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Derek Parker Royal.Plotting the Frames of Subjectivity: Identity,Death,and Narrative in Philip Roth’s The Human Stain[J].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06(1):114-140.
[6]Perkins,George,Barbara Perkins.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M].Indiana:Mc-Graw-Hil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