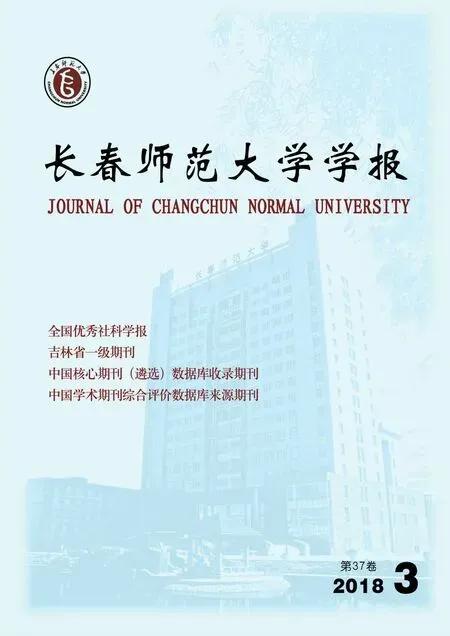论宋哲宗及徽宗时期黄庭坚的重阳簪菊词
李博昊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黄庭坚(1045-1105)一生仕途起伏。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23岁的他考中进士,得授官职,先后担任县尉、国子监教授、吉州太和县等职。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元祐更化,反变法之人陆续被启用,政局发生重大转变,黄庭坚随之迎来仕途的辉煌。元祐元年(1086),其以秘书省教书郎召入馆阁,参与校定《资治通鉴》。后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加集贤校理,升起居舍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虽然此时党派纷争仍十分激烈,但黄庭坚始终保持淡薄超脱的心态。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得势,黄庭坚遭贬四川涪州别驾,先后被安置在黔州、戎州。徽宗即位,其又被任命为舒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均未到任。崇宁元年(1102)六月知安徽太平州,九日而罢,流寓荆州、鄂州一带。崇宁二年(1103),以“幸灾谤国”罪名被除名,流放广西宜州编管。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死于贬所,终年61岁。
绍圣元年(1094)后,黄庭坚屡遭谪迁,历经人生种种坎坷,却始终风流自适。哲宗、徽宗时期数量颇多的重阳簪菊词,展示出山谷傲岸的品格与达观的心态。
一、黄庭坚赠弟重阳簪菊词
绍圣三年(1096)重九,黄庭坚作《清平乐·示知命》:“乍晴秋好。黄菊欹乌帽。不见清谈人绝倒。更忆添丁小小。 蜀娘漫点花酥。酒槽空滴真珠。兄弟四人别住,他年同插茱萸。”[1]186
“知命”,即黄庭坚之弟黄叔达。绍圣二年(1095),山谷被贬黔州。此年秋,“其弟知命自芜湖登舟,携一妾,一子,及山谷之子相,并其所生母俱来。知命中道生一女,又与其从兄嗣直会于夔州”;三年(1096)“五月六日,抵黔南”[2]23。叔达携家及庭坚子历尽坎坷,从芜湖至黔南与庭坚会面。此年重九,庭坚当与知命一起度过,词中“乍晴秋好”“蜀娘点酥”“酒槽滴真珠”等表达,展示出其逆境中却适然之心情。
元符元年(1098),黄庭坚被朝廷以“回避亲嫌”之名由黔州迁至戎州,在戎州城南租寓所一间,名曰“任运堂”。其《任运堂铭》曰:“或见僦居之小堂名任运,恐好事者或以借口。余曰:腾腾和尚歌云:‘今日任运腾腾,明日腾腾任运。’堂盖取诸此。余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但不除须发、一无能老比丘,尚不可邪?”《全宋文》卷二三一五载其《书韩愈送孟郊序赠张大同》谈到此时生活之况:“寓舍在城南屠儿村侧,蓬藋拄宇,鼪鼯同径,然颇为诸少年以文章翰墨见强,尚有中州时举子习气未除耳。至于风日晴暖,策杖扶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间,老子于诸公亦有一日之长。”[3]327黄庭坚生活艰苦,但颇为地方文人仰慕,青年学子亦向之求教。黄庭坚虽担心自身获罪连累近己诸人,却仍愿结交朋友、奖掖后进,颇有江西豪士之风。其时,黄庭坚创作了多篇和黄叔达的簪菊之作。
元符二年(1099)重阳节前后,黄庭坚作《南乡子·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次韵》:“招唤欲千回。暂得尊前笑口开。万水千山还么去,悠哉。酒面黄花欲醉谁。 顾影又徘徊。立到斜风细雨吹。见我未衰容易去,还来。不道年年即渐衰。”[1]128展示出万水千山若等闲的襟怀。黄庭坚另有一首《南乡子》仍次黄叔达韵:“未报贾船回。三径荒锄菊卧开。想得邻船霜笛罢,沾衣。不为涪翁更为谁。 风力袅萸枝。酒面红鳞惬细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1]129同样表现出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气韵。
元符二年(199),黄庭坚又作《谒金门·戏赠知命》:“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 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1]192离家万里,浮生若梦,纵然“余生今已矣”,“君”却如成蹊之桃李,“我”仍具松桂之骨力。词中纵有韶华逝去的怅惘,亦有一种“乐夫天命复奚疑”的达观。此年知命从黔南归江南,卒于荆州途中。《山谷题跋》卷六《题知命弟书后》言知命乃“江西豪士也……作小诗乐府,清丽可爱,读书不多,亦会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盖棺”[4]56。委实令人叹息!
二、黄庭坚重阳簪菊词中的典故
黄庭坚赠弟的簪菊词不仅传达出兄弟间的浓情,更展示出山谷淡薄旷达的风度。此种气宇在山谷其他簪菊词作中亦有呈现,集中体现于词内所用典故中。
绍圣四年(1097)重阳,黄庭坚谪居黔州。地方官吏仰其文名与品节,对之照拂有加。新为黔守的高左藏邀其参加重阳聚会,黄庭坚次高韵,作《定风波》:“自断此生休问天。白头波上泛孤船。老去文章无气味。惟悴。不堪驱使菊花前。 闻道使君携将吏。高会。参军吹帽晚风颠。千骑插花秋色暮。归去。翠娥扶入醉时肩。”[1]87词中使用“龙山落帽”之典,传达出一种风吹浪打皆似闲庭信步的心态。《晋书》载,孟嘉曾为桓温参军,颇为温看重。重九之日,桓温龙山宴集,众僚佐皆至,有风吹落孟嘉之帽,嘉却未察觉。温令左右之人勿言此事以观嘉之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5]2580。孟嘉之举展示出处乱不惊的恢弘气度。桓温席上的“僚佐毕集”与山谷词中的“使君高会”皆是宾朋满座,“千骑插花”的风流潇洒亦是“龙山落帽”风仪之延续。词中传达出黄庭坚翠娥扶肩的风流与追慕古人的旷达。黄庭坚钦仰孟嘉的儒雅倜傥,甚喜“龙山落帽”之典。元符二年(1099),山谷所作《鹧鸪天》仍用此典:“寒雁初来秋影寒。霜林风过叶声干。龙山落帽千年事,我对西风犹整冠。 兰委佩,菊堪餐。人情时事半悲欢。但将酩酊酬佳节,更把茱萸仔细看。”[1]140佩兰餐菊,对风整冠,此等高洁与洒脱确似孟嘉之气度翩翩。
绍圣四年(1097)重阳,山谷在黔南,处摩围之下,作《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1]87词中使用“台南戏马”的典故。戏马台,乃项羽定都彭城后为观将士驰马操练所筑。唐李善注《昭明文选》引萧子显《齐书》曰:“宋武帝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项羽戏马台射,其后相承,以为旧准。”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尚书令孔靖归隐之时,刘裕曾于重阳节在戏马台为之设宴饯行,群僚赋诗唱和。谢瞻和谢灵运各作一首《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传达赞美与惜别之意。山谷词中的“戏马台南追两谢”“风流犹拍古人肩”,展示出其笑对逆境的轩昂气宇。
崇宁二年(1103),蔡京等人加大对旧党中人的打压力度,不仅下诏销毁黄庭坚文集,还将其名刻于“元祐奸党碑”。其后黄庭坚被遣送宜州,但其在宜州为官府倾轧,不得住城中、不可租民宅、不许住寺院,只能栖身于破旧废弃的戍楼中。崇宁四年(1105),黄在宜州作《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1]132词中再用“台南戏马”之典。作此词时,黄庭坚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然风流气骨犹在。佚名《道山清话》言:“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略)。’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传达着山谷看透人生后的平静与豁达。
黄庭坚另有《清平乐》言:“休推小户。看即风光暮。萸粉菊英浮碗醑。报答风光有处。 几回笑口能开。少年不肯重来。借问牛山戏马,今为谁姓池台。”[1]184《晏子春秋》记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韩诗外传》载:“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牛山因景公之涕泣而充满感伤色彩,山谷此词却以戏马牛山之风流,一扫沉郁之气,疏阔之心胸在字里行间得以显现。
三、黄庭坚创作簪菊词之因由
黄庭坚作簪菊词与宋人的喜好有关。宋人爱簪花,其动因既有朝廷的提倡,亦有民间的追随。《宋史》载,“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阀位立,谢花,再拜讫”[6]2695。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言:“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七《簪花》亦记,洛中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7]186。
宋人簪花种类繁多,因而有诸多与簪花有关的诗作传世。如王禹偁《杏花》:“争戴满头红烂漫,至今犹杂桂枝香”;苏轼《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绿珠吹笛何时见,欲把斜红插皂罗”;杨万里“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而黄庭坚对菊情有独钟,如《鹧鸪天》:“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环绕折残枝。自然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无闲事,即芳期。菊花须插满头归。宜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送落晖”[1]146;《清平乐》:“舞鬟娟好。白发黄花帽。醉任旁观嘲潦倒。扶老偏宜年小。 舞回脸玉胸酥。缠头一斛明珠。日日梁州薄媚,年年金菊茱萸”[1]185。
《艺文类聚》言菊有五美:“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菊花傲冷,独有芳菲,自古即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离骚》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魏文帝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言:“群木百草无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8]269;钟会《菊花赋》曰:“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茂乎凝霜。挺葳蕤于苍春兮,表壮观乎金商”[9]635;陶渊明《九日闲居·并序》更言:“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其华,寄怀于言。”菊之气度风骨与身处冷境却从容自若的黄庭坚相合,当是山谷喜菊的重要原因。所以无论是“黄菊满东篱。与客携壶上翠微”“浊酒黄花,画檐十日无秋燕”,还是“黄花当户。已觉秋容暮”“萸粉菊英浮碗醑。报答风光有处”,皆展示出山谷傲岸之气骨与自适之心境。
逆境中的黄庭坚喜追忆少年时光,但非惆怅与伤感,而是豁达与豪爽。故沈际飞《草堂诗余》言:“山谷‘白发簪花不解愁’……,自叹自乐,善于处老。”作于元符二年(1099)重阳的《鹧鸪天·坐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言:“黄菊枝头破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1]142黄苏《蓼园词选》评:“曰‘破寒’,更写得菊精神出。曰‘斜吹雨’、‘倒著冠’,则有傲傲不平气在。末二句,尤有牢骚。然自清迥独出,骨力不凡。”[10]36此一评价切中肯綮,纵然风流的年少时光已逝,纵然生活中有种种磨难,但黄庭坚依然热爱生活,依然追求美好的事物,俊逸洒脱,气定神闲。数量颇多的重阳簪菊词,即是此种心境之展现。
[1]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黄庭坚.山谷诗集注·目录(年谱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成都:巴蜀书社,1994.
[4]黄庭坚.山谷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9]龚克昌.全三国赋评注[M].济南:齐鲁书社,2013.
[10]黄苏,等.清人选评词集三种·蓼园词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