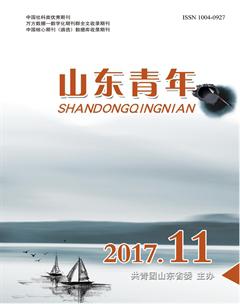收受礼金入罪要审慎
施可群
摘 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是否构成受贿罪,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如果是特殊时日正常的人情往来,收受礼金不应认定为受贿;如果是钱权交易、权力寻租,无疑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
关键词:收受礼金;受贿罪;定罪量刑 ;情感联络
一、 关于礼金的双重性质
一方面,在《说文解字》中,礼被解释为“用来敬神致福的仪式”,即在社会生活中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进而泛化成表示庆贺、友好或敬意所赠之物,而礼金就是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故先人尚礼,形成了“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文化传统。人们在逢年过节等重要时日彼此互送礼金来表达祝福,是亲朋好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因而彼时,礼金似乎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一个色彩鲜明的褒义词。
而另一方面,在现今社会,人们“提礼而色变”,礼金不仅被戏谑成“红色炸弹”,甚至被视为晃荡社会无往而不利的“通行证”,礼金披上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神秘面纱。尤其呈送礼金是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时,钱权交易很快就会一拍即合、狼狈为奸,伴生出权利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乱象,其结果必然是侵犯国家的廉政制度建设和公权力的不可收买性。因故,此时礼金似乎沦为了“潜规则”的一个代称,堕化成了不折不扣的贬义词。
二、 礼金入刑的“立法口号”
陈兴良教授曾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增设“收受礼金罪”,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谋取利益,都可以认定此罪。此論一处,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礼金入刑的讨论在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激烈得展开。大部分人士都赞成此观点,他们认为创设收受礼金罪,将极大地打击职务受贿犯罪的力度。现行法律文件中,国家对其工作人员的廉洁管控不可谓不严,不论是《刑法》第385条的受贿罪,第388条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对多种形式的行为进行了界定,将收受干股、赌博收钱、挂名领薪等符合条件的行为认定为受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变着法子收受贿赂,接受礼金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索取贿赂外,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收受贿赂型犯罪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显然,这无法对感情投资的呈送礼金的行为予以处理,遂造成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乱象丛生,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与国家机关的职务廉洁性。增设收受礼金罪,可以将此类受贿行为一网打尽,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的这个罪名的设置将解决官员的情感投资问题:一来,扩大刑法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打击力度,弥补现行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定罪不足问题,威慑潜在犯罪嫌疑人,营造廉洁守法的官场环境;再者,解决“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明困境问题,实现违法行为的罪名兜底,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尾呼应,形成严惩损害国家机关政务廉洁性的犯罪打击网。
然而,事非人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涉及贪污受贿罪在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但仔细研读可发现,其间并没有对于礼金入刑的任何表述,礼金入刑在法律上仍没有立足之地。倡议礼金入刑的美好愿景得以落空。
三、 收受礼金构罪的审慎思考
其实,早在1992年,中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金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对于收受礼金即有明文规定:一切礼品馈赠,不论价值大小,均不得接受;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礼金必须进行登记或上交。各省市机关单位也均有类似的规定,其中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礼品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严禁公职人员利用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工作调动、子女上学等机会收受礼金、礼品(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和上级单位、本单位组织的慰问)。这些,都足以说明党政机关对于收受礼金、礼品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但遗憾的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仅仅只是受到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均与刑事犯罪无涉。因此,颇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意味。由此,从应然性角度反映出,礼金无法入刑之无奈与艰辛。
当然,抛开上开之论述,从实然性的刑法理论与实践出发,收受礼金也应做非罪化倡导。
其一,收受礼金如果入刑,其作为受贿罪的兜底条款,在免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后,势必变得宽泛,造成入罪门槛低的结果。此时,当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犯罪时,就会有将本是受贿行为往收受礼金行为上靠的侥幸心理,以试图摆脱更严重的刑法处罚,这完全背离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处罚原则,也无怪乎有人将其比作又一个“嫖宿幼女罪”!如此一来,本意致力于打击腐败,解决官员“感情投资”问题的收受礼金罪在司法实践中异化成助长犯罪,减轻刑罚的法门,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其二,收受礼金如果入刑,实践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礼金数额问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个人一般情况下的受贿数额限定在3万元以上,考虑到收受礼金罪的简易构成要件,其起刑点数额肯定要比受贿罪的3万元要高,但我国地域辽阔,三里不同乡,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人们送礼的标准差异极大,那么如何确定一个切实统一的定罪标准,是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礼金具有如上双重属性,如果收受礼金入刑,是否意味着普通百姓之间的礼尚往来是情感纽带的正常维系,而对官员的礼金呈送就变成了感情投资的权钱交易呢?显然不是!假使呈送国家工作人员的礼金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即礼金的追求不在权力而在亲情友情,那么不管数额多大都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完全是民风民俗的体现。相反,如果礼金的性质是贿赂,暗中进行权钱交易,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么毫无疑问,收受礼金的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受贿行为。实践中,送礼的人往往没有明确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办事的要求,仅仅是借“礼”完成情感上的接近,而官员一般也不会立即为送礼人谋取利益或提供便利,体现着非常微妙的关系。此时,判断礼金是否属于贿赂款,应根据送礼者和收礼者的关系渊源、情感程度、收礼缘由、礼金数额、社会通识、消费水平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如果关系、情感一般,礼金数额远超社会平均认知,那么此时认定为受贿罪应该无可置疑。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短时间内礼金入刑无望的情况下,对于收受礼金是否构成贿赂罪应该慎重。但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两高的司法解释中也开了一个口子“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实践中到底如何适用此司法解释条款,是否为变相的礼金入“刑”,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赵煜:《受贿认定疑难问题及立法完善》,《法治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2-17页。
[2] 王群:《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入刑的冷思考》,《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2期,第139-142页。
[3] 郝艳兵:《“收受礼金罪”不是口号立法》,《检察日报》,2014年10月13日,第3版。
(作者单位: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浙江 慈溪 31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