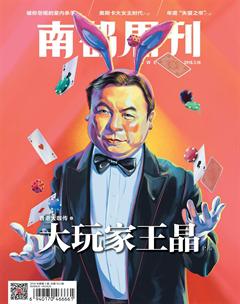吴晓波又在堆砌食材,做得半生不熟
郑渝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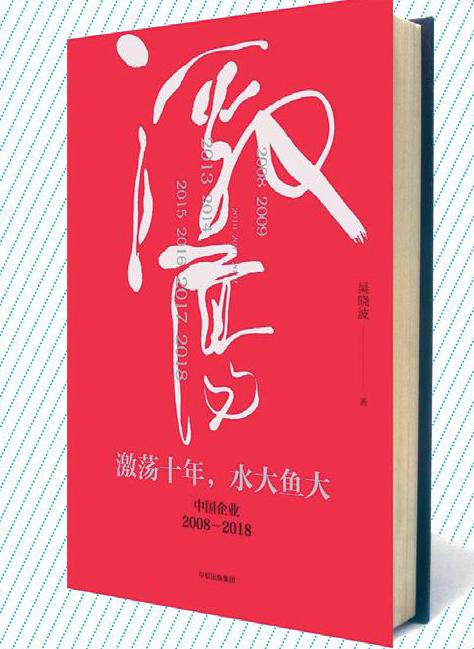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定价:58.00元
国内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2017年推出新著《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以2008年为起点,梳理回顾了最近十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各行业代表性企业的发展概况。
这本书有没有亮点?有。这可以被当成一本最近十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发展环境演变的备忘录,读者可以通过大量细节的描述,惊愕地想起,仅仅就在几年之前,还存在而今天看起来无法让人理解、接近荒诞的监管政策以及行业竞争方式。就拿腾讯来说,3Q大战之前,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双输的“战争”会导致这家巨头突然转变为大众创新的支持者。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的鲜明特点在于,就是延续了书作者《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的一贯风格。
那是什么风格呢?从威廉·曼彻斯特的底色,加入许知远式的抒情,然后用罗振宇的方式进行精简,变成一种“情怀型编年叙事”。如果你是一个愿意看经管书又很有情怀的人,阅读《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会因为读到大量的、密集的、平铺直叙并偶尔穿插抒情式表达的事件、人物、论题,变得泪流满面——但问题是,你读完这样的书,根本记不起来自己读了啥,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换句话说,《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许知远的文体,素为许多人所不喜,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很懂得把握叙述的重点,无论是感慨还是卖萌,总能找对槽点。而威廉·曼彻斯特的叙述虽然看上去拉拉杂杂,但非常擅长将历史的宿命感和忧伤贯穿进去,让重点事件和人物都变得很清晰。再说罗振宇,人家直截了当就说得很清楚:“卖干货”!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对上述三种方式的组合,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经济史论谈风格:一堆上好的经济史“食材”,用文艺的方式串联起来,主推“企业家权益”“经济环境沧桑演变”的情怀,却没有经过精致化的加工,最终“上桌”的,是半生不熟的“杂烩”。这必然让读者陷入思考疲劳。这样一本书,跟书作者巅峰时期的《大败局》相比,可谓鸿沟巨大。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传递的价值观念,也很值得商榷。这本书将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概括为:制度创新、容忍非均衡(允许非均衡发展,甚至容忍“灰度治理”)、规模效益、技术破壁四项。这个结论的得出,其实跟整本书拉拉杂杂的叙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作者也没有交待论证概括的过程。
作者所称的四项动力,以及因此造就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缺陷重重的创造发展成绩,同时也造成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日后需要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耗损更多的社会信任。
就拿所谓的容忍非均衡来说,这似乎就是鼓励创新、容许变通,甚至为了试错可以跨越底线的做法。问题是,很多情况下,容忍非均衡,会让权宜之计变成并不具有公平性的固定做法,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城市已经变得无法摆脱对“卖地财政”的依赖,并无半点意愿去抑制高企的房价。
容忍非均衡,不但可以体现为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外资投资的容忍,也能表现为拒绝履行劳工保障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的容忍。2008年围绕《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争议,大量经济学家出位炮轰劳工保护,充分暴露出这批人的法律观念的淡薄、伦理意识的空白,这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学领域是不可能想象的。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书中,你只会看到书作者轻描淡写的提到了这番争议,却没有进行任何或法理或伦理或经济学定理等方面的深入探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一些突破当时法律的探索,发挥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突破禁区和边界,就是值得倡导的经营观念。事实上,如果可以随便犯规,企业也就不存在必要的动力和压力去投资技术创新。《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将企业家权益的主張,与美其名曰“容忍非均衡”的随便突破禁区和边界的概念混在一起,无疑只会造就思想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