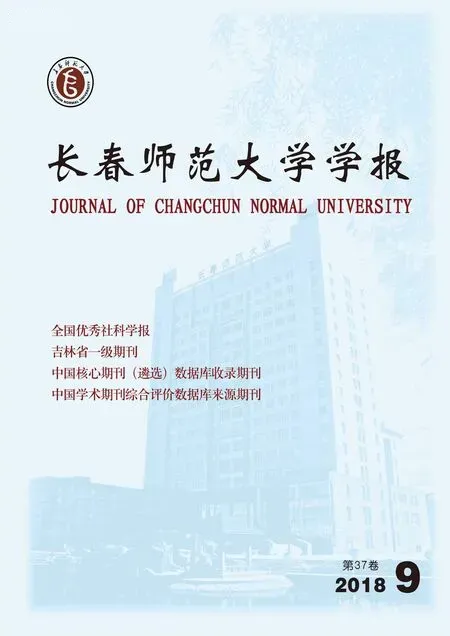鲁滨逊和摩尔的漂流印象
王春侠,范立彬
(1.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2.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笛福生于伦敦,只受过中等教育,曾经学习当牧师,后转向经商。1692年,他因为生意失败而负债累累,为谋生而为报社撰写政论文章,又因时常抨击国王和执政党而屡陷牢狱,遂转向小说创作。
1719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各界评论家对笛福的此部小说纷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说:孩童时期,这部书只是读来有趣,成人之后再去读,就会知道这是不朽的杰作。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评论道:鲁滨逊是大英帝国殖民开拓者的真正原型。法国思想家卢梭有言:《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合乎情理地解决问题和通过实践来学习的经典。英国文学史家艾伦总结说: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都遭受孤寂的折磨。笛福象征性地描述了这种孤独,把鲁滨逊和上帝一起抛到了荒岛上,因此《鲁滨逊漂流记》其实是描述了一种普通人的经历感受的寓言故事,因为我们都是鲁滨逊,像鲁滨逊那样孤独是人的命运。笛福出生的这一年正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笛福在政党倾向上立场不稳。作为一名“雇佣作家”,他今天会写文章讽刺托利党,明天又可能为托利党所用而写文章批评辉格党。所以,不少英国批评家认为笛福的人格十分低劣。尽管外界对笛福的评论褒贬,笛福在文学造诣上的光辉是不能被一笔抹杀的。他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风格笔锋犀利,揭露入骨,为他赢得了英语小说之父的美誉。笛福小说的深刻性与他悲喜交加的生活历程不可分割。
笛福曾在一首诗里说过:“没有人像我经历如此不同的命运,一生中多少次富贵,多少次赤贫”。[1]生活际遇的变化使笛福对生活在困苦中的人的情感具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更能一针见血地体会到为生计忙碌、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们想要摆脱苦难的千方百计与无计可施的辛酸。这种凄苦人生阅历成就了笛福海上冒险的孤胆英雄式小说,还打造了他彰显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关怀小说。他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男主人公鲁滨逊和《摩尔·弗兰德斯》的女主人公弗兰德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美国文艺理论家安妮特·T.鲁宾斯坦(Annette T.Rubinstein)评价说“摩尔·弗兰得斯‘正传’确实是《鲁滨孙飘流记》的姐妹篇——写的是类似鲁滨孙的女人故事”。[2]女权主义理论要求读者“从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抗拒型读者”,要求“女性读者颠覆菲勒斯批评权威,以自身的经验来对这些作品进行创造性的女性阅读”。[3]因此,本文尝试性地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还原一种鲁滨逊式的摩尔形象,从中洞察笛福先进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
一、对梦想的不言放弃
笛福和摩尔都是对自己所憧憬的目标不会轻言放弃的人。笛福不安于小康家庭的稳定生活,不顾父母的劝阻与反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历经海浪的冒险之旅。对不谙海事的鲁滨逊来说,海上风险千变万化,见识过大海狰狞的鲁滨逊萌生过退意,但“简而言之,只要风浪一退,大海海面又恢复平静,使人感到安详的时候,我的慌乱心情也趋于结束,担心和恐惧大海会吞没我的思想也便消失,过去久久不能忘怀的愿望又回来了,在危难时刻我发过的誓言和承诺也忘得一干二净。”[1]“像从前我不听从父母的话而从家中出走一样,我对目前的生活又感到不满足。我本来可以在种植园事业上兴旺发达成为富人,而现在对这种幸福的观点已不感兴趣,却想去追求一种鲁莽的和过分的生活,这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不近情理的妄想,使我又一次把自己抛进人类不幸的深渊,这是人们所未曾遇到过的深渊,如果没有这种妄想,我能够和健康的生活状态保持和谐。”[1]这并不是鲁滨逊好了伤疤忘了痛,而是因为鲁滨逊把海上历险看成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他有着对梦想的执着精神,为了能做他喜爱的事情,可以不畏艰苦,不怕丢掉性命,这份胆量和敢做敢为的勇气就是来自对梦想的砥砺。
摩尔身上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对梦想的执着态度也是可见一斑。摩尔历经数年的偷盗生涯后,积攒了一笔可以使她安稳生活的积蓄,但偷盗生活的惊险刺激时时敲打着她的神经。她在这一行当中的老练沉稳和易如反掌的数次脱险使她视偷盗为自己的专长。为了能够发展可以使自己大展身手的“事业”,也为了满足她内心无法抹杀的对物质渴求的欲望,他一次次在惊魂未定的偷盗之后又给自己设定偷盗数额的目标,使自己侥幸逃脱被抓之后,屡次踏上不归殊途,欲罢不能。可以说,摩尔和鲁滨逊一样,都有着对理想的执着精神。摩尔的“理想”不甚光彩,存在着人性贪欲的铜臭味,但她同鲁滨逊是一样的人,内心之中都存有不灭的抱负与幻想。摩尔身上反映出男子般的不懈与坚韧,与鲁滨逊具有相同的为追求自己所要成就的梦想而不惜代价的个性特征。
二、对生活的乐观持善
鲁滨逊的个人品德是健康的,他热爱劳动、不辞辛苦,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都向好的方面想,向前看,一件事不成,再重新来过,没有工具,自己想办法做。因为岛上就他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一切都得独立干。他以积极的方法求生,不自暴自弃,永远对将来生活远景有美好的愿望。“然后,我指着面前的大海,心中暗说:遇到了恶的一方面要考虑到其中的好处,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由此而来的更大的坏处。然后我又考虑到,我现在的生活如此充足不是很不错吗?如果……”[1]
鲁滨逊身处困境,身陷孤岛,在人烟罕至之所孤苦凄凉,但在逆境之中没有放弃对生存的欲望,尤其是知足常乐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他在危困境地不放弃对脱身的憧憬;他的实干精神让他踏踏实实地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境况。我们从他的行动之中可以看到鲁滨逊身上所背负的向上信念: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机会生活下去,只要能够生活下去,就总有办法让生活变得更好。
摩尔身上洋溢着对待生活无比热爱的勇气与激情。“在世上,我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朋友,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也没有人肯帮助我。”[4]她在人生之初便遭遇到颠沛流离的苦楚,但即便如此,仍旧不屈不挠地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在被诱奸最终遭到遗弃之后,她能变通地嫁给富家二儿子;在丈夫死后被驱赶出家门之后,她能为生计考量,为自己寻找具有经济背景的另一夫婿;她在遇人不淑、被现任丈夫挥霍了部分钱财而再次遭抛弃后,能够务实地看到自己已青春不在,财富不如昨日,便努力乔装,想要钓个金龟婿,却不成想又再次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上了江洋大盗的当。她对生活从来没有气馁,继续把生存的梦想寄托在社会的主宰者——男人身上。在终得佳婿、远嫁美洲、生活安定之后,不成想命运弄人,自己的夫婿竟然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可以说,生活已把摩尔逼到了绝路,没有给她一丝生活下去的余光。但摩尔就是如此乐观,在渴求生活安康而不遂人愿之时每每选择整装待发,以对待生活、对待逆境不妥协的态度毅然走上偷盗的道路,以这份不光彩的活计来独立谋生。最后,即使不幸被抓而被流放到“新世界”时,她也没有放弃对新生活的热望与求索,并在全力周旋与经营下终于与她所曾倾心、但也曾欺骗过她的男子过上安稳生活,在迟暮之年像鲁滨逊一样迎来了此生的“出岛”之日。
三、对亲情的淡然处之
两部小说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弱化了主人公与家人的亲情关系,突出了主人公个性特征的需要,并服务于笛福现实主义的写作特色。
《鲁滨逊漂流记》的开篇即是鲁滨逊对自己家庭背景的自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是中校军官,在弗兰德的英国步兵团服务。起初他在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领导下工作,后来在敦刻尔克附近和西班牙人作战时牺牲。至于另一位哥哥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就好像我的父亲和母亲对我以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1]鲁滨逊成长在缺乏手足亲情的环境中,幼时没有同龄兄弟姐妹的陪伴,有着“从小满脑子幻想着出洋远游”的梦想就不足为怪。后来,鲁滨逊毅然离开家庭,在未被困守荒岛之前在巴西开创了自己的种植园事业,但在巴西开创生活的数年间也未曾与家人父母取得任何联系。之后,鲁滨逊在荒岛一困就是27年之久。他脱困出岛后,世事已经物是人非,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和家也没有了,只找到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兄的两个孩子。所以,在漂泊的大半生中,他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温馨的团圆之乐,可能这种亲情围绕的乐趣也不是他心之所往。
《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摩尔出生在新门监狱中,父亲不详,从出生之日起就没有体验过父母双亲对她的呵护之爱。成长在福利院中的她在观念中没有形成过对家庭和亲情的概念,在日后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对骨肉亲情的叙述都显得淡然。摩尔在多次的婚姻中生育了多位子女,有的早年夭折,有的被留守夫家,有的迫于生计被卖予他人。总而言之,摩尔没有陪伴在任何一位子女的身边,整篇小说也没有浪费笔墨渲染摩尔失去子女的悲伤。对具有天生母性的女性来讲,子女是她们腹中孕育十月的生命延续,是世间的至亲至爱之人。每个女人都会无法忍受与骨肉的别离和今生的不闻不问,但摩尔做到了,即使后来有幸回到美洲新世界,与同母异父的丈夫所生下的儿子近在咫尺,也只是选择相望而居的两下生活。
笛福如此处理鲁滨逊和摩尔对待亲情的淡漠,应该是要从鲁滨逊的身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为实现自身的野心抱负而不顾及家庭温情的自私与冷酷;要从摩尔身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与无情,贫苦阶级民众为了能够苟存于世,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顾及骨肉离散。所以,笛福的现实主义写作特色能够全面诠释鲁滨逊和摩尔对亲情淡而处之的缘故。
四、对宗教信仰的游移不屑
在困守荒岛的生活历程中,鲁滨逊渐渐滋生出对宗教的情感。他知道这些生活中的迹象与上帝的意旨在某种情况下是偶发的,但还是把这些迹象和宗教观念联系起来。比如,船上的人全都淹死了,唯有他一人活在人世;他在孤岛上突然看到地上出现了麦苗和稻苗;他无意中翻开《圣经》,一眼就看到一句话,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理,他都把上述种种认为是上帝的神迹。其实,鲁滨逊一人生活在孤岛上,没有人和他交往,感到寂寞。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他就可能忧郁而亡。宗教思想有时会成为一种动力,能够支撑有机体的生存。但鲁滨逊不是绝对的宗教家,一旦脱离险境,他就把对上帝的感恩戴德抛诸脑后;在英国时他是基督教徒,到了巴西则改宗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的宗教观是为他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他的生存以宗教为依托。
在摩尔的生活轨迹中更不可能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指导。她一生中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所面对的生活现实不能给予她任何皈依宗教的机会。为了艰难地存活于世,她一生中犯偷窃、奸淫、不守贞洁之罪,所行之事处处体现的都是对摩西十诫规约的违背。对于为了朝不保夕的生计而疲于奔命的人来说,哪里还有时间去信奉宗教,哪里还有心绪去畏惧神灵。摩尔不具有对上帝的敬畏,在困顿的生活中仅存的一点良善之心消失殆尽。只要能够获取物质上的收益,她便倍感欢欣。“我的一切忏悔似乎都只是由于害怕死亡所致,并非为我过的那种邪恶生活真诚地感到悔恨。”[5]在为生活计的前提下,她就如同迷途的羔羊,直到被捉现行、面临死刑的裁决之时,才真心悔过。
五、结语
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着重叙述男性在物质世界的横冲直撞,表达了中产阶级为攫取更多财富而甘愿冒险的贪婪欲望。鲁滨逊最后逃离孤岛并获取种植园财富的结局表现了笛福思想中所存在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妥协的思想,他的意念中存有对资本家所鼓吹的辛勤劳动终能有所获这一蛊惑思想的幻想。而他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则在主题剖析方面更加深刻,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疾苦更加关注。摩尔与鲁滨逊相同的气质特征,体现了笛福女性主义意识的火花。笛福没有把摩尔塑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卑微存在,而是赋予她男子的气概。这是笛福对于女性生存能力的认可,这是把女性置于与男性平等地位的肇始。在笛福的笔下,女性不再是生活的配角,同样载满风帆,在人生旅途的荒岛中可以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