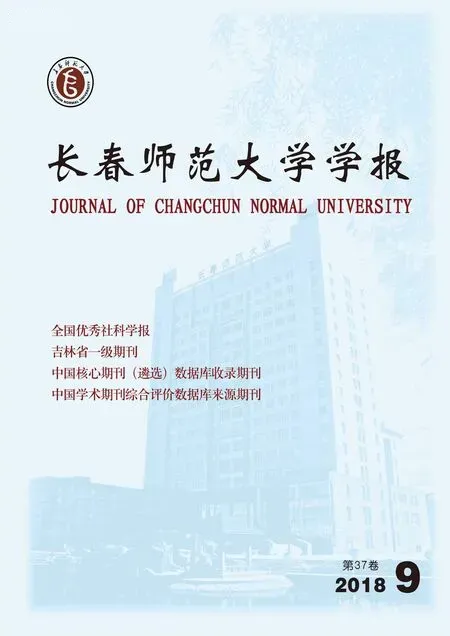从对儒家诗教之依违看《洛神赋》主题
陈丽妍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吕梁 033000)
《洛神赋》全篇大致以现实—想象—现实为发展脉络,想象占了全诗的主体部分。因此,想象部分和回归现实的过渡之处应格外受到关注。其想象发端于“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282,终于“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1]284回归现实的首句便是“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1]284-285,而本句也成为全诗最为突兀的一句,致使《洛神赋》主题之多解,如“感甄说”“寄心文帝说”“抒写理想说”等。但各家对行文构思基本可以达成一致,即始于“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终于“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由此可见,《洛神赋》的行文安排始于情、终于礼,即对儒家诗教做了最大限度的依从。因此,对《洛神赋》中所体现的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对《洛神赋》主旨的揭示。
通过对文本及相关史实的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这种依从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依从的背后隐藏了诸多文本内部的自相矛盾及对史实的有意疏离。诚如《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15即“情”是真实的,“礼义”则未必真实,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
“发乎情,止乎礼义”,是《诗大序》对“诗三百”的基本价值界定之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6-15经《毛诗序》提出之后,“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成了儒家关于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文学在汉代儒家诗教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诚如钱穆先生所说:“盖建安文学之所由异于前者,古之为文,则莫不于社会实际事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经史百家皆然。故古有文章而无文人。……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特种之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3]104曹植作为建安文学领军人物,继承了汉代文人“缘身世之感,披文以入情”的创作方法。《洛神赋》作为曹植生前的代表作,无疑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文人之文”中的至者,即融注了曹植个人的主观情感。故而,曹植在《洛神赋》中所表达的情感由何而来便成为探究其主题之关键。
一、《洛神赋》“情”之缘起
李善为《昭明文选》注“情类赋”之“情”曰:“《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基于对“情”“色”之同质性认识,即二者是同义词,李善注《洛神赋》云:
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自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4]895-896
至此,便有了《洛神赋》“感甄说”主题。诚然,在《洛神赋》中,曹植自叙有感于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从而展开对洛水女神的全面铺写。这种情感的迸发符合人类的原始本能,即“民之性也”。至于其中的洛水女神确为甄氏,还是被他父亲赐死的发妻崔氏,抑或曹植的其他思慕者,无论何者都可能引发曹植的原始冲动。但若将这种引发其情感的主体揣度成其王兄曹丕不免有些失当。据《洛神赋》开篇所叙“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以及赋文开始所叙的行程路线——“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1]282-283可知,曹植此次是从洛阳出发,背朝伊阙向东南方行进,经过通谷、轘辕、景山等地而来到洛水之畔。经洛水而思宓妃,感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而作《洛神赋》便顺理成章,无非仿效之作。诚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42,至于洛水女神是否有实指也只能见仁见智。
这里所说的“情”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情感之“情”,也包括《毛诗序》中所阐述的“在心为志”的“志”,即内心的意愿、心志、理想,它是个人的、主观的、自由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将《洛神赋》中所生发的“情”理解成曹植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未尝不可,也完全符合文中塑造的洛水女神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形象。
二、《洛神赋》“礼义”之旨归
对于《洛神赋》的主题,有学者在否定“感甄说”的同时,又提出了“寄心文帝说”。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基于对《洛神赋》篇末“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这一句的关注。此句非常符合“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传统,但仅此一句能否证明曹植写作《洛神赋》的目的就是向王兄明志,有待商榷。首先,曹植与曹丕的关系并非兄爱弟敬、兄友弟恭。曹操在世时对曹植的偏爱已经使得兄弟二人心生嫌隙。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为铜雀台题赋“援笔立成”[6]557,他亦渴望“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154。如此种种,都使曹操对其恩宠有加。然曹植终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性格以及复杂的政治形势而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这也埋下了他与曹丕之间矛盾的种子。在曹植心里,王兄曹丕城府极深,手足猜忌之心极重,所以他不可能在作品中以宓妃比曹丕,更不可能将其描写得如此美艳绝伦。如果曹植因惧祸而故意逢迎兄长,那更没必要通篇写得虚幻缥缈,将主题讳莫如深。
其次,按照《洛神赋》的行文思路,“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更像离别在即,洛水女神表达对曹植缱绻怀恋之意。这种理解亦不够稳妥,因为此时的曹植正过着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的日子。忧惶惊惧的曹植岂敢在此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君王”,更何况曹丕对曹植的憎恶始于曹操在立储之事上的徘徊不定,以及平日里曹植表现出的对参政议政的极大兴趣。而在此时,曹植已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现实处境。《宋书·礼志一》载元旦正会礼云:“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7]342依照旧制,曹植及各封地兄弟要纷纷赶往洛阳共赴盛典,但结局并不是兄友弟恭、其乐融融的场面。据《魏书·文帝纪》,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十二月出行东巡,于黄初四年(223)三月才回洛阳。也即是说,众兄弟来到洛阳仅仅是吃了一个闭门羹,曹丕的态度昭然若揭。那么,我们只能姑且认为“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是该赋由梦境拉回现实的一大转折之处,是曹植为了不致因此获罪的一种巧妙安排。这种安排虽然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但这仅是曹植不得已之举。他希望王兄能够顾念手足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掩藏真正的主题。
另外,就创作手法而言,隐藏主题的手法常见于曹植作品中,绝非《洛神赋》一篇。仅就黄初时期而言,曹植就有很多作品和《洛神赋》的安排非常相像,即作品内部矛盾迭出。如《圣皇篇》写延康元年曹丕送别兄弟赴封国的过程,诗篇以陛下的“仁慈”为核心,写曹丕给予众兄弟奇珍异宝、华盛庄严的仪仗护送,但篇尾却对曹丕当头棒喝——“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1]324-325这种行文安排恰恰说明曹植当时政治处境恶劣,而且他本人对此心知肚明。满心愤懑却不敢直言,故不得不使用障眼法,用大篇幅对曹丕歌功颂德,用小篇幅对曹丕进行无情揭露。《洛神赋》中对曹丕感恩戴德的句子不多,却安排在了全文最显眼的结尾之处,而且表达得非常直接——“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曹植作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为了自保,避免引起曹丕的怀疑猜忌。
三、结语
关于《洛神赋》的主题,着眼于儒家诗教“发乎情”的“情”,学界有了“感甄说”“寄予理想说”;着眼于儒家诗教“止乎礼义”的“礼义”,于是有了“寄心君王说”。虽然《洛神赋》行文安排非常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传统,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发乎情”之“情”是真实的,开篇便荡开笔端放手去写,但是碍于引发“情”的主体不便言说,所以不得已只能采取“隐”的形式,借虚幻缥缈的洛水女神形象达到隐藏其原型的目的。
“止乎礼义”之“礼义”却相对虚假。之所以要“止乎礼义”,既是由于受到前代诗教的影响,又是出于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考虑,虽然以最凸显的方式呈现,但仅仅放在《洛神赋》通篇的结尾之处,乃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真与假、显与隐、放与止的安排中,虽然表面上依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传统,但其实质是对儒家诗教的背离。看透了这种安排,《洛神赋》的主题便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