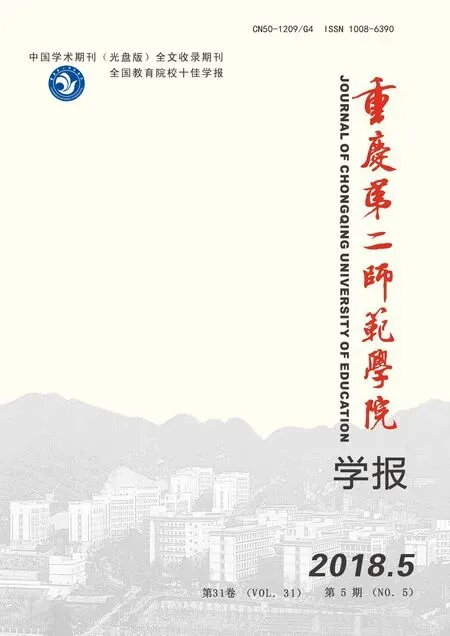清末贵州新式学堂兴办之经费考察
余小龙, 王智武
(1. 贵阳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贵阳 550005; 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资产设备处, 重庆 400067)
晚清以降,特别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以来,在清政府及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努力下,兴办新式学堂一时蔚成风气。贵州虽向属偏僻之地,亦得此风之浸润,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渐次开办。惟创办新式学堂,所费不赀,较之于富庶省份,素称瘠苦之地的贵州解决经费问题实属不易。康有为在1898年的奏折中认为“方当国事艰危,非复侈供张饰繁文之日,乃使皇上独忧社稷,而疆臣但安荣尊富,滥用民脂,而置国事于不问。竟视严旨若弁髦,犹为有人心者乎?”,要求“严旨戒饬各疆臣,清查善后局及电报招商局各溢款、陋规、滥费,尽拨为各学堂经费”,还特意补充“除贵州等极瘠苦省份外,必可每省得数十万金以为养士之用,庶几各学堂延师购书庀器皆有所资”[1]。可见贵州意欲兴学,经费实为最大困境。然当前关于清季贵州兴学的诸多研究中尚未见对于经费问题的专门讨论,只是在一些通论性的著述中提及[2]。清季兴学经费作为贵州兴学的核心问题,所牵涉方面甚多,对此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对“偏僻”省区兴学困境的真切认识。本文拟结合较少为学界所利用的《贵州教育官报》,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置经费筹措机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要求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总揽一省学务。提学使于通省学务用款会同藩臬司筹划,并详请督抚核定。学务公所分六科,其中会计掌经费之收支报销核算,省会及各府厅州县教育费用归其考核经理。府厅州县一切经费由劝学所管理,劝学所每年呈请该管长官检核,预算决算核定之后由该管长官榜示劝学所及各学区[3]。由各区劝学员负责在本学区内调查筹集学款事项,随时稽查报告劝学所,每年两学期之末,由劝学所造具表册汇报地方官。劝学所具体筹款项目:考查迎神赛会演戏之存款;绅商出资兴学禀请地方官奖励;酌量各地情形令学生缴纳学费[4]。这些皆为劝学所总董之责,“城乡款项应统一于劝学所,归总董掌管”,对总董则“应遴选公正廉明、家计殷实且谙学务者充之,不得徇情听其滥竽”[5];提学使于通省学务用款除会同藩臬司筹划外,盐运司、盐粮关道以及税厘、银元铜元各项局所,但有经理财政之责者,“均应合力通筹,详请督抚核定”。
清政府把筹措经费和推进学务作为相应官员考成的重要内容,要求除初等和中等学堂外,“凡义学私塾蒙馆等均应一体遵照”,因“筹设之责固在绅民,而提倡之责实在官长,现府厅州县热心兴学者固不乏其人,而漠视学务者亦复不少” ,须明定赏罚无以昭示劝惩。具体则视每一年增添小学简易科之多寡以定地方官之考成,“倘一年内增至二百所者,详记大功三次,一百所以上者,详记大功二次,五十所者详记功二次,不及十所者详记过一次,因循欺饰者查明详请撤退,势在必行,绝不稍为姑徇”,责令各府厅州县尽力筹款兴学,“在实任者自以三载考绩为重,在署任者勿存五日京兆之心”[6]。
事实上,虽然有相关经费管理规章,但并未落实到位。辛亥革命时,贵州一些州县甚至省会均未成立劝学所,全省实际并无统一制度。各级劝学机构之所以难以成立,是因为能真正推进兴学的人才匮乏。时任贵州巡抚林绍年便认为,“惟黔省学务至难整理,不惟款项支绌,人才尤匮乏异常”,各属奉饬选派,既苦学费无出,“且称地偏俗陋,应选无人。盖风气未开,较难措手”[7]。地方上,才不称其职的更是所在不少,如天柱县绅士罗文星在禀状中质疑杨光明的董事资格乃“贿派”,提学使司亦认为“惟办事首在得人”,要求彻查“该董事杨光明等经管款项是否涓滴归公”[8]。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仍可在《贵州教育官报》上见到对地方劝学总董资格不合的反复申斥:“选派劝学所总董务照定章,资格不得以不谙学务之绅衿充之;查学部原奏清单,学务总董选本籍绅衿年三十以外,品行端方,曾经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充任”, 然“部章于总董资格无变通之明文,各属劝学所大都以年老士绅充之,在此风气初开,非暂借旧社会之资格不足以所信用,犹可说也,今出洋游学毕业者约百余人,曾习师范者近千人,岂选七十余总董犹或难之?”而总董等大都由地方官保荐,地方官“不谙部章”,而“学司据地方官之公文以为情形熟习,众望允孚,因而札派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地方官耳目所习未必即孚人望,纵年老资深,实于学务隔阂”。如镇远五年内,“萧、黄二总董年年涉讼,果于年老资深之外稍知学务,安见外界之必排击之也。劝学所有筹款兴学之责,若仅搜刮二三闲款,徒为敛怨之地,而于学务方面专主消极,此于向来斋长何异?”[3]在《民国桐梓县志》等志书里可以看到不少劝学员往往以收捐人充任,但亦不过徒有其名,后以名实不符取消,而“薪给难筹,劝学员终未专设”[9]9。已设有劝学员的地方往往也徒具其表,至宣统三年(1911年),“各属劝学员除繁盛数处外每属多有一二员者又多在城,试问此一二员在中区各区皆置之不理,是欲视而自闭其目也”。因此,“各属学堂仅城中稍有可观,四五年来乡间直无丝毫之萌芽”,要求“如各区土著难得留心学务之人,请一律饬令遵章讲习,仅两月毕业亦非难事,但能略谙学章,任事亦有把握矣”[3]。
清政府1906年的劝学所与教育会章程颁布后,随着教育事业的推进,特别是由于政府财政不足,为了使同地区内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共同合理地运用本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推动兴学,一些经济较好的地方由地方士绅联络当地学界组织学务公所和教育会并掌握资源分配的地方教育公共机构。如在南通,各种教育基本都由张謇等规划与筹定经费,而官设的学务处在南通也未出现,基本上是以民间的学务团体替代官方本应设立的教育行政机构[10]。与这些经济发达地方不同,清末贵州虽然在省城成立了教育总会,但更多只能在省城一地对教育经费进行控制和支配,而对教育会控制权的争夺更是引发了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激烈冲突,形成了较大内耗。虽然贵州民间捐资助学的情形“十分踊跃”,然未能在省城外的各地方形成真正有力的能辅助或较为独立而由士绅掌握的地方教育机构,此亦可见贵州民间兴学动员能力的不足。
二、经费来源
兴学堂首重经费筹措,而各类学堂经费来源殊异,多寡不一。清末贵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其经费来源亦各有区别。
官立学堂经费由政府筹款。一般而言,某一级学堂由同级政府筹措款项,经费往往相对稳定可靠。其时筹办新式教育,部分稳定的经费来自各属原供乡、会、科、岁试公私应用之款,“不啻取携自如,无待筹措而已备”。此外,并将各州属历年筹备童试、院试、优拔试、乡会试等所需卷费、册费、黉仪费、贽见费、修理考棚费、摊解学院科岁两棚费、考送士子宾兴花红费等,“无论公积私捐,存银置产生息,或临时按数抽收,或由官自行拥解”[9]15。还有部分经费来自书院原有的宾兴田、棚田、学田、祭田等产业收入,因书院改办学堂而划作学款,此外各种捐、税、行费等更是种类甚多。如屠宰税,遵义知府袁玉锡在原先宰猪一头征制钱二百的基础上,通饬加收一千,用作办学堂的专款,委绅分区承征,继由收捐人认额包收包解。松桃直隶厅同知陈春岩批准收回孟溪场花、盐、油行行费,并决定收取孟溪场牛行行费,凡成交牛只,每头收行费一百二十文[11]。一些官立学堂经费还依赖于地方的特色经济,如安顺凤仪书院的办学经费包括烟土的牙捐、洋纱捐、山货牛皮捐和斗息捐等[12]。绥阳县农业初等学堂的经费全赖禁烟罚款开支,筹办时计划全年二百金,以三年预算,而其时烟苗禁绝,然“将来绝无此项罚款,恐现筹之款不敷三年之用,学堂势必终止”[8]。禁烟让学堂的办理无费可依。为了确保经费能落实,地方官往往对原先的捐税缴纳方式做一些改革,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瞿鸿锡委派教官庭植宗筹办中学堂,就规定承包大烟秤牙捐、洋纱捐、山货牛皮捐和斗息捐的商人,必须到布政司请领牙帖,领帖时所交手续费即作兴办学堂的经费[13]。
清末贵州官立学堂经费来源除了官方资产外,地方官员往往发动当地乡绅等广为筹措,此亦学堂经费之一重要来源。如遵义府中学堂修建时,知府申报贵州巡抚准开三次奖票,筹款9300余两,又函请华之鸿、之棋兄弟捐银4000两,从常年办学经费中预支1400余两[14]。刘显世在兴义任劝学所总董时,积极奔赴各乡劝导地主绅商捐资、捐谷、捐木、捐桌凳等。贵州风气晚开,幸赖各地官员提倡和动员社会力量,新式教育才能渐始培育。
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兴办经费,更多则只能依靠民间募集,由地方绅商集资或个人捐资,间或有地方公款给予支持。由于贵州各地经济状况不佳,更是积极按学部规章奖励捐资兴学者。如修文县素称瘠敝,“当此新旧过渡时代,全恃殷实绅耆毅力提倡,方于学界有益”,县属附生陈嘉言,家资殷实,智识开通,立志兴学,不惜巨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组织广智高等小学,合计九学期经费实支出银1500余两,均系其独立担任。在清末《贵州教育官报》中,能见到不少对各地捐资助学士绅的褒奖之辞,一些小康之家的普通人也踊跃捐助,如贞丰州州民韦正恩便因此而被授予匾额,称其不富裕却能“热心公益”。少数公立学堂虽名曰公立,实则为官商合办。如通省公立中学创建过程中,华之鸿捐银27000多两,地方官绅唐尔镛、任可澄运用他们在上层社会的关系,得到清政府在职与退职官员及在外地的贵阳籍官员如云南矿务大臣唐炯、江苏巡抚陈夔龙等大力资助,使这所学堂成为近代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师资最为雄厚的一所中学,“凡此校地之美,建筑之精,教授之良,管理之善,光线之合,卫生之宜,早为英博士、日教员所啧啧称羡不置者,固不待赘说也”,“诚多士之咽喉,实全黔之首领”[15]。而直至1909年,贵州省城“尚无一官立中学以为模范”,政府虽欲设法筹办,“只因库款支绌,未克及时举行”,省城官立两等小学堂堂长申请于高等小学分校改建中学并拟请减办小学两期,腾出款项以作活支经费,提学使司亦只能如此,认为此“办法甚妥协”[6]。
除了少数资财雄厚的官立和公立学堂,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堂经费筹措困难,只能勉强维持,而最困难的则属私立学堂。为了维持偏僻地方兴学,学部要求地方按照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将该地内不动产或相关营业,充入地方公款以负担地方教育设立及维持之用。私立学堂的设立一般只能借助地方庙宇、寺观、祠堂或私人房舍作为教学场所,不但地方狭小、光线昏暗,卫生条件往往亦十分恶劣。如著名的达德小学便设立在忠烈宫,乐群小学设在黑神庙,正谊设在文昌宫。省城尚且如此,地方可知。《民国桐梓县志》记载,清末桐梓实行地方自治,办理各种“新政”,各类机关杂芜,“支出纷繁,款项不敷,而收入一方,远乡匪扰,捐款减色”,“乡学截留,经费第次缩短收支,城乡学校经费,双方同归废弛”。一些私立学堂往往由一二士绅捐资开办,更是“旋兴旋废”,皆因经费无着。
除不同类型的学校经费筹措差别甚大外,不同地域也是厚薄不齐。省内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如贵阳、遵义等地,因经济相对较好,提倡得力,情形较著。少数地方虽属边僻,但有资产雄厚者热心倡办,兴办情形也较佳,其中最典型的是兴义府刘氏兴学。清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刘官礼创设“培文局”于黄草坝昭忠祠,主管全县教育行政,同时多渠道筹集办学基金:一是劝导“官民捐资兴学”,不论多少,统收于培文局账内;二是强行没收“匪产”“绝产”田地若干,划拨会馆、寺庙租谷若干,概称“学田”或“学谷”[16]。少数地方甚至得外省款项支持。《民国南笼续志》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因南笼为其先公旧治,乃捐银1000两,置田租56石助学堂常年经费,并捐置中学、小学应用图书、仪器约值银数千元。且特委宋绍锡回里考取学生朱炯等十名赴鄂肄业,所需各项岁费约2000元,“其嘉惠吾郡学子,既周且渥”。不过这样的情形殊属例外,镇远府筹拟就文明书院改办中学堂,所需经费只得由所属六厅州县承担,或与石阡府并办。《民国三合县志略》载:“兴学之不易,全黔皆然,而于苗疆边瘠尤为过之。”如位于威宁石门坎的苗族学校,其开办之初,教育经费全由柏格理及全体苗族信徒筹措,1909年后,每年由循道公会提供办学经费约小板1000元左右。石门坎办学之初,学生不但不交纳学费,还对学生发赈济盐来鼓励其读书。教会还规定每一联区挑选一名学生获教会奖学金。但此非长久之计,在苗族子弟上学率稳定之后,学校便开始收学费,学费数额为初小教徒子弟交包谷5升,教外子弟交包谷7升。高小教徒子弟交包谷7升,教外子弟交包谷l斗。学生课本、纸张、笔墨、文具全部自理[17]。
三、存在的问题
首先,学堂经费筹措时常遇到地方抵制。思南府筹设官立中学堂于思旸书院,本以旧有书院田租及城乡屠、斗各捐以充经费,而宣统二年,因筹款滋事,学堂“竟被暴民打毁”。 印江县城中肉捐由四屠户包认,“任意把持抗欠”,官方要求“宜停止包认,仿照遵义贵阳办法,酌定每猪抽捐若干,不论城乡有屠者,先由劝学所缴捐领票然后屠豕”[3]。桐梓兴办学堂,本拟酌提县属天池寺、观音寺二庙庙产,但每值收租之际,该地土豪令狐恩培等诈称该庙施主,“统率痞棍,来庙盘踞,竟至酿成讼端,历年如此”,以致该庙“焚献冷落,学款无着”[9]248。达德学堂的拓建亦是如此,因忠烈宫首士范某、陈某唆使社会不明真相群众数百人到堂哄闹诋毁,后经巡抚庞鸿书责按察使严隽煕会同提学使陈石麟、邑绅于仲芳先生调处,终决定忠烈宫前面大殿保留供南霁云将军和办庙会之用,其余房屋全部归学堂使用,使学堂庙宇“两不妨碍”[18]。事实上,如果不充分利用庙产,贵州的学务推广将更加艰难。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十年中,贵州所办的636所各类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仅遵义一县,被占的寺庙就达348座[19]。其间一些地方官吏与劣绅勾结,拷打僧尼,抢夺寺产,霸占寺庙,使情况更为复杂。
其次,经费管理混乱,陋规甚多。官属学产权责不清,如平越州绅刘锡麒擅将学堂之田跌价贱当于丁姓,丁姓又转当于宋姓,而学田既作为学堂常年经费,却“任听经手之人辗转典当”[8],从中渔利。平越州熊李氏捐入学堂之业,经万寿宫首士卖与陈希蕃,后退还于熊李氏而又不退还于学堂,“实情支离莫若此”。地方学款学业往往被一二不肖绅衿牵混谋占,以致“无怪人皆以学堂为诟病,学务遂因之多阻力”[20]。经费账目不清,在清末《贵州教育官报》所刊省视学员的学务督察报告中更是每期皆有。如余庆县账册内收入款项并未分别系何项下,“殊属含混”。清镇县劝学所收支各款清册正月项下细目与总数不符,“计多报银六两二钱,二月份新收项下细目与总数亦差,少报银二两七钱,只此一出一入已差银八两九钱”。因各属控告侵蚀学务经费之案层见迭出,提学使司通饬各地方官转饬劝学所按月将出入款榜示,并详细报告“以昭大信,以便稽核”,然“各属遵饬造报者寥寥”。劝学所尚未成立之地,虽责成该地地方官办理,“如再视为具文,劝学所已成立者即将该所职员查明撤换,未成立者,即将该地方官详请撤委”。纵如此,此类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四、经费拮据下的学堂兴办情形
因经费筹措困难,除了尽量开拓利源,不少学堂只能尽量撙节费用,以资维持。如平远州城内仅办高小一堂、初小二堂,因经费不足敷用,“各学生操衣、靴帽须令自备”,“各堂应用笔墨纸张、朱粉等项不得任意滥取,去岁十个月其沙云白纸用至一百三四十块之多,可鄙可笑可叹之至”,堂中每逢月朔及年节,爆竹和火药应“一律裁汰,惟备香烛一副可也”,“凡开学散学三节并学期考试,其酒席包子均应停止”,“实验奖资、各教员购置草席等件、视学员酒席点心、赏亲兵等一律停止”[5]。而“僻小各府物力艰难”,尚未筹设中学堂或现无力独设初级师范学堂的,“准其与附近邻府合款设立,或即府属邻府之中,其合设者摊款、选生以及一切事宜统由该府等自行商筹”[21]。因经费不足,很多学校难以为继,如绥阳县开办农业初等小学堂“惟经费就种烟罚款开支,全年当在二百金,以三年预算,必需六百金方能持久”,然“当此烟苗禁绝,将来绝无此项罚款,恐现筹之款不敷三年之用,学堂势必终止,应如何以善其后,续为经营?”[22]大定府中学堂其时仅有文科,因经费不足原拟办的“初师停办约省二千金”,原先所提供的膳食,“值此财政困难之际,明春一律停止,岁可省七八百金,以推办城乡学堂”[23]。而一些耗资甚巨的学校则只能停留在规划层面,中等工业学堂所需经常费五万两“为数颇巨”,“照本年预算支出之款固不敷甚巨,即照上年应发之数亦难支持”,贵州其时财政尚依赖邻省协饷,而“各省筹解五成协饷至今无一解者,而年终收入有限之款尚不敷支各项经费”,因此虽然实业学堂“为本年应办要务”,亦“须俟筹有的款或各省协饷到黔,再行酌量应付开办”[3],而真正开办自然无从谈起。
清末贵州在举国群趋东洋留学风气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波留学的高潮,然留学日本的贵州士子受经费不足影响者甚多,留学生监督处所存《官报》里便有大量催促贵州当局缴款的记录,而贵州当局对各项费用也实在疲于应付,左支右绌。署提学使柯劭忞称,漆运钧等九名学费系由各属筹措,原定肄习三年,“惟该生等赴东,入学日期不一,平均计算约须本年六七月始能毕业”,虽然已“札饬”地方官添筹半年学费,“以资接济”,并先由学务公所每名照数垫给银150两,回黔装资银70两,九名共垫给银1980两,然“迄今数月之久,尚未据该各地方官将此项添筹学费申解到司”。贵州地瘠民贫,各属筹款不易,只得恳请出使日本大臣“饬知该生等遵照前电,至迟限本年六月回国,以符原案而免竭蹶”[24]。官费留学生除学费、路费外,日常开销包括生病等皆在政府支付之列,《官报》中还可见贵州当局要求出使日本大臣“俯念黔中筹款维艰,嗣后留学生医药璜一项请为稍示限制,实为公便”,认为“黔省医药费一项,实较他省为钜”,但因学部章程既规定有此一项,学生有病入医院治疗或就外诊,“本处亦实无法限制使之不病不药,且不能或予或靳,致起争端”,因此要求“切实告诫学生,使知筹款艰难情形。此后,来处支取之数,或可少减”[25]。《贵州教育官报》还可见不少黔省官费生的催款通知,如贵州籍高等工业学生谭先藻被催应补学费,以免“中途忽停致令废学”,而“黔省此项学生甚少,为黔省学务起见,以应予成全”。另有女生熊姚兰本由黔学司核准补给官费,“则高等实业学生不应转令向隅”,要求“黔抚察核行司并请将积欠之日币9486.8元从速汇解”[3]。
具体到每一学堂,政府认为“地方虽极贫瘠,每年但有公私款项四五十两者即可设立一二所”,“如实在款项不敷,仍酌量收每人学费银一二两”[8]。经费的开支一般分为额支、活支两种,也有加上开办费和临时费的。额支主要为教师工资等比较固定的开支;活支一般为校内伙食、办公费和消耗性开支;开办费则包括新建校舍费用、临时费、添置设备等。据《铜仁县官立两等小学堂章程》,该学堂常年收入三类:前县属书院膏火费,各乡场市所收屠宰税,每年所收卷费谷,经费支出定为额支、活支两项。以堂长、教员、书记生、厨役、打扫夫、杂役等职薪工伙食费为额支,添设图书仪器、修补礼堂内各室等费为活支。支出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教员的薪资,清末各学堂月薪之多寡并无一定之规,全视该学堂经费之多寡而定。一些学堂并非月薪制,1911年,提学使司通饬各属因当年置闰,月薪无着,拟一律规定,如闰月之年或作12个月或作11个月开支,无闰之年或作11个月或作10个月开支,通饬劝学所查明各学堂教员职员薪水向系按月支者准其加闰,按年支者不准加闰,“以归划一”[8]。各学堂特别是乡村学堂,经费窘迫,大都聘请乡村生员贡监及学问较浅之“寒儒”,但能照部颁课本讲授者即可充当教员,且只需一人“即可遍授”[26]。而对学习师范的学生,因一切费用均由官费筹给,要求毕业后效力义务定为六年且不能无故转堂,但如果由自己私费,可减短义务为三年。
虽然经费筹措困难,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地方的倡导之下,贵州的私立小学堂依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从1905年清政府宣布“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贵州各类小学堂就从81所猛增到了781所,虽然各类学堂办学水平不一,地域分布不均且不少旋兴旋灭、徒有其表,但贵州的新式教育毕竟发端。一些从未设学的地方亦开始渐次开办学堂,水族聚居的荔波,以邑中原有文庙田及黉仪谷息,另“加委”劝学员蒙式穀、何同海、梁自成、何丙龄、莫培元、李家盛、蒙绍先等八人,分行十六里开收屠斗税,并议每里坐扣半数作开办各里小学经费。由是甲良、播缓、拉圭、巴灰、洞塘、毛兰、从善、董介八处,各成立初等小学一所,“此为城乡各学校成立之始也”[27]。
概言之,清末贵州新式教育之兴办受制经费困窘者良多。经费的筹措机制难以真正有效建立,一些地方直至辛亥革命也未能建立起新的学务机构。经费来源有限且筹措中各方势力冲突甚多,自我管理也十分混乱,且不同学校的经费状况极不平衡,大量经费只集中于少数公立、私立学校,对兴学的各层面和环节都形成了极大的制约。虽根据学部精神,尽量变通办理,以期能大力培植新式学堂,然而大量的新式学校却是旋兴旋废,在学堂数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其兴办实情则依旧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