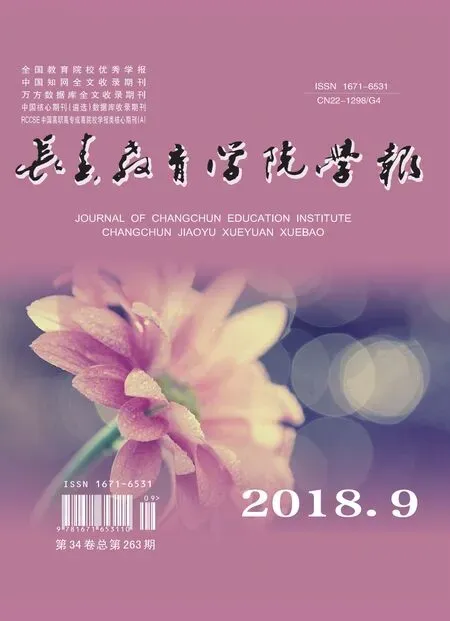汉字字形演化中的意义传递
——以“皮”旁诸字及“革”为例
宫 瑱
关键字:汉字;字形演化;意义传递
汉字是迄今为止人类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至少有四千多年历史,在古代已发展至高度完备的水平。汉字的演化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划,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造字原则历经表形、表意和最终的形声体系。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汉字七体”,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其中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已形成系统的汉字,而“《甲骨文编》中就收录了四千多个字”。[1]
汉字七体尤其是早期的甲骨文与金文古老而精深、历久而弥新,演变成至今仍为这个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所使用的现代汉字。它的创制,既凝聚着先民的智能和汗水,也负载着当时的文化背景。初民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社会认识都体现在了甲骨文的构形系统之中,因此,分析古汉字的构形系统对其进行反观,就能从一个个静态的形体走入古人动态的社会文化圈,窥见其中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当前的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意义也有过多次转折,往往无法反映出造字的本义。只有从最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入手,才能真正领会先人造字时的世界观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又实在是一座丰富的、值得挖掘的考古博物馆。
汉字是意音文字,一个汉字通常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或一个语素,这就形成了音、形、义统一的特点。但是汉字最主要的构字法则还是象形。在汉字象形构字中,字形的不断衍化也会将其原始字义带进新的字形中。探索其结构原理及先后顺序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汉字造字之初的社会文化与之后的历史变迁。
一、“皮”的造字本义
“皮”字在当代汉语中有以下意义:动植物体表的一层组织,如皮毛;兽皮或皮毛的制成品,如裘皮;包在东西外面的一层,如封皮;物体表面,如地皮;薄片状的东西,如豆腐皮;韧性大、不松脆,如皮蛋;指橡胶,如皮球;姓之一种,如皮日休。从这些意义当中大致可以发现有两大类别:其一是物体(包括动物和人)表面部分,其二是皮的相关属性或与其相像的物质。
皮的甲骨文今未有发现,但在金文中它却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常见字,主要见于九年卫鼎、壶等青铜器。
“产生或使用于某一阶段的汉字,其结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反映该时代的某种文化意识”。[2]人类历史是一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这种对自然不断地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古代的先民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存条件恶劣,不断受到自然灾害以及毒虫猛兽的袭击,生命显得异常脆弱。当人们无法掌控自然时,恐惧便随之产生,进而产生对自然的崇拜。古代的先人认为有超越人类能力的力量存在,这力量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并逐渐被神化,当人们再次遇到灾祸时,便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进行化解,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即举行各种血腥的祭祀仪式。李景生认为:“祭祀,是人类具备了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后才产生的原始信仰活动。”[3]在远古时代,一切领域的实践都是围绕以自然为主的宗教活动展开,因此祭祀活动,不仅是早期人类认识自然的主要方式,也是多种文化类型产生的根源。在皮这个汉字里,祭祀文化与汉字文化产生了碰撞。
从对皮字形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皮的本义其实是一个动词,表示用手剥人皮,比如《战国策·韩策》里的用法:皮面抉眼。后逐渐衍生出不同但相近的用法义:如《说文》: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这里的行动对象就不一定局限在人上了;《广雅》:“皮,剥也。”另有一动词词性义为酥脆的东西变韧,现仅限于部分方言亚区。
而皮的名词词性衍生义则包括了:人的皮肤或动植物表面的一层组织,如皮草;进一步衍生为所有包或围在物体外面的一层东西,如书皮、饺子皮等。
皮的形容词性则因皮的属性而引申出表面的、肤浅之义,如皮肤之见(肤浅的见解)、皮相(表面外貌)。皮所具有的韧性质感也引起用字者的注意,产生了一些更抽象的形容义:如顽皮、调皮,以及由于受申斥或责罚次数过多而感觉无所谓了。
二、“革”与皮的关系
既然说到皮,就不得不再提一下“革”这个字。
《说文》中说: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许慎编纂《说文》是从文字到文字,所以很多字的定义都不是本训。比如他还写道:“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比照前文可以知道这是不符合造字本义的。
甲骨文革是独体象形字,是依据一个完整的客观对象而造字。根据《周礼·大师》: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国语·楚语》:皮革羽毛;《荀子·礼论》:金革辔靷而不入。可知革在至少先秦之前的本义就是兽皮。到了金文中,革作为一个造字的部首创造了很多与兽皮有关的字,也就是说本字革和兽皮二者之间,在造字上是具有巨大联系的。也就是说革字准确的定义应该是:革,象兽皮之形。
可是革哪里像兽的皮呢?在古代,狩猎者在获得野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剥皮。人类到了现代仍然是从兽类的下巴部位开始剥皮的:沿着喉咙向下,用尖刀一条直线划开兽皮直到尾巴,然后分开肚皮,向两侧逐渐划开四肢阴面的皮直到四个蹄子。切除四蹄后剥下来的整兽皮还是柔软潮湿的,需要晾干才能加工和使用,使兽皮干燥的方法是将兽皮毛面向外固定在木板上。为了避免兽皮变形,要将头部和两侧的四肢皮以及肚皮拉直并撑开,用竹签或者铁钉固定在木板上,兽皮干燥后就会变硬成型,不再改变形状。
所以“革”是剥下的野兽皮,而皮是剥去人的体表软组织。甲骨文“革”和金文“皮”相比较有两点明显的不同:
一是“皮”多了一只人手,说明“皮”是一个会意字,动词,而“革”则生来是一个名词;
二是“皮”的主体部分和甲骨文“革”相比较缺少了左半部分。这也说明“皮”是一个在“革”的基础上做了改动的后生词。
当今革主要是指:去了毛,经过加工的兽皮,如人造革;其衍生义就是彻底巨大的事物根本性改变。包括:变革或更改,如革故鼎新;免除或丢掉:如革旧从新。
三、“陂、坡、波”的造字顺序
皮字被创造出来后,产生了一系列衍生字,其中主要为名词字义的是“陂、坡、波”三个字,它们都与先民日夜接触的山川水土有关,其产生的先后顺序颇为有趣,反而可能是当今已不太使用的陂字为早。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生产在其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谓一切围绕农业展开。作为文化的物质外壳,汉字也处处反映着农业这个天下第一大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民们越来越认识到靠天是远远不够的,要保障农业丰收,必须兴建大型农业水利工程。陂就是周代以后兴起的蓄水灌溉工事。“陂”字从阝,皮声。作为义符的阝本为阜,早期甲骨文中的阜像竖立的山峦。根据皮为物表的字义,陂字本意是指山峦倾斜的坡地。古人们在考虑蓄水问题时,首先便选择了丘陵环抱,四周为山坡,中间呈盆状的自然环境,这样,只需要对外围山坡稍做加工,便可以形成人工蓄水池塘。之后慢慢也将这种四面是陂的人工池塘开始称为陂,便是其现在的普遍用法,反而本义不再常见。如《淮南子·说林》记载: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春秋时期水系丰富的楚国相继建成的期思陂和芍陂为最有名的陂塘。陂中有阜的字形,反映出早期大型水利设施多善用地利依山而建,投入的人力较少,尚不像后世主要靠人力堆土的工程。
但随着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水利的需求不断扩大,无法找到那么多天然符合要求可以加工为陂塘的山间盆地,先民们开始模仿山丘,用土石人工堆砌假坡营建陂塘,这时为了区别早期的陂,便将义符阝换成了土,以示区别。之后坡逐渐接收了陂的本义,指代一切倾斜的地势,无论天然还是人工。《说文》也直言:坡,陂也。可见二字的渊源。
除了陆地上倾斜的地势,还有水里的波纹。波也是皮字家族的一员。其中的皮,既是声旁也是形旁,在这里作为义符是“坡”的省略,表示缓缓凸出的地方样子。波,金文为,左半边为(皮,坡的省略,表示缓缓凸起),右半为(水),表示在风的作用下水面凸起有如陆地上的坡状。造字本义是比喻水流坡状涌动起伏。篆文基本承续金文字形。隶书将篆文的写成,将篆文的 写成。从这里可以发现,波的造字又要晚于坡字。
波之后的衍生义较多,从水流坡状涌动起伏引申出水面起伏状的水纹,再进一步扩展为自然界一切振动在介质之间传播的过程。如超声波、电磁波、波长、波段等。
其名词性义主要包括:涌流的水,如长桥卧波;事情的意外变化,如轩然大波;流转的目光,如暗送秋波。而动词性义有:激荡,使起水波,如洞庭波兮木叶下;推而及之扩散,如波及;狂奔、逃跑,如波逃。可以看出这些字义究其根本,都基本源出最早的水波。
四、“皮”的动词与形容词性引申
皮的本义是动词,但在慢慢演化中主要以名词形式出现了。那么其动词字义就需要新的字来承袭,比如“破”和“披”。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与皮的本义是相关联的。
破里的皮,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手持器械加工皮革。破的篆文可以看作 (岩石)加上(皮,剥皮),其义表示将大的石块像切人皮一样切开。所以造字本义是将开采的石块切开,加工成有用石材。
破字的引申主要有两条线索。首先,破从本义的剖开加工石料扩大引申为开裂、分裂义,如破碎、破晓等。从这里开始,由主体主动的角度出发衍生出击溃打败的字义,如突破、破敌,这一义继续扩大为摧毁消灭,如破案、破例;而由客体被动的角度,则引申出受创衰败之义,如破灭、破败,继而引申出唯一的形容词性义有缺陷的,如破玩艺儿。
除了破,“披”也是皮部里较为常用的一个动词性字汇。
《说文解字》里披从手皮声,从旁持曰披。但根据古字,可以知道其本义应是动手拨开分开,现仍使用此义的有:披沥、披露、披肝沥胆、披荆斩棘等。引申后它才有了将服饰拨开后半套半戴之义,此义扩大到衣物名称,如披袄、披风、披肩。根据这样穿戴的方式,又产生了覆盖在头、肩、背上之义,如披星戴月、披头散发、披红挂彩。可以说,披的本义中主要被用来扩大引申的是分开。而分开后加工可被视为分析的雏形,后世使用此义的词汇也特别多,如披析(分析)、披究(分析研究)、披迷(剖析迷惑)、披拣(辨析选择)、披剔(辨析、挑选、剔除、除去)、披削(批改、删削)。
除了动词,皮还延伸出一些表达状态的字,如“疲、翍、怶”等。它们分别与不同的义符结合,见字会义,在意义的转折中传承原字的生命。
翍,望文知义,为鸟张开羽毛的样子,古同“披”,散开,也有指飞翔的样子。
而怶则指心怀奸诈或恐惧忧愁的意思,皆是心被分裂粉碎而有病状不得其完备的引申。
汉字是在古人对自然的不断实践与认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所以“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先驱。”[4]
在这种“仰观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自然描绘中,汉字具备了象形的重要特征。受到古人自然神论的影响,汉字在其产生之初就具有神性,这种神性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达到了极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成为上天与人间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先人认知自然的重要工具,不再是神秘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认知并加以改造利用的。汉字在古代社会人神地位的角色转换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转换的结果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地位,但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即“天人合一”思想,这奠定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理论基础。汉字产生于古老的契刻符号,李泽厚先生阐释了汉字发展的内在逻辑:“汉字作为意指的文字符号,它不可能是对所画物的一种具体逼真的描绘,而必须是抽象化、形式化、概括化和规范化的……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字,一方面是一种指意的符号的创造,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抽象概括的方式表现了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使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渗入文字的形象之中。”[5]象形的汉字在数千年的发展衍变中不但完成了意义符号的作用,更成为逻辑思维与审美意识的载体,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而“所谓合格的读者,就是指那些与作者的时代、民族、文化素质及阅读兴趣相近似的欣赏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