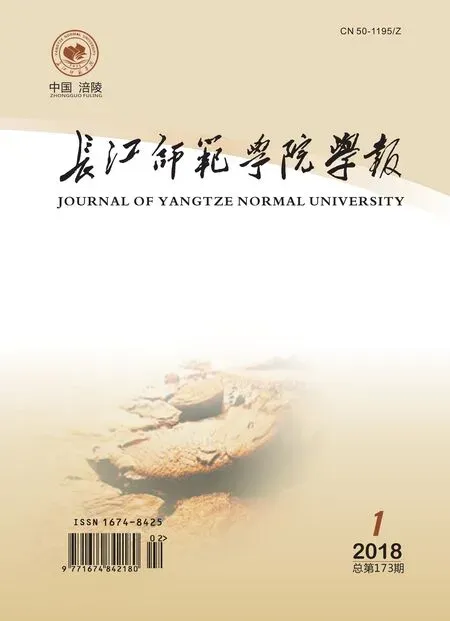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给樱桃以性别》的“双性气质”之美
张 婕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重庆 408100)
一、前言
《给樱桃以性别》是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代表作之一。《旧金山纪事报》称赞该小说“是一部以卡尔维诺的优雅口吻讲述、米兰·昆德拉的哲学形式编排的《天方夜谭》。”该小说构思巧妙,凸显了女性主义主题,对西方传统男女二元论思想进行了大胆的颠覆。珍妮特·温特森作为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锋人物,敢于打破传统观念里的女性固有定位,大胆突破传统女性的文学形象,以无边的想象、夸张犀利的语言,展现了主人公追求真空与光点的奇幻之旅,震撼读者的心灵,与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温特森在《给樱桃以性别》中彻底颠覆了男女二元模式中关于女性感性、胆小、懦弱、缺乏主见的“他者”定位,以敏锐的视觉,捕捉到了人类身上散发出来的“双性气质”之美,这是温特森内心深处的渴望,同时也是她为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呐喊出的心声。
父权制文化为了巩固其地位,刻意给女性贴上了“感性”“服从”“谦卑”“被统治性”的标签;而让男性堂而皇之的成为了“理性”“支配”“勇敢”“成就”的代名词。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利斯,普罗米修斯,帕西发尔。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能扮演次要角色。”[1]这种典型的西方传统二元论,赋予了男女各自特殊的符号,让女人被动地处于从属地位,扮演起“温顺”“被拯救”的对象,而男性则承担起主宰世界的重任,衬托出女性的柔弱与无力,这一切都是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刻意安排的。西方宗教女性主义提出了著名的“双性气质”理论,即人类身上与生俱来同时存在男女两性特质,每个人都是多元气质的融合体,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勇敢的一面;既有独立的一面,也有依赖的一面……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交织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互融合,不可分割。“双性气质”的提出无疑给阴与阳、男与女等二元对立寻求到了出路,通过男女两性精神上的完美契合来消除人类处境的对立面,从而结束男女两性相互对立不平衡的关系,彻底消除性别斗争,取而代之的则是互为补充、共存共享、非恒定的文化性别。
二、“女性上帝”的诞生——“狗妇”的男性气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到:“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子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合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2]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正是女性主义者完美的理想状态,它是消除男女不平衡关系的利器。《给樱桃以性别》中的女巨人“狗妇”便是这句话的完美写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许就是温特森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致敬。女巨人“狗妇”是温特森仿造《圣经》中的《创世纪》塑造出来的“女性上帝”[3],她既闪烁着慈爱的母性光辉,又有着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是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典型结合体。班昭《女诫》曰:“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巨人“狗妇”彻底颠覆了女性传统形象,以丑陋、庞大的身躯示人,挑战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的审美。“狗妇”这样描述自己的外貌:“我有多丑?我的鼻子扁平,我的眉毛浓稠。我的牙齿很少,仅存的几颗又黑又烂,不堪入目。我还是姑娘的时候生过水痘,留下的坑疤足以让虱子安家。”[4]21至于她的体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她的体重足以将一头名叫萨姆森的大象抛向天际,“在我们的上方,很远很远处就像白色天空中一颗黑色的星星,那就是萨姆森”[4]23。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狗妇”年幼时,父亲抱着她讲故事,她竟然“坐断了他的两条腿”;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巨人的养子约旦还是新生儿时,她巨大的手掌竟可以将孩子置于掌中坐下,“我让他坐在我的手掌上,就像我让小狗这样坐一样。我举着他,靠近我的脸庞,让他从我的那些疤痕里捡走虱子”[4]23。温特森天马星空的想象赋予了“狗妇”巨人般庞大的身躯,尽管女性落入了这样一副不受传统文学女性形象束缚的躯壳之中,非但没有否定“狗妇”的女性身份,反而完成了“狗妇”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肯定。首先,“狗妇”肩负着母亲的使命。“狗妇”自己没有生育孩子,养狗为伴,这也是她名字的由来。一天,她偶然从泰晤士河打捞起的弃婴约旦,正是由于无私的母爱,女性的温柔善良,使得“狗妇”毫不犹豫地收养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约旦,并倾尽心力抚养其长大成人。母子之间的情义也是真挚深厚、情真意切,正如“狗妇”所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他即使发现我比多数人要高大也未提及。我是他的骄傲,因为没哪个孩子的妈妈能把一打橘子同时放进嘴里。”[4]23—24作为母亲,“狗妇”无疑是尽职尽责的,既然是“孩子的妈妈”,那理所当然就是女人,女巨人庞大的躯体下隐藏着一颗柔软的女人心,母爱的伟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她身上彰显了女性的母性——养育和关爱。其次,女巨人也有着一颗女性爱美、爱打扮之心。至于衣着打扮,她总是穿着裙子,和约旦一起回老家时,她刻意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那条宽大的裙子脖子处点缀着精致的蕾丝,为了这次回家,她还戴上了帽子,并评价自己道:“我想尽管我有一些缺陷,但减去这些,我还是一个标致的人物。”[4]82她还曾声称:“如果我能赚到足够的钱买一条项链,我就会先把我的脖子洗干净再戴上。”[4]10去旅行时,约旦让她穿上最好的衣服,于是女巨人“按照他说的戴上了一顶羽毛帽子,像是鸟巢窝在树上。”[4]10除此之外,“女巨人”还拥有女性美妙动听的歌声。“狗妇”歌唱时,“声音像芦苇一样修长”,她“开始唱歌的时候,那些狗会安静地坐下,那些在夜里路过的人会停下他们的窃窃私语,想起另一些时光,一些幸福的时光”[4]9。能令人凝神静听,带来幸福感的歌声,想来必定是天籁之音,“狗妇”的歌声竟有这般抚慰人心的功效。由此可见,丑陋和庞大并没有削弱“狗妇”作为女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她身上依然散发着女性独特的人格魅力。
然而,女巨人的身上也透露着明显的男性气质。第一,她有着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狗妇”以养殖大猎狗为生,经济独立,不需要靠男人维持生计。作为母亲,她独自抚养约旦,担负起孩子保护者的形象,颠覆了男性保护女性和孩子的形象。她凭一己之力保护着孩子,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安全、完好,受保护。我希望约旦能这样活着。”[4]107她没有丈夫可以依赖,依靠的是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她可谓是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勇士。第二,“狗妇”具有男性豪放、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当有人怀疑她夹带重物,提出要搜身时,她厉声呵斥道,“你敢碰我!我会展示给你看”[4]22,于是她大胆地将裙子拉过头顶,由于天气的炎热,她什么内衣都没穿。这与父权社会要求女性“矜持”“婉约”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是对传统父权价值体系的挑战。第三,“狗妇”天生具有力挽狂澜的气概。由于“狗妇”痛斥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压抑了人性,随意践踏了自由,便单打独斗,去报复那些胜利者。她“径直冲向那些士兵,打断了第一个人的手臂,将第二个人撕裂,踢了一脚第三个人的头,将他立即踢昏”[4]84。当另一个士兵拿出滑膛枪袭击她时,她巨人般的身体却挡住了子弹,毫发无伤。女人充当了英雄,脱离了配角的命运,不再被“柔弱”所束缚,从而打破了性别的二元对立,寻求到了自由存在的方式。
“狗妇”就是这样一个兼具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文学形象。在生理性别上,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但就文化性别而言,“狗妇”却没有限制在父权制给女性定的框架内,打破了父权制僵化的性别角色和气质划分,这正印证了卡罗琳·G·海尔布伦所宣扬的:“我相信未来的救赎完全超脱性别的两极化和禁锢,而迈向一个允许自由选择个人角色和行为模式的世界。我提倡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这个理想称为‘双性同体’,这个古希腊的词汇……描绘了一种非僵化地派分男女两性特征和人类本能的情境。双性同体寻求将个人从社会规范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三、传统男性形象的颠覆——约旦的女性气质
在《迈向双性的认识》中,罗琳·G·海尔布伦认为:“双性气质”是“两性间水乳交融的精神,它指的是一个宽广的个人经验的范畴,允许女人具有侵略性,也允许男人温柔,使得人类可以不顾风俗礼仪来选择他们的定点”。女巨人的养子约旦在《给樱桃以性别》中的形象与气质完全符合这一论断。就生理性别而言,约旦的男性性别是毋庸置疑的。约旦被养母从泰晤士河打捞起来时,全身被泥巴裹得严严实实的,“狗妇”的邻居帮“他洗干净,并确定了他的性别”[4]8。约旦也同样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长大后的约旦声称“我已不再是男孩,我是个男人”[4]132。与此同时,约旦骨子里也充满了男性的英勇气概,一心想成为英雄。约旦有着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他认为:“英格兰遍地都是英雄,每个男孩都知道这点”[4]100,他渴望成为像特拉德斯坎特一样的英雄,像他一样在任何气候中繁茂生长,不畏艰险;他梦想着像英雄一样在国王复辟的时候受到最高荣誉的欢迎。最终,他如愿以偿,实现了理想与抱负,如同英雄一般游历了世界,开启了自己的追梦之旅,并得到了国王的接见。
然而在变幻莫测的时空中,约旦身上的女性气质逐渐显现出来。首先,他在外貌上散发着女性之美。“特拉德斯坎特和约旦扮成了妓女,他们在脸上抹了粉,双唇涂成绯红色”[4]86,这让士兵们都误认为他是女性,被他那优美的小碎步和眉眼所深深吸引。约旦皮肤光洁,当他穿着简单的女装回到妓院时,那里的女人夸赞着他的衣着,让约旦感到脸红的是“她们边抚摸我的脸颊边夸它光滑”[4]29。不难看出,约旦有着一副女孩般俊俏的长相:皮肤光滑,身姿优雅,风韵楚楚。最重要的是,他的女性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约旦通过航海一直在追寻心中的女神福尔图纳达,她是最好的舞者,她会闪光,是自由与光点的化身,是约旦在精神层面上向往的生活模式和存在方式,约旦“以她的身体作为路标”[4]134,为其导航,引领方向。实际上,约旦的逐梦之旅就是去实现女性理想与自由的过程,也是男性、女性两性精神世界相互结合的过程,男性拥有了女性的气质,两者契合之后,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打破了非此即彼的男女二元性别对立,使个人从固有的社会规范中解脱出来,解构了以菲勒斯中心为基础的男权社会。
四、雌雄同体的水果意象——“双性气质”的隐喻
作为全文中的中心意象,嫁接的樱桃暗示着“双性气质”,与文中的人物交相辉映。约旦将新学到的嫁接艺术运用到波尔斯特德黑樱桃和欧洲樱桃上,使得新的樱桃品种孕育而生。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嫁接的樱桃到底是雌性还是雄性?“狗妇”认为嫁接的樱桃本就是一种没有性别的东西,但这样的身份对它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困惑,于是母子俩便像造物主一般赋予了樱桃性别,“我们给了樱桃以性别,它是雌性的”[4]101。这恰恰和波伏娃所宣扬的“女人是后天变成的”相吻合,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父权制度和父权意识。父权社会将女性置于被动地位,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女性的社会属性是人为地烙印上去的。正如文中的樱桃一般,它是一种雌雄同株的蔷薇科李属类植物的统称,嫁接的樱桃既可以是雌性,也可以是雄性。因此人的社会性别也并非一成不变,女人可以有英勇无畏,男人也可以温情脉脉。约旦也认同“嫁接,就是将一种可能柔弱或不确定的植物,融进同一科目的另一种更为坚硬的植物上,以此获得两种植物的优点,在不需要种子和父母的情况下制造出第三种植物”[4]100,其中“柔弱或不确定的植物”隐喻了人身上的女性气质,而“更为坚硬的植物”象征着人身上的男性气质,“获得两种植物的优点”则意味着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温特森巧妙地用嫁接的樱桃意象突破了僵死的性别角色和气质划分,阐释了文化性别并非固定存在[5]。
温特森还擅长用图像符号来标识性别气质。她选取不同的水果作为符号来代表文中人物的叙事。菠萝这个水果意象则是用来指代约旦的叙事部分,温特森之所以选取菠萝,并非偶然,而是通过精心设计安排的。一方面,菠萝这种植物是由许多两性花共同参与形成的聚花果,常用吸芽、冠芽进行无性繁殖,而这种雌雄同体的特征正好隐喻了约旦身上的“双性气质”。另一方面,菠萝花的花语为:完美无缺,即有着追求完美的信念,而约旦正如同菠萝花一样,义无反顾地追寻心中完美的化身福尔图纳达,丝毫不畏惧航海途中的艰辛,最终寻找到内心真实的自我。在完成了对女神福尔图纳达的追寻之旅的同时,约旦也在精神层面完成了男性与女性两性精神世界最完美的结合。
五、“双性气质”的困境与出路
在《给樱桃以性别》中,“狗妇”因其男性化的气质特征而不被世人所接受,因为她不符合传统社会下约定俗成的女性形象。周围的人排斥她,她只好离群索居,“在那儿,除了五十条狗和她,没有别的同伴”[4]3。在内心深处,女巨人是孤独的,是寂寞的。爱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她太庞大了,没有人,男人或女人敢接近她。但她依然渴望爱,她所知的爱仅仅源于两个方面:“爱来自我的狗,它们从不在乎我的长相;也来自约旦,他说尽管我就像他名字中的那条河一般宽大泥泞,但我却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人。至于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中的其他人,据我所知,他们对我已经足够好了,他们总是尽量忽视我。”[4]35女巨人的男性气质让她陷入孤独的困境,她意识到人们对她的害怕是源于她长得比其他人高大,而这正是男权社会所无法包容的,传统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和障碍。在温特森看来,消除这种隔阂的方法就是彻底颠覆西方传统男女二元论思想,打破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最终,约旦肩负起为“双性气质”寻求方向与出路的使命,在寻找福尔图纳达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我不是在寻找神,我只是在寻找我自己”[4]133。他也曾疑惑那些朝圣的使徒为什么要寻找神,而不是寻找他们自己。后来,约旦领悟到了答案“也许在寻找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经意间遇见自己,在花园的某处,或者在山上看雨的时候”[4]133,此时的约旦已然找到了女性真实自我的解决方式,他期待着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相互融合,两性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包容,最终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67.
[2]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子[M].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20.
[3]张菁华.走向完整:寻找福尔图纳达——评《给樱桃以性别》[J].出版广角,2014(18):90-91.
[4]珍妮特·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M].邹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5]陈珊.从《给樱桃以性别》看温特森的性别观[J].绥化学院学报,2014(6):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