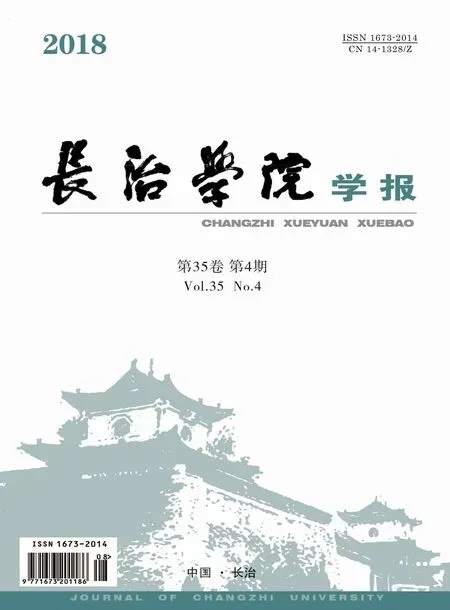家庭系统心理学视角下《最蓝的眼睛》悲剧探析
尹 元
(山西传媒学院 公共外语部,山西 榆次 030619)
一、引言
家庭系统理论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一些心理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尝试将整个家庭作为治疗对象,而不仅关注单个“病人”。由于疗效显著,最终自成体系,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流派。家庭系统心理学是家庭心理学的分支之一,它在理论上受到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对策论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家庭中的成员都相互影响;不可能脱离家庭整体而对其中某一成员充分了解;同样,对家庭各成员的了解并不等于对家庭整体功能的了解;家庭的结构,家庭中惯用的交流模式与固定的关系格局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等。
《最蓝的眼睛》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它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在白人主流社会中饱受摧残,天真地以为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就可以改变命运,却最终被父亲强奸,产下死婴而精神崩溃的悲剧人生。该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引发了无数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他们从女性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角度解读了它的悲剧根源和艺术价值。莫里森曾说:“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小说尝试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的侵犯因素可能会导致一个孩子的精神崩溃,但作者“并不想使那些导致佩科拉崩溃的角色丧失人性”[1]4。显然,小说中隐藏了一条导致佩科拉悲剧人生的家庭线索。家庭是特定社会的写照,家庭的力量甚至可能超越种族和性别的力量,从而影响人的一生。然而,国内鲜有研究者从家庭系统心理学角度对小说进行探讨。本文将从家庭背景出发,继而在种族、社会阶层、性别和民族等更大的系统内聚焦于悲剧成因。文章以家庭系统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卡特尔和麦克哥德里克(Carter&McGoldrick)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为框架,试图揭示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乔利一家人悲剧命运的家庭原因,并进一步分析莫里森采用了怎样的叙事手法将复杂的家庭背景关系暗含其中的。
二、家庭系统分析
为了考察多重压力对家庭的影响,卡特尔和麦克哥德里克提出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代际的模型。他们认为家庭内部焦虑流量与垂直应激源和水平应激源有关。这个模型的启示在于:如果一个家庭在垂直方向上已经有一定压力的话,来自水平方向的任何一点压力都将使家庭遭遇巨大的破坏[2]73。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一方面要对其成员进行心理保护;另一方面要实现对文化的顺应和传承[3]57。《最蓝的眼睛》详细描绘了黑人家庭在白人主流社会丧失自我,走向自我毁灭的畸变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通过家庭这一载体代代传承,难以打破。
(一)代际传承的家庭问题
垂直应激源是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的,如家庭态度、故事、期望、秘密、禁忌以及各种家庭问题。家庭成员在成长过程中,所听到的有关家庭的经历,包括家庭发展线路或者家庭看待新事物和新情景的偏见。还包括一些生物遗传、基因组成、性情、可能的家族先天性残疾等,以及整个家族所经历的种族、性别、贫穷等因素都属于在垂直应激源[2]22。
小说详细描述了乔利和宝琳的身世以及他们的相识和结合。乔利出生后不久便被姨婆吉米收养,根本没有见过的亲生母亲。乔利对父亲的印象也只源于姨婆的只言片语:“抛弃了怀孕的母亲一走了之”[1]144。姨婆们这代黑人妇女一生过得卑微、顺从,除了“黑人孩子和她们自己”[1]145,谁都可以差遣她们,她们经历过泪水和恐惧,在年老时收获了“悲伤与幽默、狡黠与平静”[1]146。乔利就是在这样的黑人老妇人拉扯下长大的。姨婆去世后,乔利满怀期待地寻找父亲,却被正在赌钱的父亲凶狠地呵斥。乔利内心非常失望、痛苦,竟然“在满是男人和女人的大街上,像个婴儿般拉起稀来”[1]163。他不顾一切逃离父亲所在的地方,成了真正“自由”的人:无人管束,也无人关心和疼爱。流浪中的乔利遇到了同样没有存在感的宝琳。宝琳在家中排行第九,得不到家人的关注。两岁时被铁钉穿过脚留下残疾,这让宝琳一直很自卑,而且将被忽视的原因归咎于残疾。后来宝琳成了家里最大的女孩,接管了家务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十五岁的宝琳遇到了乔利,那时候他们“年轻、相爱、精力充沛”[1]123。
从垂直方向看,乔利成长在黑人社区,从小经历隔代抚养,孤独感与生俱来,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疼爱。十四岁那年初尝性爱,却被白人撞到并羞辱,自尊心受到践踏,导致乔利陷入深深的自卑和自我憎恨的漩涡之中,此后,乔利不再拥有完善的人格。宝琳从小被忽略,她甚至渴望有人给她起绰号。乔利和宝琳带着各自的童年创伤组建了新的家庭。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在婚姻选择和其他重要关系中很容易重蹈覆辙,即倾向于选择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到的关系模式[4]143。一方面,新家庭的组建成了他们对抗外界压力的避难所:乔利不再颠沛流离,宝琳有了被需要和被重视的感觉。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结合也激发起了对方消极的一面:宝琳渴望从“丈夫那里获得安慰和快乐”[1]166;乔利却习惯自由,“排斥她对他的依赖”,“单调、毫无花样以及枯燥沉重的压力逼得他濒临绝望”[1]166。他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毫无兴趣,只有喝酒才能让他“感到略微解脱”[1]167,而宝琳试图改变并拯救堕落的乔利。
(二)家庭所经历的发展压力
家庭在发展过程中应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和变迁时,所经历的焦虑激起性事件就是水平应激源。这些事件包括各种可预见的发展压力以及不可预测的创伤(如突然死亡、慢性疾病),创伤性经历[4]23。
当孩子出生后,完整家庭中的夫妻子系统必须分化出来,从而履行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任务,同时又不能失去其夫妻子系统的功能性[3]69。小说中,佩科拉和哥哥萨米出生后,矛盾进一步激化。乔利没有过正常意义的家庭,不懂如何抚养孩子,更不知道如何处理家庭关系,自然也没有家庭规则的概念,更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宝琳想要拯救乔利,而乔利却将其视为发泄“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1]47的对象。每逢乔利喝得酩酊大醉,便会有一场夫妻大战,萨米和佩科拉要么是观众,要么也卷入其中。乔利一家在执行这些潜规则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沟通方式:萨米会与母亲结盟攻击父亲,或者索性离家出走。这与父亲当年的逃离如出一辙。而佩科拉由于年龄的限制,只能选择忍受痛苦。宝琳宁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中,与丈夫划清界线。她向孩子们灌输自尊体面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们:“在儿子心中烙上了离家出走的强烈愿望,在女儿心中刻上对成长、他人以及生活的恐惧”[1]135。
除了抚育孩子带来的可预见性的压力之外。乔利一家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加速瓦解了本来已不稳固的家庭。乔利买的新沙发刚运回家就破了,他“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起来了”[1]41,却只能自认倒霉。他弱小无助的黑人,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打压下,乔利已经沦为一个失去男性尊严、种族文化尊严和为人父尊严的废物[5]。宝琳遭受了比残疾更为严重的种族歧视进而人性扭曲。在临盆之际听到了白人医生将黑人看作牲畜的评价。在白人强势文化的精神奴役下,她盲目崇拜,用责骂和殴打对待自己的孩子,却对主人的孩子百般讨好和宠爱。她企图通过疏远家人、效力白人来找到自己的价值。小佩科拉更是白人强势文化的受害者,不仅得不到家人的爱,还承受着来自学校、朋友、甚至黑人社区的蔑视和侮辱。白人强势文化利用宗教、教育、媒体等手段宣扬白人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致使儿童产生恐惧、自卑、自我厌恶等症状。久而久之,她性格自卑,否定自我。
三、叙事策略分析
莫里森娴熟的叙事手法将乔利一家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无可改变的家庭出身、种族背景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这使得读者对这一家的悲惨遭遇多了同情与理解,而不是简单的厌恶和嫌弃。
小说融合了多角度叙事:“我”的叙述、全知全能第三人称的叙述,主要人物自己的回忆。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是小女孩克劳迪娅,她天真无邪的视角使小说读起来轻松愉快,却又因“无知”说出一些真相,使文章弥漫着浓浓的哀伤。
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旁白为事件交代了必要的背景,使读者能够看清事情的因果。小说中,佩科拉一家的生活,乔利和宝琳的生活背景介绍都是通过第三人称视角讲述的,详尽而真实地展现了黑人生活尤其是乔利一家的无助和无奈。
全文的叙述视角不断变换,由各种声音从各自角度讲述,使读者对小说的描述深信不疑并感受到透彻心扉的痛。第六章讲述了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刚烤好的馅饼,烫伤自己,并吓到白人家的小女儿,母亲出乎意料地对佩科拉拳打脚踢,却温和地安慰白人女孩。这种奴性高于母性的做法让读者感到愤怒,并且不可理喻。而作者笔锋一转在第七章讲述了宝琳的成长经历,这时读者似乎又能理解宝琳这位黑人母亲被白人价值观奴役后的无奈之举。在这一章插入了宝琳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展开的一段心灵道白,将自己的身世、遭遇和感受清晰地道与世人。第八章是小说的高潮,即父亲强奸了女儿佩科拉。作者也没有直接讲述,而是从乔利的身世讲起,讲述了他在残缺畸形的家庭中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从而使读者对这种乱伦行为惊讶之余抱有一种理解和哀叹。
四、小结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这个大系统中解读。任何行为异常的人都是不健康家庭的替罪羊,只有改变整个家庭关系模式,异常行为才能治愈。莫里森在小说中着力描写了乔利一家的家庭氛围、夫妻关系以及父性母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佩科拉的疯狂,乔利的性扭曲,以及宝琳的畸形母爱都是家庭病症的体现。像乔利一家一样的黑人家庭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经济状况,身体力行地正确教育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模式才有可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