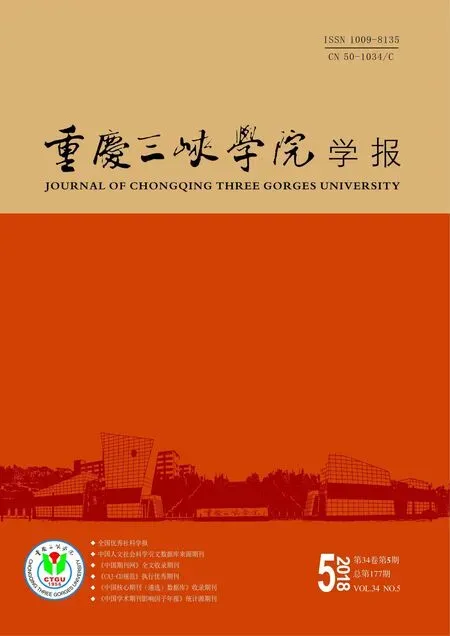清末民初“国族共同体”的文学影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本土资源
杨瑞峰
清末民初“国族共同体”的文学影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本土资源
杨瑞峰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清末民初文学探论中的中国现代民族意识以“国族同构”为基本样态,首先落实为“中国文学”概念的确立,其后又典型体现于“国民文学”的理论论争。前者确立了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以国族一体的思维借助文学媒介图构民族复兴的基本范式;后者寄寓着以“国民”的视角通过文学想象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现实愿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必须以早期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勃兴及其文学实践为理论出发点,从作为宏观客体的“民族国家”和作为微观主体的“国民”的双重尺度强调“文学”与“民族国家”的贴合,以“中华民族”范畴为理论基点,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叙述与中国现代民族意识有机结合。
清末民初;民族意识;国族同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
清末民初,救亡、启蒙、革命等主流文学话语极大地刺激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于是,一种因民族焦虑而滋生的国族意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频频亮相,要么验证了晚近中国文学对民族意识的倚重,要么因涉及到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联的深层理论问题而“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的一个截面”[1]。然而,在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满眼繁华”的情况下,民族之维确是一种稀缺话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图谱中引进“民族之维”,除了对民族概念的多义性与历史性进行辨析,更重要的还在于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范畴在早期中国的经略情势有所了解,进而探寻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民族论述的会通之处。
一、日本体验与晚清中国“民族”意识的发生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然而,尽管历史总是属于某个民族,民族本身确是颇有争议的现象。”[2]1然而,“民族”范畴自身的难以界定和它与现代社会的历史言说之中的重要性之间的对垒,却总是以后者的得胜告终,胜利的果实主要体现为中外理论家们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乐此不疲的理论界定。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集中体现为两种倾向。前者认为“民族”一词非中国本土固有,乃系清末民初留日学者假道日本引进的汉译西语。近年来,国内又有部分学者指出,“民族”一词并非日本传入的现代新式语汇,而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固有的①。
“民族”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存在,但古代中国的“民族”用例,“多是表示‘民之族属’和‘民之族类’的一般分类含义,与‘族类’一词相当,固定化程度远不如‘宗族’‘家族’”。“古人在表达相关含义时,更习惯使用的词汇,还是单音节词‘族’。”[3]部分学者认为“民族”一词是中国固有语汇,主要源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汉语“民族”一词的含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背后潜藏的“认识论断裂”,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沿着线性历史逻辑稳定发展的固有术语进行了一番想当然的知识考古。实际上,“古代中国只有家国天下,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4]38。
与之相比,认为现代中国“民族”一词首先由日本将其与西方的“nation”对译,而后传入中国的观点,似乎因笼罩着现代性的光辉而更具说服力。但所谓“日源新语”式的处理也有其简单化和武断之处。首先,从本质上讲,这种着眼于概念本身的做法,往往以概念的对译、输出与输入为考察中心,多少会忽视概念背后的文化信息和复杂的历史情势;其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用例出现在清末民初,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一词的认同与援引始终伴随着一种夹杂着情感冲击与政治威慑的复合感受,绝非“日源新语”式的笼统界说可以解释,因此,隐含在“民族”一词背后的,不仅仅是语源意义上的历史梳辨和技术层面的翻译问题,而是更为深沉更为普遍的问题的反映,即“民族”范畴在“西方—日本—中国”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和语言文字的交往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
在晚清中国,“民族”往往被想象为一种“救亡图存”的先进理念,在“夷夏之辨”“华夏中心主义”等传统族类意识的傲慢被证伪之后,国家民族在陌生而又复杂的国际交往新秩序中自我争存的有效手段。民族用义最早诞生于晚清留日学人之中。原因在于,“与当时一般士大夫阶层创痛之后漂浮的民族情绪不同,留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有机会从当时大量流行于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著作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识,形成对于作为‘主义’的民族意识的基本观念”[5]21-22。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著《支那文明史》时首次使用了日文新词“民族”[6]334。1901年,梁启超又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率先提出“中国民族”概念[7]11-12,自此,“近代的中国民族逐步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8]。其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提出“中华”概念[9]1,为当今“中华民族”概念之先声。梁启超的“民族”用例,开创了在“国族一体”的意义上理解“民族”的先河,也奠定了晚清知识分子“民族”话语叙述的基本范式和中国现代“民族”概念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特质。
梁启超之后,《浙江潮》杂志发表署名“余一”的《民族主义论》一文,文中明确指出:“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当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10]以此为开端,关于“民族”的讨论在留日学生群体中成为热点话题。除了《浙江潮》之外,留日学生以籍贯所属省份为名,创办了诸如《江苏》《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河南》等大量“同乡会”性质的杂志,这些杂志虽以省份命名,但其格局却超越了狭义的乡土情结,它们格外关心的均是民族大义,而“民族”在杂志创办者的理解中通约于“中国”②。
梁启超与当时留日学生对“民族”等于“中国”的理解,虽然受到了在日本接受的西方新思潮的启发,但却与西方“民族”发展史上常见的“地域共同体”“亲缘共同体”甚至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信仰共同体”等认知模式拉开了距离,是一种带有晚清时期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称其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表述显现了民族与国家同构的集体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的理解,默认在危难时刻,民族尺度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一前提,因而体现了我国“士大夫”文人惯有的忧世担当之外,还与西方近代以来对“民族”,尤其是“民族主义”的过分政治化理解有所不同。
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发展历史宣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功能之一。”[11]5沿着这一思路发展,往往导致“帝国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因而招致了众多人文主义学者的批判。美国学者萨义德就曾指出:“民族主义不仅引发了例外论的确凿无疑的危害和各种类似于偏执狂的‘反美主义’教义,使我们的现代历史受到了不幸的丑化;而且,它也引发了毫无节制地争强好斗的、爱国主义的主权论和隔离论,文明的冲突,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12]59因此,萨义德将“民族主义”与宗教激情、排外主义一道,视为人文主义的三大宿敌。
而在晚清中国,对“民族”的独特理解决定了“民族主义”更接近于一种“挽狂澜于既倒”式的自卫策略。当时的留日学人群体普遍认为“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10]。甚至当战败的耻辱极大地煽动了新知识分子的“民族”热情,鼓动他们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去实践“救亡”理想时,因为将中国腐朽的根源归结为满清王朝的统治,因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也被梁启超指责为“民族复仇主义”[13]1069。在梁启超看来,民族国家的建立,或民族主义的要义在于“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其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14]459。这种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本土化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早期中国民族意识的独特性,因而渗透于清末民初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今日反观,仍有可取之处。
二、中国文学、国民文学:国族焦虑的文学影像
“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现代性’的转型,文学想象一直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国家是‘作为影像被心灵世界描绘出来的想象性的政治共同体’,文学位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地位,于是,现代国家开始成为文学、文化想象的中心。”[15]13晚清民国时期文学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珠胎暗结之关联,既体现于文学理论,也体现于文学作品;先典型体现为“中国文学”概念的出现,又逐步演化为“国民文学”论争之激烈,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文学变革的理论主张等“副产品”③。
较早意识到应当从文学层面推广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依然是梁启超。
晚清中国报刊媒介的兴起与日本对于小说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迫使梁启超意识到了小说在启迪民智方面的重要性,自《新小说》创刊起,其对小说的认识也冲决了在通俗教育之普及的角度去理解的藩篱④,直接落实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1902年,《新小说》创刊,同年第14期的《新民丛报》称其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并为其刊登了一条广告,广告中宣布了《新小说》的基本条例,其中第二条为“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16]。有学者考证“正是这则不太起眼的广告,首先打出了‘中国文学’的旗号”[15]。冯骥才曾指出,“中国文学”概念的确立得益于作为“他者”的西方国家侵入导致的我国人民“国家”意识的觉醒[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概念的正式提出,意味着文学开始为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至此,文学与现代意义上有着固定的地域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的民族国家联系了起来。
“国民”价值的突显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另一重要指标,于中国而言,文学界对“国民”价值的倚重一方面是中国抵抗西方列强的必然抉择,因为“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18]3。另一方面则出自“国民”自身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正如许纪霖所言,“近代的民族国家,既是一个以国民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以民族为自我理解的文化共同体。国民与民族,构成了nation的两面”[19]41-42。因此,无论是早期的梁启超还是稍后以“国民性”批判著称的鲁迅甚至民国时期的“国民文学”论争,都对“国民”改造与新型民族国家的创立之间的关系抱持着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将近世“民族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直接表述为“舍民之外,则无有国”[20]309。进而做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21]157的论断,从而使得其“国者,积民而成”和“文学(小说)救国”论思想实现了无缝对接。其后,以“国民”尺度为文学尺度之一的思想嗣响不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国民文学”论争。
“国民文学”是一个长期为学界忽视实则内涵丰富且极具研究价值的概念。晚清初创期的“国民文学”概念总体上以梁启超的“新民”主张为目的论依据,旨在通过文学这一有效媒介勾勒出“国”与“民”之间的政治隐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文人国族焦虑心态的文学表达。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言必及“国家”“民族”“国民”“国民性”依然是“国民文学”研究的核心语汇。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2]的口号,这是关于“国民文学”的较早用例,但这里的“国民文学”显然基本等同于“平民文学”[23],没有太强的国族意识。民国期间,以“国民文学”为中心,发生了三次论争⑤,“国民文学”开始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彼此勾连。
1924年至1925年,郑伯奇、穆木天等继陈独秀之后明确提出“国民文学”的主张,招致主张“西化”的钱玄同的对话,从而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郑伯奇1924年于《创造周报》第33至第35号上连载其长文《国民文学论(上、中、下)》,文章开头即反复强调,“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据我看来,是我们中国新文坛目下最紧切的要求。”[24]从其选用的译语便可看出,郑伯奇是在现代“民族”的意义上理解“国民文学”的。接着,他拟想了提倡“国民文学”可能会遭遇的五种责难,进而系统阐述了应该提倡“国民文学”的缘由。在郑伯奇看来,“国民文学与国家主义,毫无必然的关系,而提倡国民文学,更不一定赞成国家主义”。“但艺术家既然也是人,一样地在社会上做现实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利害最切的国家,对于自己血液相同的民族,他能毫无感觉么?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对于现实生活体验最深切的。”[24]
郑伯奇的论辩感伤而犀利,映照了历史转折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心理。总体看来,他认为作家的社会属性和中国的历史现状规定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提倡“国民文学”。同时,于“国民文学”而言,“民族国家”并非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实体政治形式,它只能以意识形态化的姿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现实而非抽象的哲学层面的“自我”(作家),进而实现对“文学”的影响,而“文学”对这种影响也要有所回应。随后,穆木天在《京报副刊》发表写给郑伯奇的《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以诗歌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但穆木天所理解的“国民文学”已经和郑伯奇所呼吁的“国民文学”有所差异,在他看来,提倡“国民文学”就是要歌颂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遗产[25]。
1925年,钱玄同在《语丝》上发文,对“国民文学”“贪恋国故”的理论姿态进行批判[26]。钱玄同之所以批判“国民文学”,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国民文学”痛恨“洋方子”,表现出了愚昧的复古和保守倾向。但实际上,与其说钱玄同是对“国民文学”进行批判,毋宁说他所批判的只是穆木天,因为钱玄同所引用的“国民文学”主张,均出自穆木天写给郑伯奇的信,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穆木天的个人观点。
钱、穆之争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林语堂、王独清、周作人等均参与进来,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次论争虽然在对待“国民文学”的态度上有所分歧,但在对于“文学”应该担负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责任方面则达成了统一。正如周作人所说,所谓“国民文学”,究其实,不过是此前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投射与强化,它所希求的是文学家通过文学创作要表现一定的“国族担当”[27]。郑伯奇、穆木天均不反对“西化”,他们所吁求的是要看清本国的国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实践“文学救国”理想;而钱玄同主张“西化”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了腐朽的“王朝中国”在现代化的西方面前不堪一击,因此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知识以匡救时弊,建设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两派虽冲突激烈,却也“殊途同归”。
1934—1935年,出现了第二次“国民文学”讨论热潮,文学的国族意识形态性更为强化。与第一次“论战”相比,第二次的讨论因为特殊历史情势的规定显得相对“和谐”。1927—1937年,“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20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面的再评价”[28]416。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多数作家的政治热情被调动起来,文学界发生了成仿吾所谓的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关于“国民文学”的讨论也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做了适时调适。
1934年,上海的《民族文学》改名《国民文学》,该刊“发刊词”对“国民文学”的理想诉求与发展路向作了规定,指出“国民文学”的责任是研究“中国民族自己的固有文化”;“国民文学”要研究我国“国民之发达的历史”,因为“无国民则无国家”;“国民文学”要求在介绍外民族的文学时,要与本国实际现实相符合,“以建设发展及介绍有助于解放中国民族的文学”;“国民文学”要求在对本国文学给予充分关注的前提下树立经典作家形象(如屈原、陶潜等)以便使中国文学因独特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致于在盲目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丢失自己的个性;“国民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向帝国主义的进攻及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必然地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以图解放”[29]。这些规定与展望,确立了1930年代“国民文学”讨论的基本格调,其后李若冰所谓的将“充足的国民意识反映到文学上去,便是某民族的国民文学,或某一国的国民文学”[30]。《新垒》杂志发表的《国民文学的防御战》《再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精神》,《国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张资平翻译的《文学与社会及时代精神——国民文学之一注释》等文章虽论述角度不同,但总体上均恪守“发刊词”圈定的疆界,未曾须臾稍离。
梁启超开创了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以国族一体的思维去理解“民族”的范式;“国民文学”范畴的出现和与之相关的讨论则将文学家们从“鸳鸯蝴蝶”式的“文人梦”中拉回其首先为“一国之民”的现实,体现了以“国民”的视角借助文学想象图构“民族”复兴的现实愿景。这两个范畴的先后出现,代表了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界对“民族”的理解从客体(国)到主体(国民),从宏观(政治文化视野)到微观(文学角度)的演变路径,构成了理解我国“民族”概念现代转型的一条致思秘径。
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评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31],一直是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准则。遗憾的是,一方面,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习惯于从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汲取建设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与本国文学传统的非理性隔膜;另一方面,以“革命”话语为演绎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史进行历史溯源的经典范式又加剧了其与中国传统文论史、思想史的断裂,从而掩盖了后学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思考如何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民族叙述的理论精髓与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有机熔铸,进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将有助于匡救上述思维偏谬。
顾颉刚曾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警示国人:“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民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32]尽管顾先生的论见曾招致多方对话,但其民族叙述的基本格调却多有可取之处。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欧风美雨灌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其初创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抱持着一种对外的姿态,通过文学启蒙与政治变革的双重变奏确立了成熟的“中华民族”意识。因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当以“中华民族”范畴为理论基点。
同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要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民族论述为基础,将其与中国现代民族意识有机结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总体抗拒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均对“民族”问题有所论述。马克思曾讽刺道:“犹太人对待国家也只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即把国家看成一种异己的东西,把自己想象中的民族跟现实的民族对立起来……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33]164恩格斯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4]494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基于阶级的立场表达了对不同类型民族主义的不同态度,譬如,他认为在压迫与反抗这组“民族关系”中,被压迫民族是应该得到肯定的[35]272。上述论述,与早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文学表达多有内蕴相通之处。首先,马克思对犹太民族“民族优等论”思想的讽刺对晚清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具有“预见性”,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存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其次,对被压迫民族反抗正义的捍卫佐证了我国自晚清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尺度谋求民族独立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我们以“中华民族”这一中国境内统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之维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son)曾指出,在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时,我们应该将其“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因为“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安德森据此断定:“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36]11安德森的精辟论述,无疑为我们从文学角度理解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的发展实况则验证了其合理性。故此,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是在理性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中渗透文化维度,坚守“民族的核心是文化”的价值判断的必然选择。
此外,我们还需意识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与“文学功能论”的阐释框架高度吻合。乔纳森·卡勒曾指出“文学在传授中立的审美经验的同时,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37]38。于卡勒而言,文学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读者敞开的,集中体现为一种能够“提供普遍性”的文本机制,而当其提供的“普遍性”面对能够读懂某一文本语言的读者时,二者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民族性的作用”。卡勒的理论看似抽象,实则具体而辩证。在他看来,文学越是强调功能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它的民族作用就越强大。例如,“肯定简·奥斯丁眼里的世界具有普遍性,反倒使英国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成为一个品位高雅、行为规范的地方”[37]。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因此,“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了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38]31所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要在保持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同时,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的合流。
总之,对民族国家之历史命途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思考,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民族意识的持续灌注与全情生发以及对文学与现代民族的确立之间关系的把握,是清末民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突出特点。而清末民初中国理论家们的民族叙述与文学思想对更为完善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设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正在于要强调“民族国家”与“文学”的贴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一宝贵的历史经验正在逐渐被遗忘,而中国当代文论的最大困境也主要在于对理论过于崇拜,对民族国家和文学现实之关系关注得太少。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曾经“红极一时”的“民族国家”话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与文学性或者纯文学性彼此抵牾的存在。然而,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完全脱节的文学无法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如一个没有国族意识的文人无法从根本上确立具有伟岸价值的人文关怀。鉴于此,我们必须直面本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珍视从这一历史脉络中提取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判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当代文论体系。
[1] 黄念然,刘芳.“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探索[J].学习与实践,2017(3):113-120.
[2]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 黄兴涛.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J].人文杂志,2011(4):140-144.
[4]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 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7.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胡亚敏.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12-20.
[9]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文集7.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1903(1):19-27.
[11]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 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1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5] 杨霞.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6] 新民丛报[N].第14号,1902-08-18.
[17] 冯骥才.关于“中国文学”的概念[J].文学自由谈,1996(4):56-57.
[18] 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代序.
[19]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0]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1] 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G]//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02-01.
[23] 王向远.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0-98.
[24]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J].创造周报,1924年第33号.
[25] 穆木天.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J].京报副刊,第80期,1925-03-06.
[26]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J].语丝,第20期,1925-03.
[27] 周作人.答木天[J].语丝,第34期,1925-07-06.
[28]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9] 国民文学·发刊词[J].国民文学,1934(创刊号).
[30] 李若冰.我国国民文学的回顾与展望[J].国民文学,1934(创刊号).
[3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4).
[3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9),1939-02-13.
[33]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4]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7]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8]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相关论述参见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邸永君《“民族”一词非舶来品》,《中国民族报》,2004年2月20日;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②能够代表这种思想的典型事例是当时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杂志,但因为始终忧心“中国之存亡”,该杂志在出版了5期之后,改名为《汉声》,因为在主创者看来,当时最紧急的事情莫过于“扬民族之风潮,兆汉祀之既绝!”显然,“民族”在他们的理解中就是“中国”。参见《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叙论”;《汉声》1903年6月第1期相关表述。
③“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宏大的话题,不仅涉及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而且几乎蔓延在晚清至民国(甚至如今)这段时期内的整个文学场之中,涉及到的理论家、作家、文学思潮既多且杂,难以简单说清。但鉴于本文的写作思路侧重于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时代理想,这一宏大选题又无法回避,权衡之下,本文撇开文学作品的相关论述,并且摈除了诸如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等一定程度上已为学界常识的讨论,主要从梁启超“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到民国时期论争激烈但学界至今着墨不多的几次“国民文学”论争入手进行论述。
④早期梁启超对于小说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认为小说有利于通俗教育的普及方面,譬如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等文章中表述的观点,都属于这一层面。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⑤“国民文学”的第三次论战是1944年以《中国文学(北京)》为阵地的“国民文学”讨论的余波,影响不大,且总体上并未超越此前的“国民文学”论争。
The Literary Image of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ative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View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YANG Ruife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exploration takes the “national isomorphism” as the basic pattern. Firs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Second, it is typically reflected in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former established the standpoi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basic paradig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th the idea of national unity and the media. The latter commits the vision of realizing national culture rejuvenation through literary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view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early Chinese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literary practice. From the dual scale of “nation state” as the macro object and “national” as the micro subject emphasis on joint of “literature” and the “nation state”. Based on the Chinese nation scope, 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classical Marxism is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national consciousness;national isomorphism;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 national view
I0-02
A
1009-8135(2018)05-0090-09
杨瑞峰(1990—),男,甘肃天水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艺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