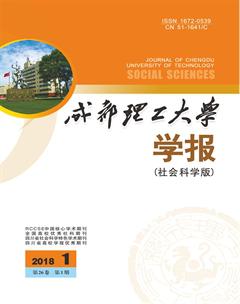论《中庸》“诚”的先验性价值お
吴玉琨
摘要:
“诚”作为先秦儒家经典《中庸》中的重要理论,被视为宇宙的源泉和亘古亘今的现实存在,是人类社会相处和内心体察自省的价值归旨。“诚”被《中庸》赋予一种先验性的价值存在,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前而无始、后而无终的绝对存在。“诚”生化万物,是宇宙万物的源泉,贯穿万物,是宇宙万物活动生存的依据,统领万物,是宇宙万物价值的最终归宿。
关键词:中庸;诚;先验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1005904
《中庸》是先秦儒家最具有思辨价值的经典,“诚”在《中庸》的文本中占据绝大篇幅。“盖中庸之道,一诚而已矣。”[1]62《中庸》一书“散于万事,即所谓费,惟‘诚之一字足以贯之。”[1]1537“诚”是《中庸》的主旨,文本中讲鬼神、讲忠恕道德、讲政治、讲万物生化最终的归旨都落在一个“诚”字上。
一、作为宇宙源泉的“诚”
在《中庸》看来,“诚”是宇宙万物的源泉,一切事物都是由“诚”发散化育的。“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杀了便冬藏,元亨利贞终始循环,万古常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3]33“诚”是贯彻万物之中的,没有一刻的停顿,是四季交替变化的来源和万物之主宰。“‘诚被首先规定为天的根本性质”[4]136,是一种先验性的本源假设,《中庸》的作者设定“诚”为天的根本性质,在宋代理学家处,“诚”又被视为理。“诚只是实。又云:诚是理。一作只是理。”[5]102朱熹是将“诚”和“理”等量齐观的。可以认为,朱熹“理一分殊”中的“理”派生万物,是万物原本具有的真实存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学者认为,“诚”具有同等的价值内涵,即“诚”乃万物源泉。但先秦时期的价值一元论思想是否与朱熹的一元论立场相同呢?答案是否定的。“至诚尽性一章以下,朱子分天道、人道,都是硬派,不甚贴合。”[6]132清代理学家在解读《中庸》时认为,朱熹“理”的思想和先秦“诚”的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也有不甚贴合的地方。朱熹认为,人心之外别有一个“天理”,是绝对权威的存在,人人都要遵循;在人心之中且有个“性”字,朱熹的工夫修养论是要使得这个“性”字复尽天理,这也是后代理学家认为朱熹“分天道、人道”不贴合的原因所在。
《中庸》中的“诚”在本源价值上是一贯的,事与物背后是个“诚”,人性背后亦是个“诚”。《中庸》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7]35,“诚”是生化客观事物、贯彻客观事物终始的。朱熹在解此句时认为:“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7]35“诚”犹如先验的存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因为它的存在而生化繁复。在理学家看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做万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诚为体,故不诚则无此物。终始,是彻头彻尾底意。”[8]1579“诚”是先天而存在的价值源泉,是生化万物的实有。与朱熹分天道、人道不同,诚是内外一贯的,在物的背后是诚,人性背后也是诚。这样就形成了人与天的相通相贯。“诚”的一贯性实现了人心与客观物质的直接沟通,既体察了自我内心的“诚”,也体察了纷繁复杂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诚”。“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7]34原因所在即“诚”是内外一贯的。“誠”之所以内外一贯的本因在于人与一切客观事物都是“诚”的表象,“诚”是世界精神的核心。
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学者通常的“解经”都是从宋儒那里“接着讲”的。“诚”之一字在本源上有没有上述所谓的先验性价值,或者只是作“诚悫”解。朱熹在训诂仁义礼智等名义章目中认为:“诚,实理也,亦诚悫也。由汉以来,专以诚悫言诚。至程子乃以实理言,后学皆弃诚悫之说不观。中庸亦有言实理为诚处,亦有言诚悫为诚处。不可只以实为诚,而以诚悫为非诚也。”[5]102在先秦儒家的朴素唯心主义那里,认为“诚”不仅是宇宙质料“因”的来源,也是贯彻万物始终的如同“气”的存在的动力因的所在,是君子实现“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功夫修养论的途径。这样看来,“诚”不仅可以作为功夫修养论的“诚悫”来讲,也可作为先验存在的真理来讲。
二、作为物之终始的“诚”
在先秦儒学家朴素的唯心主义思想中,“诚”不仅是生化万物的价值源泉,同样是贯彻万物生命始终的类似“气”的一种存在。这种个体生命存在之前就具有的被视为人文价值核心的“理”贯穿于物的生死始终。宋朝陈淳认为:“且诚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这理,到赋形之后未死之前,这道理便无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发见,但人不之察耳。”[3]33“诚”作为一种“理”的价值存在,贯穿于物质生死过程之中。即使更多的愚夫愚妇没有体察到这一点,但是它确是真实而无妄地绝对存在着的,这一点似乎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认同。
南宋朱熹认为:“‘诚者,物之终始。来处是诚,去处亦是诚。诚则有物,不诚则无物。”[8]1578“诚”的价值先决性决定了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与物的社会存在过程之间,也存在于物质的生与死之间。这个物质作用拟化于人的“体用”上就是“诚”贯穿于人的一切社会交际之中。等到人离开了这个现实世界,“诚”的世俗价值也就完成了。“看来凡物之生,必实有其理而生。及其终也,亦是此理合到那里尽了。”[8]1577由此看来,“诚”的社会效用主义功能就显而易见了,它贯穿于物质生死之间,规范于社会价值构造,使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至于生前死后的“诚”的赋形性与存在性问题,宋代的理学家并不关心。儒学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在这个物的社会现实存在之中,“不诚则无此物。终始,是彻头彻尾底意。”[8]1579虽然是彻头彻尾,但是这个长度的标尺还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规度的。“从头起至结局,便是有物底地头。”[8]1577
“诚”生化万物,但作为生化之后得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并没有得以和“诚”隔离起来。“诚”在物的生死之中始终贯彻,化身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天道和内在的“理”。这是一种儒学唯心主义大师所理想的应然状态,这种“诚”应该是贯彻于社会一切人的生存交际之中的,即成为一种尺度。但是否存在“不诚”的情况呢,如同性善在应然状态下是贯彻于人物始终的,对于社会的种种恶如何解释一样,先秦的儒学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直接漠视掉了“不诚”存在的可能性。“诚,便贯通乎物之终始,若不诚,则虽为其事,与无事同。”[8]1578这种直接漠视掉“不诚”的现实存在的可能性,虽然保住了“诚”的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前而无始、后而无终的价值一元论的绝对存在,但不得不说是理论上的重大缺憾。
《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不论真伪大抵是先秦孔门学派的核心经典。劳思光先生在论及先秦孔门学派的遗留问题以及哲学体系上的缺憾时指出:“但就纯哲学问题说,则此一切肯定能否成立,必视一基本问题能否解决,此即‘自觉心或‘主宰力如何证立之问题。”[9]116孔子基本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调和方向,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仁”与“为仁”,但孔子从未提及“仁”的来源问题,在哲学价值上也即是“仁”与“性”的关系问题。《中庸》的作者继承了孔门学派的基本思路,假定“诚”是人物自觉性和主宰力的绝大力量,漠视了现实“不诚”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视现实不诚之物的存在是由于不能尽其心之诚。虽然本意在于构建世界现实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就规模和体系的完整性上不及宋代理学。
三、作为道德归宿的“诚”
《中庸》“诚”学最后一步即落在君子为“诚”的功夫修养论上,这是《中庸》“诚”学体系的收尾,也是其世俗价值的核心所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32又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7]33这两处都是在讲“诚”与“为诚”的区别,一个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诚,一个是功夫修养论上的为诚。“论先后,第二义为先,论轻重,第一义为重。”[12]53
“为诚”也即“诚之”,是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工夫修养的重要方法。儒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提到:“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10]256在他看来“诚”是为学立世的咽喉关键和心髓精微之处。不仅明代大儒,其实宋代理学家也有相似看法:“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11]49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为学的根本培壅即是“立诚”。但仔细分析“二程”的这句话似乎又将“诚”与“勉”二分了,在今天看来“不勉”犹是“不诚”,是根本没有培壅的表现。在具体的修养工夫上,“立诚”只是“为诚”的第一步,“为诚”的关键在于“至诚”。“君子无所不用其极”7[6]将“为诚”的工夫修养论推到极致。
“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7[34],“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7[39]可见“至诚”是“为诚”工夫的重要步骤,是体察真正的诚学本体论的关键,是立身处世不断精进追求的价值表现。因为《中庸》的诚学世界观是一贯的,因此当个人通过修身诚意地学习体察到了自我内心之中最高境界的“诚”之后,也即体察到了宇宙万物的“诚”,达到了最高的宇宙境界。熊十力从心性论出发认为:“从来圣哲,皆由修养工夫纯熟,常使神明昭彻,而不累于形气,即宇宙真体,默喻足当躬,不待外求。”[13]88宇宙的最高精神即在自我的内心之中,通过尽心诚意地默默体察,孜孜不舍地向着最高的“诚”推进,至诚也就豁然贯通、神明昭彻。
《中庸》的诚学本体论认为有一寸物就有一寸诚,因其物质背后意志之为诚,万物一体必然成为其哲学后果。万物一体,一体同源在诚这里得到归结,诚成为了最高的生命价值所在。在诚的背景作用下,万物“各诚其诚”,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38这里用佛教的话讲,其实是“事事无碍法界”,万物“各诚其诚”,每一事物最终要达到的都是其先天使命和价值归宿的最高至诚。在万物一体的关系作用下,万物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爱人如爱己,爱物如爱己。当然这是诚学本体论落实到具体的功夫修养论上的结果。“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7[40]“诚”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君子治理天下的标尺。
四、结语
《中庸》的诚学本体论是先秦儒家在哲学本体论上的重要突破,“诚”被赋予一种先验性的价值存在,有一寸诚即有一寸物,诚统摄万物,贯彻万物存在的终始,成为绝对一元性的价值归宿。虽然诚学本体论的思想体系较为简单朴素,规模和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体察不及宋明儒规模深刻,但《中庸》作者所具有的诚学思想是规模宏大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中庸》所言“君子之道费而隐”,程子所谓“放之而弥六合”,《中庸》诚学所展现的是一种万殊一体的哲学构想。《中庸》的诚学思想树立了一种世间存在的来源性、价值合理性和哲学的归属性,为后世儒家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做出了肇啓之功。
参考文献:
[1]熊赐履. 学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3]陈淳. 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4]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6.
[5]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李光地. 榕村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7]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书局, 2016.
[8]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9]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一册)[M].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12.
[11]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陈来.仁学本体论[J].文史哲, 2014,(4):41-63.
[13]熊十力.境由心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Abstract:“Sincerity” as a important theory in Pre-Qin Confucian classics Zhong Yong, is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existence and th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s the human society and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introspection along inner purpose. “sincerity” as the transcendental value is to give a priori value exists, is small and no inside, big and no outside, before and no beginning, no end of the absolute existence. Sincerity of all things,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through all things, is the basis for the survival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is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the universe.
Key words: doctrine of the mean; sincerity; priori; value
编辑:鲁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