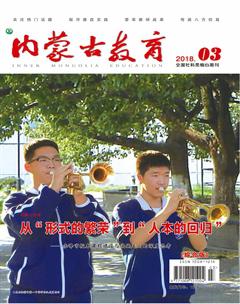父亲走了
王丛
2017年12月30日下午3时, 96岁的老父亲突然辞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生于1922年,当算教育世家出身:他的外祖父、父亲及两个哥哥都是当地有名气的塾师。
父亲的外祖父,是进京赶过考的。据《敖汉旗志》记载,我们家祖上是晚清时从山东迁居过来的,跟闯关东、走西口差不多。后经几代人辛勤的劳作,才成为中农的。我的祖父从小边耕边读,他的老师,就是我的太姥爷。当时出行骑着一头黑驴,配有鞍子铃铛。父在田里干农活,每听到铃铛响,就知道是老师来了,必定跑去,拽住他的驴缰绳,非得让他给讲一段书才放行。大概正是因为看中了祖父的勤奋好学吧,太姥爷就从祖父的老师变成了祖父的岳父。
祖父在当地名气极大,儒家典籍熟极如流自不必说,其他如医卜星相,阴阳堪舆,也都有所涉猎且造诣匪浅。我看到过他留下来的手抄《三字经》和对联,书法精妙,允称大家,我对书法的兴趣,就是从观摩他的墨迹开始的。甚至,盖房搭屋,榨油漏粉,这些劳动技能他也都不陌生,耕田种地,自然更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洞察世事,人情练达。他有五个儿子:我的大伯父、三伯父,还有我父亲,都读了书,做了老师。二伯父、四伯父没有读书,做了工匠。这教育体制还是双轨的。分家时,油坊给了二伯父,粉坊给了四伯父,以作为他们没能读书的补偿。土改时,我家先被划成地主,浮财被分,后来又复评为中农,被分的浮财应该退还,但祖父说,浮财不用退还了,成分划回来就好。当时,没人知道家庭成分意味着什么,但他却能敏锐地感觉到其中必定大有干系。果然,他的这个举措赢得了贫下中农的好感,使整个家族后来受惠无穷。
我记事时,祖父已病卧有年,不能再教我什么,但他因我爱读书而非常喜欢我。某次父亲来接我,他嘱咐父亲:“别因为他看书训斥他!”平时对我很严厉让我畏惧的父亲低头回答:“嗯。”像一个乖孩子,比我在他面前都听话。
父亲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哥哥们心疼他,不让他干活,只让他读书,在劳作着的哥哥们面前,他摇头晃脑地尤其读得起劲儿。到他晚年时,哥哥们早都去世了,我想他一定怀念他们,但是他从来不说,只有一次,他叹气说了一句:“唉!我十五岁了锄镰未入手……”
我觉得,祖父的一生真的是很成功,在他的治理下,我们的家族达到了旧时家庭的理想标准:耕读传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我又觉得,传统教育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的是系统、完整、有层次的教育目标。“格物致知”可视为智育,“诚意正心”是德育,这是教育的过程,是内在的;“修齐治平”,是教育的结果或目标,是外在的。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由低到高,升幂排列。前半部分是学,后半部分是用。就普通人而言,最高的目标就是修身齐家,而这个目标,我的祖父是达成了。
父亲就是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身上也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家庭教育的烙印。
父亲旧学的功底是很扎实的。
小时候听他读唐诗,就是 “吟诵”吧?调子很好听。有读起来轻松,有兴趣,方便记忆之功效。我就想,今天一味否定“唱读”,是不是也值得商榷呢?为此,我曾经以《朗读、诵读与唱读》为题,写过一文,发表在2003年第4期《阅读与写作》上。我的长子也是中学语文教师,曾问我吟诵的事,我就用从父亲那里学來的调子吟诵给他听,他学会了又读给学生,学生都很有兴趣。父亲无意间的举动,竟惠及两代人。
有一次父亲背《诗经》,我问他,你都能背下来?他抬头看看我,好像很奇怪我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然后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啊,我们那时候,四书五经都得背下来。”十几岁的孩子,能背四书五经,这教育成果,不能算差吧?
1942年,19岁的父亲开始教私塾,直到1948年,他从一个私塾先生,变成了一个“人民教师”。
父亲一生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且主要活动在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正是乡村教育事业最简陋的时候。从教以后,他先后辗转于烧锅营子、贺杖子、马架子、山嘴儿等自然村的教学点,且教的都是复式班,甚至很多时都是四级复式。学生虽然不算太多,但工作却十分繁重。因为需要一个老师在一节课中给三四个年级上课。
小时夜梦中醒来,总看见父亲还在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他的教案,板书,作业的批语,都是工工整整的楷书,没有一笔潦草。我参加教育工作后,虽然也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自问还是认真的,这多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除了在烧锅营子教学点把家搬去以外,其他的教学点离家都很远,父亲要住在学校,自己做饭吃。在贺杖子村教学时,离家最远,大约有五六十里山路,交通不便,只能徒步行走,回趟家要走五个多小时。父亲最多一个月回家一次,星期六贪黑回来,星期日起早就返校,不管天气好坏。
我母亲很聪慧,但她不曾有读书的机会。她很喜欢文艺,爱看戏、看驴皮影、听大鼓书,但是这机会实在太少,于是,就渴望我们给她读小说。我上学后不久,大概是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就可以给她读小说了。某次我给她读一本雕版印刷的旧通俗小说,读到一个词“然也”,父亲问我:“然也”是什么意思?我一愣,因为读时根本没想。于是看上文,回答父亲说就是“是啊”的意思。父亲高兴得哈哈大笑(他是极少这样笑的)。
我读书时没有注意“然也”的意思,母亲听书时自然也不会注意,“然也”如此,还有一些词大概也如此。但是她还是要听,看来书的主要意思她是听懂了的。这似乎说明,不论是听和读,都是以句为单位,而不是以词为单位,一个句子中一两个词不明白,一般不会影响对句子意思的理解。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把词语解释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是否就值得讨论了?
父亲和我都喜欢默读,不愿朗读给母亲听,实在躲不过去才给母亲读一会儿。母亲有时就生气,骂我们是哑巴。后来,我参军、工作,不常在母亲身边了;再后来,母亲的耳朵聋了;再后来,母亲去世了。我想读,读给谁听呢?
因为我语文好,于是父亲便以为他这个儿子是天才,一年级后,让我跳级读三年。他忽略了,虽然我语文不错,但数学是弱项,更何况隔了一个年级,数学怎么可能听得懂?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我又被打回原地,继续读二年级。
从烧锅营子搬回老家,我的一个本家哥哥会拉二胡,这引起了我对音乐的极大兴趣。我也学着拉二胡吹笛子,到处抄歌曲,跟着二胡笛子唱简谱,只是不知道自己唱得对不对。那年,父亲订了《吉林教育》,有一期封三有一首歌曲,父亲说,你整天呵呵咧咧地唱,把这首歌给我排排我听听(我们这里把识简谱称为“排歌”)。我就唱了一句谱子,他大为惊奇:“嗯?唱得还挺准?”于是我才知道,我于不知不觉间能识简谱了。
父亲离休前,我们曾是同事,我在村校,他在教学点。有一次教研活动,听我的课,是作文指导。我那时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教学,只是本能地感到语文的读和写应该结合起来。于是,在学完《松树的风格》后,我让学生把课文中描写松树的部分选出来,重新组织整合,以“松树”为题写一篇说明文。这一课我自我感觉不错,评课时老师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唯独父亲没有表扬,而是提了一些不足。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父亲一生老实忠厚,谦虚谨慎,不图名利,与世无争。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他人的事。这一点,为所有接触他了解他的人所称道。
父亲晚年也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过程度不算重,只是话少,记忆力衰退,出去散步,经常迷路而不能回家。可有时,他却又表现得很明白。即使疾病侵蚀了父亲的智力,但在他身上有两件事没有发生变化:一是读书,二是对儿孙们的喜爱。
父亲爱书。1947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父亲参加了担架队,曾住在一家大地主家,主人都跑了,屋子里散乱地堆着许多没有带走的书,他就挑了一些背在身上,随着部队辗转各地。这一背就是大半年,直到1948年战争结束。这些书,我看到的,有《字汇》十二卷,《左传句解》四卷,还有什么,我记不得了。现在,想象父亲背着沉重的书,在枪声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抬伤员的身影,就想,这对书得爱到什么程度,才会做到这样?
父亲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之外,所剩无几。这“所剩”大概都被他买书了。这样做的坏处,是家里没有积蓄,到处都是书;好处,则是让我在书堆中长大。“文革”使我在小学毕业后失去了读中学的机会,但是,那些书,却让我成了教师,考上了函大,还能够发表文章。这证明,存书,比存钱强。
父亲一辈子都在读书。他读书,是纯粹地读书,没有功利目的,不为结果,只为过程。即使他已經记不得所读的内容了,他仍然读书;即使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了,逝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还在读书。书,陪伴了他一生。这使我对读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读书这事,不仅属于语文,更是属于生命。
大概是人的年龄愈大,就愈重亲情,晚辈们来看他,他虽然多已叫不出名字,但脸上总是堆满发自内心的笑容,对第三代、第四代尤其如此。2015年中考结束,我接了哥哥的孙子来家里住了几天,父亲高兴至极,生命涌现出了几年来未曾有过的活力,竟然指导这个大孙子读起了《三字经》。我妹妹的孙子、我的两个孙子回家,父亲也都极为开心,甚至会流下激动的泪水。
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从今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读书的背影;再也看不到他看见儿孙时的笑容了。父亲是个普通教师,做的只是普通的事。但是,普通人才是社会的主体,普通人做好普通的事,是一个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所以,我感恩、怀念我的父亲,愿他身下的大地,永安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