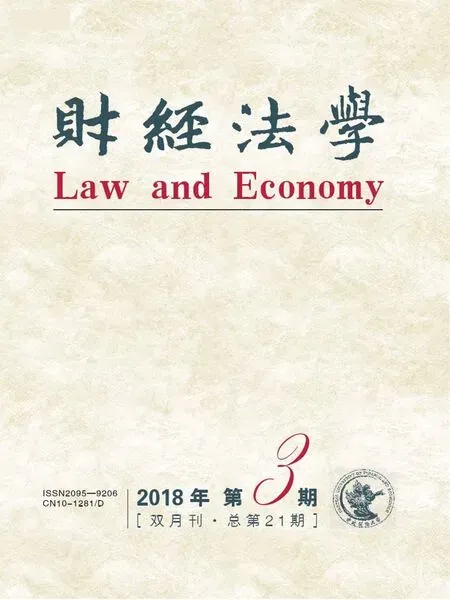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制定
翁武耀
一、引言
从财政收入来源的角度审视现代国家,都符合税收国家的一般特征。[注]2017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和为236 60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44 360亿元,比重为61%。参见财政部国库司:《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mofhome/guokusi/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801/t20180125_280011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8日。税收对于一国取得充足财政收入以提供良好公共服务至关重要,公民纳税义务也因此往往属于一国的宪法性义务,我国亦不例外。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同时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还分别就财产权、平等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保护进行了规定。这表明,从纳税人义务和权利平衡的角度,国家对纳税人的课税并非一项绝对的权力,国家在行使课税权时还必须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纳税人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宪法的修改,我国虽然先后经历“1984年税改”“1994年税改”和“2004年税改”,[注]参见张守文:“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86页。但不管是从税法制定的形式方面,还是从税法内容的实质方面,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总体上都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尽管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首次规定私有财产权并予以保护以及保障基本人权,对“2004年税改”以及之后的税收立法、税法修改及解释等国家课税权行使时更多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违宪审查在实践中的缺失,宪法条文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力,以致国家在行使课税权行使时不注重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依然存在与纳税人权利保护不足相关的诸多有违税收正义的问题。例如,过于偏重国库主义,纳税人税负沉重,税法稳定性缺失,课税公平价值牺牲过度,政府课税权过大,人大税收立法介入不足以及税收司法过于谦抑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财税领域首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大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注]参见施正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完善税收制度”,《国际税收》2014年第3期,第21页。由此,我国在进入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同时,纳税人权利保护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并将贯彻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之中。这是因为税收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税改还需要特别满足民主政治、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非经济工具方面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无疑与纳税人权利保护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2016年年底《环境保护税法》的制定,2017年年底《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的制定,正在热议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方案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为主要导向,[注]参见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及征管条件研究课题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及征管条件研究”,《税务研究》2017年第2期,第38页;张平、侯一麟:“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第118页。以及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或完善纳税人税法制定(修改)参与权、事先裁定权、延期(分期)纳税权等程序性权利,[注]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载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01/2015010039793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1月6日。反映出纳税人权利保护在税收法制改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一种进步目前还仅仅体现在量上,并没有反映纳税人权利保护质的变化。因为这种税收立法上的进步,更多地源于立法者对中央或上级部门决议或政策的执行,而非源于对税收立法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法律的遵循,因此进步不仅有限而且不稳定。实际上,目前我国还仅仅在《立法法》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本身还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的问题)来约束、规范税收立法、执法等涉税活动,对于促进纳税人权利保护质的进步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新时期纳税人权利保护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尤其是“依法治国”成为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理政思路,有必要论证这样一项重要议题:我国是否遵循目前国际上对纳税人权利保护进行专门立法的发展趋势,即在包括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各种纳税人权利宪章、宣言或法案的颁布层出不穷。为此,本文将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制定怎样模式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以及该法应当规定哪些重要内容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二、税法体制中的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与挑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在1980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税收法定原则得到了初步贯彻,不过,此时尚属于对纳税人权利的不自觉保护。[注]参见方赛迎:“改革开放30年我国税法建设的回顾和展望——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视角”,《税务研究》2009年第1期,第68页。这种情况随着1992年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制定发生了改变,该法第一条立法宗旨首次明确规定“……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该法规定了诸多纳税人权利。例如,征税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实施课税活动以及检举权、申请减免税权、复议和诉讼权、代理权等。[注]参见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此后,2001年第一次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新增和完善了诸多纳税人权利,例如,第七条新增税的知悉权,尤其是在第八条集中规定了一批纳税人权利,新增保密权和陈述申辩权等。在税收实体法层面,纳税人权利保护亦有重要的成果,例如,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明确以纳税人平等权为改革指导思想,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法。尽管如此,我国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并将面临新的挑战。
(一)税法形式内容上的问题与法律确定性的不足
此处税法形式内容上的问题主要涉及税法制定、解释等权力的行使以及由此形成的税收法源体系和规则本身的问题,不涉及税法具体的实质内容。
1.税收法源位阶不高、政府立法权过大
税收实体法目前仅有个人所得税法等六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他12项税种的基本规则都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且大部分都是基于全国人大的空白授权。同时,这些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操作性不强,这是因为这些法规“大多是抽象宽松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必要的定义性条款,且常常运用‘有必要’‘有理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注]刘剑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现实路径”,《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19页。例如,《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对何谓工资、薪金等所得类别,《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对何谓货物都未做规定。为此,这些法规又授权给国务院或财税主管部门进行立法解释制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如《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此外,我国在实施税制改革试点时,颁布的税收法源也没有法律或全国人大授权的基础,例如,2011年开始的“房产税”试点和“营改增”试点,前者仅仅基于国务院的会议精神,上海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府通过发布政府规章就决定实施,[注]参见《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后者仅仅基于国务院的同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发布通知就实施。[注]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
2.税收立法赋予政府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政府在课税权行使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不过我国现有税收立法在许多方面赋予了政府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将税率的调整权赋予国务院,本身具有合理之处,为应对成品油价格的波动,国务院以环保目的对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进行及时调整,有助于政府实施相关的调控职能。[注]参见翁武耀:“再论税收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落实——基于意大利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的研究”,《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第131页。不过,《消费税暂行条例》对于国务院调整税率的权力没有规定约束条件,诸如调整参考的客观标准、幅度或最高限值,这使得政府这种规则修正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限制。又如,与我国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存在大量课税不明问题相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据此颁布了大量的税收通告,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以具体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这使得我国财税主管部门在税法行政解释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注]参见前注〔8〕,刘剑文文,第19页。再如,我国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还赋予基层税务机关在执法时的大量自由裁量权,[注]参见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155页。表现在课税权力行使方式的可选择性、行使时限的不确定性、行使标准的难认定性等方面。[注]参见李占通:“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不应‘太自由’”,载《人民政协报》2016年4月18日(005版)。
3.税法碎片化、缺乏稳定性
我国没有统一的税法典,也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收通则法),欠缺对税法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和综合问题进行体系性的规定,[注]参见施正文:“中国税法通则立法的问题与构想”,《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第155页。而有关具体税种的税收实体法内容散见于各税种法中,尤其是在实践中发挥主要作用、数量庞大的税收通告。目前,我国税收规范性文件主要由约30部税收行政法规、约50部税收行政规章、超过5 500部税收通告所组成,[注]参见前注〔8〕,刘剑文文,第18页。税法碎片化问题较严重。以2016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为例,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就有近80份,涉及综合规定、行业规定(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征收管理、纳税服务、发票管理、委托代征和其他规定。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税法以外的法律法规范税的内容的情形,尤其是修改税法中的相关内容,容易导致同位阶法源之间涉税内容的不协调,而这也加深了税法的碎片化程度。例如,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慈善法》与原《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不同规定。[注]即《慈善法》规定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所幸,为与《慈善法》保持一致,2017年2月24日《企业所得税法》做出了相应修改。此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变革之中,相应的税制改革或税法修订也在持续进行,为此,税法相关原则、制度、规则、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可以认为我国税法体制尚未定型,税法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税法存在大量溯及既往适用的现象,例如,规范性文件的生效时间早于该文件的发布时间、将发生在规范性文件生效时间之前的行为适用新规定等。[注]参见翟继光:“论税法中的溯及既往原则”,《税务研究》2010年第2期,第69页。税法溯及既往适用进一步损害了税法的稳定性。
4.税法规则的不清晰和不明确
我国税法规则在许多方面存在不清晰、不明确的问题,不利于纳税人完整、准确认识自身行为的纳税义务:(1)相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条文数量过少、篇幅过小。例如,《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只有15条,2 500字左右,《增值税暂行条例》目前只有29条,5 500字左右。再如,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纳税人享有延期申报的权利,但有关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未有相应规定,[注]参见刘蓉、杜剑:“纳税人权利保护与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税务研究》2007年第2期,第53页。使得该权利缺乏操作性。本应对《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纳税人权利进行更为详尽化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几乎未做任何规定。[注]参见许多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有效路径——建立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第59页。(2)在税法内部结构上,条文数量少的税法,例如《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没有章、节的划分。而对于条文数量较多的税法,例如《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税收征收管理法》,虽然有章、节的划分,章、节有标题指出本章或本节的规范对象,但与条文数量少的税法一样,条文都没有标题以指出规范对象。(3)在使用参见其他税收条款的立法技术时,通常仅仅指出该条款的一些识别要点(所在税法的名称、编号等),而未引述该条款文本内容。例如国家税务总局《网络发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5.拟制性规范大量使用
我国在税法解释上价值取向偏向国库主义,以下以拟制性规范为例予以说明。拟制是指法律规定将不同的两项行为等同处理,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例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以及作为投资、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无偿赠送他人视同销售行为。事实上,拟制性规范在我国税法解释中被大量使用,不仅在实体法中,也在程序法中,同时,不仅存在于立法解释中,也存在于行政解释中。虽然拟制性规范可以扩大纳税人、税基等课税要件的范围、填补税法漏洞以及便利税务征管,进而提高税收收入,但是大量使用拟制性规范并不利于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注]参见叶金育:“回归法律之治:税法拟制性规范研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21页。因为拟制性规范涉及应税行为的基本内容,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应当在税收法律中进行规定,而不应由政府及其征税部门“任意”来规定。此外,事实上,拟制性规范绝对地将不同的两项行为等同处理,在可能确保量能课税(私法上不同的行为可能体现相同的捐税能力)的同时,也可能背离实质公平,因为其不允许纳税人就特殊情况提出反证以推翻拟制性规范的适用。这也反映了我国税法在实质公平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对此,下文也将具体阐述。
以上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前面两个方面以及第五个方面主要反映了政府在税法规则制定和解释方面拥有不受有效限制的权力,严重损害了课税民主性。余下两个方面则主要反映了税法体系、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这导致纳税人在寻求、认识可适用性的税法规则方面的困难。为此,问题又进一步体现为纳税人法律确定性利益的损害,即作为税法应用的相对人,纳税人对自身事实或行为的税收法律后果很难准确预见,或者说,纳税人对自身权利是否应当得到应用很难预见。[注]在这方面,意大利学者有着专门论证。Cfr.Gianmarco Gometz,La certezza giuridica come prevedibilità,Giappichelli,2005。而法律确定性是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在于税收法定原则应用下所塑造的税收体制中。[注]Cfr.Vacca Ivan,Abuso del diritto ed elusione fiscale,in Rivista di diritto tributario,2008 fasc. 12,pt.1,p.1071.当然,下文将论述的两大方面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对法律确定性利益的损害,只是这里更为集中罢了。
(二)税法实质内容上的问题与课税公平性的不足
除了在税法形式内容上,我国在税法实质内容上也存在诸多问题,而相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上述税法形式内容上的问题。
1.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
根据现有税收实体法,我国目前税制结构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以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情况为例,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项主要的间接税收入就占全部税收收入总额的57.2%,而个人所得税仅占8.3%。[注]参见财政部国库司:“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载http://www.mof.gov.cn/mofhome/guokusi/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801/t20180125_280011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8日。此外,我国尚未对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也没有开征遗产税。这样的税制结构,虽然在保障税收收入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公平税制方面却体现出巨大的不足。这是因为直接税以所得、财产等直接体现捐税能力的因素为征税客体,直接税能更好地体现征税的个体化,同时也适合采取累进征税,可以更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而间接税更容易导致征税的客观化,忽略纳税人的不同情形,同时也不适合采取累进征税,无法对贫富差距进行有效调节。
2.个人所得税再分配功能缺失与增值税纳税人税负偏重
以下以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例,说明我国税种法对纳税人权利规范存在的不足:(1)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再分配功能方面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首先,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制,虽然有助于征税效率,但无法按照纳税人的真实捐税能力进行征税。其次,在费用扣除上没有考虑纳税人家庭情况(例如赡养、抚养情况以及医疗、教育等情形),而是一律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扣除,无法体现个体化征税,这也体现为纳税人扣除权的不完善。再次,税率结构不合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所得等积极所得虽然都适用累进税率,但税率各不相同,税负也不同。而利息、股息、租赁所得等消极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负通常情况下却低于积极所得。[注]参见施正文:“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第33页。最后,高收入者消极所得的逃避税问题严重。(2)增值税作为对消费的课税,通常由消费者承担,不过在现有《增值税暂行条例》以及“营改增”实施办法下,作为纳税人的经营者也在承担增值税且税负偏重,而这与纳税人抵扣权立法不完善有着紧密关联。首先,我国增值税法尚未引入“抵扣权”的概念,未明确从权利的角度对增值税的抵扣制度进行规范。[注]参见翁武耀:“论增值税抵扣权的产生”,《税务研究》2014年第12期,第54页。其次,未对抵扣权何时产生进行规定,[注]按照欧盟增值税法的规定,抵扣权应当在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缴纳义务产生的时刻产生。参见 Article 167 of EU 2006 VAT Directive。也未明确规定抵扣权实施应具有立即性、完整性和全面性的特征。[注]立即性指纳税人无需等到购买的货物或服务被实际使用的时候才行使抵扣权;完整性指可抵扣的税款应当是在购买货物或服务时所承担的所有的税款;全面性指抵扣权的行使应面向纳税人开展的所有活动或与之相关联,并不是仅仅针对某项(特定)直接的交易。参见翁武耀:“论增值税抵扣权的范围”,《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59~60页。最后,未赋予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发票下的抵扣权,同时就剩余可抵扣进项税,未赋予纳税人退税权,并未以法律特别规定的方式赋予纳税人选择与其他特定税收债务抵销的权利。[注]参见翁武耀:“论增值税抵扣权的行使——基于中欧增值税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2015年第5期,第114页。
3.税收征管法中的纳税人权利立法不完善
我国现有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1)尚未规定的权利。例如公平对待权,公平对待权要求税务机关对所有纳税人一视同仁,在课税时依据法律仅根据纳税人的负税能力进行相同或不同的对待。再如事前裁定权,根据该权利,纳税人为了获知一项税收规则的正确解释并且在具体案件中的相关适用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请求给予相关意见,纳税人得以事前知晓税务机关的判断以及避免事后的一些不利结果。[注]参见翁武耀:《欧盟增值税反避税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页。(2)需要修订的权利。例如申请减免税的权利,事实上合法节税效果不仅可以通过享受税收优惠而取得,还可以通过利用税制或税收规则差异等方式来取得,因此需要修订为合法节税权。[注]参见翁武耀:“避税概念的法律分析”,《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804页。这与我国当前片面强调反避税而忽视对反避税权力的限制有关,事实上反避税权力不受有效制约,纳税人法律确定性、经营自由等利益亦将受到损害。再如司法救济权,目前税收征管法规定了两个前置,即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非常不利于纳税人司法救济权的实现。(3)有必要提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及其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推定课税规则,即有关纳税人在未设置账簿等情形下的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权力。在核实课征难以实行的情况下,推定课税无疑可以提高征收效率,防范税收流失,但是由于现行规定过于简单、适用条件也不合理并且缺乏正当程序制约,[注]参见刘继虎:“论推定课税的法律规制”,《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54~57页。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容易滥用推定课税权,从而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不稳定性,更对公平课税造成损害。[注]参见王惠:“推定课税权制度探讨”,《法学家》2004年第3期,第118页。
以上三个方面税法实质内容上的问题,反映了我国税法的制定对国库主义的强调以及过于偏重效率价值,而这又十分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首先,总体而言,税法体制没有很好地体现公平价值,税法重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无法得以实现,同时纳税人享受公平课税的基本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导致税负分摊不公。其次,纳税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的具体权利存在的诸多不完善与课税公平性的不足紧密相关,这也使得纳税人在面对税务机关课税权力时处于弱势地位。
(三)主要建立在管理理念基础上的征纳关系
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来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形成的征纳关系在理念上经过由税务机关的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在管理理念下,征税关系表现为管理与被管理以及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从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税务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课税实现主要通过税务机关的行政命令和处分,纳税人只是被动地予以服从。显然,在这样的征纳关系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地位并不平等,税务机关通常追求课税的更大权力,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则主要依赖税务机关的执法强度和处罚的严厉性。[注]参见刘剑文:“税收征管制度的一般经验与中国问题——兼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32页。在服务理念下,征税关系表现为服务与被服务以及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协作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不存在由谁主导的问题,课税实现主要通过双方的协作,税务机关除发布行政命令和处分外,更需要提供纳税服务。显然,在这样的征纳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地位平等,纳税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也使得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主要源自纳税人与税务机关间的相互信赖和协作以及纳税人作为税收治理共同体主体地位的认同。
我国目前税务征纳关系仍主要建立在管理理念基础上,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征纳理念,也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符合:(1)规范税收征纳关系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制定时,以“管理”来命名该法,之后经过1995年和2001年两次修订,该法名称保持不变。即使在目前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中,2015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依然未对法律名称进行修改。从税收征管法的名称就可以发现我国在征纳关系中的管理理念,也可以认为这是管理理念的法律依据所在。[注]事实上,我国税收征管法名称完全可以参考法国《税收程序法》、日本《国税征收法》、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等进行修改,去掉“管理”两字。(2)管理理念不仅体现为税法赋予政府及其征税部门更大的课税权,也体现为纳税人相关权利的不足。前者前文已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但关于后者,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管理理念,现有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诚实推定权的缺失,该权利推定纳税人在实施税务活动时是诚实的,征税机关在没有调查、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质疑纳税人的纳税情况是否合法并进而采取相应行为。[注]参见刘剑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的几个基本问题——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中心”,《法学》2015年第6期,第9页。而在管理理念下,纳税人被假定是“性本恶”的。在这样一种理念和诚实推定权缺失下,纳税人善意以及信赖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又如,修正申报权的缺失,该权利允许纳税人在申报期以后还可以对自己申报的错误内容进行修正。该权利正是基于纳税人诚实纳税、申报的推定,并旨在保护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的信赖。再如,税务争议和解、调解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未明确规定,而和解和调解制度强调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地位平等,强调兼顾双方的各自利益以达成折中结果。(3)管理理念还体现在税务机关征税的实践中,而这主要表现为税务机关不按税法进行征税。例如,“为了服务于招商引资或稽征便利等目的,税法的一些规定在现实中被任意地打折扣、搞变通。”[注]前注〔8〕,刘剑文文,第19页。与此相关,在税收优惠上,我国存在“区域优惠政策内容过滥、形式过多、种类过杂、‘政出多门’等混乱局面”。[注]熊伟:“法治视野下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研究”,《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154页。同时,地方擅自取消或终止税收优惠政策的现象又时而发生。又如,基于国库利益,我国税收征管长期实行层层下达税收任务的模式,即长期存在按指标征税,而指标完成的多少也成为衡量各级税务机关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这样,必带来对纳税人征“过头税”的问题。[注]参见许多奇:“论税法量能平等负担原则”,《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第74页。事实上,税务机关以这种方式进行课税,体现了其在课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而“纳税人可能大多处在‘半守法’的状态,他们并不是按照法律要求纳税,而是依据地方税务征管人员的要求纳税。”[注]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155页。
(四)挑战:税制复杂化与纳税人义务、负担加重
考虑到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除面临上述三大方面的问题,自然人纳税人权利保护还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也使得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将更为严峻。相关的挑战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税制将变得更为复杂。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为方向,并将废除费用“一刀切”扣除而实行差别扣除,辅之以家庭申报和年申报制度。与现有分类所得税制相比,上述改革内容将使个人所得税制变得更为复杂,增加纳税人的遵从成本。这主要体现在纳税人需要完整、准确掌握更多不同且更为复杂的技术性税收规则,尤其在费用扣除方面。而差别化费用扣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纳税人需要保存并向税务机关提交抚养、赡养、房贷利息等扣除的证据。[注]参见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及征管条件研究课题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及征管条件研究”,《税务研究》2017年第2期,第44页。(2)纳税人协力义务和负担将加重。与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立法相对应,根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当前税收征管法修订的一大内容便是加强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为此,自然人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将变得越发繁重,例如,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将被明确,纳税人依法自行计算确定自己的纳税义务和自行申报,并对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同时,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税务检查、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也将覆盖自然人。而为完善涉税信息情报制度,包括纳税主体与非纳税主体在内的广泛主体将承担作为第三方向税务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注]参见滕祥志:“论《税收征管法》的修改”,《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96~97页。此外,我国政府已承诺将于2018年9月实施经合组织(OECD)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即根据《统一报告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对居民实施全球征税并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注]参见刘天永:“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交换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税务报》2017年3月21日(7版)。这样,纳税人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三、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视域下的专门立法
(一)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为论证如何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尤其是为何需要以及如何制定专门立法,有必要先阐明造成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现有问题的主要原因。简单而言,在过于偏重国库主义以及税收宏观调控功能背景下的政府及其征税部门“任意”“专断”的课税权,换言之,政府及其征税部门的税收立法、执法以及税法解释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当然,这背后与我国长期信奉政府“万能”“高效”等观念、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以及将GDP与税收增长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有着紧密关联,归根到底,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足。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尽管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政府及其征税部门的课税权缘何在法律制度层面缺乏有效的制约。对此,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人大介入的缺失。虽然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但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拥有宪法解释和实施监督的权力。不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至今未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做出违宪而撤销的决定,尽管违宪的规范性文件事实上并不少见。[注]参见丁一:《纳税人权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2)司法介入的不足,尽管对于政府课税权的制约,司法本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注]相关原因,参见前注〔40〕,崔威文,第135~155页。例如,税务专业审判人员与机构的缺乏,法院对税收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排除。关于后者,虽然根据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可以附带审理一部分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规章除外),但只能就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不涉及合理性问题,且不能直接裁决废止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只能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3)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本身的不完善,这也是下文将重点阐释的内容。
关于第三方面的原因,有必要先明确纳税人权利的范围。由于我国税收法律长期以来局限于在税收征管领域来理解和界定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被严重狭隘化了,[注]参见王玮:“纳税人权利与我国税收遵从度的提升”,《税务研究》2008年第4期,第74页。这就造成了我国相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的严重滞后。事实上,纳税人权利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位性法律权利,即由宪法、超国家法律(例如国际条约)、法律(指税收程序法以外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第二位性法律权利,即由税收程序法所保护的权利;第一位性行政权利,即由条例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所保护的权利;第二位性行政权利,即由征税部门发布的指南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所保护的权利。[注]See Duncan Bentley,Taxpayers’ Rights:Theory,Origin and Implement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7,pp.112~136.与这四类纳税人权利范围相对应,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也需要从这四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不过,我国在纳税人第一位性法律权利的立法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能有效制约税收立法、税法解释等活动的也主要是这一类立法。这类立法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大、司法介入的缺失,换言之,人大违宪审查或法院合法性审查客观上需要更多、更明确的有利于纳税人的宪法和法律(条款)依据。那么,这类立法到底存在怎样的不足?对此,需要从我国的宪法谈起。
1.宪法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的缺乏
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纳税人在课税的过程中亦享有,但是缺乏对纳税人课税同意权和课税公平权这两项基本权利的原则性规定。具体而言,我国《宪法》目前仅在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涉税条款,缺乏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代表税收公平原则)这两项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在宪法上未规定纳税人基本权利使得宣示性的效力都无从谈起,这对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纳税人权利保护需要建立在宪法保护的基础上,尤其表现为宪法性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确定,这构成了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赖以发展的基石,这也是西方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经验。例如,德国现有宪法第十四条规定了财产权限制的法定原则,[注]See art.14(1)(3),sec.1 of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45.而德国宪法法院依据宪法平等原则和社会国原则,在税法领域中解释出了宪法性的量能课税原则。[注]Cfr.Bieter Birk,Diritto tributario tedesco,Traduzione a cura di Enrico De Mita,Giuffre Editore,2006,pp.12~13 e pp.48~49.再如,意大利现有宪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五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税收等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注]Cfr.art.23 and art.53 della Costituzion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1947.关于意大利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详见前注〔11〕,翁武耀文,第121~129页;关于意大利量能课税原则,详见翁武耀:“量能课税原则与我国新一轮税收法制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89~101页。
2.法律对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具体化规定的不足
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在执行中相关具体内容的违背,这与法律对这两项原则的具体化规定不足有着紧密关联。
首先,关于税收法定原则,需要先明确一点:税收法律保留具有相对性,只有税收定性规则(涉及纳税主体、课税客体、与纳税义务产生相关的时间内容和与纳税义务产生相关的空间内容)才需要在法律中规定,税收定量规则(涉及税基和税率)以及税收优惠规则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以在非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这样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例如人大授权立法下)也可以行使税收规则制定权。[注]参见前注〔11〕,翁武耀文,第130~132页。因此,虽然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修订后进一步规定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需要制定法律,但是该条不仅在有关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化规定(涉及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应用)方面存在不足,内容本身还需要修订。与第一部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第一大方面的问题以及将面临的挑战相对应,在法律中尚缺乏的税收法定原则具体化规则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课税应当根据法律实施;(2)政府税收规则制定权需要受到严格限制;(3)税法规则应当清晰、明确和可获知性。
其次,关于量能课税原则,需要先明确两点:其一,基于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理论,在经济方面,所有人需要为国家获得必需品做出贡献,其中,很大一方面就体现在为国家的公共费用筹集资金,因此可以认为量能课税原则是公民社会连带责任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化。[注]Cfr.Luigi Ferlazzo Natoli, Fattispecie tributaria e capacità contributiva,Milano-Dott.A. Giuffere Editore-1979,p.49.其二,在现代社会,为实现实质公平,体现为经济能力的负税能力构成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摊税负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量能课税原则是公平原则在税法领域的具体化。不同于税收法定原则,我国目前不仅在宪法中没有规定量能课税原则,也没有在任何一部法律中规定该项原则。至于在法律中尚缺乏的量能课税原则具体化规定,与第一部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第二大方面的问题以及将面临的挑战相对应,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构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且税制整体符合累进标准;(2)个人和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不得课税;(3)原则上根据纳税人真实的捐税能力课税(这有助于限制拟制性规范和推定课税的使用);(4)税收优惠在必要的范围和特定的条件下使用,不得过度;(5)引入针对所有税种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同时限制反避税权力的使用。
3.法律对一般法律原则在税收领域应用规定的缺乏
税法是我国法律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体制中的诸多一般法律原则可以也应当应用于税法。不过,相关一般法律原则在税法中的应用在我国目前并不尽人意,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即反映了相关一般法律原则的未遵守,而这主要源于这些一般法律原则在税收领域仅仅是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将这些一般法律原则在税收领域成文法化无疑更能有效发挥其对税收立法等税收活动的约束力。那么,哪些一般法律原则应当但尚未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对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原则:(1)法律确定性原则。我国三大方面的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都体现出对该原则的背离,同时,纳税人权利保护将面临的挑战也反映出遵守该原则的必要性。因此,在肯定法律确定性原则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该原则的落实与前述税收法定原则、量能课税原则以及其他一般法律原则的落实存在紧密关联。总之,法律确定性是实证主义法律传统所创制的一项基本保护(制度),“在税收领域,在征税要求实现的每一个阶段,从纳税义务产生到完全实现,法律确定性都为纳税人保护构筑了屏障”。[注]P.Pistone,Abuso del diritto ed elusione fiscale,Padova,1995,p.276.(2)法律溯及既往禁止原则。除源于法律确定性原则外,该原则在税法领域还特别源于量能课税原则以及征税部门课税诚实信用的要求。当然,作为例外情况的税法溯及既往的情况也需要深入研究并规定。(3)诚信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原则早已跳出私法、行政法的应用范围,征税部门诚信要求与纳税人信赖保护有助于税法确定性原则的落实,同时有助于促进新型征纳关系(以向纳税人服务为主旨)的构建以及税法从干预行政法到协同合作法的转变。[注]关于税法从干预行政法到协同合作法的转变,参见葛克昌:“税法本质特色与税捐权利救济”,《人大法律评论》2016年卷第2辑,第87页。(4)权利滥用禁止原则。该原则源自私法,强调权利的非绝对性,权利需要在特定的范围和条件下行使。税法中的权利滥用即指纳税人以扭曲或不正常的方式行使扣除权、抵扣权等纳税人权利,从而获得一项不正当或有违税法目的的税收利益,构成所谓的避税行为。[注]参见前注〔31〕,翁武耀文,第803页。为此,可以以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构建反避税规则。
(二)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及其定位
相比于前两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集中于税法本身以及可行性及其难易程度的角度,无疑需要着力解决第三项的原因。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的完善亦可以倒逼人大、司法介入(以限制政府的课税权)。据此,我国应当如何来完善纳税人权利立法?以下将围绕专门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
1.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完善与专门立法
总体而言,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需要从三个层面来完善,除上述已分析的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这两项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规则和相关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在税种法和税收程序法中引入或完善扣除权、抵扣权、事前裁定权、救济权等具体权利。不过,为从更深层次、全面解决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和挑战以及追求全方面约束课税权力实施的效力,显然更需要从前面两个层面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进行完善,而不是在第三个层面如同打补丁般地进行具体权利的完善。换言之,我国当前更需要为纳税人提供全新、升级的用于抵御课税权侵犯的屏障。事实上,前面两个层面立法的完善是第三个层面立法完善的基础,没有前面两个层面立法的完善,第三个层面立法完善将难以尽善尽美。至于前面两个层面,考虑到涉及宪法修改,应当说第一个层面立法的完善难度要更大一些,同时,即使第一个层面的立法完善无法实施,如果第二个层面立法得以完善,亦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第一个层面立法的不完善。因此,我国当前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的完善需要着重关注第二个层面。
那么,我国应当如何在第二个层面实施立法的完善?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即修订现有的税收征管法、制定税收基本法和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不过,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第一条路径,原因也显而易见:(1)从理论上而言,税收征管法并不规范纳税人第一位性的法律权利。(2)作为程序法,税收征管法并不能有效约束税收立法活动,尤其是在实体税法层面。虽然现有税收征管法也亦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行了规定,但这并不意味这项基本原则的全部应用的内容都可以或应当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应当仅在程序层面重申、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注]参见前注〔36〕,刘剑文文,第8页。(3)即使在程序法层面,税收征管法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应用的具体规则以及一些一般法律原则,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税种征管,因为税收征管法并不适用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非税务机关征收的税种。[注]参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条。(4)我国目前税法存在的碎片化和缺乏稳定性的问题,特别需要通过税法法典化来解决,而制定税收通则法或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不仅有助于解决税法碎片化和缺乏稳定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税法法典化的关键一步。
关于后两条路径,应当认为两者都可以完成第二个层面立法的完善,但我国采取后者可能是现阶段更为明智的选择,理由如下:(1)相比于对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税收基本法难度和复杂性无疑更大。(2)我国在十几年前曾将税收通则法提上立法议程,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呼吁和热议(亦有争议),[注]参见汤贡亮:“对制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9~13页;参见施正文、徐孟洲:“税法通则立法基本问题探讨”,《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第57~62页;参见涂龙力、涂京联:“税收基本法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兼与施正文、徐孟洲同志商榷”,《税务研究》2005年第8期,第56~58页。但最终搁浅,至今没有出台,同时学界关于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呼声现已渐弱。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主要也是旨在实现税收正义与纳税人权利保护,为此学界也应当更换一下路径,呼吁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定专门立法。此外,该专门立法亦可以部分发挥税收基本法的功能。(3)专门针对某类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实施立法,我国已经有先例,即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事实上,相比于单个消费者面对大企业,单个纳税人面对国家或征税部门,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毕竟国家和征税部门掌握了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权力,这样,更有必要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定专门立法。(4)正如下文将阐述的那样,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定专门立法,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做法,具有可借鉴的域外经验。
2.其他国家和地区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与经验借鉴
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专门宣示,法国最早在1975年颁布了《纳税人宪章》(Charte du Contribuable),加拿大和英国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颁布了《纳税人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axpayer Rights)和《纳税人宪章》(Taxpayer’s Charter)。美国则在1988年颁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Taxpayer Bill of Rights),后经多次修改,美国国会于2015年将该法案提出的纳税人10项权利编入了《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注]See IRC § 7803 (a) (3),available at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6.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1月20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合组织(OECD)在1990年发布了一项报告,建议成员国引入纳税人宪章。[注]See OECD,Taxpay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A survey of the legal situation in OECD countries,1990.随后,包括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一些非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部分地区相继颁布纳税人(权利)宪章或法案等,[注]参见潘雷驰:“纳税人权利对纳税服务边界影响的研究”,《税收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41页。并总体上发展出两种模式:一种是征税部门颁布的一项宣告,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宣告没有法律效力;另一种是规定在法律中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前者除了法国、英国以外,还包括澳大利亚1997年《纳税人宪章》(Taxpayer’s Charter)等,后者除了美国以外,还包括意大利2000年《纳税人权利宪章》(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注]Cfr.la legge 27 luglio 2000,n.212,recante lo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原文参见以下网址:https://www.cafitalia.eu/documenti/statuto_contribuente. pdf,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1日。、2005年墨西哥《联邦纳税人权利法》(Ley Federal de los Derechos del Contribuyente)[注]墨西哥《联邦纳税人权利法》原文参见以下网址:http://leyco.org/mex/fed/lfd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和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注]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原文参见以下网址: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1日。等。类似于美国税法典,还有一些国家税法典或税收基本法也专门规定了纳税人权利,例如,俄罗斯1998年《税法典》(Налоговый кодекс)第二十一条“纳税人权利”(Rights of Taxpayers)规定了纳税人15项权利,[注]参见Tax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罗斯《税法典》英文版本),available at following website: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ru/ru071en.pdf,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再如,西班牙2003年《税收一般法》(Ley General Tributaria)第三十四条“纳税人的权利和保障”(Derechos y garantías de los obligados tributarios)规定了20项权利。[注]西班牙《税收一般法》原文参见以下网址:http://noticias.juridicas.com/base_datos/Fiscal/l58-200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
综上,可以发现域外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呈现以下特点:英美法系国家更多地采取纳税人宪章的模式,主要通过征税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来宣示纳税人的权利,而大陆法系国家更多采取纳税人权利法案的模式,主要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既宣示纳税人的权利也以更有力的法律效力约束税收立法等税收活动。对此,需要明确以下几点:(1)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通常采取第一种模式,与这些国家宪治(有助于保护宪法上的纳税人基本权利)以及作为判例法国家司法审查、监督的发达有着紧密关联。(2)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通常采取第二种模式,主要因为这些国家是成文法国家,法典化程度高,包括在税法领域。同时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用权利概念作为核心表达工具、抽象推理演绎而成法典秩序”的传统,[注]冉昊:“两大法系法律实施系统比较——财产法律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60页。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是税法法典化的重要内容。(3)德国和法国作为最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代表,之所以没有制定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宪治也很发达,同时都已经制定税法典或税收基本法,对纳税人权利保护进行了完善的规定,例如德国1977年《税法典》(Abgabenordnung)[注]参见Fiscal Code of Germany(德国《税法典》英文版本),available at following website: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ao/englisch_ao.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1日。和法国1950年《税收总法典》(Code Général des Impts)[注]法国《税收总法典》原文参见以下网址: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69577&dateTexte=vig,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0月21日。。当然,俄罗斯《税法典》和西班牙《税收一般法》也可以归为这类。与此相对应,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尚未制定税法典或税收基本法。(4)从时间上来看,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产生相对较晚,因此可以认为第二种模式代表了当前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的国际发展趋势。基于上述四点经验,考虑到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法治发展的滞后以及税法法典化和税收基本法的缺失,不难得出我国应当采取第二种模式的结论,这也与前文基于我国国情的问题、原因、对策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由于下文将主要根据第二种模式的经验(分别是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具体论证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为便于理解,这里先就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和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基本内容予以说明。
首先,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意大利议会于2000年7月27日审议通过了第212号法律,即《纳税人权利宪章》,根据意大利学者考察,该宪章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为应对经济危机,意大利政府职能不断扩大,政府也频繁实施授权立法,尤其是在税收领域。意大利税收制度一方面逐步碎片化,即税收立法往往根据不同具体事项制定不同的具体规则,而法律应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使得税收立法逐步减弱。另一方面,税收规则不断溢出,税收规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化非常快,使得税收制度缺乏稳定性。[注]Cfr.Gianni Marongiu,Lo Statuto del contribuente e i vincoli al legislatore,atti di convegno di studi 2008-Lo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pp.10~11.此外,由于过度追求国库利益,纳税人在承担高税负的同时,由于税收程序在课税阶段主要依靠纳税人的积极合作(自我申报等协力义务履行),纳税人遵从成本也极大提高。[注]Cfr.Michele Rossi,Lo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 a dieci anni dalla sua entrata in vigore,in Innovazione e diritto,2010,n.7 (speciale),p.77.宪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一般原则”,主要规定宪章条款是为执行宪法上的相关条款而制定,并规定宪章条款构成意大利税法体制的一般原则。第二条“税收规则的清晰和透明”。第三条“税收规则的时间效力”,主要规定原则上税收规则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第四条“法律令在税收领域的使用”,主要规定政府通过法律令行使规则制定权的限制。第五条“纳税人的信息(权)”。第六条“公文的认识和简化”。第七条“公文的清晰和理由说明”。第八条“财产完整性的保护”,主要从纳税人税收债务的抵销、承担以及退税等方面规定纳税人财产的保护。第九条“期限延长”,主要规定纳税人在特殊的情形纳税义务履行期限可以中止或延长。第十条“信赖(affidamento)和诚实、善意(buona fede)保护”。此外,需要特别指出,2015年8月5日,意大利颁布了第128号立法令(关于在纳税人与征税部门关系中的法律确定性),[注]Cfr.il decreto legislativo 5 agosto 2015,n.128,recante disposizioni sulla certezza del diritto nei rapporti tra Fisco e Contribuente.规定在宪章第十条引入一项关于反避税的附加第十条。第十一条“纳税人的事前裁定”。第十二条“处于税务检查中的纳税人权利及保护”。第十三条“纳税人保护官”。第十四条“非居民纳税人”,主要规定居住在境外的纳税人获取与纳税相关信息的权利。第十五条“对实施税收检查人员的行为守则”。余下六条主要规定宪章及相关条款的执行、生效问题。
其次,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我国台湾地区“立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审议通过了该法,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看来,该法“系首部维护纳税人权,落实宪法税捐负担正义为使命,扭转数十年来税捐偏重提升稽征效能、确保‘国库’收入,将形式税捐法制落实到法治‘国家’要求,更强调民生福利国家‘宪法’精神,将税法迈向社会法‘治国’时代需求。”[注]葛克昌:“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评析”,2017年第二十六届两岸税法研讨会论文集:《纳税人权利保护新发展、房地产税制与社会公平》,第31页。该法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有关立法目的及优先适用规定,规定“为落实‘宪法’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及其他相关基本权利之保障,确保纳税者权利,实现课税公平及贯彻正当法律程序,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有关主管机关;第三条有关税捐法定主义;第四条有关最低生活费不受课税权利,涉及生存权及人性尊严保障;第五条有关量能课税原则;第六条有关租税优惠不得过度;第七条有关实质课税与租税规避责任;第八条和第九条有关涉税信息公开;第十条至第十三条有关正当程序保障;第十四条有关推计课税,主要规定对推计课税实施的限制;第十五条有关禁止过度原则,主要规定处罚不得过度;第十六条有关减责事由;第十七条有关诉愿审议委员会;第十八条有关税务专业法庭;第十九条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委员会;第二十条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官;第二十一条有关纳税者行政救济保障;余下两条主要规定施行细则的制定和生效问题。
3.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定位
作为本部分论述的结论,需要明确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的定位,即有关立法目的:基于保护纳税人权利、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的目的,我国需要制定的专门立法应超出纳税人权利宣示的作用,不能像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公告2009年第1号)那样,仅仅罗列现有主要的纳税人权利,而是以完善纳税人第一位性法律权利为主要内容,规定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具体化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等,从而有效约束包括税收立法在内的国家课税权(尤其是政府课税权)。不过,关于定位,还有以下两项相关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首先,关于专门立法的名称。鉴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主要的问题在于选择“法”还是“宪章”来命名。虽然相对于“法”,“宪章”似乎被用于规定更加圣神、根本的内容,但现在“宪章”的使用,通常旨在发挥其利于宣示的作用,如《纳税人宪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然,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是例外,也正是这一例外,使得有必要斟酌一番。不过,对于我国而言,应当认为选择“法”更符合我国法律命名的习惯,同时,也是彰显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法律约束力的需要。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和《纳税人权利法》之间进行选择。应当认为两者皆可行,不存在实质的差异,不过,在选择“法”的情形下,选择前者更合适,突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目的,也是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等已有法律例的遵循。
其次,关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效力。对于行政法规及(法律位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自然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于与其他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相比效力是否优先。对此,需要从三个层面来理解:(1)在形式层面,也就是按照我国《立法法》关于现有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从高到低,分别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而法律与法律之间的效力等级是相同的,因为都是由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事实上,即使制定税收通则法,按照现有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税收通则法与其他税收法律在效力上也是同等的,不构成上位法与下位法或母法与子法的隶属关系。[注]参见前注〔15〕,施正文文,第159页。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与其他税收法律(例如《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在法律效力等级上是相同的。在这方面,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亦是如此,正如意大利学者指出的那样,该宪章并不被视为宪法性法律,仅仅是普通法律,相对于其他法律,在法律位阶上没有特殊的优先效力。[注]参见前注〔71〕,第76页。(2)上述论点这并不意味着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对其他税收法律就没有影响,该法的影响主要源自其规定的内容的特殊性。具体而言,由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用于规定宪法性的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具体化规则和法律体制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该法的条款应具有规范和解释其他税法规则的价值。这不仅针对税收立法者,也针对税法解释者,尤其是后者,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中的条款应当代表着所有税收条款的解释标准。[注]意大利学者即如此看待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条款。参见前注〔70〕,第20页。在解释或应用任何税收条款的含义和适用范围等内容时,如果出现疑问,税法解释者应当以最符合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方式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解释路径是一致的。(3)正如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一条规定的那样,相对明确的是,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如果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就相关内容的规则属于特别规则,就可以基于特别法优先于其他的一般法而适用。
四、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借鉴的视角
在论证我国需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及其定位之后,本部分将就该法应当保护哪些主要内容提出建议并阐释。对此,本部分将在回应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从借鉴意大利现有宪法、《纳税人权利宪章》(以下简称意大利宪章)和我国台湾地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以下简称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这个视角进行论述。
(一)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
所谓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能体现税法自身应有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例如正义、法的确定性、公平等),贯穿于税收实体法和程序(诉讼)法等全部税收法规以及对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等都具有指导作用。[注]参见朱大旗:“论税法的基本原则”,《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30页。税收法定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即属于税法基本原则,进一步而言,属于宪法性的税法基本原则,因为它们(应)以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为依据。前者主要体现了法治国理念,强调个人自由和财产免受侵犯,从形式上限制课税公权力,后者主要体现社会国理念,强调国家干预和实现实质公平,从实质上限制课税公权力。考虑到我国宪法尚未规定这两项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对这两项原则以及相关具体化规则进行明确规定。需要先行说明的是,意大利宪章并没有规定有关这两项原则的基本条款,这是因为意大利现有宪法已有明确规定。
1.税收法定原则
需要阐释的内容如下:(1)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在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基本条款时应修正《立法法》关于税收法定原则规定过细的问题,与税收法律保留的相对性有所冲突。正如前文已经说明,需要在法律中规定的是税收定性规则,税率、税基等税收定量规则和税收优惠规则的确定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以在非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税收法律保留的相对性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尤其是在紧密情况下)和地方财政自主的实现。关于后者,有学者更是提出《立法法》的规定遏制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生存空间。[注]参见苗连营:“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59页。事实上,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条款,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原则性地规定课税应当根据法律来实施。例如,意大利现有宪法第二十三规定:“如果不是根据法律,人身或财产的给付不可以被课征。”再如,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者有依法律纳税之权利与义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基本条款的规定亦可规定为:税收应当制定法律,纳税人根据法律纳税。(2)税收立法需要去行政化,但并不完全否定政府基于授权实施税收立法,尤其是在税制改革、试点的过程中,这也是源于税收法律保留的相对性。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在不否定政府授权立法的同时,还需要具体规定对政府授权立法的限制,以制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例如禁止人大空白授权、政府不得转授权以及在多少期限内需要转化为人大制定的法律等内容。此外,对于政府定量规则的确定权,法律在授权时需要规定税率或税基确定的最高限值或客观标准。(3)针对我国财税主管部门频繁发布税收通告规范课税事项,为防止财税主管部门对个别课税事项行使实质的立法权,增加纳税人法律未规定的纳税义务,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主管机关所发布之行政规则及解释函令,仅得解释法律原意、规范执行法律所必要之技术性、细节性事项,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纳税义务或减免税捐”,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还需要具体规定财税主管部门发布的税收通告只能解释法律原意、规范法律执行规则,禁止增加纳税人法律未规定的纳税义务。
2.量能课税原则
需要阐释的内容如下:(1)针对我国目前税制缺乏公平性、新一轮税制改革又以建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为方向,为提高我国税制的公平性以及加快建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必须通过明确规定的方式在我国税法体制中引入量能课税原则。意大利现有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所有人必须根据他们的捐税能力分摊公共费用。税制符合累进标准。”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纳税者依其实质负担能力负担税捐,无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为差别待遇。”因此,借鉴这两条规定,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亦可规定“纳税人根据自身的负税能力承担税负”,作为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条款。(2)量能课税原则要求负税能力大的纳税人承担更大的税负,以承担更大的社会连带责任,而累积课税是贯彻这一点的理想工具。为此,符合实质公平的税制往往是累进性的,当然,累进并不要求所有税种都实施累进课税,主要是通过直接税应用累进课税实现整体税制的累进性。这样,借鉴意大利宪章的规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也可以具体规定税制符合累进标准。(3)负税能力虽然由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所体现,但并不意味着等同于经济能力,从生存权等基本人权保障的角度,负税能力仅指纳税人除去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的那部分经济能力后的剩余经济能力。[注]Cfr.Gaspare Falsitta,Manuale di diritto tributario,parte generale,CEDAM,2010, p.163.因此,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四条关于纳税人最低生活费不受课税权利的规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还需要具体规定纳税人及其扶养亲属生活基本费用不得课税。同时,量能课税原则还禁止过度课税,而我国目前存在税负过重(例如与不动产相关的交易)的问题,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还需要具体规定课税不能达到(实质)没收的效果并避免对经营活动的存在、持续或合理发展造成侵害。[注]Cfr.Gianfranco Gaffuri,Garanzie di giustizia e diritto tributario: la capacità contributova,in IUSTITIA,anno lxi,no.4,ottobre-dicembre,2008,p.443.(4)量能课税强调按照纳税人真实的负税能力课税,但是当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或税务机关查实纳税人真实负税能力将付出巨大成本,也允许以纳税人推测的负税能力课税。针对我国目前税务机关推计课税存在可能的滥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在肯定推计课税的同时,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例如,“应斟酌与推计具有关联性之一切重要事项,依合理客观之程序及适切之方法为之”“推计,有二种以上之方法时,应依最能切近实额之方法为之”等,具体规定类似的限制推计课税的规则。此外,为避免推测的负税能力明显大于真实的负税能力,还应具体规定纳税人的反证权利以推翻推计课税。[注]意大利宪法法院就此曾明确予以认可。Cfr.la sentenza della Corte Costituzionale del 11 marzo 1991,n.103。(5)量能课税强调以负税能力的相同与否给予纳税人相同或不同的税收待遇,据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需要具体明确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拟制性规范本身并不违背量能课税,但我国税收立法者需要审慎使用拟制性规范,不得过度、滥用,在特定的情形(不体现相同的负税能力)允许纳税人以例外的方式不按照拟制性规范进行纳税;其次,税收优惠使相同负税能力的纳税人受到不同税收待遇,背离量能课税,因此必须有合理的政策目的以及在与该政策有效期相对应的期限内实施。因此,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税收立法者(尤其是地方)亦不得滥用、过度使用税收优惠。
(二)税法规则清晰、明确和可获知性与纳税人信息权保护
1.税法规则清晰、明确
法律的良好实施建立在存在由清晰、明确规则组成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因为法律规则清晰、明确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必要因素。具体而言,法律规则清晰、明确不仅是落实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法律体制越是由清晰、明确的规则所组成,越能满足平等或公平原则。这是因为这样的法律体制能够限制法律规则的任意解释,可避免法律规则在实践中被有区别地适用。[注]Cfr.Filippo Varazi,Contributo alla certezza della norma tributaria,in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a cura di Augusto Fantozzi e Andrea Fedele,Giuffre,2005,p.68.因此,法律规则清晰、明确这一一般法律原则需要在税法中应用,该原则通过对税收立法提出要求,可制约税法解释和执行活动,这样,不仅基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需要,也是基于税法公平适用的需要,对于纳税人不受课税权任意、专断行使的侵害有着特殊的意义。而税法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使得在税法中应用规则清晰、明确原则更有必要。此外,也应当看到,税法规则清晰、明确,进而能被纳税人所理解,是纳税人切实、及时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并构成纳税人税收信息权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现有税法体制,除了税收法律中的规则本身不清晰、不明确以外,基本原则确立及其对规则指引的不足、规则与基本原则协调的不足(例如,对于增值税法而言的中性原则)、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以及税法碎片化、不稳定,都给纳税人准确、完整认识自身交易活动纳税义务或其他税收法律后果带来了很大困难,何况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将增加我国税法体制的复杂性,还将进一步加大这一困难。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需要特别规定税法规则应当清晰、明确,而相关的具体规则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伴随税收法律内容的增加,例如,如果《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甚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一些通告)规定的诸多内容都规定在《个人所得税法》和未来制定的增值税法中,当然这也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提高税收法律规则清晰、明确的需要,为使税收法律规定的繁多内容更明确、可理解,需要对税收法律进行内部结构优化。具体而言,应当对条文内容进行大、小范围的分类,即在条以上再设置章、节一个或两个层级,同时,对章、节、条注明名称,标明内容的规范对象。这样的优化还可以具体化其他法律对某法的引用,即引用时可具体标明章、节或条的名称,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标明法律的颁布日期或条文编号。意大利宪章第二条第一款就规定如下:“包含税收条款的法律……应当在标题中提及(规范)对象。内部进一步地划分单位和单个条文的标题应当提及所规范的条款对象。”(2)为确保税收法律条款规范对象所属领域规范的同一性,需要尽可能避免来自非税法律(即法律不以税收为规范对象)的“侵入”规则对同一性的破坏,[注]同上,第76页。即涉及诸如我国《慈善法》等税法以外的法律规定涉税规则的合理性问题,因为这类“侵入”规则往往与现有税法中的相关规则相冲突或矛盾。为此,意大利宪章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以税收为规范对象的法律……不能包含税收属性的条款,除非是那些紧密地固有于该法规范对象的条款。”根据该条规定的启示,税法以外的法律通常应当不规定涉税规则,这有助于避免不同立法者对同一领域规定矛盾、不协调的规则,从而造成适用规则的不明确,同时在税法以外的法律中规定具体涉税规则,客观上也增加纳税人获知的成本。当然,作为例外情况,与税法以外的法律规范对象存在紧密逻辑关联的涉税规则可以规定在该法律中,此时,应避免与相关税法规则的冲突或明确适用问题。同时,相关税法可以通过一项专门的条款规定“侵入”规则或提示相关的内容来保持规范的同一性。[注]同上。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可考虑借鉴意大利宪章的规则。(3)针对我国税法在参见其他税收条款时出现的规则不明确问题,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亦可以借鉴意大利宪章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参见规定在涉税规范性文件中的其他条款,需要同时指出意图参见条款的概括内容。”根据该规定,参见除了指出参见条款编号及其所在的法律名称外,还要指出参见条款的概括内容。事实上,为使适用的规则更明晰,更便于纳税人认识,参见时指出的信息应尽可能详细,例如参见法律的颁布日期和编号、条的名称(规范对象)等,如果具体涉及款,还包括款的序号。(4)正如意大利宪章第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那样,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还需要明确的是,如果纳税人的违法行为是由税法规则的不清晰、不明确所引起的,即源于税法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纳税人不应当受到处罚。
2.税法规则的可获知性
除了税法规则需要清晰、明确以外,纳税人税收信息权的保护还要求征税部门实施必要的举措,以确保纳税人可以获知适用的税法规则。为此,意大利宪章第五条在一般层面上(针对不特定纳税人)规定:“(1)征税部门应当采取合适的举措使得纳税人可以完整和便利地认识税收领域的立法和行政条款,并负责编排配套、协调的文本以及让纳税人在每一个征税机构都可以使用这些文本。征税部门也应当采取合适的电子信息方面的举措,以允许信息的实时更新,并让纳税人免费使用电子信息。(2)征税部门应当及时并通过合适的工具让纳税人认识所有由其颁布的通告和决议以及任何其他关于组织、职能和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或政令。”类似的规则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中也需要明确规定。
总之,税法规则的清晰、明确和可获知性应当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该原则在减低纳税人税法遵从成本的同时,还利于征税部门理解和管理税法体制,这也是征税部门实施税收事前裁定的重要基础。[注]显然,建立税收事前裁定制度也有利于纳税人信息权的保护。此外不能忽视,税法规则的清晰、明确和可获知性可降低纳税人实施逃避税行为的借口。[注]参见前注〔70〕,第18页。
(三)税法溯及既往的禁止与例外
1.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溯及既往禁止
溯及既往涉及规则在时间上的效力,是指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过去发生效力,其源于这样一种权力实施的结果:基于对不特定对象的约束效力,针对一项行为或事实,该规范性文件以一种与之前规范该行为或事实不同的方式再思量,或者,该规范性文件赋予这一行为或事实一种法律上的重要意义,而之前这一行为或事实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意义。[注]Cfr.Valeria Mastroiacovo, L’efficacia della norma tributaria nel tempo,in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a cura di Augusto Fantozzi e Andrea Fedele,Giuffre,2005,p.101.换言之,如果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扩展至已完成的行为或事实,或者扩展至已经产生的权利(diritti sorti),[注]即所有者已经取得的权利,即使条件发生改变。例如,之前赋予一主体的权利(获取退休金、特许经营权等),该主体基于善意取得,即使相关法律制度发生变化,该主体对该权利的取得也不能受质疑。就构成溯及既往。[注]参见前注〔87〕,第102页。在税法领域,这样的效力可以表现为:通过规则的修改或创新,与之前的规范效果相比,对特定的情形课税、提高税率或增加程序性义务。溯及既往会使公民从管理自己财富、经营活动和自由时间等方面做出的最好选择变得徒劳或者(最好)效果减损,使公民对法律制度稳定性失去信心。因此,溯及既往背离了法律确定性,也严重妨碍了经济自由和企业创业自由。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溯及既往禁止无疑也应当在税法中应用,况且,税法溯及既往亦有可能背离量能课税原则,因为根据负税能力现实性的特征,对过去的负税能力(极有可能现已不存在)不得课税。[注]参见前注〔79〕,第171页。针对我国税法体制中存在的规范性文件溯及既往问题,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借鉴意大利宪章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规定税收规则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作为在税法规则时间效力方面的一般规则约束税收立法者和税法解释者。关于溯及既往禁止的一般规则,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溯及既往本身具有复杂性,溯及既往发生的情形在实践中也并非千篇一律。当然,对于以下一类溯及既往的情形予以否定,并不存在异议:新的规范性文件推翻基于消灭事实的介入已经被认为是竭尽的法律情势,其中,消灭事实既包括物质上的消灭事实,例如,所得耗尽、房屋毁灭等,也包括法律上对法律情势产生根本影响的事实,例如既决案件、因过期限而失效、终止或者履行(完毕)等。[注]参见前注〔87〕,第105页。这样,溯及既往还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形:新的规范性文件将法律效力扩展至已经完成的行为或事实,但这些行为或事实还没有因为物质上或法律上的消灭事实而竭尽。如果对于这样一类溯及既往情形的禁止还不至于受到根本的质疑的话,那么以下另一类所谓不确切的溯及既往情形是否应当否定就可能产生争议:新的规范性文件通过考虑在过去已经查实的行为或事实并赋予新的“外形”,对之前的规范进行新的构建,但构建的效力仅限于未来。[注]同上,第106页。事实上,这类溯及既往与规范性文件的立即适用很难区分,而在税法领域,这类溯及既往又是最为频繁发生的。对此,正如前文已指出的那样,在税法规则适用上出现疑问,税法解释者应当以最符合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中的相关原则来解决,这样,如果税法规则具有溯及既往性和排除溯及既往性双重解释,解释者应当采纳后者的解释。
其次,对于周期税,例如所得税和财产税,一项纳税人义务的产生需要考虑一个时间周期,通常是一个公历年度,[注]与周期税相对应的是瞬间税,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一项纳税人义务的产生无需考虑一个时间周期,在一项交易或行为完成的时候即刻产生。参见翁武耀:“法律视角下增值税课征属性再认识——R.P.Capano《增值税》一书中的意大利理论观点述评”,《财经法学》2017年第1期,第31页。溯及既往的问题需要说明一点。以企业所得税为例,周期(一年)的所得取得才代表一项应税行为,对于这样一类复杂的行为,经过一个周期的时间在判断行为已经完成或已经产生一项权利时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这一周期内,规范性文件对某项事实(例如固定资产支出)的法律意义进行了修改(例如折旧标准),在这周期内可以适用该新规定吗?事实上,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于周期税,曾区分了真正(autentica)的溯及既往和非真正的溯及既往两种类型:前者,一项在某一年颁布的法律从前一年开始生效,对已经完结的关系产生效力;后者,法律在一年当中颁布,但是在年底前,产生从同一年第1天生效的效力。[注]参见前注〔87〕,第109页。不过,即便是非真正的溯及既往,意大利宪章第三条第一款针对周期税特别规定了“关于周期税,引入的修改只能从在规定修改的条款生效之日所在周期的下一个周期开始适用。”条款生效之日必然要晚于发布之日,如果规定生效之日为下一年度1月1日,条款就需要在下下一个年度开始适用。意大利宪章这一创新,值得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借鉴。
2.税法中的溯及既往
溯及既往的禁止并非是绝对禁止,否则,对立法已有的错误或问题也将无法有效采取补救措施。[注]参见前注〔70〕,第14页。因此,作为一般规则的例外,税法亦存在溯及既往的情形:正如意大利宪章第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那样,需要明确在纳税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溯及既往的情形是,对规范性文件实施有权解释而形成的税法解释性规则,即使在规范性文件之后颁布,也应当与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时间相同,因为解释性规则并不对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修改或创新,仅仅是阐释原有的含义。又如,对于纳税人有利的税法规则可以溯及既往,因为这与纳税人权利保护并不冲突,可以视为是基于平衡强势的课税权的必要性而引入的不对称规定,或者是立法的一种自我补救措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可斟酌规定。再如,满足若干特定的条件下,意大利宪法法院曾以并不违反量能课税原则而认可溯及既往。这些特定条件包括:从行为或事实的完成到适用新规则经过的时间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即在合理的跨度内),完成的行为或事实的经济效果依然留存在纳税人的财产中(即负税能力依法存在)以及对于事后的课税具有可预见性(例如,考虑到相关税制中存在规则漏洞等)。[注]Cfr.la sentenza della Corte Costituzionale del 20 luglio 1994,n.315.对于第三项条件,如果课税又具有反避税的目的,溯及既往的正当性可能更强。对于这一类溯及既往,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亦可斟酌规定。
(四)诚信原则与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
1.诚信原则
新型征纳关系的构建亦是一项纳税人权利保护法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而体现为平等、协作关系的新型征纳关系,以纳税人与征税部门双方相互信任和尊重为重要特征之一。为此,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为约束征税部门,不仅需要规定纳税人诚实推定权,还需要规定征税部门在课税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尽管该原则亦约束纳税人。诚信原则的基础在于社会连带责任,强调社会组织以成员间的相互依存为基础。事实上,前文论述的税法规则清晰、明确原则(否则纳税人不受处罚)和溯及既往禁止原则亦与征税部门受诚信原则约束相关,但正如意大利宪章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那样,“纳税人和征税部门的关系遵循协作和诚信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还是应当在专门的条款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以作为征税部门的行为法则。根据行政法学说,诚信原则一方面是行政活动的指引,属于一项关于进程、方法的规则,另一方面又承担补全规则条款的功能。[注]Cfr.Alessandro Meloncelli,Affidamento e buon fede nel rapporto tributario,in Statuto dei diritti del contribuente,a cura di Augusto Fantozzi e Andrea Fedele,Giuffre,2005,p.542.当然,这里主要关注于前者,即诚信作为所有公、私主体间的关系都要符合的标尺,主体应当根据良心和忠诚来实施行为,尤其是征税部门等公主体。
那么,什么是诚信的行为?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主观的诚信,表现为行为主体尊重法律规定的一种心理,即使该主体处于一个无知或被蒙蔽的状态;其次,客观的诚信,表现为面对他人,行为主体持有这样一种真诚和正确的态度,即旨在阻止他人的合法期望被落空。[注]同上,第537页。显然,主观的诚信(涉及遵守法律的行为)可以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无关,而客观的诚信必然涉及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换言之,根据客观的诚信行动法则,行为主体需要承担不让他人的合法期望落空的义务。后者无疑对征税部门施加了要求更高的义务,即有关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义务,这是因为纳税人合法期望免受落空正是通过保护信赖利益的方式实现的。
2.纳税人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在法律上的功能在于保护这样一类主体:对某物或某人施加了信任,进而因为信任而限制自身的某种行为或选择。信赖保护可以从源自私法的权利外观主义中寻求法理基础。权利外观主义涉及当权利、意思等的真实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不一致时应当保护哪一方当事人的问题,其中,外观是指能引起集体(不特定人)错误的现实外在虚假信号,需要区别于错误,即形成于某一特定主体中的现实的虚假表明,并不与存在误导的外部因素相关联。在征纳关系中,征税部门对某一税法规则进行解释,可能阐释出一项有关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真实法律情势,也可能仅仅是在规则内容中没有依据的外观。不管是何种情形,纳税人基于信任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具有特殊威望的征税部门提供的解释指引(很有可能随后被修改),此时,对于纳税人而言,并不存在一项属于主观范围的错误,而是形成一种包含在社会上被一般化的、可赞同的经验内容的现象。[注]同上,第534~535页。此时,需要保护纳税人的信赖或合法期望,因为纳税人的行为是基于征税部门的行为而实施,从而限制了自己的行为或选择,同时,事后可能的课税变更或违法行为等并不是由纳税人的过错所引起。为此,纳税人不应当承受相关的不利益,并且依然享有行为实施所带来的利益。意大利宪章第十条第二款还规定:“当纳税人遵循了征税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即使之后征税部门修改了该文件的内容,或者,当纳税人的行为是直接源于征税部门的延迟、遗漏或错误的事实而实施的,不得向纳税人课以处罚,也不得向纳税人要求支付利息。”与此相关,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无疑信赖利益保护与诚信原则在客观层面的含义上具有紧密关联,两者保护了纳税人已经产生的权利,其中纳税人因并不存在的法律情势或与真实法律情势有着本质不同的法律情势而实施行为。这样,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在规定诚信原则的同时,可以也应当规定纳税人信赖保护的条款:纳税人的信赖由征税部门一项能被确定为“外观的”合法情形的行为所引起,纳税人据此调整了自身的一项行为(以符合该征税部门的行为),或者因征税部门以明确或默认的方式接受纳税人的一项行为,纳税人产生合理的信服以及对按照法律实施行为的信服,纳税人的信赖应当受保护。[注]Cfr.Michele Cantillo,Lo Statuto del contribuente nella giurisprudenza,in ANTI,13/12/2005,p.4.此外,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可借鉴意大利宪章第十条第二、三款的规则规定体现信赖保护的具体规则。
(五)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与反避税限制
1.权利滥用禁止原则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诚信原则在税法中的应用亦包括对纳税人行为的约束,而纳税人实施的避税行为(实质上违背税法的目的)显然并不符合纳税人诚信的要求。此外,避税行为人通过非正常的交易安排实现与通过正常交易安排同样的经济效果,掩盖了其真实的、与非避税行为人一样的负税能力,对其更有利的课税待遇违背量能课税原则。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规定反避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确保课税公平这一纳税人基本权利。此外,我国目前只有在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一般反避税规则,同时缺乏避税概念的完整定义,纳税人权利保护法需要界定避税概念,进而引入应用于整个税法体制的一般反避税规则,毕竟在税制将变得越发复杂的背景下,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种的避税问题也应当给予重视。对此,还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不同反避税理论之间,我国应当采用何种理论?源自私法的权利滥用禁止理论通常由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而商业目的或实质重于形式理论通常由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尽管不同的反避税理论对避税要件的认定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异。[注]参见前注〔31〕,翁武耀文,第807页。考虑到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反避税理论上似乎更有理由采用权利滥用禁止理论,至少在形式上。何况最新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使得这一一般法律原则在我国亦有了成文法的基础,有利于该原则在包括税法在内的其他法律部门中应用,同时有助于突出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紧密关联。此外,随着纳税人权利的完善,尤其是税收实体法中的权利,纳税人权利滥用的现象也将更为频繁地发生。对此,正如意大利宪章附加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那样,“不管纳税人具有什么样的意图,如果一项或多项交易缺乏经济实质,本质上为实现不正当的税收利益,尽管税收规则形式上得到了遵守,构成权利滥用……”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反避税规则中应用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可以直接将避税命名为权利滥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反避税中就完全不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事实上,在反避税中融合两大法系国家理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种通行做法。
其次,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在对避税概念进行界定时,为了使之与合法节税相区别,必须指出避税的核心特征或构成要件,即取得的税收利益不正当、违背税法的目的。意大利宪章附加第十条第二款第b)项就规定:“不正当的税收利益是指利益的实现与税收规则的目的或税法体制的原则相冲突。”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七条第三项关于避税的界定也规定了“……获得租税利益,违背税法之立法目的……”事实上,违背立法目的内涵于权利滥用禁止理论,不过,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一般反避税规则并没有规定这一内容,这与我国目前以商业目的或实质重于形式理论构建反避税规则相关。
2.反避税限制
反避税虽然必要,但是如果征税部门滥用反避税权力,又会对纳税人法律确定性、合法预期以及合法节税等利益造成侵害,因此不能矫枉过正。比较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在反避税权力限制方面,相关立法也不够完善,对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借鉴意大利宪章的规定予以完善。意大利宪章关于反避税的附加第十条在多个方面体现了反避税限制的内容:(1)具体界定避税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除前文提到的内容外,第二款第a)项规定:“缺乏经济实质的交易是指不足以产生有意义的不同于税收利益效果的交易。经济实质的缺乏尤其体现为单个交易的定性与交易整体的法律基础不符以及法律工具的使用与市场正常的逻辑不符。”第三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能被非税收(非次要的)有效理由所正当化的交易,都不是权利滥用下的交易。”(2)第四款规定了合法节税权,即“纳税人具有在法律提供的可选择的不同规则之间以及在承担不同税负的交易之间选择的自由”。(3)第五款规定纳税人就交易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可以提出反避税事前裁定。(4)第六款规定征税部门反避税查定程序要求,例如在做出权利滥用查定决定之前需要给予纳税人辩解(针对征税部门认定权利滥用的理由)的机会,否则查定决定无效。(5)第九款规定征税部门避税认定的举证责任,即征税部门有义务证明滥用行为的存在。(6)第十一款规定反避税效果中的第三人利益保护,即“不同于本条规定适用的主体可以要求退还因为滥用交易而缴纳的税款”。[注]关于意大利反避税事前裁定程序、避税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反避税效果,分别参见前注〔30〕,翁武耀文,第234~239页、第231~233页和第207~212页。基于上述这些内容,不难发现意大利宪章对反避税限制的规定是非常全面和详实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规定。
(六)其他主要内容
关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规定的其他主要内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简要作如下说明:(1)正当程序原则在税法中应用。当然,正当程序原则主要规范税收征纳环节,具体体现该原则的规则可在税收征管法修订中进行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可视情况进行补充规定。(2)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应用。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强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及权利义务的对等,但该理论目前在我国尚未被广泛接受,为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应用作出明确规定,可以借鉴意大利宪章第八条第一款“税收债务也可以通过抵销而消灭”的规定,引入税收债务概念并从规定税收债务抵销制度入手。(3)纳税人保护官制度的引入。纳税人保护官属于制约征税部门公权力行使的纳税人维权组织,这是因为个别纳税人面对代表公权力的征税部门,不仅在信息上不对等、专业知识上不对等,而且法律手段上亦不对等。[注]参见戴芳:“发达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官制度及其借鉴”,《涉外税务》2012年第7期,第39页。事实上,不仅意大利宪章和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但凡一国和地区对纳税人权利保护进行专门立法,都规定了纳税人保护官制度,例如美国《纳税人权利法案》。[注]See Title I of Public Law 104~168-Taxpayer Bill of Rights II.(4)税务专业司法审判机构建设。这对于加强税务司法、制衡政府及其征税部门课税权进而保护纳税人权利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而目前我国在税务专业司法审判机构及其人员建设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为此,虽然我国像意大利那样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条件还不成熟,[注]参见翁武耀:“意大利税务委员会制度及借鉴”,《税务研究》2017年第3期,第85~91页。但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法”第十八条“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业法……”的规定,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中规定在一定级别以上的法院设立税务审判庭。
五、结论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税法体制中的纳税人权利保护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诸多有违现代税法之正义和公平要求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在过于追求国库主义下政府及其征税部门课税权不受有效制约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纳税人对政府及其征税部门课税信任将逐步减损。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虽然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改革下将面临新的挑战,但新时期也给我国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毕竟此刻税收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治理工具的高度。同时,新时期下伴随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民主和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扭转我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的局面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综观其他国家和地区,通常以宪治为基础、以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为起点建立体系化的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其中,纳税人权利保护专门立法——以纳税人(权利)宪章、法案为代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税收基本法或税法典缺失下的弥补措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往往承担起宪法上关于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具体化的重任,发挥约束税收立法、执法和税法解释等课税权实施活动的功效。此外,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双创”战略,以期加快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要达此目的,必须全面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适时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对于规范政府课税行为,保障国家减税降负政策实施,保护经营主体的创业热情和切身利益,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无论是从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出发,还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可借鉴的经验,我国都应当将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提上立法议程中来,实现宪法性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具体化规则以及有利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般法律原则在税法中的成文法化,向我国税法法典化进程迈出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