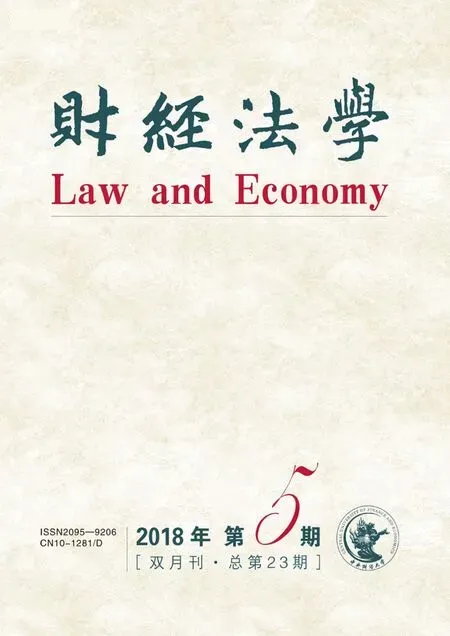信息公开与“权利滥用”
——日本的现实和应对
石龙潭
一、前言
最近,笔者正在从事有关信息公开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解析过程中发现,中国的信息公开在现实与理论当中遇到了许多问题,诸如大量、多次申请,以及与此相关的大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所谓的“权利滥用”。就此,中国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也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解决方案。本文把目光聚焦于日本。首先,看看同样的现象在日本是否存在,它的问题点在哪里?其次,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判例等,对这个问题从制度和理论层面加以详细分析,看看日本是如何应对的,还存在哪些课题?最后,以日本的现实与应对为背景,就如何解决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问题略抒己见,以期为中国同仁思考同类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二、日本信息公开的现状与问题点
(一)日本信息公开的现状
客观地讲,“权利滥用”作为日本信息公开的伴生性问题,自从该制度导入以来一直困扰着理论与实务界。尽管日本的信息公开采取双轨制,〔1〕参见石龙潭: “日本的信息公开制度:回顾、现状与展望”,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即国家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2〕该法律的日文名称为“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而地方自治体则适用各自所制定的信息公开条例,但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就此,总务省曾经做过全国性调查并将结果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在网上公布。〔3〕详情参见《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该文件的日文名称为“情報公開制度における権利の濫用”,载 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04143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 7月 16日。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总务省出台的《依据〈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实施行政处分时的审查基准》〔4〕该文件的日文名称为“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に基づく処分に係る審査基準”。中甚至明确规定,当公开申请相当于权利滥用时,行政机关可决定不予公开。而地方自治体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在此仅以大阪市为例介绍若干典型实例。〔5〕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1~33頁。
1.某市民向大阪市消防局申请公开多达近8万张纸的信息。即便保守估计全部处理完毕大概也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同一人曾经向包括市消防局在内的三个部门分别要求公开多达1万到2万张纸的信息,实施机关花费了长达数月到近两年不等的时间制作好了行政文书,该人却从没有来阅览过。
2.实施机关向A的主治医照会有关信息。A认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照会主治医令人难以理喻,于是向实施机关申请公开该照会的有关依据。实施机关在提供相关信息的同时反复向A做出说明,但均无法获得A的谅解。在其后的三年间,A反复请求同一内容的信息公开,与此同时,针对实施机关就其公开申请所做的决定 (行政处分)大多提起行政复议。
3.B针对特定的区政府反复申请信息公开,一旦发现工作人员出错,如公文书中的日期与星期不符等,就在现场大声呵斥,并反复出现上述行为。后来B的行为不断升级,甚至开始向女性工作人员探询隐私,在语言上恫吓等等。
4.C要求公开“某局的所有文件”,数量特别巨大,却拒绝行政机关希望对对象文书予以一定限定的请求。
5.大阪市导入信息公开制度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信息公开的申请数量逐年增加。但在另一方面,也遇到了预想不到的课题。“大量申请专业户 (职业申请人)”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在全市不断增加的信息公开申请当中,来自数名特定人士的公开申请以及行政复议从2010年以后开始急剧增加 (例如,从2010年到2012年,来自上述A的公开申请约410件,行政复议约320件;来自B的公开申请约290件,行政复议约60件。在2012年度,由A与B提起的行政复议竟然占到了总数约260件的八成)。
然而,上述现象并不局限于大阪市。从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初到今天,在地方自治体的实务现场被反复提起的就是:应该如何应对公开申请权的滥用或曰权利滥用式的大量公开申请。〔6〕藤原静雄「情報共有の政策法務―自治体情報法制の今日的課題」ジュリスト1404号79頁。而诸如无故请求大量资料公开等带有骚扰或妨碍行政机关工作之嫌的信息公开申请,可以说一直困扰着地方自治体的相关工作人员。〔7〕三宅弘「『大量の情報公開請求と却下』問題」自治体法務研究2014·春53頁。
(二)日本信息公开的问题点
现行信息公开基于国民主权、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说明责任等理念,在制度设计上不问公开申请的理由与目的,而且任何人包括如笔者这样的外国人在内都有权提出,因此,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事项反复提出申请或者一次性要求大量行政文书公开等,以现行信息公开的制度性理念来看或许并不与之相悖。〔8〕比如,《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3条就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而且不问理由与目的。然而,正如我们从大阪市的事例当中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信息公开申请权遭到滥用式行使,行政机关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力穷于应对,这恐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如上所述,诸如因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不满而请求公开该机关的所有文书、以行政监督的名义持续反复地向整个行政机关 (或者特定科室)请求公开、针对特定科室的文书按照档案反复要求大量的文书公开、针对工作人员出现胁迫性的言行、即使获得实施机关的公开决定也拒绝阅览相关文书等行为,存在很多负面影响。首先,会长期且大量地占用和耗费行政机关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其次,也与前一点相关,行政机关对特定人士的公开申请,不得不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予以应对,其结果是极易给实施机关的判断以及“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9〕有关该审查会的性质与作用等,参见前注〔1〕,石龙潭文,第88~89页。等的审议造成延迟,从而影响到其他公开申请人的正当权益,相对地降低对其他市民的服务水准,以致动摇公众对信息公开制度的信赖。再次,这种局面,对信息公开部门本身也会形成压力,容易使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产生怀疑,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出现消极态势。最后,从公众有权平等享受行政资源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行为恐怕也存在问题。
总而言之,面对如上所述的权利滥用式的信息公开申请,若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不仅会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公众丧失对信息公开制度的信心,而且还有可能使之演变成为深刻危及信息公开制度本身的危机要素。〔10〕曽我部真裕「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について」法学論叢176巻2·3号326頁。因此,理论与实务界大多主张,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以积极应对。
三、理论上、制度上的应对
严格说来,信息公开中的权利滥用,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次性申请大量的信息公开 (大量申请)、特定的个人针对特定或不特定的事项反复多次申请公开 (反复申请)以及与此相关大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大量行政争讼)等。大量申请与反复申请事涉申请权的滥用,而大量行政争讼则涉及诉权的滥用等,因各自性质有所不同本应分别加以理论探讨,但由于篇幅有限,而且日本的理论与实务以及判例等大多以大量申请为中心,因此,本文除非有必要适当言及,否则主要以大量申请为对象,来看一看日本在理论与制度上是如何应对的。
(一)大量申请≠权利滥用
不过,在此首先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现行法上,对于公开申请的数量以及次数没有任何限制,而且,诸如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申请、〔11〕商业性申请,不仅牵涉到信息的利用与再生产、产业的创出与振兴、官民信息共享等层面,而且在现行制度下,要么免费要么手续费被控制在低于实际费用的水准,事实上申请人的利润追求最终是要靠纳税人的税金来实现的。因此,需要以不同的视角和原理来加以探讨。但因篇幅有限,在此止于问题提起。国内最近的讨论可参见高秦伟:“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商业利用及其应对”,《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35~151页。与大规模工程或大型公共设施相关的文书 (像有关核电站的文书)、事涉出现重大问题的行政机关整体的调查以及时间跨度相对较大的统计资料等等,因文书的性质公开申请不得不变得大量的情形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大量申请与权利滥用之间并不能够划等号。
那么,在信息公开制度的制定当初,是否预想到了这种大量申请的情形,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以下,让我们以《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为例来具体看一看。
在制定之际,该法要求行政机关接到信息公开申请之后必须在30天以内作出是否公开的决定 (第10条第1款)。同时,为了应对大量公开申请,规定在事务处理上确有困难以及存在其他正当理由时,行政机关的期限可以以30天为限对上述期限予以适当延长 (同条第2款)。并进一步规定,当与公开申请相关的行政文书数量特别巨大,若从公开申请之日起60天以内对其全部作出是否公开的决定会给工作造成显著妨碍时,行政机关之长还可以不受第10条所限,可暂就与公开申请相关的行政文书的相当部分在该期限内做出是否公开的决定,而对剩余的行政文书,则只要在相当期限内实施判断即可 (第 11 条)。〔12〕也就是说,规定处理期限特例的第11条,允许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受第10条所定的期限限制,在认为相当的期限内实施公开即可。就此,日本律师协会主张,对于第11条所定的“剩余的行政文书”,不应以“相当期限”,而应以30~60天程度的具体期间来界定。这种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量:超出第10条所定的期限原本就属于非正常状态。即便受到允许,若不就其期限以一倍于第10条所定的期间等形式加以明确界定,有关期限的规定就会形同虚设。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恣意滥用第11条所定的“相当期限”,需要对其予以监督,从而对该处理特例条款有可能遭到行政机关的恣意运用敲响了警钟。
以上表明,在《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当初,已经预想到了大量申请的情形,并就应对之策预设了处理期限的特例。因而,学界一般认为,“大量申请并非等同于权利滥用,(权利滥用与否)需要就是否存在使行政停滞的意思进行举证”。〔13〕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条解説 [第6版]』(有斐閣、2014年)133頁。虽数量巨大但有其合理性时,可以采取分割申请、抽样申请等办法应对,仍然应对不了的最后可以以特例延长。同时实务界主张,“即便作为信息公开申请对象的行政文书数量特别巨大,可能会给工作实施带来显著障碍,……但除非存在以使行政机关工作停滞、混乱等为目的的情形,否则 (这种大量申请)不相当于权利滥用。单纯地在事务处理上产生困难时,可依据处理期限的特例(《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11条)来加以应对”。〔14〕総務省行政管理局『詳解情報公開法』(財務省印刷局、2001年)100頁。而判例也主张,不能单纯以大量申请或者商业性申请就断言权利滥用。〔15〕在此介绍一个有关商业性申请的具体事例:某地图制作厂商要求公开居民住址簿等,行政机关以处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由做出拒绝公开的决定,该厂商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决定。就此,德岛地方法院主张,即使相关处理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但行政机关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的人员调整等应对,从而做出撤销拒绝公开决定的判决 (徳島地判平成19·2·22判例集不登載)。其他相关判例参见東京地判平成15·10·31判例集不登載、徳島地判平成19·2·22判例集不登載、高松高判平成19·8·31TKC·DB、佐賀地判平成19·10·5判例自治307号10頁、さいたま地判平成19·10·31TKC·DB等。
由此可见,即便需要考虑实施机关的工作负担,也不能单纯以文书数量巨大就主张该申请属于权利滥用,包括商业性申请在内的大量申请也是现行法所允许的,不能将大量申请直接视为权利滥用乃当今学界、实务界以及判例的共识。
然而,在此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只对一般意义上的大量申请制定了特别条款,而对于该项权利的滥用则没有设置任何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是如何应对权利滥用式的信息公开申请的呢?
回顾日本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它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大的重心转移:一次是以全面贯彻公开原则为核心的推进信息公开制度的改革,另一次是以信息公开制度中出现“权利滥用”为契机,要求对公开申请权予以一定制约而实施的制度微调。〔16〕参见前注〔5〕,宮之前亮文,第39页。前者肇始于导入信息公开制度的初期,而后者则发生在进入制度安定期的近年。在这两次变革当中,就如何解决权利滥用式的信息公开申请,从基本理念到具体应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导入信息公开制度早期的应对
《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制定之前,日本于1995年3月设立了“行政信息公开部会”,作为“行政改革委员会”的专门部会,该部会在1996年11月发表了《信息公开法要纲案》和《信息公开法要纲案的基本观点》。〔17〕该两个文件的日文名称分别为“情報公開法要綱案”和“情報公開法要綱案の考え方”。尽管在要纲案的制作过程当中,就公开申请权的滥用是应该以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原理(《民法》第1条第3款)来应对还是用明文写明存在意见分歧,但最后立法者选择了前者。这一点,如上所述,从该法没有就权利滥用做任何规定,以及《信息公开法要纲案的基本观点》的以下说明来看,也是一目了然的。该文件中设有“5(6)处理期限以及数量特别巨大的行政文书的公开申请的处理”一栏,指出,“针对诸如请求公开特定部署所拥有的全部行政文书、以削弱行政机关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公开申请等,尽管没有设置特别规定,但可以通过适用有关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应对”。
同时,当时的大多数地方自治体也主张,如果在信息公开中出现权利的滥用,应该通过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处理。〔18〕参见前注〔6〕,藤原静雄文,第80页。
可见,尽管在国法层次上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以及大多数地方自治体的条例当中,均不见直接应对滥用公开申请权的规定,但以作为法的一般原理的禁止权利滥用来应对可以说是立法者的初衷。
那么,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既然任何制度和权利都有可能遭到滥用,当时为什么要刻意回避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在信息公开制度中设置有关滥用公开申请权的条款呢?
第一,可以说是客观原因或者远因吧。长期以来行政法学疏忽有关禁止权利滥用原理的研究,理论储备明显不足。尤其是针对私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行使权利时,就是否应该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理、在何种场合才能够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等等,缺乏充分的理论梳理与考证。因此,在该原理的认定与适用上通常消极且谨慎。
总体而言,禁止权利滥用等民法上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在采用公法私法两元论的传统行政法学中,也作为贯穿法全体的一般原理,不仅直接适用于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而且在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当中也得以类推适用。而在公法私法两元论遭到否定的当今,就更是如此。今天,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一般认为它适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
然而,长期以来,行政法学在论述禁止权利滥用时,仅限于行政机关行使权限的场合 (理论上准确地讲,应该是指“权限的逾越与滥用”,即围绕《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0条的适用场合,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分之际是否存在裁量权限的逾越与滥用),几乎把私人行使权利的场合排除在外,一直热衷于通过遏制行政机关裁量权限的逾越与滥用来保护私人的权利和利益。很久以来,私人在行使权利时也会出现权利滥用,对此,行政法学虽没有全盘否定但认定消极且谨慎,几乎不存在被认定为权利滥用的事例。〔19〕濱西隆男「行政法における権利濫用禁止の原則についての覚書」季刊行政管理研究122号35~43頁。同时,该氏主张,私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行使权利时之所以权利滥用不易被认定,除文中所述的消极态度之外,也同此前在行政实务以及判例当中几乎不见权利滥用受到认定的实例有关。究其原因,第一,起因于行政法规的制定方法。即,在制定行政法规之际,一般要求私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行使,需要满足行政法所定的一定要件才获允许,以此就有效地避免了权利滥用的发生。第二,也同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法规的姿态有关。即,当行政机关认为适用行政法规允许私人在行政法上行使权利有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时,通常会采用一定办法来防患于未然,比如附加一定条件(如附款)以对权利行使予以限制或者依据行政机关的解释基准、裁量基准,原则上不允许私人行使与上述基准不相符的权利等。参见该文献第37页。
第二,与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本身有关,笔者愿意称之为主观原因。信息公开制度,立足于国民主权、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说明责任等理念,具有开放式的架构,不问理由与目的,对申请主体没有任何限定。从保障与监督行政机关正确运营这个角度而言,申请越多其效果越佳也越可期。因此,公众对公开申请权的积极行使,不仅不应该受到束缚,反倒应该受到广泛欢迎。从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理念来看,从正面对公开申请权予以限制,在制度理念上自相矛盾,也意味着自我否定。
第三,作为近因,也同制度的发展时机有关。在信息公开的早期即构筑期,如上所述,人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如何推进信息公开的彻底。而在导入新制度之际若设置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很容易对申请人产生萎缩效果,从而影响监督行政履行说明责任这一制度初衷的实现。说得通俗一些,你不能一边鼓励人们积极要求信息公开,一边在有人申请时,却反过来指责人家在数量和次数上超标。因此,应该承认,早期的信息公开立足于性善说的立场,期待藉由实施机关与申请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调和来达到制度的正确运营目的,回避设置与权利滥用相关的条款,若出现公开申请权的滥用则把它交由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这在立法政策上并无不妥。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导入信息公开制度的早期,针对大量申请,学界几乎是持欢迎态度的。在2008年9月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等委员交流研讨会”上,大量申请信息公开的市民被称为“特定的个别热心人士”。与会者就如何应对“来自于特定的个别热心人士的大量申请以及大量行政复议”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多数人主张,应该通过充实体制人员、与公开申请人之间构筑信赖关系、征收手续费、以文书不确定为由拒绝、窗口应对 (即通过劝说、开导、说明等行政指导的方式)、窗口应对中如出现威吓等可利用警察、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理等来加以应对。〔20〕「第6回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等委員交流フォーラム概要」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31号21~23頁。同时,在判例中,除极少数例外外,几乎看不到被认定为权利滥用的例子。〔21〕藤原静雄「情報公開請求の拒否と権利濫用」法学教室2012年3月号4頁。
顺便说明一下,在《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制定之际,虽然也有意见主张应该采纳地方自治体的作法不征收公开申请手续费,但最后还是规定,公开申请人在申请阶段,依政令必须缴纳政令所定金额的公开申请手续费 (第16条第1款)。因此,即便是权利滥用式的公开申请,一件也要缴纳300日元的公开申请手续费 (但电子申请时减为200日元)。同时,在接受公开之际,与地方自治体相同,还要根据实际发生费用的金额缴纳公开实施手续费 (第16条第1款)。因此,大量申请以及反复申请时,应缴纳手续费的金额也会比例式地上升。尽管手续费本身只不过是考虑到行政机关的事务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设定的,〔22〕参见前注〔13〕,宇賀克也书,第151~156页。但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滥用式的公开申请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近年的应对
如上所述,作为日本信息公开的伴生性问题,“权利滥用”一直困扰着理论与实务界,而且近来呈现出愈发严重的态势。鉴于此,在信息公开已经步入制度安定期的近年,理论与实务界大多主张,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首先在国法层面,《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于2011年4月迎来了它实施后的第10个年头。日本计划于2011年对《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等进行首次大幅修改。〔23〕有关这次修法的详情,参见前注〔1〕,石龙潭文,第80~85页。另外,该修正案于2012年11月在审议中途即成为废案,2013年以民主党 (当时)案的形式虽再次提交国会,能否获得执政党的赞同、审议通过依然属于未知数。不过,即便如此,由于该法案的内容是基于前十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所拟定的,基本上代表了当前的问题意识与改革方向。同时,就设立禁止权利滥用条款的性质本身而言,至少在结果上它是对行政方有利的改革,很难想象今后会因行政机关的反对而夭折。为了迎接这次修改,早在2010年4月就设立了由内阁阁僚及专家学者等组成的“行政透明化研讨小组”,就行政透明性的应然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制定《信息公开法修正案》的过程当中,立足于使用者的立场,为了使该制度更加便于公众利用,倾向于原则上废止公开申请手续费并降低公开实施手续费。〔24〕在修正案中,立足于让国民更加便于行使公开申请权的观点,规定废止公开申请手续费的同时,考虑到申请权行使内容的实际状况,针对所谓的商业性利用,站在受益者负担的立场,与现行法相同,规定继续征收公开申请手续费。但是由于担心由此会招致公开申请权的滥用,是否应该以明文的形式设置禁止滥用条款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2010年《行政透明化研讨小组总结报告》即所谓大臣案中,作为“5-(2)”写明,“伴随 (1)的公开申请手续费的废止与公开实施手续费的减额,应当明确正当的公开申请以及正确利用被公开信息等观点”。受此影响,在2011年4月22日提交国会的《信息公开法修正案》中,在原有第5条文本 (当有人申请行政文书公开时行政机关负有公开义务)的基础上,追加了但书条款:“但当该申请相当于权利滥用、有违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风俗等时,不在此限。”即以明文的形式规定,当公开申请属于权利滥用等时,行政机关不负有公开义务。
此外,考虑到行政在实施公开决定时所花费的成本,作为针对权利滥用式申请 (如大量申请后却拒绝接受公开等)的应对之策,在适用公开决定等处理期限的特例的同时新设了“预交手续费制度”(第16条第5—7款)。即在适用处理期限的特例规定之际,当行政机关于当初的公开决定期间内对被申请公开对象文书的相当部分已经做出公开等决定时,申请人在得到通知后的30天之内,必须预交剩余的行政文书若全部公开时所应缴纳的公开实施手续费 (其金额由政令在所需金额的范围内确定)。〔25〕关于“预交手续费制度”,有学者认为,这固然是一个好办法,然而遗憾的是,它只对大量申请有效但对反复申请却显得力不从心。参见前注〔10〕,曽我部真裕文,第325页。
其次,在地方自治体层面,如前所述,当初大多认为,如果在信息公开中出现权利滥用,应该通过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加以应对。可是,即便是针对如本文中所列举的那种极端事例,多数地方自治体对于是否应该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也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法无明文根据情况下适用该法理存在心理抵触。于是,有的地方自治体开始修改信息公开条例,增加相关根据条款。非营利组织“全国市民监督专员联络会议”〔26〕该组织的日文名称为“全国市民オンブズマン連絡会議”。该团体是为了监督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等的不正当或违法行政活动并对其予以纠正,作为市民监督专员信息交换、经验交流以及共同研究的平台,于1994年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现由分布在全国的77个市民专员团体组成,总部设在名古屋。有关该团体近年活动的详情,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杉本裕明『社会を変えた情報公開―ドキュメント·市民オンブズマン』(共栄書房、2016年)。于2013年公开发表的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中是否存在以权利滥用为由“可以拒绝或驳回”规定的调查结果 》〔27〕该文件的日文名称为“情報公開条例 権利濫用で 「拒否·却下できる」規定 調査結果”。这个调查,是以了解全国的地方自治体信息公开条例当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的规定为目的而实施的。继2010年、2012年之后,本次为第三次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7月31日,在其调查的47家都道府县、783个市、23个特别区中,有72家地方自治团体在信息公开条例中设定了禁止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内容,占8.3%。而这个比率近年还在逐年增加,比如,2016年4月开始施行的修改后的《久留美市信息公开条例》,除了在第7条和第11条中追加了有关权利滥用的记述之外,还就何谓权利滥用、何种场合才相当于公开申请权的滥用以及权利滥用的具体类型等,另行制定了《关于公文书公开申请中的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28〕该文件的日文名称为“公文書開示請求の権利濫用に関する判断基準”,载https://www.city.kurume.fukuoka.jp/1500soshiki/9008soumu/3010oshirase/2016-0328-2305-189.html,最 后 访 问时间:2018年7月16日。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所谓“权利滥用”,一般是指某行为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权利行使的外观,但若从该行为的具体内容以及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其脱离了权利的本来目的,因此无法被视为正当权利行使的行为。
第二,判断是否相当于权利滥用之际,应该在考虑公开申请的样态、应允公开申请时对实施机关工作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一般市民所蒙受的不利影响等基础之上,就其是否超越了社会常识所允许的妥当范围加以个别判断。
第三,诸如以给实施机关工作造成混乱或停滞为目的、明显背离了公开申请权的本来目的的公开申请等,就相当于权利滥用。
第四,公开申请中的权利滥用的类型包括:(1)在请求公开之际就事先表明不予阅览、不接受复印件的交付以及其他拒绝公开实施之意,或者只是请求公开,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反复出现拒绝阅览、拒绝接受复印件的交付,以及拒绝缴纳与复印件交付相关的费用等行为的。以这些行为来判断,申请人显然不具有接受公开之意。(2)尽管已经知晓与公开申请相关的内容,但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然反复请求公开同样内容,或者撤回已经提交的公开申请之后,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对同一内容的文书反复请求公开的。显然,其公开申请的目的不在于公文书公开本身。(3)集中对同一实施机关连续请求公开,从公开申请的样态、内容以及公开申请人的言行等判断,显然抱有削弱实施机关的工作能力或者使实施机关的工作停滞等恶意的。(4)集中对由特定工作人员制作和取得的公文书连续申请公开,或者在公开申请之际针对特定工作人员予以诽谤、中伤甚或采取威胁态度,从公开申请的样态、内容以及公开申请人的言行等来看,显然对特定的工作人员抱有恶意的。(5)有可能违法或不正当使用因公开而获得的公文书的。
第五,当公开申请的对象文书数量特别巨大时 (限于与公开申请相关的文书已经确定,即被要求公开的文书能够与其他文书明显区别开来的场合),不得单纯以数量巨大为由拒绝公开申请,也不得向公开申请人暗示有可能拒绝。应当通过要求对申请公开的范围予以限定、依据条例第13条的规定对决定公开与否的期限予以延长等应对。
第六,是否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应在依据本基准以及公开申请人的言行、公开申请的内容与方法等,同时综合考虑公开申请给实施机关工作所带来的停滞以及其他各种要素的基础上慎重判断。必须注意避免发生轻易做出不公开决定 (拒绝)的情形。此外,在适用时,除事先与总务部总务科协商之外,还应征询律师等的意见。
与国家与地方层面均出现禁止权利滥用规定的明文化动向相并行,近年,围绕行政文书的公开申请,出现了将私人方的申请权行使判定为权利滥用的事例,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比如,在“横须贺市行政文书公开申请拒绝处分撤销案”中,原告X向该市申请公开土木部用地科在某年度工作中所产生的所有公文书、资料以及业务委托、物件等的合同书等,就此,被告横须贺市曾经再三要求X就到底要求公开何种信息在内容上进行补正,但X均予以拒绝。该市考虑到本案对象文书的数量非常巨大 (多达120个纸盒箱),于是以“实施本案所申请的公开,超出了条例所预想的执行业务的合理范围,本案申请不属于权利的正当行使”为由,作出拒绝公开的决定。于是X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分。一审法院在承认本案文书已经确定 (即当时有相当于120个纸盒箱的文书由市里保管,显然作为申请对象能够与其他文书区别开来)的基础上指出,本案条例之所以要求公开申请人要正当行使公开申请权,是因为即便公开申请权受到认可,也不意味着该权利通常不受任何制约。显然,条例要求在权利行使之际要符合公文书公开制度的目的,不允许与该目的不相符的公开申请,对于超出制度目的的申请应该以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应对。但在以权利滥用为由实施具体判断时必须慎重,只有申请在客观上给实施机关的工作带来显著妨碍,并且申请人在主观层面上是以阻碍行政机关的工作为目的等特殊场合方能认定。最后,判决本案存在权利滥用、驳回X的请求。〔29〕横浜地判平成22·10·6判例地方自治345号25頁。
可见,针对申请权的滥用,法院主张可以适用作为一般法理的禁止权利滥用的同时,要求在具体实施判断之际必须慎重,并附加了以下的条件:申请在客观上给实施机关的工作带来显著妨碍,并且申请人在主观层面上是以阻碍行政机关的工作为目的。而这与前述学界所主张的“需要就是否存在使行政停滞的意思进行举证”以及实务界所主张的“除非存在以使行政机关工作停滞、混乱等为目的的情形”等一脉相承。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早期,立法者已经预想到了大量申请的情形,并就应对之策预设了处理期限的特例。尽管在国法以及大多数地方自治体的条例当中,均不见直接应对滥用公开申请权的规定,但以作为法的一般原理的禁止权利滥用来应对可以说是立法者的初衷。同时,虽然手续费在防止权利滥用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而到了制度安定期的近年,《信息公开法修正案》除了以明文的形式规定公开申请属于权利滥用时行政机关不负有公开义务之外,还新设了作为针对权利滥用式申请的应对之策的“预交手续费制度”。同时,地方自治体信息公开条例中也出现了增设禁止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规定的势头。可见,禁止权利滥用规定的明文化和将其与手续费挂钩是近年理论与制度上应对的特征。另外,司法也一改往日的消极态势,出现了将私人方的申请权行使积极认定为权利滥用的事例。
四、禁止权利滥用的若干问题
(一)信息公开与禁止权利滥用原理的适用
严格来讲,禁止权利的滥用,在私人方与行政方都会成为问题。在私人方,其代表例有申请权的滥用。〔30〕桜井敬子ほか 『行政法〔第4版〕』(弘文堂、2014年)26頁。现行法中,信息公开制度中的公开申请权不问请求目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申请。因此,同一申请人针对同一事项反复提出申请,或者一次性要求公开大量的行政文书等行为,是否相当于公开申请权的滥用成为问题。那么,信息公开中当行政机关认为公开申请属于权利滥用时是否可以通过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理予以拒绝即实施不公开决定呢?有关这一点,学说与实务中主要存在着以下的几种观点。
1.肯定说
虽然2011年提交国会的《信息公开法修正案》中增设了明文规定,但该修正案于2012年即成为废案,至今悬而未决。因此,现行信息公开法中仍不见有关申请权滥用的明文规定。尽管如此,学界一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原则的禁止权利滥用原理的射程同样及于该种行为。〔31〕同上,第27页。换言之,如果属于权利滥用就可以作出不公开决定 (拒绝)这一点,作为法的一般原则是允许的。
而从实务界来看,如上所述,在总务省出台的《依据〈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实施行政处分时的审查基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当公开申请相当于权利滥用时行政机关可决定不予公开。同时,《信息公开法要纲案的基本观点》以及《信息公开法修正案》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2.否定说
但也有个别学者主张,在信息公开中不允许以权利滥用为由拒绝公开。这种观点强调,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的知情权以及督促行政机关面向主权人践行自己所肩负的说明责任。因此,在其制度的本来框架内,既不问公开申请的目的 (因何而申请公开)又不在意申请人的主观意图 (学术研究还是商业性利用等),同时也不过问如何利用通过公开申请而获得的信息。
在判断申请对象的信息是否可以公开之际,行政机关不应考虑公开申请人的意图以及利用目的等。被申请信息是否属于可以不公开的例外事项,应结合信息本身客观判断,而不应该受公开申请人是谁、公开申请的意图何在、公开申请人的利用目的等左右。
近年,地方自治体的信息公开条例中,有的增设了公开申请人的责任与义务规定等,但是,这类规定无非是伦理性规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公开申请是否可以拒绝,无论在国法还是地方条例层次,归根到底只能以是否属于法规所明定的可以不予公开的例外事项来判断,而以包括权利滥用在内的其他理由来拒绝公开当属违法。以权利滥用为由拒绝公开,无非是给滥用拒绝公开之举开了绿灯。公开申请既然合法,就不允许拒绝公开。〔32〕松井茂記『情報公開法〔第2版〕』(有斐閣、2003年)60~62頁、143~144頁。
尽管否定说在强调制度本质以及追求彻底的信息公开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通说则站在肯定说的立场上,主张即便是在信息公开领域也应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理,这一点无论从立法者的初衷,还是从导入信息公开制度早期以及近年的应对上来看都是相同的。
(二)禁止权利滥用明文化的可否
不过,在围绕是否应该对该原理加以明文化处理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1.肯定说
肯定说主张应该把有关权利滥用的规定写入相关法规,这种呼声主要来自于信息公开的实施现场。我们同样以大阪市为例,宮之前亮氏指出,针对滥用式的公开申请,在条例制定当初一般认为以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应对即可。可是,一旦碰到具体事例,到了具体适用阶段,就会因在缺少明文规定的前提下是否可以适用、将市民视为权利滥用者是否合适等而瞻前顾后,实际上该一般法理一直没有得以适用。〔33〕参见前注〔5〕,宮之前亮文,第36~37页。因而,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大多希望能够制定相关根据规定。在一个强调“依法律行政”的国度里,对于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而言,只有理论上的抽象的适用可能性显然不够,在具体案件的应对之际,当然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关根据。近年,由于担心遭遇权利滥用,有的地方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增设相关根据条款,这无疑是上述主张的结果。
2.否定说
以“全国市民监督专员联络会议”为代表的非营利团体等,由于担心一旦在现行法中增设有关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定,该条款本身就有被行政机关滥用之虞,因此对于明文化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在《关于信息公开条例中是否存在以权利滥用为由“可以拒绝或驳回”规定的调查结果》中,该团体指出,“既然所谓的相当于权利滥用是指以任何人的眼光来看都无须对当事人的权利行使予以保护的场合,那么就没有必要以条文的形式来明定。用条文对权利滥用加以特别界定,似乎给在不相当于权利滥用的场合也可以以‘权利滥用’这一新的理由来加以驳回埋下了伏笔”。由于在信息公开中该团体始终扮演着督促行政机关彻底实施信息公开的角色,因此产生上述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后,在修改信息公开相关法规、设定权利滥用规定之际,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利滥用规定的危险性也要有所考虑。
3.折中说
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针对是否应该设置有关权利滥用的明文规定持开放态度,主张入法也好不入法也罢,该原理都是客观存在的。宇贺克也教授指出,“《日本国宪法》第12条禁止国民滥用权利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即使国民具有申请权,但在出现申请权滥用时,该申请也会因不合法而遭到拒绝。这一点,与是否存在禁止权利滥用的明文规定无关”。〔34〕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説Ⅰ行政法総論〔第5版〕』(有斐閣、2013年)53頁。盐野宏教授也指出,将权利滥用写入法律与否并非是本质性问题,如果说把权利滥用的要件也一同写入另当别论,否则写不写都无所谓。〔35〕塩野宏発言「情報公開法の10年―法制化と運用〔第3回〕」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46号17頁。
可见,在是否应该对该原理加以明文化处理上日本尚未达成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在制度安定期的近年国家与地方层面均出现禁止权利滥用规定的明文化动向,但从“全国市民监督专员联络会议”所做的《关于信息公开条例中是否存在以权利滥用为由“可以拒绝或驳回”规定的调查结果 》来看,导入相关内容的地方自治体的比率还不算太高。
(三)权利滥用还是文书不确定?
信息公开领域可以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理,就此学界与实务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针对大量申请,多数地方自治体和法院都是通过运用该原理来应对的。然而,在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时,由于现实中碰到了不易举证、判定基准不明确、实施机关援用时容易产生犹豫等问题,〔36〕参见前注〔10〕,曽我部真裕文,第308、315页。近年出现了不以权利滥用而是以作为被申请对象的行政文书没有确定来处理的先例。
前述“横须贺市行政文书公开申请拒绝处分撤销案”中,其二审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针对X提起的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主张,这种要求公开特定部署所有文书的概括式申请,虽然在形式与外形上暂且明确,但是不相当于本案条例所定的“公文书指定的必要事项”的记载。而且,申请人并不真正希望全部阅览文书,也不存在能够在所定期限内全部阅览完毕的特殊情况。迫使工作人员对并非申请人要求的文书也要展开同样的调查与判断之举,无非是为了使实施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产生疲敝,不仅会给行政机关的其他工作带来停滞,而且还会抹杀将“公文书指定的必要事项”作为必须记载事项这一规定的宗旨。以该宗旨来看,对文言加以形式性的解释未必正确。〔37〕東京高判平成23·7·20日判例地方自治354号9頁。上述判决,作为本领域的少数先例之一具有重大意义。即针对公开申请人的大量申请,它提醒我们可以通过对象文书的确定性这一要件来加以应对。〔38〕佐伯彰洋「行政文書公開請求拒否処分取消請求控訴事件」判例地方自治365号17頁。
同时,内阁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在就某个大量申请案件所做的答复意见中指出:要求公开特定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全部行政文书这种申请,尽管文书范围在形式与外形上大体明确,但是,一般而言,行政组织的活动多种多样,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人申请公开与其相关的所有文书。此外,如果容许这种概括式的申请,作为其对象的文书势必数量巨大,不仅申请人自身难以阅览、誊写,同时也会给行政工作带来极大的妨碍。因此,这种概括式的大量申请,作为申请权行使对象的文书尚未确定。文书的确定这一概念,是为了正确且顺利地运营公开申请制度而设立的功能性概念,可以对其加以如上所述的解释。〔39〕内閣府情報公開個人情報審査会平成20年度 (行情)答申308号。
这种被称为“文书确定的能动性解释”〔40〕藤原静雄「参加者から要望のあったテーマについて―権利濫用の法理と判例の動向」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47号17頁。的手法,作为规避适用权利滥用原理的手段受到学界的瞩目。有学者认为,针对大量申请作为应对之策可以考虑适用权利滥用和文书的不确定等,今后有必要探讨对“确定”这一概念做能动性解释,在综合实施机关的负担、对象文书的分量、公开的困难性等要素之后,结合信息公开制度的宗旨来判断对象文书是否确定。〔41〕藤原静雄発言「第6回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等委員交流フォーラム概要」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31号23頁。
也有人着眼于,“横须贺市行政文书公开申请拒绝处分撤销案”的一审也主张应该慎用权利滥用的法理,但却判定本案公文书已经确定并另行做出权利滥用的判断路径,同时考虑到不能够单纯以文书的数量巨大来认定权利的滥用已经成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共识,因此主张,如一审那样,即便是大量请求,也对文书的确定性要件予以宽泛解释,然后另行对权利滥用进行探讨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方法。然而,若另行对权利滥用进行探讨,鉴于不问公开申请目的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宗旨,就不得不慎重适用权利滥用的法理,因此无法成为针对大量申请的有效应对之策。相反,如二审判决那样,若把权利滥用的要件植入文书的确定性要件当中,就没有必要再对权利滥用予以另行探讨,对公开申请也较易拒绝。从而肯定了利用文书的确定性这一要件来加以应对的可能性。〔42〕参见前注〔38〕,佐伯彰洋文,第18页。
还有学者主张,作为大量申请应对之策的权利滥用与文书的确定并非势不两立,两者相互补充,应适当分工,可以并用。尽管近年出现了东京高等法院等以文书是否确定的问题来处理的先例,但总体而言,还是应该以权利滥用来应对。〔43〕参见前注〔10〕,曽我部真裕文,第314、316、326页。
可见,面对大量申请,是应该以权利滥用还是文书不确定来应对,日本并没有形成共识。两者处于不同层次,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明确。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般市民,并不知晓行政的内部情况,而且即便检索目录已经完善,由于民众对于何种文书到底载有何种内容不易知情,因此在公开申请书中书写一些概括式的内容也在所难免。如果把权利滥用的法理纳入到文书的确定性要件当中,恐怕正当的申请也有受阻之虞。〔44〕参见前注〔38〕,佐伯彰洋文,第18页。
(四)今后的课题
从日本信息公开的现实和“权利滥用”的应对来看,有待今后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
第一,作为权利自身属性的问题,从公众参政的视角来看,要求公开行政文书的权利,虽然在法律上是以主观权利的形式构成,但实质上却有可能作为客观权利来行使,或许有必要对其在理论上重新定位。这种权利的行使,即便在主观上符合公共福利原则,但也有可能会在客观上与其发生冲突。〔45〕参见前注〔19〕,濱西隆男文,第41页。因此,摆脱理论的束缚,明确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法律属性恐怕是当务之急。
第二,至今为止,信息公开制度中所谓的权利滥用到底是指何物,人们就此尚未达成共识,从而在判断之际缺乏客观性,这是导致适用时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46〕参见前注〔5〕,宮之前亮文,第36~37页。因而,在明确界定权利滥用的基础上确立客观且公正的判断基准也是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三,对于私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行使权利时到底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适用禁止滥用权利原则,在理论上至今尚未完全厘清。〔47〕参见前注〔19〕,濱西隆男文,第36页。
第四,对于权利滥用式的公开申请,除了在信息公开法规当中适当增加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以及征收手续费等内容修改之外,还可以考虑靠窗口应对,即通过劝说、开导、说明等行政指导来应对。但是,光靠这些手段是不够的,今后需要在法规的解释论、制度改革论等层面上展开广泛讨论,找出既可以真正对权利滥用式的公开申请予以驳回,又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这种权限的两全之策。〔48〕参见前注〔10〕,曽我部真裕文,第306~307页。
第五,面对大量申请,除了权利滥用之外或许还可以考虑以文书不确定来应对,然而后者针对反复申请或者大量行政争讼等则显得力不从心。
五、结语——兼谈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在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务当中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权利滥用”这一课题。作为应对之策,尽管存在少数反对意见,但主流观点还是主张有必要通过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法理来加以积极应对。同时,何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应该如何确立、到底何种场合才适合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理、“文书确定的能动性解释”能否成为替代适用权利滥用原理的有效手段等等,有待今后理论与实务进一步发展,需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形来加以整理和探讨的课题依然很多。
结合日本的现实与应对,笔者认为中国今后在修改或制定信息公开法规之际,可以考虑适当设置有关禁止权利滥用的条款。但是需要注意,在把相关规定写入法规时最好能够以指南等方式出台一些与之配套的细则。这是因为,入法也好不入法也罢,禁止权利滥用原理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盐野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制定具体的判断基准,单纯地把禁止权利滥用写入法规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不能单纯停留于禁止权利滥用条款的设置,还要对该条款遭到行政机关“滥用”的危险性有所考虑,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依笔者看来,在这一点上,2016年实施的《久留美市信息公开条例》给了中国很好的启示。即除了在法规中设置有关权利滥用的抽象条款之外,还另行制定了《关于公文书公开申请中的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其中就何谓权利滥用、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权利滥用的典型事例、权利滥用的类型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时还规定,当公开申请的对象文书数量巨大时,不得单纯以数量巨大为由拒绝公开,而应通过要求对申请公开的范围予以限定或者利用特例期限等应对。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是否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理,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慎重判断,避免发生轻易拒绝的情形。
此外,久留美市为了在具体适用作为一般法理的“禁止权利滥用”时能够保持审慎,又进一步要求:第一,应该在充分考虑到《久留美市信息公开条例》的宗旨 (保障知情权、行政的说明责任)的基础上,慎重适用;第二,听取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充分研讨;第三,适用“禁止权利滥用”法理实施行政处分之际,需向由律师等组成的第三方机关“久留美市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报告。〔49〕「公文書開示請求の権利濫用に関する判断基準を定めました」https://www.city.kurume.fukuoka.jp/1500soshiki/9008soumu/3010oshirase/2016-0328-2305-189.html,2018年8月6日アクセス。
上述久留美市的尝试,当然无法解决信息公开与“权利滥用”的全部问题,但对于思考何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应该如何确立、到底何种场合才适合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等,颇具启发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及积极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说明责任,始终是信息公开的主题与使命。作为制度衍生品的“权利滥用”的解决,不宜也不能“矫枉过正”。
最后,请允许笔者说句题外话。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行政法学者,笔者对于日本重视信息公开的组织与平台建设颇有感触。比如在各级行政机关除了配备专职人员司职信息公开之外,还设置了诸如“都道府县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会”、“大城市信息公开等主管人员会议”等交流平台。同时还创办了一份专业杂志〔50〕该杂志的日文名称为“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并通过这份杂志定期发表有关信息公开等的权威文件与统计数据、召集“全国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等委员交流研讨会”、为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甚至社会人士提供平台发表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等,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各界间的横向与纵向交流,提高了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因此,中国是否可以考虑在国务院主管部门牵头下设立各级政府专职人员间的各种交流组织,同时由国务院亲自或委托高校等主办一份有关信息公开 (也可涵盖个人信息保护甚至公文管理等领域)的专业杂志,为相关人员的信息交流、理论研究等提供一个定期而可靠的平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