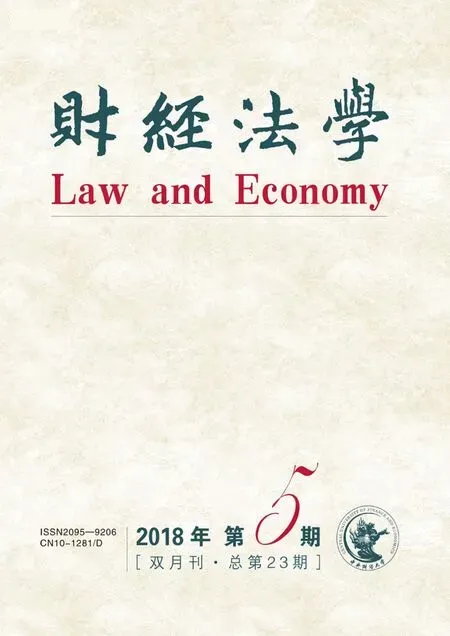“宪法上人权”的效力不及于私人间
——对人权第三人效力上的“无效力说”的再评价
[日]高桥和之 著
陈道英 译
前言
宪法上的人权规定在私人间是否具有效力的理论,即所谓“私人间效力论”或“第三人效力论”是人权总论中的一个重要论点。传统的宪法理论认为人权是针对国家的权利,仅适用于国家 (或公权力)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就现代而言,由于私人间频发重大的人权侵害事件,无法应对这一问题的人权理论就无法负担起最大限度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学的使命。各种形式的认为人权规定的效力也及于私人间的理论构成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在这种问题意识下,传统的非适用、无效力说遭到了轻易的抛弃。现在,以私人间适用为当然的前提,围绕着如何适用的技术问题存在着间接适用说与直接适用说的对立。除此之外,认为这种对立毫无意义而主张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宪法适用说”也得到了提倡,最近甚至还出现了利用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这一新的观念来重新认识间接适用说的观点。〔1〕关于学说的现状,参见了以下文献。芦部信喜『人権保障規定の私人間における効力』公法研究26号 (1964年),同「私人間における基本的人権の保障」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基本的人権I総論』(1968年)(同に芦部『現代人権論』[有斐閣,1974年]所収),芦部編『憲法II人権 (1)』(有斐閣,1978年)「第2章 私人権における人権の保障」[芦部],阿部照哉「私人権における基本権の効力」公法研究26号 (1964年)(同『基本的人権の法理』[有斐閣,1976年]所収),同「私法関係と基本的人権」憲法の判例 [第3版](ジュリ増刊)(1977年)4頁,同「私法関係と人権 (三菱樹脂事件)」憲法の基本判例 (別冊法教) (1985年)14頁,中山勲「人権保障の私人間に対する効力」坂大法学55号 (1965年)66頁,同「基本権の第三者効力論再考——西ドイツ型のアプローチについて」坂大法学141=142号 (1987年)275頁,今村成和「政治的思想信条による雇用上の差別」法時509号 (1971年)37頁 (同『人権と裁判』[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1973年]所収),三並敏克「基本権の第三者効力 (一)」立命館法学96号 (1971年)8頁,同「基本権の第三者効力論——西ドイツにおける直接的効力説の検討とデューリッヒ学説に対する批判的検討を中心にして」立命館法学116=117=118号 (1974年)29頁,中村睦男「私法関係と人権」ジュリ500号 (1972年)26頁,山口精一「人権と私法関係」日本国憲法——30年の軌跡と展望」(ジュリ638号臨時増刊) (1977年)257頁,同「私人相互間における権利保障」憲法の争点 [新版](ジュリ増刊) (1985年)58頁,同『基本権の理論』 (信山社,1996年),稲田陽一「人権の私人間の適用」憲法三 0 年の理論と展望 (法時594号臨時増刊)(1977年)34頁,木村俊夫「『基本権の第三者効力』理論の再検討」九大法学34号 (1977年)29頁,同 「シュワーべの基本権効力理論」九大法学40号 (1980年)1頁,木下智史「私人間における人権保障と裁判所——ステート·アクション論に関する覚書」神戸学院法学18巻1=2号 (1987年)79頁,同「私人間における人権保障と裁判所·再考——私人間効力論を超えて」 『現代立憲主義と司法権 (佐藤幸治還曆記念)』(青林書院、1988年)205頁,釜田泰介「人権規定の効力」憲法の基本問題 (別冊法教)1988年)160頁,棟居快行『人権論の新構成』(信山社,1992年),同「人権の私人間効力」憲法の基本判例 [第2版](法教増刊)(1996年)14頁,中野雅紀「第三者による侵害に対する基本権保護」大学院研究年報·法学研究科篇 (中央大学)22号 (1992年)1頁,山本敬三「現代社会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と私的自治 (一)(二)」法学論叢133巻4号1頁·5号1頁 (1993年),小山剛「基本権保護区の法理」(成文堂,1998年),同「私人間における権利の保障」憲法の争点[新版](ジュリ増刊)(1999年)54頁,山崎栄一「基本権保護義務とその概念の拡大」六甲台論集·法学政治学篇43巻3号 (1997年)189頁,君塚正臣「伝統的第三者効力論·再考 (一)(二)——日本の憲法学は憲法の私人間効力をどう考えてきたのか」法学論集 (関西大学)50巻5号 (2000年)124頁·6号 (2001年)105頁,榎透「人権規定を私人間に直接適用しないことの意味」比較社会文化研究 (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分化研究科)7号 (2000年)1頁,同「『国家からの自由』と 『国家による自由』の交錯——ステイト·アクション法理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2002年),中山茂樹「私人間効力について——憲法上の権利の概念の整理から」法学論集 (西南学院)33巻4号 (2001年)95頁。但是,这些观点都是德国学说压倒性影响的产物,虽然对美国的政府行为理论有所参考,但对法国的情况却完全置之不理,从整体上讲,讨论具有强烈的、作为特例的德国的味道。当然,即使是德国的理论,如果的确是与日本的问题相适应的理论,对其进行参照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检视迄今为止的日本的讨论就可以发现,原来倡导私人间效力理论的论者并非是在直面传统理论在日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传统的非适用说为什么面临着困境?这种情况下的非适用说究竟是怎样的理论?在法国,依笔者的愚见,至少直到现在,认为即使是在私人间也应该承认人权效力的观点在正式承认人权规定的法律效力后,似乎再没有其他论述,也没有当然予以适用的观点,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法国的学说是以“非适用说”为前提的。如果即使是这样,也不认为存在困境,又是为什么?也许,那是因为法国在对“非适用说”的理解方法上与德国和日本有所不同的缘故。此外,美国的政府行为论虽然在日本被理解为是间接适用说的一种形式,但它实际上是以“非适用说”为前提的。美国宪法的人权规定仅仅适用于政府 (公权力)的行为 (action),也就是说不适用于私人,因此这一理论扩大了“政府行为”的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将私人的行为纳入到政府行为的范围之中,这才是该理论的根本。由此看来,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来看,不正是“非适用说”即使是在现代人权论中也构成了原则吗?产生这样的疑问也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至少,“适用说”构成了例外。如果是这样的话,笔者认为应该将这种特殊的思考方式的由来意识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应该追求的理论进行再思考。本稿即为这样的一种尝试。在本稿中笔者试以确立了近代立宪主义的典型理论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人权思想为模型,将私人间效力理论的无意识的前提意识化。
一、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人与市民权利宣言”)虽然是宣布应该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原理的文件,但近代立宪主义的人权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众所周知,该宣言以近代自然权思想为基础,这一点在《宣言》的第1条(“在自由与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2〕有关《人权宣言》的条文,由译者依据英文版译出,载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rightsof.htm,最后访问时间:2007年8月18日,并参考了中文译文,载 http://www.chuanjiaoban.com/bkck/show.php?itemid=12,最后访问时间:2007年8月18日。——译者注。)及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由于自然权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权利,因此在国家成立以前对任何人都得主张,在理论上不能称之为“对国家的权利”。这一点,从《宣言》的第4条也可明了。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得为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均只以保证社会其他成员得享同样的权利为限”,认为自然权利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制约,也就是可以相互主张的权利。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人权在进入政治社会以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呢?进而,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规定政治社会结构的是宪法。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并非宪法,仅仅是规定此后将要制定的宪法应该引为依据的原理的文件,作为这种文件,人权宣言在1791年《宪法》的开头得到了记载。接着开头的人权宣言,1791年《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国民会议欲在其刚刚承认及宣布的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法国宪法,兹不可逆转地废除各有害于自由及权利的平等的制度”,〔3〕有关1791年法国《宪法》的条文,由译者依据英文版译出,载http://sourcebook.fsc.edu/history/constitutionof179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7年8月18日。——译者注。其后又对应予废除的各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列举。此外,其后的第1编“宪法所保障的根本规定”也将担任公职、纳税、刑罚的平等,居住、迁移、身体的自由,言论、出版、宗教的自由,集会的自由,请愿的自由等各种权利作为“自然的、市民的〔4〕英文为 civil。——译者注。权利”予以保障。由此,自然权就转变为了“宪法上的权利”。但是,自然权并未因做出上述规定的段落使用了“宪法将 (以下权利)作为自然的、市民的权利加以保障”的固定用语被宪法化,而在观念上丧失了自然权性。不仅如此,如同从同一个地方的“立法权不得制定有害或妨碍本编规定的、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的、市民的权利之行使的法律;但是,由于自由即得为一切无害于他人或公共安全的行为,法律得针对攻击公共安全或他人权利从而可能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规定处罚”的规定也能够知道的,人们预设权利间会产生冲突,并期待由法律来调整这一冲突。这一点从《人权宣言》第4条就可以看出来。该条规定:“自由就是得为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均只以保证社会其他成员得享同样的权利为限。此类限制只得由法律规定之。”这就假设了自然权利之间会产生相互冲突,而对这种冲突的调整由法律来进行。这一原理由1791年宪法“宪法化”。而且,意味深长的是,1791年《宪法》在第1编的结尾授命立法者“制定在王国全土通行的民法典 (Code de Lois civiles)”。这就是以自然权利思想为基础,期待由民法典对私人间的民事关系进行调整。
由以上分析可以明了制宪者的如下构想。首先,其出发点是一切个人均享有得对任何人主张的自然权利。国家的目的就是保护这种自然权利,由此国家也就负担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制定了宪法并组织了国家。宪法将自然权作为宪法上的权利加以规定并责成国家机关对其保护与尊重。由此,“宪法上的权利”的对象是国家,尤其是立法权受到这一“宪法上的权利”的拘束 (第1编)。进而,执行权与司法权受到来自法律的拘束,由此实现对宪法上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私人间的自然权利冲突的调整,也就是自然权利的保护则是由法律来承担的。从《人权宣言》“(权利的)限制由法律规定之” (第4条)以及“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第5条)之规定可以看出,私人间权利的调整是法律的专有领域,宪法上的人权规定不被假设为适用于这一领域。简而言之,人权,作为自然权利,虽然在私人间也具有效力,但对它的调整是由法律来进行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肩负着不得“有害或妨碍本编规定的、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的、市民的权利之行使”的义务 (尊重义务)。那么,私人间的人权保障是如何进行的呢?首先,通过对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处罚加以保障。上文所引用过的“法律得针对攻击公共安全或他人权利从而可能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规定处罚”的规定应该说表明的就是这种假设。实际上,在制定1791年宪法的同时就制定了刑法典 (Code péna des 25 septembre-6 octobre 1791)。其次,由民法典进行保障。1791年宪法授命制定民法典就可以看作是与这种假设相呼应的结果。这时的民法典当然应该被假设为是以人权宣言表明的原理为基础的。实际上,其后制定出来的拿破仑民法典被认为是调整革命后确立的新社会的私人间关系的基本法。因此,宪法首先规定立法权不得制定侵害人权的法律,其次将国家保障私人间人权的义务交由以刑法与民法为中心的法律来履行。这样,宪法将国家作为对象,并未假设其在私人间得到适用。私人间的人权 (自然权利)的保护与调整委之以法律来进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上的人权在私人间的“非适用、无效力说”。但是,既然认为由法律对自然权利进行调整,那么也就当然可以推定自然权思想在法律的解释上得到了事实上的反映。
二、立宪君主制下的理论
拿破仑失败后复辟的波旁王朝由于复活了封建制度的君主制原理而自然不可能接受以自然权的人权和国民主权为基础的革命原理。话虽如此,但是它也不可能无视革命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所产生的社会与意识上的变化。因此波旁王朝采取了在维持君主制原理的理论的同时承认国民一定权利的战略。也就是说,回避采用具有革命色彩的制定“宪法”(constitution)的语言,而以封建制度下国王对城市、团体及公司等赋予特权时采用的“特许状”(Charte)的形式承认了“臣民”(sujets)的“法兰西人的公权”(Droit public des Francais)。这一文书即《1814年6月4日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elle du 4 juin 1814)。在这份文件中,作为法兰西人的公权,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论地位、称号)、与纳税的财产成比例的平等、担任公职的平等、人身自由、宗教自由 (只是天主教为国教)、言论及出版的自由、财产权等。但是这些权利都是主权者的君主向臣民赋予的作为“法兰西人的公权”的权利,与在君主存在以前即应享有的自然权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由君主赋予的权利只能向君主主张。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说,在君主单方面规定的宪章中,会不会假设私人享有对其他私人的权利是个很大疑问。该《宪章》未安排预设私人间权利冲突的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也并非偶然。但是,由于《宪章》规定了民法典 (拿破仑民法典)只要与该宪章未有抵触,在修正之前均有效力 (第68条),《宪章》所赋予的公权从内容上讲与革命时期的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可以说是基本上相同的。如果这样考虑的话,民法典应该说是继续作为调整私人间关系的体制而存在。但是,从法理上而言,应该说是成立了切断与自然权思想的关系的实定法理论。因此,民法典所调整的已经不是人权 (自然权)的冲突了。那么是否是公权的冲突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权是只能对君主主张的权利,从法理上讲在私人间是无所谓公权的冲突的。当然,实际上某一私人的公权的行使与他人的公权行使在事实上是无法并存的。但,这至多只是事实上的冲突,而谈不上是得相互间主张的权利的冲突。虽说如此,也不能因为是事实上的冲突就置之不理。因此,法律为了避免产生事实上的冲突而对公权进行了限制。在立宪君主制下,对公权的限制原则上由法律予以保留。因此,在这里由法律加以调整的情况也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在不能说是由法律对私人间的权利冲突进行调整这一点上,与1791年宪法在理论上是存在差异的。
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下的理论也基本相同。在德国,虽然实证主义国家法学将公权的赋予者由君主转换为国家,但在切断了公权与自然权的联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其理论构造并无二致。由于公权并非先于国家的权利,因此也不存在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公权的理论。国家 (君主)虽然为了独立的目的 (例如警察国家的目的)而介入社会,但其承诺在介入社会时尊重国民的公权。因此,这种公权被假设为是对国家主张的权利。不仅如此,德国的国家法学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理论前提的,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分别,公权强调其公法性,这就更强调和纯化了不适用于私人间关系的观念。〔5〕君主 (国家)虽然负有尊重对臣民约定的“公权”的义务,但这一“公权”并非对私人的权利,不存在私人侵害公权的理论,因此国家并不负有“保护义务”。正是在立宪君主制下才能以纯粹的形式贯彻“私的自治”,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最严密的分离。可以说这正是一种以君主制原理为骨架,再移植以立宪主义而自然达到的理论。
《魏玛宪法》采用了国民主权 (第1条第2款),否定了君主立宪制,因此在对基本权的解释上导入自然权思想的理论也就是可能的了。但是,众所周知,该宪法下的通说并未抛弃法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是基本上维持了公权论的框架。但是,由于《魏玛宪法》第118条第1款“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内,有用言语,文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并不得因劳动或雇佣关系,剥夺其此种权利。如其人使用此权利时,无论何人,亦不得妨害之”〔6〕有关 《魏玛宪法》条文的翻译,参见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5300/154/2006/4/xi70741131111124600214229-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7年8月19日。——译者注。的后半段与第159条“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规定及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的规定〔7〕翻译采取高田敏=初宿正典編訳 『ドイツ憲法集 [第3版]』(信山社,2001年)。假设了对私人间关系的调整,因此对于问题的所在有了萌芽性的意识,但这些规定应该理解为宪法的例外规定,还没有达到对自由权的对国家性这样的公权论的原则性思考范式进行再检讨的地步。〔8〕中山勲「人権保障の私人間に対する効力」坂大法学55号 (1965年)73頁。
三、第三人效力论的成立
第三人效力论是在德国基本法下的德国宪法学的教条之下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基本法下的德国会产生这样的理论。众所周知,由于基本法以“不可侵犯、不能让渡的人权”的自然权定式对基本权加以保障,因此采用与法国革命时期同样的理论,由法律对私人间的人权 (作为实定的基本权利基础的自然权)冲突进行调整,在法律上,进行这样的解释应该也是可能的。在德国民法典下,也并不存在困难之处。民法典中并不缺少能成为“引进”自然权的器皿的一般条款。既然如此,为什么会产生“第三人效力”这样的德国独有的解释理论呢?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德国传统的公权论的思考模式来考虑这个问题。〔9〕这一点是缺少德国宪法素养的我的大胆而鲁莽的猜测,期待精通德国宪法的学者的指教。
基本法自身由于不可能采取立宪君主制,也就不存在产生公权论的制度前提。然而,要舍弃长期以来亲近的传统的思考模式却也并非易事。因此,私人间人权保障的问题就表现为以公权论的框架为出发点,设定其是否应该及于私人间 (第三者关系)(Ob的问题〔10〕即“是否的问题”。——译者注。)、如何产生影响 (Wie的问题〔11〕即“怎样的问题”。——译者注。)这样的问题。以公权论的框架作为出发点,就限定于以公法与私法相区分为前提进行思考,作为公法关系上权利的公权要在私法关系上也产生效力就比较困难。这就有必要将德国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通过某种理论设定为贯通公法与私法两者的原理,或者是位于两者之上的原理。可以注意到,由此观点即可发现德国的第三人效力理论,直接效力说也好,间接效力说也好,都可以说是以某种形式对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赋予超越其性质的 “客观价值”的理论。〔12〕但是,对于指代“客观价值”的用语及其内容,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根据木村俊夫教授的介绍,尼伯代认为“《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格尊严’……的规定是自然法原则。因此,这一规定是超国家、超实定法的,具有优越于宪法制定者及《基本法》第1条第1款以外的所有基本权规定的地位,并得约束上者”(参见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38页)构成直接效力论的基础。同属直接适用说的莱斯纳则认为“人格尊严的规定与其他基本权是异质的。它不是基本权,而是作为‘最高构成原理’的‘主导命题’。人格尊严是价值,是构成基本权诸价值体系基础的原理。人格尊严是不可分的。因此这一价值概念应该是全面妥当的。因此,将这一原则具体化的基本权受到全方位的保障”(参见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44页。唯笔者省略了插入的原文及引用页码数)。间接效力说的杜立希也指出,“人格尊严是伦理价值在宪法中予以实定化的法的价值。这一人格尊严在实定化之前为要求社会尊重的伦理价值,转换为法的价值后也不失全方位的妥当性”“人格尊严从宪法的表述上是宪法的最高规范,是全部法秩序的最高构成原理”(参见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47页。省略页码数)。此外,克莱因设定“作为宪法的客观法规定、同时作为宪法外的法律领域的最高法规”的“原则规范”,认为它对私法关系产生影响 (参见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52页)。此外施瓦布指出,“区分规制法共同体成员外部行为的‘初级规范’与对违反初级规范者进行强制的‘次级规范’,基本权属于初级规范,与次级规范的层次相区别位于公法、私法的上位”(参见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54页)。而且,这种价值不仅与自然权或伦理的价值相关联,而且基本上也具有实定法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可以感觉到与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存在不同之处。
在日本,提倡直接效力的学者对于直接适用于私人间的人权也以某种形式赋予了它超越公法关系的意义。〔13〕例如,橋本公亘『憲法原論 [新版]』(有斐閣,1966年)167頁以下,认为原则规范与制度保障为“客观的法规范”,与平常的基本权利不同,在私人间也具有直接效力。但是,意味深长的是,日本的间接效力说则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尝试,而是采取了将具有针对国家的性质的人权就这样对私法的一般规定(《民法》第90条)的内容进行填塞这样的构成。〔14〕虽然存在着充实着人权的“精神”而构成的判决 (参见前注〔1〕,小山剛书,第213页,第260页注9。),但似乎感觉在人权的填充上有理论上的弱点。然而,如果宪法上的人权是针对国家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通过《民法》第90条的公序良俗的媒介就能将其转换为对私人的权利呢?对此却未予说明。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的是今村教授。今村教授针对以《民法》第90条的“公序”为媒介的间接适用说批判道:“私人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之违反‘公序’其实是因为其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相抵触。将‘公序’切实变为‘公序’的力量并不在《民法》第90条的规定自身。”〔15〕前注〔1〕,今村成和书,第70页。简而言之,这就是指出正是因为人权在私人间已经具有效力,对人权的侵犯才违反了公序,反之,也就是说如果人权在私人间不具有效力,就根本谈不上对它的侵害,随之也就谈不上对公序的违反了。即,日本的间接效力说暗地里是以宪法上的人权实际上在私人间也具有某种形式的效力为前提的。由此今村教授指出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在宪法在私人间的适用这一点上并无变化,直接或间接只是法技术上的差别。〔16〕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的对立只是法技术上的问题,这样的理解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例如,浦部法穗『『全訂憲法学教室』 (日本評論社,2000年)70頁,中村睦男『憲法30講 [新版]』(青林書院,1999年)50頁。但是,如果以人权的针对国家性这样的传统人权观 (宪法观)为前提,为什么它在私人间也具有效力,就成为应该回答的问题。如果不否定传统的人权观是无法径直绕过这个问题而委之以如何适用的法技术论的。但是,如果说间接适用说实际上认为人权在私人间也有效力的话,难道不应该先于技术问题而首先追问其根据之所在吗?德国的间接效力说并非采取将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直接引进私法的一般规定的手法,而是采取首先构成“客观价值”的迂回的方法,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吧。也就是说,在向私法的一般规定引进基本权利之前,有必要将应该引进的基本权利转换为即使是在私人间也具有效力。由“对国家的基本权利”向“全方位的客观价值”的转换作为前提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四、对德国理论的疑问
但是,德国的间接效力说是否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却是另外的问题。例如,杜立希认为《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格尊严”为“伦理价值在宪法中实定化的法律价值”,这一伦理价值由于“在实定化前要求社会的尊重”,因此“即使是在转换为法律价值之后在全方位上也不失其正当性”,〔17〕前注〔1〕,木村俊夫文,第47页的介绍。但问题是这一“法律价值”的性质。如果它假设的是“自然权”这样的价值,那么这一理论与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就可以说是相同的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填充进私法的一般条款的就应该是自然权这样的伦理价值,而不应该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法律价值。但是,杜立希既然有“转换为法律价值”的表述,那么可以想见,在杜立希的考虑中这一法律价值就应该具有与自然权不同的性质,是一种“实定法”的价值。而且,由于杜立希认为它尚未丧失“全方位”性,那么就应该认为它是在转变为针对国家的“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之前的客观的法律价值。但是,既然说它是具有全方位性的实定法价值,那它又为什么不能直接在私人间适用呢?恐怕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价值尚处于抽象阶段,如果要予以现实的适用,还需对其进行“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大概是构想为一方面作为针对国家的“主观基本权”的规定在宪法中实行,另一方面在私人间通过向私法的一般条款中填充价值的方法来实现的吧。其结果就是宪法内部既具有全方位的基本权 (客观的法律价值),又具有针对国家的具体的基本权,这样宪法或基本权规定的性质就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了。宪法并非为了保护前宪法的“伦理价值”而组织国家权力的规范,基本权规定并非为对国家在实现这一任务时不得侵犯的国民权利的记载,或者说宪法并不止于此;宪法带有宣布应该适用于作为全社会的基础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法律价值的性质。后面这种宪法观、人权观如果贯彻到底的话,就会颠覆近代立宪主义观念,它掩盖了宪法、人权不再是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成为对国民的约束这一转变,不能不说具有不能忽视的重大意义。〔18〕芦部信喜「人権論五□ 年を回想して」公法研究59号 (1997年)1頁 (同『宗教·人権·憲法学』[有斐閣,1999年]所収)所指出的与此亦有关系。因此,借用赫塞的话,芦部指出,“在德国,将基本权理解为法秩序全体的客观原理的观念很强,如果采用这种思路,就与国家负担着为了实现国民的基本权而应竭尽所能、尽积极的义务的国家观联系起来了”(第14页),虽然在这种观念下宪法法院被赋予了强大的任务,但这种理解是以德国的特殊国情为基础的,能否直接导入日本的解释论则是一个问题。
可以称为德国间接效力说先例的宪法法院判决的吕特案也蕴涵着基本同样的问题。该判决指出,虽然“基本权首要的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侵害而规定的权利”,但“基本权绝不是价值中立的秩序。在基本权的条章中,客观价值秩序也得到了具体化。这一价值体系作为宪法的根本决断,对于一切领域的法律都是适用的。民法规定也不得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抵触”。〔19〕前注〔1〕,芦部编书,第82页“芦部”。在此是适用什么理论导出“客观的价值秩序”的呢?如果基本权“首要的”是针对国家的权利,那么在基本权中具体化的客观价值秩序是否也应该认为是针对国家的呢?在客观价值是由针对国家的 (主观的)基本权导出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突破针对国家性?这一点要成其为可能,难道不是应该从实际上客观价值秩序才是首要的这一点出发来考虑吗?首先设定“作为宪法的根本决断,对于一切领域的法都是适当的”客观价值体系,然后由此推导出针对国家的主观的基本权利,如果这样进行考虑,或者,同样的,假设针对国家的基本权背后存在着具有全方位性质的客观价值秩序,宪法对其也作为法律价值予以承认这样来考虑的话,就大致可以予以说明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会从中发现宪法观、人权观的转变。
五、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论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在维持基本权的针对国家性的近代立宪主义框架,因此避免了宪法观、人权观的转变的同时,对私人间效力予以说明的强有力的理论,这就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论。〔20〕有关保护义务论,参见前注〔1〕,小山剛书,山本敬三文。这一理论认为在私人A侵犯私人B的基本权利时,国家负有保护B的义务。因此,国家应对A的侵害行为予以阻止或给予责令其赔偿等救济,而由于此时A也得向国家主张其基本权利,因此国家就需要调整尊重A的基本权利与保护B的基本权利的义务之间的关系。但是,重要的是,这种尊重义务也好,保护义务也好,都是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可以说仍然是在传统的针对国家性的框架之内的。虽然这种理论进行了巧妙的解释,但是仍然是存在若干疑问的。首先,A所侵犯B的基本权利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以基本权利的针对国家性为前提,那么B对A就谈不上具有基本权利。当然,这一问题是绕不开的。因此,在这里回避了基本权利这样的表述,而是采取了如“基本权利的法益”这样的称谓。〔21〕参见前注〔1〕,小山剛书,第221页。但是,如果这样处理的话,问题就变成了这一“基本权利的法益”的来源了。这种法益的根据何在?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它并非宪法上的法益。那么,它是法律层面上的法益吗?如果说它是法律层面上的法益的话,那么为什么国家会对其负担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呢?如果说这种法益是自然权性质的话,那么就与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相整合了。如果说是自然权的话,的确是可以向任何人主张,而国家对其负担保护义务也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国家的保护义务论是否以自然权思想理论为基础,至今却尚未明朗。
针对保护义务论的第二个疑问就是,担负保护义务的“国家”具体究竟是指什么?当然,可以回答是包含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尤其是,处于这种考虑的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司法权。但是,如同将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考虑进来即可明白的,由国家的保护义务径直导出司法权的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宪法规定了国家应如何履行其所承担的保护义务,作为对这一宪法的解释,就有必要导出司法权的权力。宪法如果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法益”依据法律予以保护的话,那么将它作为保护义务的实现方式也是非常可能的,法院如果以法律的不存在或欠缺为理由否定对“基本权利的法益”的侵害的救济,就不能说构成对保护义务的违反。由于宪法要求国家的保护义务由司法权单独承担这一点并未构成前提,因此要构成对保护义务的违反,首先就有必要对它加以论证。
六、对非适用说的再评价
这里的非适用说指的是“宪法上的人权”规定不适用于私人间的学说。从迄今为止的分析来看,显然非适用说能够分为两种学说。其一为法国革命期间确立的人权理论,据此对私人间的人权 (自然权)调整由法律进行。另一种则以德国的公权理论为基础,因此私人间的公权冲突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它在事实上的冲突则由法律予以调整。〔22〕参见前注〔1〕,棟居快行书,第106~107页指出,“国家承认侵害者、被侵害者双方的自由,这种容许个人任意的 (不)行使的事态可以认为是私人间的容许规范的并存 (不抵触)”,但这种论述潜意识里不正是以基本权利在私人间不具效力为前提的吗?
这两种学说的差异在于,在适用私法一般条款调整人权冲突的场合它们会导致较大的不同。前者由于假设在私人间存在人权冲突,因此就可能在解释、适用一般条款之际调整这种冲突。与此相对,在后者的情况下不存在应该“引进”一般条款的针对私人的权利。因此,以这一公权论的框架为出发点,如果要实现私人间的权利保障,首先就必须解决构建私人间具有某种效力的“法的价值”的问题。这时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弃公权论的框架,从自然权论出发重建法律体系应该说也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与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同型、同构造的理论。但是,也许对于惯于法实证主义的思考方法的人来说,以自然权为视点重建保障自然权的法律体系的想法会比较困难,反之他们会采取从实定法的角度眺望处于其对面的自然权,从实定法的内侧将这一价值纳入进来的进路。这时,纳入实定法内部的价值一方面与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产生关联,同时也与之相异,处于其上位,作为具有全方位效力的实定法的客观价值得以成立。由此,就从立宪主义的宪法观、人权观迈出了一大步。
在德国,由于其宪法的历史与基本法的特殊的构造,这种理论的展开可能得以正当化。对这一点,笔者无力进行评价。在这里笔者想提出来的是,日本在轻易地采用德国特殊的思路之前,也许应该努力贯彻立宪主义的理论。这一模型存在于法国革命时期的理论中,要导入新奇的理论,等到确认这一模型在日本国宪法下的法律体系之中已经无法具有实效性之后也不迟。在笔者看来,要在日本引入第三人效力理论还为时尚早。
根据法国模型,以宪法为顶点的日本的实定法体系确立了保障作为自然权的价值的人权的法律结构,私人间的人权保障由以民法为中心的私法来进行。因此,私法的解释必须与人权价值相契合。只是,这里所谓的与人权价值相契合的解释并不一定是与宪法规定的实定的人权价值相契合的解释,也就是不一定是合宪解释。作为解释基准的是自然权的人权价值,而不是作为“宪法上权利”的人权价值。〔23〕与此相对,行政法规的解释基准是实定的人权价值,而这正是合宪解释的要求。本来,即使是私法,从理论上来看也不是不存在合宪解释的可能的。在对私人间自然权调整失败的法律有可能侵害针对国家的人权的情况下,做出不侵害人权的解释的情况即属此类。既然民法是以实现受到自然权保障的私人间关系为目的的规定,在解释时与此目的相契合也就是当然的事情。民法规定了立法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而必要的诸种制度。〔24〕第三人效力论最成问题的就是以契约自由为中心的私的自治制度。契约自由正是立法者为了使作为自然权的“自律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创设的最好的制度。但是,由于它是法律上的制度,因此不具备宪法上的价值。由此出发,以自然权为解释基准最好是限定在对民法的解释上。尽管在认为“宪法上的人权”的效力及于私人间的情况下,为了将契约自由与人权作为同样的价值进行衡量,就有必要将契约自由本身当作人权予以构成,并出现了契约自由,以及更一般的私的自治的宪法根据问题,但笔者认为对私的自治作为法律层面的制度进行理解就足够了。这其中就包含着具有调整私人间人权 (自然权)冲突意义的内容。这种规定,不论其调整的方式为何,都会导致私人侵害受到国家保障的人权的情况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定就违反了宪法。但是,这是立法者对尊重人权义务的违反所致,而并非对保护义务的违反所致。〔25〕作为日本国宪法的解释,将国家对人权 (自然权)的保护义务作为实定宪法上的义务加以承认是可能的。但是,即使是在此情况下,承认违反义务的情况与成立违反尊重义务的情况相比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因为与尊重义务要求国家的不作为相对应,保护义务要求的是国家的作为的缘故。问题是如何理解民法一般条款的性质,例如《民法》第90条就不能理解为由立法者自己进行对人权的调整,当然应该理解为是规定委托给法院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当作第90条解释基准的当然应该是作为自然权的人权。这是因为立法者将拥有的对自然权的调整权力予以了委托。宪法上的人权为针对国家的权利,在私人间不具有效力。
为了进一步寻求对非适用说的支持,就有必要回答几个疑问。最先想到的问题是,这一学说难道不是主张复活18世纪的自然权思想吗?在启蒙主义的自然权思想久已失去支持的今天,即使是要复活自然权当时的面貌,也是难以期待该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的。主张对非适用说再评价的笔者的意图并非是要复活这样的自然权论。虽然迄今为止的讨论都是以自然权为表现形式的,但这首先只是为了使讨论的构造更为明快,笔者真正关心的并非自然权,而是实定法律体系为了实现具有理论上超过实定法性质的价值的手段,是包涵着自然权论的理论构造。《宪法》第13条规定:“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通说认为,这是宣布日本国宪法所依据的根本价值的规定。宪法以全体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的社会的实现为目标,为此而规定了法的构造。〔26〕有关笔者如何理解“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参见高橋和之 「すべての国民を 『を 『個人として尊重』する意味』」『行政法の発展と変革 (上)(塩野宏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閣,2001年)269頁。这一宪法作为目的的“个人尊严”的价值在法理上为超越宪法的价值,是为宪法提供道德哲学的根据的价值。可以“推测”,这一意义上的道德哲学的价值为社会 (国家)的构成原理,《宪法》第13条就是作为这样的构成原理而得到采用的。如果承认这一推论,就可以认为,这一价值自身在一切社会关系上都具有道德适当性。但是,《宪法》第13条自身由于是宪法上的规定,因此只能对国家产生法律拘束力。同样的,《宪法》第13条后段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宪法》第14条以下的个别人权,也都是以国家为对象的。宪法是规定以通过法律体系实现道德哲学价值为目标的程序的规范。〔27〕虽然表述为规定“程序”,但表明的并非是对司法哲学上程序理论的采用,指的是运用法律体系的程序,在这一程序上必须尊重人权等实体价值,至于司法审查及于此点则自不待言。参见高橋和之「「司法制度の憲法的枠組——法の支配と司法権」公法研究63号 (2001年)1頁。另一方面,私法构成了以在私人间实现同样的道德哲学的价值为目的的法律体系。战后进行《民法》修订时,《民法》第1条之2规定“本法以个人尊严……为宗旨进行解释”就正意味了这一点。个人尊严作为社会的构成原理是宪法与民法背后设定的统一的价值原理,与导入作为最高规范的宪法并流入下位规范的民法的法的价值在性质上是迥然相异的。
对非适用说可以想到的第二个疑问就是,如何说明宪法中以私人间的直接适用为当然前提的人权规定的存在?笔者的新非适用说根据人权规定的对象限定为国家,主张更好的维持立宪主义的理论。但是,《魏玛宪法》中已经有了假设私人间直接适用的规定,日本国 《宪法》中也有第15条第4款 (投票的秘密)、第18条 (禁止奴隶的拘束)、第28条 (劳动基本权)等条款,认为这些条款事关直接适用在学说上已经没有异议了。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非适用说不正失去了作为宪法解释能够通行的基础吗?确实,在现代宪法下,宪法观、人权观逐渐发生着变化,从宪法在形式上的最高性来看,不能否认会产生宪法中包括对全部的法律秩序都适用的价值的想法。与这一倾向相对立,笔者认为,作为对日本国宪法的解释,只要有可能就要努力贯彻立宪主义的理论。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宪法解释的话,上述条文就不一定是假设了直接适用,不如将其解读为赋予立法者制定实施这一规定的法律的义务。实际上,立法者已经为此制定了法律,而宪法所设定的程序也正在起着作用。非得倡导直接适用不可的理由在哪里呢?
那么,立法者怠于履行宪法要求的制定法律的义务时又如何呢?这就是能够想到的第三个疑问。在上述例子中,确实立法者制定了必要的法律。但是,无法保障立法者常常忠实履行这一义务。特别是与社会中人权状况的变化相对应,为了保障人权需要修改法律及制定新的法律的时候,不是会发生立法机关由于种种理由无法迅速做出应对、放任重大的人权侵害不予救济的情况吗?这一疑问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而第三人效力理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上的问题而提出的。〔28〕虽然第三人效力理论表面上提出的是人权规定的效力是否也及于私人间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却是私人间人权保障的任务到底是应该由立法者来完成还是由法院来完成。前注〔1〕,棟居快行书,虽然将此作为“谁来适用人权规定?立法者还是法官?”的问题进行了整理,“立法者适用人权规定”这样奇妙的表述,大概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吧。另外,虽然栋居认为“法官的私人间适用构成高权的侵害行为的情况下,虽然从侵害保留的考虑方法出发法律的依据是为必要,但间接适用说以《民法》第90条充当了这一法律依据”(第68页),但这是法律保留与行政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司法则是个问题。由于法院不得以法律不存在为由拒绝裁判,因此判决即使将“侵害”(制约)人权,但如果为了解决争议所必要,不是也必须做出判决吗?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纯粹只不过是理论上的问题。更正确的说,只不过是为了在德国公权论的框架下捕捉私人间人权保障的问题而产生的伪问题。如果以法国模式进行考虑的话,调整人权冲突的框架在民法典内就已经做出了规定。例如《民法》第90条、第709条,对其按照适合“个人尊严”来解释就足够了。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论宪法上的人权规定是直接还是间接适用。
结语
从人权论的观点出发,必须将日本的实定法体系作为保障社会 (国家)基本价值(个人尊严)的手段来理解,并且在解释、运用上都应符合这一目的。虽然以各领域的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为基础,概括性的法律诸领域是具有一定的相互自律性,但在对各领域进行根本的规范的道德哲学的价值层面上,实定法体系却是具有共通性的。这一实定法体系以法律在形式上的区别为基础,通过授权关系或形式效力上的高低关系形成法律的阶梯性构造。虽然宪法位于其顶点,但作为最高规范的日本国《宪法》却在第13条中规定了“个人尊严”。由此,作为道德哲学价值的“个人尊严”被纳入到实定宪法中来。但是,既然宪法这一法领域的特性在于以国家为对象,那么宪法上的“个人尊严”,仅限于在道德哲学上具有全方位性,就转换为了针对国家的要求。确实,宪法是最高规范,拘束下位规范。但是这一拘束也不能超越“针对国家性”。因此,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律只有在制约私人得向国家主张的人权上受到宪法的拘束,而在私人相互间的水平关系上,宪法的人权规定却是没有效力的,也不能对之进行拘束。但是,私法也受到自己据以建立的道德价值的影响。因此,对私法的解释必须与日本实定法体系的基本价值相契合。《民法》第1条之2确认了个人尊严应为影响民法解释的基本价值。《民法》第90条这样的一般条款含有立法者委托法官进行与基本价值相契合的法律创造的意思。
宪法为作为保障、实现社会基本价值的手段而创设国家的文书 (instrument),为此列举了国家应予保护的人权,为进行此活动规定了国家机关的组织、权力和程序。简言之,宪法是规定国家展开人权保障的法律程序的法律文件。因此,宪法,以及宪法上人权的对象是国家,它并不调整私人间的法律关系。这就是近代以来立宪主义的宪法观、人权观。如果希望宪法规定在私人间直接或间接适用,就有必要审慎地了解为此要对立宪主义进行怎样的、何种程度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