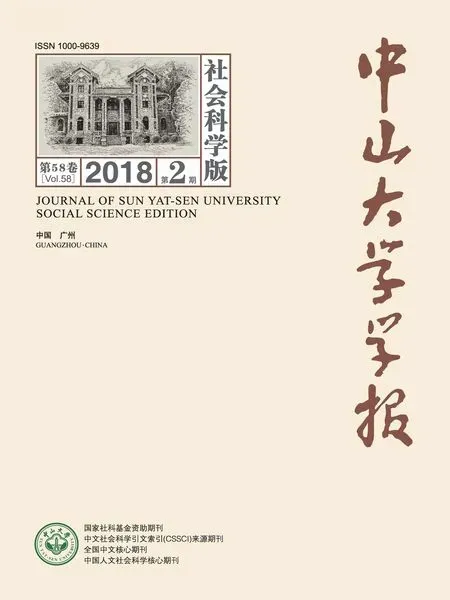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
——以《曹风·鸤鸠》为例
赵 培
一
传世本《诗经》为汉代《诗》学四家齐、鲁、韩、毛中的《毛诗》。通行的《毛诗注疏》文本,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六艺之源,传统经学主要有两派意见。今文经派将“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①[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古文经派则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易诗礼乐,三皇已肇其端矣”②③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1页。,孔子只是典籍的整理者与文化的托命人。就《诗》学而言,古文经派认为王逸《楚辞注》所言“造驾辩之曲,作网罟之歌”,即《诗》之始③。今文经派则认为《诗》学之端,肇自孔子删诗。审之现代学术标准,古文之说或更近实际。然汉人立说之依据,已不得知,故而我们不宜妄谈《诗》之来源同三皇五帝之关系。
郭店楚墓竹书《性自命出》篇第十五、十六简载:“时(诗)、箸(书)、豊(礼)、乐,其司(始)出皆生于人。时(诗),又(有)为为之也。箸(书),又(有)为言之也。豊(礼)、乐,又(有)为(举)之也。”④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第59页,释文第179页。按:郭店简的《六德》和《语丛一》中亦见到作为“六艺”的“诗”字。已见“六艺”之名。实际上,先秦典籍及出土文献中引《诗》的内容,基本上未出《毛诗》系统⑤何志华、朱国藩编:《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按:三家诗和毛诗的不同,基本上不涉及一篇之中句义参差的情况,说明三百篇的规模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粗就。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结合二者可以推定,《诗》的文本,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了毛诗的规模,且内容基本稳定①按:公元前3世纪之前,《诗》的存在形态究竟如何?柯马丁(MartinKern)教授认为:“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可能还有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体,而是‘六艺’这一通行于中国文化领域的更大的道德、教学、礼仪、社会—政治的原则和实践的一部分。”(参[美]柯马丁:《诗经的形成》,收入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和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其观点很有启发意义,关于此问题,尚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内容的稳定,从汉语史的角度言之,即其由词所组成的句义基本稳定。而文本形态除内容外②按:此处所谓的“内容”,是就文本的词义系统而言,将字形分离出来另谈。,还有一个文字形态。我们能够发现,以上举《性自命出》之文校之今本,其文字形态差异明显,即从字形层面言之,此文本并不稳定。文字形态上的不稳定,意味着字词对应关系非一观可知,后世的传注者(如毛、郑二公),若没能清楚地意识到并正确处理好其间的对应,那么他们再诠释的行为本身,就很有可能破坏了内容的稳定③按:所谓“破坏了内容的稳定”,指未能准确地对应好字词关系,使后代的解释跟文本自身的期待之间产生罅隙。。
本文拟探讨的毛传和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的异同,一则试图跳出后世文字形态的束缚,借古文字史的知识去探究《诗经》早期文本字词对应的真正面貌,就前文提及的第二个层面而言,我们的努力同时亦是对毛传和郑笺再诠释行为的重新审查。
汉初,经文与传解之书,当别为二。就《诗经》而言,孔颖达《正义》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④⑨ [唐]孔颖达:《毛诗注疏》,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南宋刊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卷1,第36,33页。可知经传相合已是后汉马融以后事。那么郑君笺《诗》时所见合于《毛传》之《诗经》,已非毛公作传时所据之本。其后笺、疏之合于经传,情况或同之,故段玉裁有云:“治《毛诗》而所治者乃朱子《诗传》,则非《毛诗》也。”⑤[清]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题辞”,《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段氏七叶衍祥堂刻本,第64册,第57页。经籍的流传如是复杂,再加上主要书写载体由简帛到纸张(石经一直存在,但从未成为主要载体),文本传布方式从钞写到刻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在没有异文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忽略今传文本中存在的信息层次问题⑥按:异文层次方面较新的研究,请参赵培:《先秦两汉典籍异文与共时和历时文本之间关系析论——以〈老子〉文本的层次性为例》,张显成、胡波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215—251页。。
要之,汉语字词对应系统的历时性变化直接导致了毛、郑所据之《诗经》文本和更早期文本的差异。历代学者对经、注、疏等的处理,又会产生并不完全匹配的嫁接式文本,再加上简帛经传的刊刻上石,石经文字的雕版开印以及经籍传抄和重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讹误,诸类因素很好地解释了乾嘉学者何以如此重视经籍校勘。我们对毛传、郑笺作据《诗经》文本面貌的努力还原,正是利用越来越多的先秦两汉的出土材料,在清儒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对更早时期开展“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的研究⑦[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二
《汉书·艺文志》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⑧[汉]班固:《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依此,则传当为毛苌所作。孔颖达《毛诗正义》引《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⑨据此,则传又当为大毛公亨所作,其作传在小毛公苌立河间博士之前。《史记·五宗世家》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①[汉]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第六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33—2534页。可知毛苌景帝时为河间献王博士,则毛亨作传当在文帝时期。综上言之,毛公之学自有渊源,而毛传之出当在汉初。
古文字的隶变从战国中期一直延续到今隶的出现②赵平安:《隶变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这就为《毛传》所据之《诗经》文本文字可能具有的形态添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偶然的局部的不确定性,却存在于一个毋庸置疑的大趋势当中,那就是汉初先秦文本的秦系文字化:
汉初无论是在字体上,还是在语言的书面形态上,都完全继承了秦代,致使许多后代世世沿用的书面语言规则,一直可以上溯到战国秦文字。汉儒整理和传抄先秦古书,往往根据当时的字体和书面形态进行改造,致使现在我们看到的先秦典籍中的语言书面形态,往往与秦系文字相同。③张世超、张玉春:《汉语言书面形态学初探》,《秦简文字编》,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若《毛传》为大毛公之发明,则其所本之《诗经》文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当中,其文字形态当属秦系④按:据周波研究,秦、西汉前期的出土文字资料中依然保留有六国文字字形及用字的遗迹,但已非主体。在下文的研究中,我们会考虑六国文字遗迹在对象文本中存在的可能性。但这一时期文字的形态,当以秦系为主体,因为秦的“书同文字”的确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参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第二章“从秦到西汉前期的用字状况看‘书同文字’”,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244—282页。。然而毛传并非毛公自创,其学问自有渊源。传解所出的时代或远早于毛公。那么,其所依之本,当又具有战国或更早的文字特征,若在战国时期,其所属系别又难凿定,而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下文将就此思路,通过毛传、郑笺的内容以及古文字学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知识,来对《曹风·鸤鸠》的文本展开讨论。
三
《鸤鸠》在《毛诗》中属《曹风》,四章,章六句。其首章为⑤按:《毛诗》文本内容,以国家图书馆藏(9585号),宋刻经注附释文20卷本《毛诗》为准。此本有《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此章中“其仪一兮”,毛传:“言执义一则用心周。”郑笺:“仪,义也。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⑥《毛诗》卷7,《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毛传、郑笺皆以“义”释“仪”,依毛传之体,当有“仪,义也”,似不需郑笺赘笔。我们认为毛传本“仪”本为“义”,而郑笺所据本已作“仪”。郭店楚墓竹书《缁衣》篇第三十九简引此句作“其义弌也”⑦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20页,释文第131页。,《五行》第十六简引作“其义也”⑧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32页,释文第149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二十二简作“丌义一氏”⑨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图版第34页,释文第151页。,《缁衣》第二十简作“丌义一也”⑩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图版第64页,释文第195页。。可知战国楚地出土简书未见作“仪”者,而多作“义”。王四年相邦张仪戈、十三年相邦仪戈“仪”作“义”①四年相邦张仪戈,1983年8月出土于广州市越秀区象岗山南越王墓东耳室,收入钟柏生、陈昭容等主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编号1412,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十三年相邦仪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增订本),编号11394,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按:下文出现的铜器编号,均据《殷周金文集成》,不再一一注明出处,《集成》未收者,则出注说明。。则秦系文字用“义”表“仪”。此外,“仪”的仪表之义,在先秦文字中对应的字形还有“”、“”、“”、“宜”等②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5—548页。。出土先秦材料中并未见“仪”字,此字形至汉代简牍材料中始见③臧克和主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也即汉代与“仪表、仪式”义相对应的字形才稳定成字形“仪”,而传世先秦典籍中“仪”字实则是汉人或其后文本整齐后的结果。毛传所据本当为“义”,故无需训解,而郑笺所见已为“仪”字,才又增释“仪,义也”。
“其仪一兮”中的“兮”字,毛传和郑笺无注解,三家诗有异文“也”④[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0—501页。。上博简《孔子诗论》作“氏”。“兮”字和“乎”同源,形、音、义均有关联,故《说文》云“(乎)从兮,象声上越扬之形也”,言“兮,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但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经分化⑤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页。。“兮”字出现较“也”字早,就辞例来看,战国时期,二字都可作句中或句尾的语气词。汉代依旧如此,我们不能确断孰是毛传时所据之本。“氏”为定母支部字,“也”为以纽歌部字,可通。故“氏”当属于“也”字系列,属于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异文。而“兮”和“也”亦当为口传过程中的义近互用。
此句中的“其”字,战国秦汉出土材料中多见写作“亓(丌)”。侯马盟书(四九:二)载:“丌明亟之。”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50页。阜阳汉简《诗经》○四一号:“雨雪亓方(雱)。”⑦胡平生、韩自平编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图版三。段玉裁注《说文》“丌”字云:“字亦作亓,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亓。”⑧[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版,第199页下。故毛传所本之此句当为“亓(其)义一兮(也)”。
我们首先讨论了可明确判断毛传和郑笺所据本的区别的“其仪一兮”一句的早期形态,首章的其他部分,虽难以断定毛郑所据一定有别,但其文本原貌亦需考辨。
“鸤鸠在桑”,马王堆汉墓帛书作“尸叴在桑”,汉石经作“尸囗囗囗”。“鸤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二十一简作“”⑨程燕:《诗经异文辑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鸤”字不见于先秦两汉出土文字资料,其字大约产生于汉代,《方言》云:“鸠,梁宋间谓之鹪。鸤又作。”⑩[清]钱绎撰集:《方言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上海图书馆藏红蝠山房本影印,第474—475页。“鸠”字始见于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为鸟虫书,字形隶定作“”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增订本),编号11621。。稍后战国包山楚简一八三号简文亦见,就其字形言之,其本义当为鸠类禽鸟。马王堆帛书的字形当亦属于此字形序列,故早期“鸠”字当含“口”部。

表一:词“淑”所对应字形的战国分区特征表
就“淑”字而言,秦系文字本身从“盄”到“叔”的变化(春秋早期到战国),后又在战国文字到秦汉文字的变化中反映了出来。东方诸国从“弔”的字形逐渐被整合掉了。毛传所见本或已为“叔”②按:战国文字中“叔”亦具有区域性区别字“弔”,为战国文字隶变的过程中,用“叔”代“弔”提供了条件。从水的“淑”字形,则是“叔”字形稳定作其假借义“伯叔”之后,另造的区别字。另外,这种整合的痕迹,更能从先秦典籍对“弔”字形的保留上得到证明,如《左传》哀公十二年“旻天不弔”,《周礼·春官·大祝》注云:弔作淑。。
“心如结兮”,上博《孔子诗论》第二十二简,“如”作“女”。“女”属泥母鱼部,“如”属日母鱼部,二字声韵具可通,《释名》云“女,如也”,即为声训③程燕:《诗经异文辑考》,第45页。按:程文中言“根据章太炎的‘娘日归泥’说”,实际上娘日纽近,归不归日母,二字均可通,故略去章氏之说。。“女”“如”相通,就“如”义而言,东方诸国,像楚、齐、三晋、燕基本上两字形混用,而秦系文字已稳定地用“如”字(石鼓文、睡虎地秦简等材料所示)④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第186页。。毛传所本当如秦系。
四
《鸤鸠》第二章: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其带伊丝。
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其子在梅”,“梅”字为形声字,其字形《说文》所收小篆始见。《诗经》诸篇中,梅有“酸果”和“枏树”二义。《说文解字》“梅”字下,段玉裁注云:“《召南》之梅,今之酸果也;《秦》《陈》之梅,今之枏树也。”⑤[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39页。《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鸮萃止。”二诗中的“梅”,毛传:“梅,枏也。”⑥《毛诗》卷6、7,《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此处之梅,毛公无传,《摽有梅》处亦无传,或当近之。马瑞辰云:“梅,当为‘梅杏’之梅,以下‘在棘’、‘在榛’类之,知皆为小树,不当为梅枏也。”⑦[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2页。
“梅”字形晚出,不见于战国秦汉出土材料。《摽有梅》之“梅”,《经典释文》云“梅,《韩诗》作‘楳’”⑧《毛诗》卷1,《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阜阳汉简《诗经》十六简作“囗囗”⑨胡平生、韩自平编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图版一。。可知早期字形当从“某”,“梅”似为东汉始造的形声字,其本义即指“楠木”⑩李学勤主编:《字源》,第492页。,传世先秦典籍中的“梅”字为后代所改。毛传之所以要在《终南》《墓门》两诗出注“梅,枏也”,盖因其所见之本从“某”,非字形之本用,故传之。
“其弁伊骐”,“骐”字,毛传:“骐文也。”郑笺:“骐当为,以玉为之。”此处,毛、郑多据本当均为“骐”字,只是毛释其为以皮弁之纹彩,郑解其为皮弁之玉饰。据出土材料观之,“骐”字晚至战国已出现,而从玉之“”并未见于先秦两汉出土文字材料,故此处当以“骐”为是,释义以毛传为长①按:于茀以阜阳汉简此字写作“”,而认为早期字形更可能为从丝从的字形。此说亦有可能。参氏著《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五
《鸤鸠》第三章: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仪不忒”,“忒”字,毛传:“忒,疑也。”郑笺补益之曰:“执义不疑,则可为四国之长。”②《曹风·鸤鸠》,《毛诗》卷7,《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后世字书当中,“忒”的“疑惑”义,多据此而来。而实际上,毛传的“疑也”,所据之字形并非“忒”,而是“貣”字。
《说文》云:“忒,更也。从心,弋声。”③[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09页。可知,“忒”有变更之义。《尔雅·释言》云:“爽,忒也。”邢昺疏引孙炎言:“忒,变杂不一。”④《尔雅注疏》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本,第38页下。《诗·鲁颂·閟宫》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玄笺:“忒,变也。”⑤《鲁颂·閟宫》,《毛诗》卷20,《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由变更而引申出差错之义。《易·豫》云:“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⑥《周易正义》卷2,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本,第48页下。此处,“忒”与“过”相对,释为差错。辞例中多见其差错义。
“忒”从“心”从“弋”的字形,最早见于花园庄东地甲骨,为地名。其后直到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方再见,为人名⑦高明、涂白奎编著:《古文字类编》(增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两字形皆从“戈”。就“忒”字形的“差错”义言之,最早但见于《说文》所收小篆,其后见于著录的最早字形为东汉延熹六年南阳桐柏的《淮源庙碑》⑧臧克和主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第936页。。“忒”的差错义,见诸出土文献,早期常借用其他字来表示:
1. 弋。下民之式,敬之母(毋)弋(忒)!(《楚帛书》乙)
2. 代。古今四伦,道数不代(忒),圣王是法,法则明分。(《马王堆帛书·九主》)
3. 贷。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忒)。(《帛乙老子·道经》)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下经》此句作:“为天下武,恒德不貣(忒)。”
4. 貣。正月尽期,吉日不貣(忒)。(競孙不服壶12381)
“忒”的通假字主要有上列几种,对应的古文字形参下表:
结合上表,和“忒”相通的这些字基本从“弋”,而根据“弋”形的不同写法可分为三类(参表二):一类以“兢孙旟也鬲”为代表,所从“弋”旁横画下面加一平行小短横,包括蔡侯申镈和钟、镈甲(15797)、楚帛书、郭店和上博简等上面的文字;一类以“越王者旨於睗钟”为代表,从“弋”旁,无饰笔,包括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等;第三类以镈乙(15798)为代表,“弋”旁写作“戈”,包括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中的“贷”等所从的字形等。

第一类競孙旟也鬲03036競孙不服壶12381蔡侯申镈乙15821蔡侯申歌钟戊15537镈甲15797 楚帛书乙 郭店简·上博简·缁衣郭店简·缁衣 缁衣第二类镈丙15799越王者旨於睗钟一15417越王者旨於睗钟三15419马王堆帛书·九主马王堆·论约北大竹书·老子道经简196银雀山竹书·攻权银雀山竹书·形篇乙第三类镈乙15798马王堆老子乙·道经马王堆帛书老子甲·道经
第一类字形,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习见,这一类字形中的“弋”虽然都加了羡笔,即横笔下面与之平行的另一短笔(或为一粗点画),但仍当为“弋”。李家浩认为双横“弋”字形的出现更导致了“弋”、“戈”形近易混①李家浩:《战国布考》,《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165页。。何琳仪进一步将其总结为规律性的“形近互作”(参表三)②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而第三类字形的出现正好可以作为“弋”“戈”形近互作的证据。

表三:“戈”“弋”形近互作字形举例
据白于蓝统计,战国秦汉简帛古书中“忒”的通假字出现次数分别为:弋(2次)、代(3次)、貣(2次)、贷(5次)③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4—385页。。“戈”“弋”互作,“忒”的通假字序列中“貣”的字形,存在三种写法(参表三中“貣”字形)。将这三种字形全考虑进来,《殷周金文集成》中“貣”通假为“忒”的有21例。
“贷”这一字形,始见于汉代。《说文》云:“贷,施也。”段玉裁注:“谓我施人曰贷也。”①④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80,280页。《广雅·释诂三》:“贷,予也。”②[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据嘉庆间王氏家刻本影印版,第98页。可知,“贷”为施予、借出义。而秦之前,此义由“貣”字来承担。《秦律十八种·司空》:“人奴妾系城旦舂,貣衣食公。”③张世超、张玉春撰集:《秦简文字编》,第465页。“貣衣”指私人奴婢被拘系进行“城旦舂”劳役的时候,公家提供衣服和食物。说明秦时借出义也用“貣”字。《说文》:“貣,从人求物也。从贝,弋声。”④《荀子·儒效》云:“虽行貣而食。”杨倞注:“行貣,行乞也。”⑤[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6—127页。要之,“贷”字出现后,“貣”“贷”二字用法上是有分工的:貣主于“借”,贷主于“予”。
两字用法上的区别,在《汉书》中有清楚反映。《汉书索引》中“貣”字出现9次,均为借入义;“贷”出现55次,基本为借出义⑥李波:《汉书索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862、1867页。。然而,据《史记索引》统计,除卷38《宋微子世家》引《尚书·洪范》“衍貣”用“貣”字外,其余31处皆用“贷”⑦[汉]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五册,第1941页。按:此处保留“貣”字形,盖因其为《尚书》之引文,受到相对稳定的经学文本的限制。所以此惟一的“貣”字的存在,正反映出后世的《史记》文本是一个整齐过的文本。,已不见借入和借出用字的区别⑧李晓光:《史记索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1274页。。如《史记·货殖列传》“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借入义已用“贷”字⑨[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册,第3952页。。当然,此种现象的出现或跟文本传抄和刊刻相关,不能据以言司马迁原本中“貣”“贷”无别。然而,即便单就《史记》文本传播本身来看,后代用字倾向于“贷”,则无疑问。这种趋势的发展结果是,“贷”最终取代了“貣”,两字的别义分化并不成功。
从音义关系的角度来看,“贷”字形出现之前,“借入”和“借出”的义项也不是合并的,古人通过语音将其区分开来⑩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页。。所以,“貣”和“贷”在形音别义之前,还经历过单纯依靠字音别义的阶段。《群经音辨·辨彼此异音》云:“取于人曰贷。他得切,字亦作貣。与之曰贷,他代切。”⑪[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卷6,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畿辅丛书》本,第146页。周祖谟据此认为“貣”和“贷”属于因意义不同而变调者⑫周祖谟:《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04—105页。。孙玉文认为,上古时候借入和借出的“貣”字音义已别,而语音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声调上⑬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第38页。。也就是说,“贷”字形出现以前,“貣”和“贷”虽然词义上有别,这种区别只体现在音调上,其字形则相同。所以,上举“忒”“贷”互通的例子,亦当属于“貣”字形跟“忒”通假的范畴。
结合前文所析,那么“貣”字作为“忒”的通假字就一共出现了28次,远较弋(2次)和代(3次)为多。因而,我们可以说,“贷”字形出现以前,“忒”的差错义主要是“貣”字形来行使的。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毛传的“忒,疑也”。王引之已指出,古无训“忒”为疑者。《尔雅·释言》亦无“忒,疑也”之文。惟《释诂》曰:“贰,疑也。”进而认为毛郑本“忒”作“贰”,故训为疑①[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道光十年刻本,第23—24页。。
王引之分析词义,认为当以“貣”字为是,但毛传内容,说明其所据本已讹作“贰”。实际上,“贰”字形更晚出,故毛传所据本此句实当为“其义不”。“”字形对应“忒”和“贰”两词,也就是说“忒”“贰”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过同形字。毛公误将透母职部的“(忒)”字认作日母脂部字的“(贰)”,故释其为“疑也”②按:此处言“认作”,实有如下考虑。“忒”处在必须押韵的位置上,而且重复押韵。故毛公不一定读为“贰”。更有可能,毛公仍读成“忒”,但由于同形字的关系,把贰的疑义放了进来。。
“正是四国”,毛传:“正,是也。”郑笺:“正,长也。执义不疑,则可为四国之长,言任为侯伯。”③《曹风·鸤鸠》,《毛诗》卷7,《四部丛刊》影印国图藏宋刻本。《吕览·先己篇》及《荀子·富国篇》用此句诗,皆表“正身然后兼人”之义,胡承珙《毛诗后笺》据此引诗,皆为正身然后正国,与《毛传》训“正”为“是”义同,认为毛义甚精,不必改训为“长”。黄焯平议同之④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实际上,如《说文》所载“是”字“从日、正”,此字形至晚在春秋时候已出现⑤李学勤主编:《字源》,第111页。,故“正”“是”互训是有文字上的依据的,而训为“长”则逊之。此句毛、郑所本当无疑。
六
若以《诗经》原本面貌的字词对应情况为标准,结合前文所析《鸤鸠》一诗的传笺内容,可以发现毛传与郑笺皆有“不足”,但毛传略胜之。毛传胜于郑笺,正是因为毛传时代的文本层次要少于郑笺时代。目前学术界通用的先秦文本,实际上承继了唐开成石经文本格局,虽时有改移,但大貌依旧。有清诸儒的校勘训释,使得我们对宋代经书之面貌,已比较清楚。随着先秦两汉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多,我们发现,唐儒(颜师古、孔颖达等)正定文字经义,宋代损益上版,最终刻定下来的经书面貌跟早期经书存在的实际情况差别颇大,这说明后代经书较之郑笺时代,又具有了更多的历时和共时层面的信息层。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世经学文本展开信息层的剥离分析工作,同时追问早期经典的实际存在状态。
我们认为,汉语中一直存在着一些稳定演进的字词对应关系,也即某一词义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有的甚至从古至今如此),在某一政治稳定的区域,总是对应着稳定的字形⑥按:古文字笔势和书写方式发生变化,但构形部件不变,依然属于我们所谓的“稳定”范畴。。口传的过程,使得很多音近或音同的字形出现了互用现象,但同时我们又能发现明显的字形使用倾向,如前文所析,“忒”义习惯对应“貣”字形。汉语的这种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尝试从汉语史,尤其是文字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文本。从细节出发,尽可能地逐一剥离能够反映文本层次的信息,最终弄清楚早期文本的实际存在状态。
就毛传所反映的《鸤鸠》文本而言,其所包含的同文本相关的信息层次可以一直追溯到毛传学派的源头,也即最早的阅读者和阐释者所见的文本。因为学派知识的传播可以是口传,亦可以是脱离文本而存在的,并且是随时可以增益补充的⑦按:此处所言的“增益补充”,指的是在师法家法范围之内的调整。,所以我们从传笺之中所分析得出的不应该只是单一文本的信息。以毛传时代为例,当汉初的毛公读到一个经过秦文字政策整齐后的文本时,他很有可能就当时的文本来损益自己的学说,亦有可能依照自己的知识来改定一个文本。我们试图尝试的,是通过个案的分析将文本流佈过程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同时为进一步全面地分析早期文本及其存在形态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