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阵营
——创作随谈
■林东林
前些年,写散文较多。注意,我说的是散文,还不是最近几年所写的随笔。这些后来结集为《谋国者》《身体的乡愁》《情到浓时情转薄》和《替全世界去仰望》的几本书,出版于2003年和2004年前后,既有取材于历史、人文和乡土的主题书写,也有市场性强但是文学性比较弱的情感专栏结集。回头看,这类写作主题鲜明、风格庞杂,但大部分还不脱于真善美和真善美的变体,易懂而浅薄,多情而煽情,甚至带有海明威所说的“过火的报刊文字插进一点虚假的史诗性的东西”。它们多是为了迎合附着在历史、乡土等题材上的公共情感和集体感慨,少于个人结实的识见与体验。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它们有的出于后青春期的懵懂和躁动,而有的则出于文字带来的虚荣和被鼓动,动机接近于功利,所以近几年我常有“悔其少作”的心理。少作可悔,但已不可毁,它们白纸黑字地摆在一排排书架上或落满积灰的角落里,成为一个作者创作的记录,或者是罪证。
说它们是散文,是因为它们出自杂志报章副刊和绝大多数散文图书所代表的中国散文传统。这种渊源于古代文赋、在现代中国被确定形式、而后以抒情和半叙事半抒情为面貌出现的被广为接受的文体,有着异常宽广的边界——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戏剧、不是诗歌那么它就是散文——和共通的特征和气质:恋古拟古,抒情滥情,升华总结,文艺腔调,才子习气。然而在缺少真正阅读但又基数庞大的大众读者那里,这类文字华美、内容空洞、很不及物也不很及己的写作,曾经还被以“有文采”、“有才气”、“感人肺腑”等廉价的文学标准所赞赏,但是事实上它们很少触及我们的现实经验和复杂真实的个体情感。一个字,假;两个字,太假。犹如那些异口同声、千人一面地被书写着的亲情、大地、乡愁、苦难、经历、爱情一样,内容和意义皆被虚置的写作在固化中达到了僵化,它们与它们坐在各个城市一隅、出身半乡半城、徐图以个人意淫实现集体意淫的作者(包括我)一起,与当下横亘着一道惊人的却被视如无睹的鸿沟。
2014年年底,在从北京来到武汉工作后,因为与诗人交接往来众多(原先也与一些诗人有过不少往来),我的写作文体也开始涉及诗歌。与散文的理性、逻辑性和线性结构相比,诗歌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它更注重的是直觉、跳跃和想象,对于已经形成散文叙述表达习惯的我来说,这种惯性带来的束缚和在此基础上的转型无疑难度巨大。所以与很多诗人最初的诗歌写作一样,我的诗歌写作也起源于模仿,对题材、语调和结构的模仿,这当然不乏会导致一些做作和造作之作——而且就诗歌本身而言它也是一种做作的文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写诗的过程、把一首首诗写好的过程,其实也正在于将做作去无限靠近自然的过程,去掉模仿他者和建立自我表达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形成语言和形式的辨识度,另一方面是情感和主题的调试与确认,跟很多诗人一样,我也想在同质化中实现一种“我”的异质化,或者说在异质化中找到并实现那个真正的“我”。

《谋国者》
我想说的是,诗歌写作让我意识到了“我”的自觉。这对我后来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不写散文了,而是写随笔。事实上,我也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出两者的差异,也无意为两者下定义,但我要做的是放弃之前那种脱胎于真善美和假大空的写法传统。随笔,犹言随手下笔,然而要做到这个“随”是很难的,在它“随”的背后其实有着精细而巧妙的“不随”,既不随众人之言,也不随自己的随心所欲(把写作看成一项手艺活,作者需要将情感和偏好降到冰点)。归根结底,还是写法问题,以我的随笔写作来说,它们的主要方式是近似白描式的叙述,少抒情甚至杜绝抒情,或者说以叙述本身去抒情。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散文/随笔无论在写什么还是在怎么写上都还面临诗歌和小说在西方文学带领下早已完成的现代性问题。所以在写法上,我甚至会尝试以小说、非虚构甚至是诗歌的手法去越界,为随笔文体模糊边界进而扩大其承载力。同时在内容上,这些随笔或也取材于我早年的乡村经历、人人事事和后来的南来北往,但我也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情感和命运的复制者——重复他人写过的(除非我自信能比他们写得更好),而是将更多目光投之于水面下那些紧贴当下的复杂体验。
简单讲,我的随笔写作有两大类。一类是知性和智性方向的,有叙有议,兼具细节和思想的双重侧重,主要是受布罗茨基的影响,多少也有一点E.B.怀特的影子;另一类是经验和经历方向的,白描,叙述,拒绝抒情和议论,主要是受韩东、曹寇等人的影响,可能也与周晓枫和塞壬等人有那么一点关系,但我不太喜欢周晓枫巴洛克式的绵密繁复和塞壬过于苦难和尖利的抒情方式,虽然我很佩服她们的随笔写作。我这两类“去散文化”的随笔写作,目前还未集结出版,而且客观来讲,它可能还处于我“去散文化”的挣扎之中。而在大的范围内,如果说非虚构作品也可以归属随笔的话,我也写过一些非虚构式的随笔,这类写作起始于我自2009年以来给《南方人物周刊》和《新民周刊》等杂志做的人物专访,这是我后来开启以1960年代七位诗人为对象的“跟着诗人回家”写作计划(《跟着诗人回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缘由之一。同时,因为在某些地方的居留与观察,我还以北回归线上的一座广西县城为对象,写作并出版了带有田野调查和社学会、人类学性质的《线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回到前文所说的诗歌。自从2015年始,诗歌写作是我在写作上的文体转向,同时它也是一种练笔,是一种与我的随笔写作并线行进而又一显一隐的练笔,我尝试着将我的诗歌和随笔写作建立一种互文关系和共构状态。一方面,诗歌是对我随笔写作的开启和丰富(我坚信一个诗人的随笔比一个随笔作者的随笔会更好,也更接近于随笔的本意);另一方面,诗歌也是我另辟文体的自我革命(我也坚信在不同文体之间的穿越既有益于对每种文体的丰富与补充,同时也会更深入)。读诗和写诗三年下来,我略感满意的自己的作品不足百篇,但相比于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积,其实我更在意的是它给我所带来的观念影响。譬如,对文白夹杂的语言和文雅精致的文学语言的放弃和对日常口语甚至俗语俚语的重拾,后者在诗歌(也包括其他文体)中恰切运用的力量和质感完胜前者,而且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再譬如,一首被人喜欢的诗歌和它在诗歌意义上的好坏很可能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写一首诗时你是出于想写一首被人喜欢的诗歌还是想写一首真正的诗歌的动机,很多人都在写讨巧迎合式的诗歌,但我们永远缺乏的是不被人喜欢但又真正应该写的诗歌,在这个意义上,很多诗人当下的写作是无效和失重的。
最近在张家界的一个诗人见面会上,我也谈及关于诗歌写作的两点感想。拾人牙慧,借用几位诗人朋友的话来说,其一是“败笔为生(张执浩语),跌到高处(韩东语)”,其二是“一无所见,清清楚楚”(邓兴语)。所谓“败笔为生”,也即是完美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学会在瑕疵与残缺的陪伴中笔耕不辍,也必须在不尽如己意和十不及一的表达中去争取准确抵达,这是语言和写作的宿命;所谓“跌到高处”,就是必须放下来、松下来,“试图高级是一种极端的功利,高级可以达成,但必降低”,也就是说真正的超越产生于跌下来时的高,刻意想写好,很多时候一定写不好,即使写好了,也只是可见的好;而“一无所见,清清楚楚”则源于我和转向小说写作的诗人邓兴的聊天,他对好短篇小说的这个标准也完全适用于诗歌,即在引而不发的节制和隐忍中铺以匠工的精心,犹如在炉火上千万次锻打铁块,让一首诗呈现出“什么也没说、什么都说了”的质感。事实上,以上所言并不限于诗歌,它们适用于所有写作,只不过让我在诗歌写作中感触最深。
我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当代诗人中的一位是韩东(同时也是小说家和导演)。作为“第三代”诗人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文本典范意义的他,其诗歌有着显而易见的现代意识(既有情感和主题,也有语言和形式),他对语言本身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与自觉——正如他早年所说的“诗到语言为止”,同时他对写作(不仅仅是诗歌)也有着其他人难以企及的热情、勤奋和手艺人般的虔诚。与一些灿星高照的天才诗人和靠才华胜人一筹的诗人相比,他们诗歌的“不可学”和“一学即死”,反证了韩东诗歌的“可学”和“值得学”,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的诗歌不好或者缺乏唯一性,而是说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诗歌和这样写诗歌(冷峻,节制,隐忍,一如他那高僧般的光洁头颅),一遍一遍,不断地修改,不厌其烦地修改,每天都以去工作室定点上下班的方式写作和修改(修改比写作更接近于写作),直至靠近和抵达某种境界(或者想象中的境界)。现在,包括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想我都会以他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练习“手上功夫”,去掌握一些结实有力的手艺、经验和见识,而非将阅读得来的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已经拥有的。
半年之前,我还开始写起了小说,短篇小说,至今一共写了完整的四篇,但我还没足够的勇气将它们拿去发表或示人。小说给我带来了与诗歌和随笔不一样的写作体验,正如大众所认知的那样,诗歌和随笔基本来自于非虚构,而小说基本来自于虚构——小说家写的不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而是可能会发生的,但小说并不基于真实的虚构却表达了一种真相,它甚至是真实永远也难以抵达的真相。应该说,迄今为止数量并不多的小说书写让我建立了(也正在建立中)一种虚构能力和在“虚”中把握“实”的能力。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事实上也并没有无缘无故的虚构,所有虚构在细节和轮廓上都指向于作者的经历见闻,也即是现实之实,所以我也会把自己的经验揉碎了埋进小说的各个角落,让它散发出生活本身的质感和纹理感。所以我倾向于写真的,贴着自己和周遭人的生活表面去写,甚至对真实的生活经历进行加工,然后把这些真的写到“假”起来和“飘”起来,通过这种“假”和“飘”去嫁接和打通大众的公共心理,在个体中实现集体的共振,呈现出小说的普适意味。这一点我记得韩东和曹寇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
短篇小说约等于诗,这既是很多写作者也是很多读者的共识。对我来说,从诗歌写作开始兼而尝试写短篇小说,内里可能也正是源于这种认知。我之所以也有这样的认知,可能还跟我对“小说并不等于故事”的观念有关,就像一首诗并不一定就非要表达意义和情感一样,一篇小说也并不一定就非要表达一个故事。当然我并不否认一个好故事能够写成一篇好小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故事的好坏也决定了一篇小说的好坏,但我觉得反过来说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故事之外,小说还有更多的东西。至于这“更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困惑过并还在困惑之中,但我确信其有,譬如它可能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个场面或者是一种写法。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个故事,那三两句话和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也完全能够做到,但小说文本的价值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写法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而这一点从马原早期小说中的叙述圈套中即能看出。
一个写作者同时在三种和三种以上的文体间穿越是危险的,这种危险性在于很难精于一道,最后很可能哪一种文体都写不到很高的段位。这是前一段诗人刘年在酒桌上跟我说的,我也非常认可,但在另一方面,我又很难舍弃另外两种文体去专攻一种,所以也只能是在不同阶段去不同侧重了。而且,当今写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文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小说、诗歌和随笔这几种文体间的壁垒、藩篱和门户之见也十分严重,虽然不少诗人也在写小说甚至在两个文体上都卓有成就,但是更多的写作者是专择其一并视另一种而不见。大体而言,诗人和小说家会互相无视乃至轻视,而他们又都看不上散文/随笔这种“人尽可夫”、谁都可以写写的尴尬文体,当然他们在主攻文体之外也会弄笔写写随笔。而具体深入到每种文体内部,民间和体制、先锋与主流、派别与派别、师承与师承等写作态度和审美趣味的分野与对峙更是司空见惯。也就是说,无论是客观环境还是主观意愿,无论是出于策略还是真正热爱,为了写好、写出名、写成家,一个写作者很可能慢慢地被逼迫或窄化到某种文体和写作方向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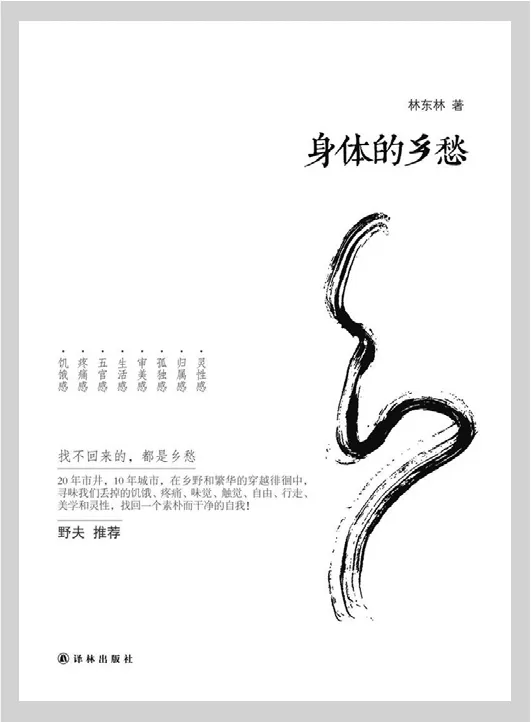
《身体的乡愁》
但我的一个认识是,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文体,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归根结底其实都只有一种文体:文字。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文体不重要,也不是说它们之间的边界和属性不明确,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我视文字为一种手段,一种包含了目的的手段,敏感而深入的感受力和通过文字所呈现出来的表达力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写作者的两翼。所以无论哪种文体、分属哪个阵营,它们只都指向于一个阵营,即一个写作者独自直面世界、直面命运、最终直面虚无的阵营。诗歌、小说、随笔等文体之异,只是一个人手中的锄头、犁铧和弓箭的工具之异,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手感、材质与纹理,但却绝无性质之别,它们作为让你有所隐遁、时出时入的掩体,也作为让你仰卧其上、怀抱星空的草垛,共同的立足点是坑坑洼洼的大地。为了抵抗虚无,一个写作者写下洋洋洒洒的各类文字,但最终只能抵达虚无,也随之会被更多的虚无所淹没。所以,写出再好的作品也不足以归为“成就”,文学也无所谓繁荣不繁荣,一个写作者也更不应有骄傲和沾沾自喜之理,事实再大的写作才华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那不过是你被遭遇永恒时发出的一声低吟。

林东林,诗人、作家。曾就职于北京、上海、桂林等地。现居武汉,兼任《汉诗》编辑。著有《谋国者》(上海三联书店)、《身体的乡愁》(译林出版社)、《跟着诗人回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情到浓时情转薄》(江苏文艺出版社)、《替全世界去仰望》(文化艺术出版社)、《线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历史、人文和文学作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