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给世界以光亮
■魏天无
林东林的新书《跟着诗人回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并不是一本简单的诗人访谈录,像时下许多文学报刊开设的访谈录或对话录栏目一样。他把访谈录这种文体,重新拉回到充满魅力与活力的传统的路途上——就像他跟随着七位诗人一同往回走,走向趣味横生、单纯快乐的童年、少年的老路上——那就是:面对面的畅谈,彼此的注视与聆听,鲜活的现场感,交谈双方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自网络时代以来,托信息技术之福,各类访谈录呈爆发式增长,绝大部分却变成了“纸上谈兵”: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变成字符与字符的滚动叠加,临场应变的机智幽默的话锋变成对着电脑屏幕刻意“调配”出的搞笑轻松。有了网络信号,访谈者就再也不需要与被访者反复约定时间和地点,也不需要去做充分的案头工作以应付现场的突发状况;访谈者在电脑上敲出问题,被访者下载文档像考生面对试卷一样字斟句酌,并且可以自由延长“交卷”时间。如果读者和我一样时常感到许多访谈录面无人色,缺少活生生的气息,那往往是访谈者缺乏敬业精神和写作的职业道德。
阅读经验告诉我,好的访谈录固然与被访者的眼界、学识、性情、气质的独特密不可分,但也与访谈者的精心选择、充足准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分不开;甚至可以说,访谈者提问的水平和技巧,决定着他能从被访者那里挖掘出多少鲜为人知的“宝藏”,是访谈者影响着对话的基本走向及其品位、趣味。《滚石》特约编辑乔纳森·科特,曾对苏珊·桑塔格做过长达12小时的访谈。在他的巧妙的提问和引导之下,《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本访谈录,让一位“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苏珊·桑塔格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对文学自由的求索、对他者的尊重和关怀,以及决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也给阅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林东林的《跟着诗人回家》是一部精心撰构之作,不仅凸显了七位诗人的家世、成长、阅读、命运和记忆,以及这些元素对他们诗歌写作的塑形,而且也表明了访谈者并非旁观者,而是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存在着,就像他在书中所言:“通过我的‘入故乡’去切入他们的‘出故乡’,呈现他们作为诗人和写作诗歌的某些景深,或许还有不断闪回在他们诗路和命运之路上的时代侧影”。他的目的是追随诗人去“原”乡,那些正在或已经消逝的故乡,回不去的家园,只在诗人们的一首一首的诗作中闪烁和明灭。他在每一篇访谈前都撰写了一篇随笔,如实表达他在跟随诗人回家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构成了他与诗人对谈的背景,并不断修正着他的提问的指向,而不是像我们屡见不鲜的访谈,把对话变成了让作家诗人填写的生平与创作履历的问卷调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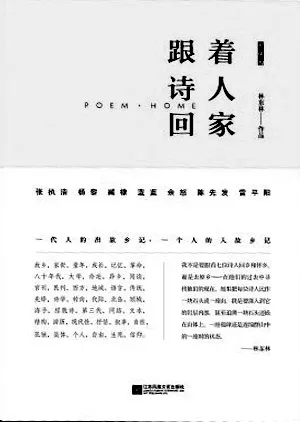
《跟着诗人回家》
选择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这七位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诗人作为“原”乡和访谈的对象,或许是因为,他们是怀有古典意味的“乡愁”的最后一代;他们还可以返身去指认故乡,哪怕它们已面目全非,令人痛心疾首。也或许是因为,在这个时代被边缘化的诗人形象,与被冷落、被遗弃的乡村或小镇形象,有着某种同构关系;而他们各自的人生观与文学观,也与其“出身”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同时,作为世界的抒情者,诗人对于时光飞逝、人生无常、物是人非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他们更能道出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以及为持存这一状态需要付出的艰辛努力。比如,在林东林眼里,张执浩是一位“写我们都看见过的却没有看清的事物”的诗人,一位以“自我发现”来为消逝的生活作证的诗人。在访谈中,诗人也以自己的写作观印证了东林跟随诗人“原”乡的意义:“写作并不仅是一味往前,不是通过数量累积把自己带向功名或成功,更大程度是为了返回和找到初心,找到自己在被异化时内心世界的来龙去脉:我为什么在这里?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人?”而对于诗人蓝蓝,由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她已很难说出“何处是我家”。林东林从她身上看到了两个蓝蓝,“一个是充满美好乡野记忆的、纯朴而恬静的蓝蓝,而另一个是人到中年之后带着粗粝、决绝和尖锐疼痛感的蓝蓝”,两者互为一体。在深圳读大学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蓝蓝不无感伤地说,每当推开窗户,“我只能抬头往上看,只有天空没有变”。尽管随处可见这世界恶的一面,但诗人仍不忘告诫自己要把愤怒铸成爱,用爱来与恶抗争,决不与恶同行。
访谈录这种形式,决定了它可能拥有更广大的受众群体,而不仅仅是文学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文学史家的“现场”素材。林东林作为访谈者的意图,也不只是为七位诗人“立此存照”,而是希望通过“贴身”的观察、了解和体验,来思索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面临“失根”危险的人如何自处,又如何与他人相处。在跟随诗人回家的步伐和探询诗人写作的独特风貌的时候,这本访谈录提示着阅读者,诗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诗人是“一个替别人做梦的人”(张执浩),在许多人的梦醒时分。诗人为我们观察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提供了另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阅读者所看到的必然比其他人更丰富多彩,他就会察觉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一个梦、一条路、一种声音。当诗人雷平阳说“我在我的整个写作之中”的时候,其另一句潜台词是“我的写作在整个时代之中”,但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变得越来越陌生,也越来越诡异。在此情境中,写作不是反映、折射、表现、再现生活;写作就是“叫”,就是“哀鸣”。诗人就是基诺人观念里的蝉,那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直到人间和天国的门都在叫声中訇然中开。而对于诗人陈先发而言,时代的危机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危机,因为我们在时代中,危机内在于我们自身,提醒我们的责任。因此,过得轻松自在未必是好事,极可能是假相。“写作的本质是发现一代人新的困境甚至是制造一种新的困境”,因为只有这样人才不会在生活和写作的惯性轨道上滑下去,才有希望避免某一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诗人兼评论家、学者臧棣则用“灵魂的地理学”,为他心目中的诗歌,也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定位,“我想最大限度地在诗的写作中重温人类经验中的天真的一面,诗的天真是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智慧”。而最深刻的危机莫过于,我们逐渐丧失了天真的能力,失却了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浑浑噩噩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甚至默认了各种伪装成真理的陈词滥调的催眠和腐蚀。由此不难发现,引发林东林兴趣的与其说是诗和诗人,不如说是人。他是在越来越同质化的人群中辨识越来越稀少的异质的个体。
苏珊·桑塔格坦承:“我喜欢访谈的形式,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中最困难的事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反常的活动。”今天,对话活动显得意味深长,是因为它不仅契合了以对话达成共识、消除纷争、彼此尊重的时代潮流,而且,读者也可能被真诚、机智、风趣的对话“卷入”其中,借此清理自己的想法,反思个人的局限。《跟着诗人回家》无疑具有这种效力,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效力。访谈者林东林是一个替我们发问的人,他以发问来保持住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并激发起读者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愿望,不再把自己闭锁在孤独中。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希求有完美的答案,但在追问中,一线亮光或许会透射进平淡无奇、循规蹈矩的生活。我喜欢的作家、诗人卡夫卡在与文学青年雅诺施的谈话中说:“沐浴在虚假幸福的光照之中的人最终必定会在某个荒凉的角落被自己的惧怕和利己欲窒息而死。”因此我们需要从“荒凉的角落”走出来,挡住“虚假幸福的光照”,去自我发现幸福的最初源泉。在《跟着诗人回家》中,七位风格迥异、性情各具的诗人也许会同意,在今天,写作者的意义就在于,让写下的东西重新给世界以光亮,让他自己隐匿在黑暗中,继续做梦。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学术》副主编,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专著(合著)四部,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