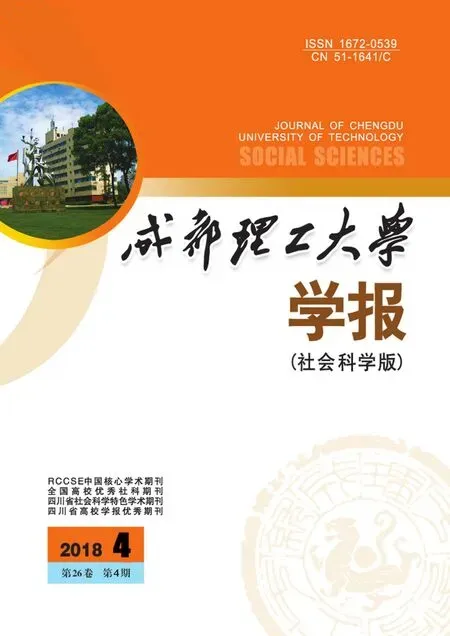多恩爱情诗中的生死悖论
胡小玲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内江 641100)
一、引言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的诗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创作注重形式的视觉冲击力和表达方式的大胆创新,而且还在于他丰富的情感。多恩的爱情诗中往往充满了复杂而矛盾的情感,而诗人的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又与诗人对悖论语言的娴熟运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悖论指的是看似矛盾实际或者可能正确的说法。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克林思·布鲁克斯就曾用悖论来描写诗歌语言的特征,并指出悖论语言是理想的诗歌语言。布鲁克斯还重点分析了多恩的诗歌,强调悖论是多恩诗歌的特色[1]19。显然,悖论在多恩的诗歌中无处不在。在多恩诗歌中的众多悖论中,笔者认为,生与死是多恩最为关注的悖论之一,也最能体现多恩对生命的深邃思考,蕴涵了诗人深厚的人文关怀。
二、生与死的对立
生与死是人类所关注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这一重要话题,诗人多恩也表现得十分敏感。在表达最炽热的爱情时候,多恩也未曾遗忘过死亡。在多恩的以《歌和十四行诗》命名的五十五首爱情诗中,有三十二首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死亡。在这些诗歌中,要么是多恩自己死了,要么是其爱恋的女子死了,要么就是两人都死了[2]。死亡曾让多恩恐惧,但是死亡又让多恩充满了渴望,因为死亡可以使得生命通向不朽与永生。多恩经常将生看作走向死亡的开始,而死亡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存在。多恩在《紧急时刻的祷告》的第十七章中曾说:
教会安葬一个人也与我有关,因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属于同一卷书;一个人死了,就好像书中的一章,并不会被撕去,而是被转变为另一种更美好的语言;书中的每一章都会这样加以美好的转变;上帝藉不同的形式来转变每个人的生命:有的通过年龄,有的通过病痛,有的通过战争,有的通过审判;不过,上帝之手行动在每一次转变中,就像在图书馆中整理好书籍,让所有的书彼此敞开。[3]
很明显,多恩对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复活理念深信不疑,他相信人死之后,上帝会赐予每个人另一种更美好的存在,即永生。在多恩看来,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生与死的界限已经模糊化。可以说,生与死的对立是多恩一生中最为矛盾的选择之一。
在《周年纪念日》中,多恩虽是在阐释“我们”的永不衰败的完美爱情,但是却是通过死亡的比照来强调这份永恒的爱情。在诗歌开篇第一节就表达出世间万物包括太阳这个时间的统帅都在慢慢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可是“我们”的爱情不受时间的限制,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摧残:
所有君王,及其所有宠臣,
所有名誉、美貌、才智的光荣,
制造流逝的时间的太阳自己,
如今,都比那时老了一岁,
那是你我初次相见的时节:
所有别的东西,都渐近毁灭,
惟有我们的爱情永不衰败;
这,没有明日,也没有昨日,
一直在跑,却从不从我们身边逃离,
而是忠实地保持它最初、最后、永恒的日子。[4]33
在“我们的爱情”面前,“君王”“宠臣”“名誉”“美貌”“才智”,甚至是“制造流逝的时间的太阳自己”都显得是如此的腐朽不堪。“我们的爱情”并没有像所有其他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衰退,而是“一直在跑”,却始终如一,永恒不变。这里的“跑”意象指时间的流逝,但更多的是奔向永恒,一种时间流逝,也可以说是死亡而带来的永生。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爱情的终结,相反却是新的起点——死开启了生。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在诗人看来,假如掩埋“我们”尸体的是一座坟墓,“死亡便不是离异”,因为只要有爱情常住的灵魂“从它们的墓穴中迁出时,那上空将增长一份爱情”。那么,死亡便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爱情在天国的一个起点,从而获得永生。“我们的爱情”原本就是人间俗物,也将随着时间的结束,死亡的到来而由此终结,但是却因灵魂、天国的存在而得到延伸、升华,并通向永恒。“我们”的爱情在走向死亡中获得了永生。从整首诗来看,生与死的悖论不仅彰显了“我们”的永恒爱情,也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的不朽爱情的魅力。又如《早安》一诗,多恩在最后一节强调,当恋人们的灵与肉和谐一致、融为一体时,他们是不会畏惧死亡的,因为死亡会给恋人带来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完美世界。
《成圣》中的凤凰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死亡即复活与再生的思想内涵。“我们”自比为双性同体的凤凰:“我俩合一,就是它的写照,/两性结合,构成这中性的鸟”。“我们”如若“非靠爱生”,却“总能死于爱”。凤凰毁于自己的火焰之中,再从灰烬之中重生,循环不已。“我们”为寻求那真挚的爱情而共同奔赴死亡,在熊熊烈火之中获得永生,从此远离尘世,追寻极乐的爱情。在多恩的时代,死亡喻指性爱。那凤凰的烈焰恰是“我们”的情欲之火。正是在情感烈焰中的凤凰离开尘世,从死亡中走向不朽,走向永生:
我们死而复生,又照旧起来,
神秘之力来自爱。[1]245
这恰巧表达出“我们”的爱情并非是仅仅沉溺于世俗的肉欲,而是圣洁的完美爱情。因此,只有这圣洁的爱情才配得上“在十四行诗中建筑寓所”,才让“我们”成圣。
在《计算》一诗中,多恩同样运用了生与死的悖论来深化“我”与“你”的不朽爱情。多恩写道:
最初的二十年里,从昨天算起,
我都难以相信,你竟然会离去,
以后四十年,我靠往昔的恩爱度日,
又四十年靠希望,只要你愿意,希望还会延续。
泪水淹没了一百年,叹息吹逝了二百岁,
一千年之久,我既不思想,也无作为,
意无旁骛,全部身心都只念着一个你;
或者再过一千年,连这念头也忘记。
可是,不要把这叫做长生;而应将我——
由于已死——视为不朽;鬼魂还会死么?[4]109
多恩在本首诗中对时间进行夸张化处理,营造出一种气势恢宏的氛围。诗人要表达的是“我”对“你”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描写“你”“我”之间的情意绵绵,并没有爱情诗中的娇柔,而是用了大量的数字来夸大时间的长度。“二十年”的时间也无法让“我”相信“你”已经悄然离开人世;“四十年”的时间靠往日的恩爱度日;另一个“四十年”“你”“我”的爱情还有希望会延续。在这另一个“四十年”里,“我”也将远离尘世,但是“你”“我”在死后仍有希望继续“我们”的爱情,因为只要“你”“我”愿意,“我们”在尘世未完结的爱情会在天国得到延续。“我”对“你”的真挚感情并非是这短短几十年可以衡量的。一句“泪水淹没了一百年,叹息吹逝了二百岁,一千年之久”通过彼特拉克式的传统意象和夸张的手法将“我”对“你”的深厚情感跨越到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通过层层递进,时间被无数倍地放大。在无限放大的时间的参照下,“我”对“你”的爱情也被无限放大,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正如多恩在《太阳升起了》中所吟唱:“可爱情都是一样,季节或天气,不会分辨,/或钟点、日子、月份——这些是时间的破布片”[5]。在诗歌末尾,多恩强调“不要把这叫做长生”,而应称“我”为“不朽”。“长生”即为不死,而“不朽”则暗指死后的一种再生。显然,最后两行诗句表达了“我”对“你”的爱情并非经历的是简单的时间跨度,并非长生不死的永久,而是经历生死后的一种永恒,暗含了生与死的对立。可以看出,在诗歌结尾,“我”与“你”的永恒不朽的爱情在生与死的对立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在多恩那里,死亡并不是一个人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存在开始的起点;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遗产》中,虽然“我”已经死去,但是却如一个活人一般,会说,会活动,会思考,还是自己的遗嘱执行人:
我听见我说,“立即给她捎信,
说是我自己”——那是你,不是我——
“杀了我”,当我感到要死的时刻,
我吩咐我在逝去后,寄出我的心;
可是我呀,当撕开我,在心
所在之处搜寻时;却什么也找不着,
这又一次杀了我,因为我生前一向诚实,
却竟然在最后的遗嘱中欺骗了你。[4]25
在死后,“我”仍旧能够听见(heard),感知(felt)死亡时刻的降临,吩咐(bid)寄出“我”的心,此外“我”仍旧能够记得“我生前一向诚实”,也能理智地辨别出自己的欺骗行为。作为人,与植物、动物最大的差别即理性。整个宇宙是多元的存在,如天使、人类、动物、植物和金石。多元的存在都是按照等级秩序由最高的存在,通过每种可能的等级逐渐下降,直到最低级的无生命的存在。金石只有存在,没有生命。植物则具有生命,但与动物相比却相对没有生命。植物只有生长功能;动物既具有生长功能又具有感觉功能;人除了具有生长和感觉功能外,还有理性[6]。在本首诗中,读者可以发现“我”虽然已经死去,但是“我”仍然具备作为生命存在的感知与理性。多恩在《悖论》一诗中宣称,“我”既是“我”,又是“我”的坟墓和墓志铭;包括“我”在内的死人们又在回忆并谈论着彼此的前生,作为死者的“我”还能辨别谎言。这样的描述让读者感到人在死后还可以继续思考,而“我”既是死的,又是生的。显然,多恩式的死亡比生更具有生命力,正如他所说“书中的每一章都会这样加以美好的转变”。
此外,多恩的一些爱情诗还以死亡来抒写生的状态,体现出生即是死的悖论观。《别离辞·节哀》开篇就将生离与死别联系在一起:
正如德高的人逝世很安然,
对灵魂轻轻的说一声走,
悲恸的朋友们聚在旁边,
有的说断气了,有的说没有。[7]
“我们”的短暂离别被看作德高望重的人的安然离世。本是短暂的分离却被诗人夸大到了永世相隔,但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们”也表现得十分轻松。一个简单的“走”字形象而准确地刻画出“我们”对待死亡的泰然。正如多恩在《断气》中声称:“一个死竟如此廉价,就像说:走。”死亡与活着似乎没什么区别,就像一个“走”字。“泪浪”“叹风”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多余的,这些只能是“亵渎我们的欢乐”。诗人通过时间的终极、死亡来抒写生的状态,烘托出真心相爱的人对待别离的一种泰然自若。
在《歌》(最甜蜜的爱,我不走)一诗中,多恩拿自己开玩笑,将装死看作真死:
最甜蜜的爱,我不走,
若只因对你心生倦怠,
或希望这世界能够
给我一个更合适的爱;
可是既然我必
最终死去,那最好,
拿我自己开玩笑,
这样靠装死而死。[4]23
诗歌一开始就直接表明,“我”不愿离开这“最甜蜜的爱”。虽然略显突兀,却写出了“我”对这份甜蜜的爱的难以割舍。可是,既然“我”终将死去,终将离开这甜蜜的爱,那就不妨假装自己死去。在“我”看来,死亡可以考验自己与恋人间的爱情。因此,在诗歌结尾,“我”告诉爱人:“我们”的死亡只不过是“转向一侧去睡”,但是“我们”彼此仍然是保持活着的人,是永远不会分离的。这和本诗第一行中的“我不走”形成了照应。纵观全诗,“我不走”不仅仅是简单地指活着的人的短暂的离开,同时还暗指了死亡。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将“我”与“最甜蜜的爱”分离。整首诗歌传递出“我”的死亡的假亦是真,真亦是假,道出了在爱的世界中,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生死悖论。
三、结语
综上可知,生与死是多恩所热衷的一个悖论,多恩爱情诗充满了他对生与死的沉思。
对于多恩来说,生与死的界限已经被消解、模糊化,他或者以生存的状态来抒写死亡,或者以死亡的状态来抒写生存。生与死相互依存,相互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生与死的转变皆是由于爱而引发的。多恩热衷于在诗歌中抒写生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多恩从小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殉教和复活思想,殉教被认为是生命的不朽,是生命的最高价值。这让多恩渴望死亡,由此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一种轻松,有时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基督教的复活理念让多恩深信不疑,使得多恩坚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极,而是另一种生命存在的起点,是一种比生更具有活力的存在状态。二是由于多恩的一生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他在四岁的时候经历了父亲的死亡。五岁的时候,大姐伊丽莎白病逝。九岁时,五妹玛丽和六妹凯瑟琳病逝。二十一岁时弟弟亨利因卷入宗教纷争遭逮捕入狱而死于瘟疫。之后,妻子以及四个儿女的相继死亡让他几度精神崩溃。此外,瘟疫时常横行伦敦,导致大量死亡;多恩也曾多次感染瘟疫,病情危重,直面死亡。显然,对生与死的思考贯穿了多恩的一生。面对死亡,多恩流露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多恩对生与死的深刻思考以及态度激发了人们不断地去审视生与死的意义,而多恩诗歌的价值也在人们的审视中得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