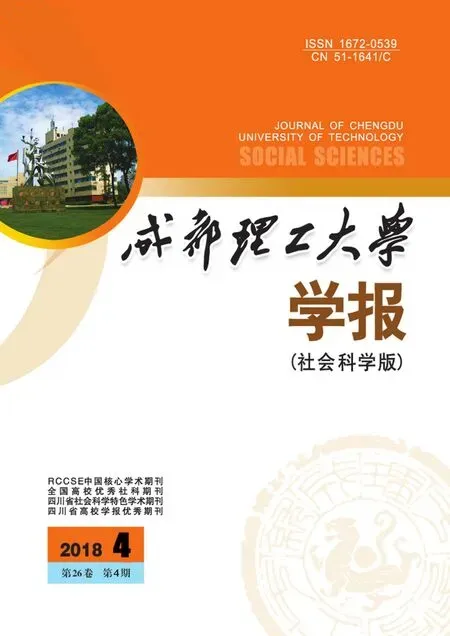持有型犯罪概念新探
农海东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南宁 5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考察近几年学者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研究探索,不难发现,学界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研究可谓争议不断,表现为对持有性质界定的各执一词及以各自所持理论为基础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不同界定,如以持有“行为说”为基础对持有型犯罪概念行为层面的界定及以持有“状态说”为基础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状态角度的界定。标准不一、缺乏权威性界定已成研究持有型犯罪概念的常态现象。然而,与持有型犯罪概念研究纷争不断的乱象不同,理论上对持有型犯罪特征的概括与总结却呈现和谐一致景象。从研究事物本质而言,外在特征是事物本质的最佳体现,从具体到抽象应是事物本质理论研究的正确思维。然而在持有型犯罪领域,长久的理论研究逐渐使持有及持有型犯罪概念探索形成“先论证性质、概念,后分析特征”的思维定势。先抽象后具体的思维路线容易产生理论与现实相脱离问题,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研究路线正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在本文看来,当前持有及持有型犯罪概念研究成果存在与自身特征不相匹配问题,因此需要打破“先论证性质、概念,后分析特征”的思维定势,回归由具体到抽象、从分析特征到性质、概念总结的思维路线,以得出正确结论。
二、我国持有型犯罪特征辨析
一般而言,刑法罪名间的区分常常是通过对各罪特征的完整把握得以实现,而对特征的把握有赖于对犯罪主客观构成、各罪于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犯罪司法实务标准等因素的正确理解。从概念归纳角度看,理论上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正确界定也是对同种类不同各罪的持有型犯罪特征进行本质抽象的结果。
(一)持有非法性
根据持有物品性质的不同,持有可分为两类,即支配普通物品的持有与支配管制类物品的持有。前者为常态化持有,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公民私权的具体化,往往受民法所调整,如放置家中的电视机、冰箱或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皆是常态化持有的不同形式表现。后者为非常态化持有,涉及国家管制制度的秩序维护,往往由行政法、刑法规制。支配管制类物品的持有类型根据是否具备国家授权又可进一步分为授权持有管制类物品与非授权持有管制类物品两类,前者如警察因公务所需持有枪支、弹药为授权持有,后者如公民个人非法私藏枪支、弹药即为非授权持有。本文所讨论持有型犯罪中的“持有”便是在非授权种类意义上所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持有型犯罪中持有的非法性特点。
持有非法性的有无由国家授权与持有物品性质所决定。由于司法实践中持有型犯罪惩治对象往往是非法持有的公民个人,因而认定犯罪的持有非法性有无更多体现在持有物品性质上(因为国家授权并不具备一般性特征,国家授权更多的是体现在行政领域如警察授权配枪、医疗机构授权使用精神麻醉药品等,因此刑法上持有管制类物品更多是在非授权意义上使用)。由此可推出,持有非法性体现为“持有+管制类物品”模式,即单纯持有本身并不具备引发刑法上危害社会的危险性,而只有在与管制类物品相结合(持有管制类物品)后所形成破坏现实的危险才是刑法规制的重点。
(二)持有对象法定性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不难得出,凡持有型犯罪的对象,必定是国家管制物品,然并非所有的国家管制物品,皆可成为持有型犯罪的对象。如果说国家对某特定物品实行管制规定是基于多种因素考虑而做出,那么,作为管制物品本身危险性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危险性是管制物品的天然特征,换言之,管制物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危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危险。此危险性,或有害于自身、或有害于他人(如枪支弹药、毒品),或可能造成客观上的损害、或可能副作用于精神层面(如毒品、淫秽物品)。基于此,实行国家管制实属当然之举。然而不同特定物品因种类特性不同,其外在危险性亦有大小之分,如需运用刑法予以规制,则不得不考虑危险程度、谦抑性等问题,显然具备达到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才是刑法介入调整的前提,同时符合谦抑之精神。因此,实践中采用持有危险性小的管制物品由行政法调整,持有危险性较大的管制物品由刑法持有型犯罪予规制的立法安排,是对谦抑性的严格遵循。对部分危险性较大的管制物品实行刑法规制,也决定了持有型犯罪对象范围的有限性,调整的有限性意味着法定性,换言之,法定性是持有型犯罪对象的鲜明特点,只有刑法纳入调整的管制物品才能成为持有型犯罪的对象。
(三)状态性与行为性相统一
状态性与行为性相统一是持有最具独特的表征。一方面,状态性是持有事实层面的内在属性。无论理论上对持有法律的性质争议如何发展,持有事实上作为一种状态存在是学界普遍的共识,状态性是持有最本质的属性。持有事实状态属性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持有的现实内容之中。就持有的内容而言,对特定物品的控制、支配是持有内容的本质,现实中持有一般表现为行为人携带、藏匿、拥有某些特定物品。考察上述内容特点,持有之所以于事实层面被判断为一种状态而非行为,皆因持有控制、支配特定物品并不以身体上之动静为必要,换言之,持有的完成并不必然伴随一定的身体动静。如拥有、藏匿某特定物品,在某些场合下并不一定需要行为人存在一定的身体动作或积极性行为,而只要特定物品是在行为人控制、支配范围内且其对此控制、支配存在认知,此时也可称之为持有。就此意义而言,持有是一种人对物的关系状态体现,是事实状态而非行为。另一方面,行为性是持有法律层面的外在属性。行为性特点是引发学界对持有性质理论长久争议的关键点。从属性位阶关系看,如果说持有状态性是持有的天然本质属性,那么持有行为性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伴随持有状态产生而显现于外部的具体外在属性。持有行为性特点体现在某些场合下推动携带、藏匿、拥有特定物品等持有状态实现的实行行为,此实行行为既可以贯穿于持有状态存续的始终(如非法随身携带枪支行为),也可以仅存在于持有状态存续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如非法取得假币到藏匿假币行为)。分析持有行为性内容特点不难得出,持有行为性特点并不能完整概括持有的全部内涵,因此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持有状态中的实行行为只不过是推动持有状态实现的重要元素,因此其与持有状态性的本质内涵仍有所区别,是一种可以被法律评价的具体外在属性。
(四)主观故意性
持有型犯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表现为行为人故意非法持有刑法规定的特定物品行为,过失持有特定物品行为不能构成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故意性特点首先由持有本身内容特点所决定。在本文看来,持有型犯罪持有的内容可从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理解,在抽象层面,持有表现为对某种特定物品的支配和控制,而在具体层面持有则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携带、储藏等行为。根据一般社会经验法则,无论是抽象的支配、控制还是具体的携带、储藏行为,对持有主体主观心态的考察往往是从行为具备有意性角度出发,盖因日常所言对某种物品的支配、控制多是行为主体有意为之,而少有无意的支配、控制存在,因而人们对支配、控制的问题讨论往往习惯于给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贴上有意性标签。从“立法者不关心稀罕之事”的法律精神角度而言,这极大程度地说明刑法上持有具备有意性特点。其次,持有型犯罪主观故意性特点也由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所决定。从考察行为的危害性角度,在同等条件下,故意持有特定物品与过失持有特定物品相比,前者更具有明显的危险性,如故意持有毒品的危害性比过失持有毒品的危害性要大、故意持有假币的危害性比过失持有假币的危害性要大。就此而言,故意持有特定物品显然更具有刑法调整的必要性。
三、现有理论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界定及其缺陷
从具体到抽象是研究事物本质的正确思维路线,对性质、概念的总结尤其如此。持有型犯罪概念的总结必然是在把握持有型犯罪特征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结论,持有型犯罪概念的表述也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持有型犯罪特点。从相反的角度而言,如果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界定无法完整体现持有型犯罪的特征,那么此概念界定及其理论根据是否具备合理性显然存在疑问。
(一)以持有“行为说”为根据的界定及其缺陷
随着持有型犯罪立法不断向前推进,学者对持有性质之理论争议渐成为一种常态,形成“行为说”与“状态说”两种主要观点。与颇具颠覆性的“状态说”理论相比,传统的“行为说”理论大概使学者更易于接受,因而经过漫长争议而逐渐发展成为其中的主流。在本文看来,“行为说”是一种集合型概念,由“作为说”“不作为说”及“第三种行为方式说”三种具体学说组成。简要梳理三者观点的差异,“作为说”认为持有是一种行为,而持有型犯罪则是行为人以积极性行为违反刑法关于禁止持有某些特定物品规定的一种作为犯罪[2]。“不作为说”也认为持有是一种行为,但在持有作为、不作为属性界定问题上,“不作为说”主张持有是一种不作为犯罪,即持有是行为人以消极性行为违反刑法所规定的对某些特定物品负有上交或者销毁义务的一种不作为[3]。“第三种行为方式说”也持“持有是行为”立场,认为在行为分类上,作为与不作为的二元划分并不能完全概括行为的所有属性,在两者之外应当存在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即第三种行为方式。持有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理论上将其视为作为或者不作为都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局限性,持有应属于区别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第三种行为方式[4]。总而言之,“行为说”诸多理论皆认为持有的性质是一种行为,就所持立场来看,“行为说”是站在刑法是行为规范而非状态规范的立场,认为刑法调整人的行为而非某种状态,将持有视为行为更有利于维护传统以行为为基本规范对象的刑法体系构架。理论上对持有及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研究也是以此立场为出发点,体现在犯罪概念阐述中是对持有行为的具体化描述,如“持有型犯罪是以持有为共同构成要件行为的一类犯罪,是指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支配或者控制某种特定物品,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一类行为。”[1]不难看出,“构成要件行为”“行为”等字眼描述是对“行为说”基本立场的贯彻。
从主客观相统一角度考察犯罪概念的界定,以“行为说”为根据的持有型犯罪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缺陷,体现在对持有型犯罪客观方面特点概括不全。正如上文所言,行为性与状态性共存是持有最鲜明的特色,这就决定了对持有概念的界定必然无法忽视持有的这一特点,从相反的角度而言,任何忽略持有行为性与状态性特点或仅把握其中之一而忽视其余部分特点而作出的概念结论皆存在一定局限性。以“行为说”为基础的持有型犯罪概念界定便属于后者,此类概念界定将持有型犯罪定位为一种纯粹的行为犯罪固然是对持有行为性特点的准确把握,但显然此界定并不能完全归纳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质,遗漏持有的状态性特点决定了此类界定存在缺陷是必然的。
(二)以持有“状态说”为根据的界定及其缺陷
另一种观点“状态说”认为持有的本质是一种状态,与行为不同,持有不过是一种现象的归属状态或者关系,并不必然具有违法行为上的身体动静,因此刑法规定持有型犯罪是以持有状态为调整对象[5]。 “状态说”对“行为说”的批判是建立在把握持有事实状态属性的基础之上,认为“行为说”将持有视为行为是对持有本质属性即事实状态的违背,因而并不能体现持有的特殊性质。与上文相似,学者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总结也体现了以“状态说”理论为基础的推理。如有学者即认为“持有型犯罪,是以刑法规定特定物品的非法持有状态作为刑事责任追究基础的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6]此处学者即认为持有型犯罪是对非法持有特定物品这种状态的规制。
同样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角度分析,以“状态说”为基础的持有型犯罪概念界定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明显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界定缺少对主观方面的考察。正如学者对“状态说”所作的其理论缺少主观认知性内容的批判,抑或在“状态说”看来,持有状态的存在及其入刑并不以主体是否具备一定主观心态为必要,因而与“状态说”理论相对应,对持有型犯罪概念的阐述也缺乏对主体主观方面的考察,此显然有违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二是概念界定未能完全概括持有的特殊性。如果说前述以“行为说”为基础的概念界定只把握了持有的行为性而忽略持有的状态性,那么此处以“状态说”为基础的概念界定则显然与之相反,即只把握持有的状态性而忽略持有的行为性。因此,以“状态说”为基础的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界定同样无法完整体现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
四、建议及结论
首先,持有型犯罪概念的界定主观上要完成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认定。在本文看来,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立法、司法实践活动,刑法相关概念的理论研究也同样需要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此,具体犯罪概念的表述中除必要的犯罪客观方面描述外,应当体现主观方面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犯罪概念阐释对主观方面特征的体现并不必然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实现,也有可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如把握概念的完整意蕴来实现,这样的区分是由不同犯罪的客观方面特征所决定的。如危险驾驶罪,其概念表述显然并未明确表达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特征,但在一般社会经验法则看来,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具有明显的有意性特点,因此司法实践中往往可以通过把握其客观表现推敲行为主体背后的主观心态。相反,某些犯罪中单以客观特征描述并不能简单推导出行为主体的主观心态,因此,要在概念中对主体主观方面加以强调。如故意杀人罪,该罪之所以强调杀人的主观故意性,多是因其客观表现“杀人”并不明显表现主体的有意性特征,实践中杀人既可以表示故意杀人,也可以表示过失杀人,因此故意杀人罪需要在概念中明确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性,以区分过失杀人情形。正如前文所述,持有型犯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客观上的支配、控制虽体现相当程度的有意性,但持有主观上仍存在故意与过失之分,因此,同样为将过失持有与故意持有进行有效区分,持有型犯罪概念有必要对持有主体的主观心态加以强调。
其次,持有型犯罪概念的准确界定客观上要完成对两个问题的解答。一是犯罪对象范围确定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危险犯,持有型犯罪构成中危险结果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所持物品而非“持有”本身所表现。“持有”作为一种日常现象,本身并不具备犯罪危险性,而只有在与一定危险物品相结合之后才显示出其危害社会的危险。行为人持有何种类型的物品或者说犯罪对象种类范围的确定是认定持有型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要素。就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持有型犯罪所明确规定的犯罪对象具体包括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武器、危险品;爆炸物;毒品;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几种。结合持有型各罪的犯罪构成分析不难发现,有的各罪行为人持有一定危险物即成立相应持有型罪名,如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而有的各罪行为人单纯持有一定危险物并不必然成立持有型犯罪,往往需伴随一定场合的出现放大其危险性才成立相应犯罪,如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有的各罪在持有物品上明显体现违禁品性质,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中的枪支、弹药,而有的各罪其持有危险品却并不必然包含在违禁品范畴之内,如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中的武器以及持有假币罪中的假币。由此可推出,使用“违禁品”一词作为持有型犯罪中危险犯罪物品的一般性表述显然不相匹配,而前述所提“特定物品”则可适中概括持有型犯罪危险物品的一般特征。
二是“持有”性质界定问题。正如上文所分析,持有事物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当前几种学说理论皆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这就进一步导致以此诸多学说理论为根基的概念归纳也存在不足。无论“行为说”(作为说、不作为说、第三种行为方式说)还是“状态说”之间理论如何发展,持有事实上作为一种状态存在已成两说间的共识,这是事实层面对持有性质的无争议评价。然而,持有并不单纯是事实上的状态存在,现实中仍表现出一定的行为性特征,容易与行为相混淆。这就导致在法律层面持有应如何进行定性成为理论争议焦点,换言之,“行为说”与“状态说”所争议是持有应当以何种姿态进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前者认为是行为,后者认为是状态。立足于持有的本质分析,“行为说”与“状态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就“行为说”而言,因持有是一种状态,“行为说”并不能解释持有,坚持将持有视为行为会掩盖持有的本质特征。就“状态说”来看,因刑法是一种行为规范,“状态说”并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精神,坚持刑法调整持有状态的说法有违刑法行为规范的设置。
既然“行为说”与“状态说”皆无法作为充分解释持有入刑的理论支撑,那么在两者之外探索持有入刑的理论根据则成为必要。在本文看来,“拟制行为”理论更适合作为持有型犯罪的理论根据。“拟制行为”理论认为,持有虽然是一种状态,但却具有行为性特征,持有与行为虽本质不同,但表征相似,完全符合拟制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因此主张将持有拟制为一种“行为”,以解释持有入刑[7]。从拟制可行性来看,持有具备满足法律拟制的条件。一方面,法律拟制要求拟制范围限于事实且不修改现行法律规定。将持有拟制为行为是对持有性质的理论界定,也是对持有法律性质的进一步确证,此举并不改变持有型犯罪的原有规定。另一方面,法律拟制要求拟制对象与目标之间具有异物相似性。从事物本质来看,持有与行为存在本质差别,前者是物的支配、控制状态,后者一般表现为违反规范的身体动静,但持有与行为之间仍具有一定相似性,即两者皆具有高度相似的行为性特征。此外,法律拟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从拟制效果看,将持有拟制为行为必然使司法实践认定犯罪更具有可操作性,最终仍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解决问题角度而言,“拟制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对上述两说缺陷问题的合理解决。一方面,将持有拟制为“行为”可以对外宣示持有的状态特殊性,并不会导致抹杀持有状态属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将持有拟制为“行为”是对刑法行为规范设置的契合,并不会引发倾覆刑法体系风险。
综上所述,所谓持有,是指具备违法行为性特征,违反刑法规定故意支配、控制特定物品的状态。与此相对,持有型犯罪的概念是指以故意支配、控制特定物品所显示出的持有违法行为性特征为调整对象,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一种特殊类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