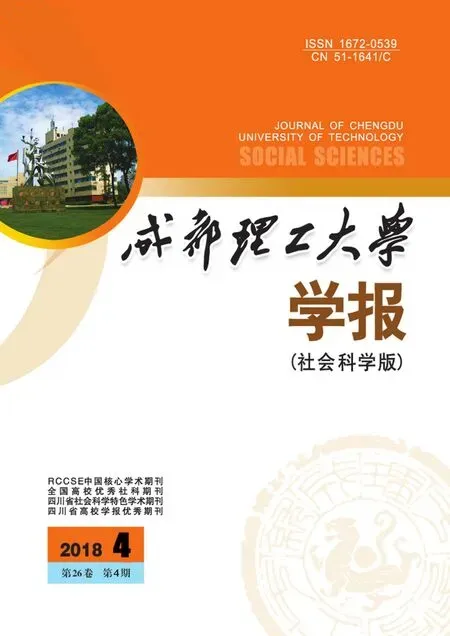自我与民族的书写
——阿摩司·奥兹与《爱与黑暗的故事》
唐 蕾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全书以“我”的视角见证了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大小事件,其中最成功的部分是以色列人的家庭生活和童年的成长经历。浓郁的人情氛围和良好的阅读环境给奥兹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奥兹在作品中推荐了很多人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这部作品和奥兹所推崇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风格正好相反,不求主题高尚、故事宏大,而力求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之不易,细腻而牵动人心,一下子就能够抓住了人们的神经。奥兹的这部《爱与黑暗的故事》由此而萌发灵感,成为他向世人展示自己平庸生活的一面旗帜,在此以后,他不再惧怕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平常和柔弱。
这部作品有几大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家庭亲情、知识分子生活、真诚的写作态度、名士云集时代的见证者和宽容与爱的主题。奥兹所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表现这些内容,但在这一部作品中相对集中地容纳了上述所有的创作特点。作品层次清晰、饱含着浓浓的人情,融入了作家深厚的情感和细密的思索。
一、家庭亲情
犹太民族推崇家庭观念和家庭教育,即便在流亡和动荡的岁月中,也能够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平稳而踏实的家庭环境。奥兹的父辈和先人们都曾遭受过苦难和阴霾,但是他们从不会让孩子为自己分担忧愁和烦恼,而是想方设法为孩子营造快乐和幸福,给他们创建一个正常而有序的家庭环境。奥兹的父亲身为饱学之士,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大学里谋得一席之地,在知识分子严重富足而劳动力严重缺失的以色列,只能委屈自己做着一份安稳但与才学不匹配的工作,他常常为自己才学无人赏识而深感苦恼,但没有因此消沉退缩,而一直怀揣求知的理想,引导孩子走向写作和研究之路。父亲对知识的尊重和探求深深地影响到儿时的奥兹,这种耳濡目染的浸润伴随奥兹一生。奥兹在书里这样说过:“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2这一丰富而又完美的童年融入了浓浓的亲情和关爱,是奥兹成长道路上接纳的最丰厚的礼物。作品中平淡而自然的生活画面、严厉而治学认真的父亲、听话而多思的孩子、六岁时的读书“成人礼”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和诗意。奥兹每一步的成长都受到来自身后家庭的深切关注。在幽暗和忧愁的岁月里,来自家庭的爱伴随着奥兹茁壮成长。
《爱与黑暗的故事》讲述了“我”“父亲”“母亲”“祖父”亚历山大、“伯伯”约瑟夫和姨妈们等亲人们的故事。浓浓的亲情、淳朴的民间生活、良好的读书氛围和成长环境为奥兹的写作之路作了长远的铺垫。家庭主题是奥兹作品中最常表现的主题之一,它所呈现出来的、特有的以色列家庭伦理和家庭温情打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奥兹试图用一种宽容而纪实的手法再现以色列近几代移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向人们展示他们曲折而艰辛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伟人,但在最卑微的生活里,亲人们都能努力保持自由人的尊严和人格,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未来。亚历山大祖父和祖母移民的过程见证了欧洲犹太人大迁徙的历史进程,虽然其间充满险恶和磨难,但在作品中,却被作家有意以一种自然的温情和人性的诗意弱化,没有生硬和阴暗的内容,却洋溢着轻快和喜庆的气氛。幽暗和光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但这在奥兹的作品中却有所取舍。奥兹看到了幽暗,却用明亮而温情的笔法记录了流亡岁月里人们生活中善意而温暖的点点滴滴,表现了一个个充满人味儿的小故事。犹太人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很有东方特色,这种大家庭的相处模式丰富和规范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犹太流散民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亚非,有的扎根本土,他们的语言和习惯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多元化是奥兹了解世界各地语言和文化的契机。奥兹的母亲范妮娅来自波兰,而父亲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把欧洲的两种文化和多样的语言融入到了奥兹的童年生活中。 母亲给奥兹疼爱和呵护,给他讲离奇而神秘的故事;父亲手把手地教给他知识,引领他走向写作之路。约瑟夫伯伯家门庭若市、人来人往,曾一度是阿格农、车尔尼霍夫斯基等名流光顾的地方,是以色列知识分子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沙龙之一。约瑟夫伯伯给童年的奥兹点燃了求知的梦想,他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幼小的心灵。奥兹的作品和他的个性是吻合的,温和、平实而没有突兀和尖锐,宛如一杯温开水,让人读起来深感慰藉。奥兹擅长在平凡生活中塑造如“大地之盐”般的平凡人,写他们复杂又单纯的人性,表现他们幽暗而光明的生活,找出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动人之处。一场又一场的家庭聚会、宴席上的美食、倾听大人们的谈话、一个人的玩耍,成为奥兹童年记忆中主要的内容。小说以单向性的线索历时性地记载了童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这一部分中,其不遗余力的表现手法让人难免会联想起简·奥斯汀小说的风格,同样的细碎,但也同样的趣味横生,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奥兹曾经为自己经历匮乏和生活平淡而写不出宏伟巨制而懊恼过,但这一部作品却正因为它的平凡和平淡而打动人心,就像他在书里写到第一次碰到安德森·舍伍德《小城畸人》时一样能够点亮人生。
奥兹在写这部自传体小说时,基本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叙述结构,在叙事策略上也使用了截取一段一段家庭生活片断为特点的创作手法。儿时的记忆片断以家庭生活为叙事单元前后相连,形成了有序而连贯的书写结构,看似零碎,但井然有序。
二、一如既往的“掉书袋”
奥兹关注和钻研每个人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背景。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长串名字和书名,这对研究以色列现代文学有帮助,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奥兹的生平及影响。奥兹的童年和青少年阶段阅读过大量优秀的作品,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例如: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拉海尔、车尔尼霍夫斯基、阿格农、屠格涅夫、儒勒·凡尔纳、海明威、舍伍德·安德森、杰伯廷斯基等作家。除了作家,也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诸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格涅辛等人。约瑟夫·海姆·布伦纳在奥兹的眼中是典型的俄国犹太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阿格农则是典型的加利西亚小伙子,同时又是虔诚的阅读《塔木德》式的学生。在学习知识、尝试创作的路上,奥兹学习父亲认真求实的作法,不偏致、多甄别,因此,他从未完全听信于一种声音或一个立场,在其创作中体现出多元的、开放的阅读视角。父亲“嗜好崇高,而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我父亲热切崇拜亚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还崇拜丘吉尔的演说”,“妈妈脸上露出拉海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温柔微笑”[1]255。奥兹从父母的阅读体验中学习了解不同风格作品的艺术魅力,在自己的创作中尝试表现一种无所不包的艺术张力。奥兹相信父亲所说的书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有的人写的书没有生气,而他认为另一些人的书则充满生命力,甚至可以点亮别人的人生。值得一提的是,奥兹数次提到了父亲的好友以色列·扎黑——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奥兹援引父亲的评价“用头脑在写书”高度肯定扎黑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儿时的奥兹一时无法明白大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但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1]135。青少年时期的奥兹阅读过大量的名著,其中包括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凯旋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等带有英雄情结的作品,唤起心中强烈的冒险和游历的想法,然而环顾四方,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活,也没有“激情的波西米亚生活”。在“恶性循环”的阅读体验中,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强烈震撼了他幼小的内心。他在“这部质朴无华的作品”中发现了欢乐和狂喜。奥兹在书里这样写道:“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1]501奥兹把这本书看作点亮自己一生的作品,他从《小城畸人》作品中发现了世界就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笔下。这些优秀的作品引领着作家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而他也慷慨地把它们呈现于世人面前与之分享。
奥兹的作品全面而深刻、细腻而富于生活气息,描写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情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的语言显然带有某种共性和大众性。然而,大量的文化典故和知识点想当然地屏蔽了一部分没有耐心和缺乏文化基础的读者。换而言之,奥兹的作品是有特定选择性和指向性的。奥兹无意去卖弄知识、卖弄学问,而是他痴迷于探究文化史的下意识所致。奥兹的作品中不仅有大量的文学史知识,还大量涉及宗教、历史、军事、政治、经济、伦理等多学科的知识和常识,显示出他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人文素养。人们初接触奥兹作品时,往往是由于其生动而有趣的故事而深受吸引,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对之作品深入地了解,被奥兹一路引领——“向上攀升”。奥兹像一个对世界充满柔情、好奇的孩童,又像一位伟大的导师,引领人们不断地了解自我、了解世界,达到一种全面和丰富。这也是经典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所在,它具有跨越民族界限和时间界限的跨越性。奥兹的作品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有关文学史的知识点,而且在这些庞杂的知识点中还有大量的重合和重复,这些重合和重复是了解奥兹的一把钥匙。作家在一部作品中不断重复和不断强调的作品和作家一定是对他影响最多的作品和作家,这一定不可以被忽略不计,而应当被视为通向作家思想深处的关键。
三、真诚不隐瞒的态度
有些作家愿意把10%交给读者,有些交出50%,有些70%;而奥兹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以他100%的诚意和本分把自己交给了读者,这十分难得,让人敬佩他的勇气和诚实。除了真诚的态度,还有对生活真实的反映,“不虚美,不隐恶”——坦诚自己不可克服的性格弱点并还原以色列上百年来真实而充满坎坷的求索之途。奥兹始终站在某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放远视线、拓展格局,对人性和人情生活充满深切的感悟和体察。这个知识分子富足有余的以色列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被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体现了作家客观而求实的写作风格。
奥兹以自己作为主线,见证了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历史,并详细记录了家族艰难曲折的迁徙过程和生动的家庭生活。奥兹对每一位家族的成员展开了庞大而细致的谱系梳理,甚至对于每一个人的缺点和弱点都没有轻易地忽略过。奥兹有意塑造真实而复杂的艺术形象,因此没有刻意地隐瞒每个人的瑕疵,但是他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基于真实生活基础之上的再创造。父亲的求实和勤勉的知识分子个性、母亲的温柔和才思、贝京的热情和力量、亚历山大祖父的多情和活力、“我”的聪颖和敏锐,个个跃然纸上,形象生动。人往往是善恶和美丑的杂糅体,例如:父亲有他的自私和多情、母亲敏感而多虑、贝京偏致而冲动、亚历山大祖父滥情而自私、“我”的敏感和幽暗。奥兹的文字往往充满诗意,但却不会显得生硬造作,原因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都遵循情感和审美艺术的自然规律。奥兹不惧怕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的懦弱、自我、忧郁、叛逆和闪烁,而是勇敢地把自己的生活全部展现出来,体现出一位作家虔诚的写作态度和真诚的人格魅力。奥兹认为人性是复杂而流动的,他认为人们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中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一个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也可能是穷兵黩武的独夫;一个人可以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盲目冲动的小丑;一个人可能是万众瞩目的领袖,也可能是遗臭万年的刽子手;一个人既可能是一个仁慈善良的长者,又可能是无情自私的爱人。人的可写之处正在于人的复杂和人性的深不可测,这在奥兹的作品往往是最想表现而又最难表现的部分。奥兹给予每个艺术形象以可能多相应比例的篇幅去铺垫和展示,他浓墨重彩表现的人物是他人生道路上对之影响深远的人们,而他轻描淡写的人物群成为我们了解以色列社会最关键的部分。奥兹对父母家庭的依赖和诀别、对基布兹的憧憬和失望、对以色列知识分子的尊敬和鄙视、对自己的肯定和否定,每一种心思的变化和情绪的波动都以细腻的文字摘录下来,内容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一部《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段人生的成长经历,正如作家在书里所言:“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2奥兹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甚至时常会否定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的真诚和朴实是其作品能够收获肯定的重要原因。奥兹从未有意取悦读者,而是诚实地面向过去、展望未来。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1]4
四、名人辈出的见证者
了不起的思想者、著名的政客、隐遁的大学者、不得志的有为知识分子等人物和奥兹的一生纠结在一起,奥兹有幸参与和目睹了大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因此,他是幸运的。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奥兹大格局的写作视阈。众人的双臂将奥兹高高地举起——奥兹高高地站在小山顶上眺望远方,凝思足下。
奥兹是在爱与忧愁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以色列文人。奥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而在他笔下,塑造最成功的也是知识分子。奥兹相比其他人要幸运得多,他生活在欧洲知识精英文化大迁徙的转型时期,得以有机会和名家巨匠同处一城并见证以色列新国家由动荡到平稳、由散乱到整合的建设过程。奥兹在作品中充当了串联历史事实的主线,同时也充当了以色列的书记官,将个人生活和历史事件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有说服力。马丁·布伯、阿格农、布伦纳、车尔尼霍夫斯基、约瑟夫·克劳斯纳等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就住在奥兹家的隔壁或者临近几条街道上,他们甚至常常和奥兹亲密接触,尽管这些还非严肃的、文学意义上的真正影响,但是儿时生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以色列对作家影响深远。对奥兹一生影响最深的学者当属奥兹的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一生致力于勤学苦读,唯一的人生愿望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著书立说、扬名天下,然而在名家辈出、知识分子严重过剩的时代,其梦想也最终只能是走向流失,但父亲对奥兹儿时的教育以及人生道路的指引是奥兹实现作家之梦的重要支撑。作品中也深入而细致地讨论了以色列知识淳正的学术氛围受到人情生活严重干预的真实现状,对此,作品通过对父亲一生执着求索的艰辛历程反观了以色列知识界的幽暗和扭曲。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对于所有的阴暗和不合理并未坚持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他始终能够从人性和人情的角度反观社会不良现状。奥兹甚至认为这种不合理性是人性幽暗之所在,但他相信幽暗并非全部,而只是一部分,如果彻底无视这些不良现状是对现实世界的无知和鲁莽。这部作品提到的著作有近百部,而重要的学者有几十位,他们的光芒即使在最幽暗的时代也无法被遮挡,即使某一个时候不能为人们真正理解和接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大浪淘沙,最终会迎来真正的读者和他们的时代。奥兹相信,严肃而有良知的著作永远不以取悦他人为目的,因此,世俗的评价和计算无法和它们真正的价值等同。奥兹在作品中对沉默隐忍的知识分子表现出高度的肯定和认可,他们成为奥兹创作生涯里坚持走下去的动力和信心。
以色列的建立和作家的童年阶段是重合的,奥兹亲历了联合国大会公布结果的惊心动魄一幕。童年和少年阶段的奥兹是个充满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的孩子,他追随祖先和父辈们重归“应许之地”的梦想,把自己看成新以色列国家十字军复国主义的一分子。本·古里安被看作以色列新国家的民族英雄,而梅纳赫姆·赫京则是奥兹少年时期的偶像。但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也是树立偶像和推翻偶像的过程,奥兹并没有盲目地崇拜这些人,而是严肃地审视和思考他们每个人在政治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他们的功与过都有客观而理性的评价,表现出一位作家独立而生动的人格魅力。
五、爱与宽容的主题
奥兹在作品中表达的爱的主题并非犹太教教义的忠恕之道,而是建立在一种人性和人道基础之上的爱与宽容,主张各民族、异质文化之间对话、沟通和理解。奥兹反对偏致的宗教热情、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伪善的国际援助,他主张民族融合、和平相处。
奥兹对阿拉伯人的态度暧昧,想亲近但又不得其法,表现出对民族问题一分为二的理性思考。他同情阿拉伯人,在所有的作品中从未把他们描写成丑陋的敌人,而是和犹太人一样受苦受难的上帝子民。对战争的反思、两族仇恨以及战争起因均作出理性的思考。
奥兹既想保家卫国、捍卫犹太人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又满怀对阿拉伯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强调爱与宽容、两族共促,但对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民族居住点等问题也深感困惑。“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未必能同舟共济,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运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化身。”[1]349
奥兹童年时代受到父辈们民族情绪的影响很大,他曾经自诩为新一代的“十字军复国主义者”,仇恨纳粹、英国占领军和反犹组织,儿时的游戏里最爱玩的就是虚拟战争,他把自己假想为犹太军,攻占一个又一个难克的堡垒、一次一次打败英国占领军和阿拉伯人。他崇尚皮肤黝黑、力大无比的英雄,为自己的羸弱和矮小感到羞愧,他甚至和很多新一代犹太人一样,不明白犹太大屠杀是怎么能够造成的,他不明白那么多犹太人怎么就心甘情愿束手就擒,为他们的懦弱和服从深感耻辱。儿时的奥兹身上有强烈的民族热情和爱国热忱,他形容自己是“披着热爱和平外衣的小沙文主义者,一个道貌岸然、满口甜言蜜语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年仅九岁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喧嚣鼓噪者”[1]341。但是,阿拉伯人就生活在犹太人隔壁,他们更多的人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地生活,过着与人无过的生活。奥兹从未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真正的敌人,甚至同情他们的遭遇。在作品中,奥兹喜欢用“阿拉伯兄弟”和“大叔”称呼他们,喜欢描写他们朴实的日常生活。
十几岁离家前往基布兹过独立生活的奥兹对阿拉伯人问题开始独立而深入的思考,一次和同伴交谈的经历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月朗星稀的夜晚,两个男孩坐在荒凉的草地上仰望星空,伙伴对奥兹说:“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1]444两个孩子对于应该获得和怎么获得生存权问题的讨论折射出以色列人对于巴以问题矛盾多元的态度及立场。奥兹从儿时激越的民族主义立场转变为宽容而温和的对话立场,这是个体获得成长的过程。奥兹提倡的爱与宽容,是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界限的选择。
对每个个体予以尊重、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给予宽容和理解,这是奥兹所理解的多元文化观念。其中,宽容的人情观念不仅体现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在对于人性复杂性的洞察以及对人情的包容和接纳。奥兹笔下的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小问题,但在奥兹的笔下,他们的缺点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如果没有被如实地表现出来,就会让人感觉不真实、不够味甚至不完整。奥兹对待人情生活和人性的理解带有辩证式的思考,他首先承认人性的不完美性;其次,不将人性的不完美当成无可救药的致命弱点,而是致力于从另一个面去解读其存在的自然性和合理性。亚历山大爷爷的浪漫和无情也正是他的快乐和多情,在灰暗的岁月里,他可以让自己永远都像十八岁,虽然看似自私地享受生活,但无形中给别人带来生的活力和感染力。奥兹写爷爷的时候,饱含着对他乐观生活态度的欣赏和肯定,因为他就是生命力的体现。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最值得人们歌颂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奥兹的宽容哲学既是指对异质文化的宽容和理解,也是指对人性不完美性的宽容和接受。
六、结语
在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塑造了几十个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奥兹喜欢将身上的闪光点和缺点融合在一起写,因此,他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而不会显得生硬呆板。奥兹作品胜在平和温暖的包容力,而不是激烈突兀的批判。每一部作品都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个家庭生活内部讨论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奥兹善于反思、善于追问,体现出一个作家对生命本身深刻的理解和关切,没有避重就轻,而是诚实地面对矛盾并试图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