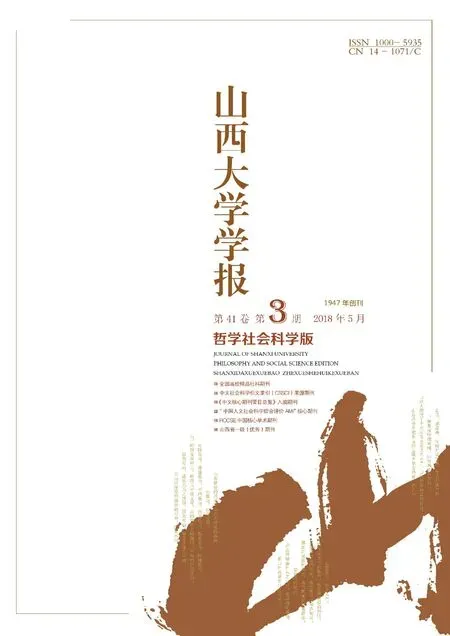论宪法权利规范的性质
胡显发,王夏昊
(1.中国政法大学 证据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2.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1967年,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明确提出,法律规范在性质上可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规范,即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法学理论家都接受了德沃金的观点。[1]由此便衍生出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规定的诸多权利构成了宪法的基本内容;这一基本构成究竟具有规则性的特征还是具有原则性的特征,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依据内容的不同,宪法规范可以被分为两类:组织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后者既关涉公民个人的权利也关涉公共权力,它不仅规定了公民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指示出了公共权力的界限;因此,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只论述宪法权利规范的性质。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方式的不同以及它们相互抵触的解决方式不同。因此,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具有不同规范的特性,就决定了宪法权利适用的理论、方式、方法的不同。正如阿列克西所说,对宪法权利规范的解释或建构(construction)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个是狭义的严格的规则方式,另一个是广义的包容的原则方式。这两种纯粹的方式没有在任何地方被实现,但是,它们代表不同的趋势,其中哪一个方式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宪法解释学的中心问题。[2]131-132我们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法律原则以及法律规则的基本概念问题。
一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分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分建立在对它们的上位概念—规范—的理解基础之上。何谓规范?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规范”属于“应该或应然(Ought)”领域,而不属于“是或实然(Is)”领域。“应该”与“是”的区分是西方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我们将其作为不可再被进一步定义的两种基本模式。“应该”又可被区分为“应该是(ought to be)”和“应该做(ought to do)”,[3]前者的意思是某事情被命令、禁止或允许具有什么性质,例如“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共道德”;后者的意思是某事情被命令、禁止或允许做,例如“军人的配偶离婚必须征得军人的同意”。
法律规则是“应该做”的规范,法律原则是“应该是”的规范。前者的内容是要求规范主体“做”或“实施”某行为或活动(do action),而后者的内容是要求规范主体的行为或活动符合某种性质或实现某个目标。“某事情应该是”常常是一个省略语,它包含了默示地指示(implicit reference),这个默示指示通常是某目标(end)或目的(goal);如果这些目标或目的被承诺,那么“应该是”的东西便会被转化为某种命令或需求。而且,“某事情应该是”这个省略语常常显示了对于讨论中的目标的一种肯定态度,目标是我们珍视的或希望的或热切促进的某种东西。因此,这里应该使用的最好术语也许是评价的(evalutive)。[4]199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法律原则处理的是命令“什么应该是”的事件的理想状态(the ideal state of affairs)。[5]18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理念与法律原则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里的法律理念抑或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价值。例如法律保护了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也就意味着自由与平等是应该被尊重的。同时,价值的背后包含着一定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在实践中通过诸多方式得以满足或者实现。[6]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法律原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最佳水准的一种命令。
虽然同为一种法律命令,但是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前者是在一定条件下趋于最佳化、最合理化的命令,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后者则是一种确定性的命令。在具体的某个案件中,依靠某种客观的法律事实、通过一定的法律适用来实现法律原则。这种实现与满足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同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则的使用,另一方面取决于与之具有同等地位的其他法律原则。[7]
如上所述,法律原则之所以是最佳化的命令,原因在于它是“应该是”的规范。“应该是”的规范主要关涉事态的性质,规范主体如何行为或活动去产生或维持这种性质,需要规范主体根据特定场合而决定。[4]200法律规则是确定性命令(definitive commands),是指法律规则在事实与法律的可能范围之内具有固定或确定意义(fixed points);具体地说,如果一个法律规则被有效地适用,那么,它所规定的内容将会不多不少地、确切地被实现或实施。[8]48法律规则之所以是确定性的命令是因为它是“应该做”的规范。“应该做”的规范内容只规定了规范主体做或实施什么行为或活动,而没有规定行为或活动及其结果应该符合什么性质或达到什么目标,因此,规范主体只需要去做规范所命令、禁止或允许的行为或活动。这就是说“应该做”的规范的内容是确定的,因此,不需要规范主体在特定场合去判断他所做的规范所命令、禁止或允许的行为或活动及其结果的性质或目标。
法律原则处于法律中的深层面,而法律规则处于法律中的浅层面。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所以处于法律中的不同层面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即“应该是”的规范和“应该做”的规范。在逻辑上,“应该做”的规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应该做”的规范作为某规范权威发布的真正规范要以发布给规范主体的“应该是”的规范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做”的规范可以作为“技术规范”(technical norms),即关于规范主体为了满足“应该是”的规范而必须做某事情的规范。[4]185这样,我们就看到,在逻辑上,无论我们就“应该做”的规范做怎样的解释,它都是附属于“应该是”的规范,或者说它是以“应该是”的规范为前提。因此,特定国家的法体系是由两个层面组成的模式。第一个层面是由法律原则组成的,第二个层面是由法律规则组成的。*法学家Hage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出:法律是个双层模式,第一个层面是原则与目标组成的,它们表达了一个法律体系的根本理念;第二个层面是由法律规则组成的,法律规则是原则与目标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总结。见Hage. 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and a Logic to Match[M]. in Logical Mode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Edited by Henry Prakke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201-202.因此可以看出,法律原则的另一个侧面是法律价值,抑或说是法律理念;后者通过前者成文化、法律化,进而反映了法律原则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具体化,就成了法律规则,它是对许多具体事实的一种衡量和判断。Maccormick是英国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法律体系是否成熟,其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将许多不同的法律规则并列到一起时,它们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十分融洽的关系。同时,这些具体的法律规则与作为一般性、抽象性的法律原则之间也应该是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满足这个标准时,就可以认为这些法律规则是某个抽象性原则的细化的体现。当然作为法律原则的一般规范需要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规范来指导实践,必须合理可行而且具有正当性。因此可以认为,一个成为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可以体现出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普适的价值。[9]
无论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规则,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抽象性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被称之为法律的初始特征。在这一点上,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同样具有很大不同。例如对于法律规则而言,在对某一个具体的案件进行裁判的时候,它就是做出判决的最后的、决定性的理由。相比之下,法律原则则并不是做出裁判的最终理由。如前文所述,法律原则的满足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也许在某个个案中,法律原则是可行的、合理的,但是将其放在另外一个个案中。就会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其可行性进而被其他的法律原则所替代。但并不是说法律规则永远具有绝对的确定性的特征,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规则的适用常常存在诸多的例外的情形。那么此时,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特征就转化成了初始性特征。即使是转变之后,两者的原始性特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差异的。
在实践中,如果遇到某一个法律规则的适用并不能一以贯之,而是存在一定的适用上的例外,则有两种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承认这个规则本身的效力,同时否认例外的适用;抑或者,认为例外是应该被支持的,进而否定原则本身的效力。在否认原则支持例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两者背后的法律原则来进行权衡比较,进而得出最终的结论。[8]58法律原则具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征,那就是存在许多平行关系的其他的法律原则。因此,从这种与生俱来的初始性的特征来看,法律原则要强于法律规则。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原则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其相对于法律规则而言,在实践操作中并不能直接适用、成为定案的依据;而是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也就是说,在对某个具体的裁判活动发挥效用之前,需要法律借助法律规范这一桥梁。[10]301-321
上述的论述说明,一般情况下,法律原则是初显性理由,而法律规则是决定性理由。而且无论是初显性理由还是决定性理由,它们都可作为具体法律决定的理由。[8]59它们作为具体法律决定的理由的不同就决定了它们适用的方式不同。在法律适用中,有两种基本的操作:一种是涵摄(subsumption),另一种是衡量(balancing)。法律规则的适用方式是涵摄,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是衡量。[11]
二 宪法权利规范不具有规则的特性
根据前文所述的区分标准,宪法中的权利规范是一种规则,就意味着它是“应该做”的规范。这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规范的内容是直接规定人们做或实施某个行为。这个结论与宪法权利的性质与功能相背离。一个国家的宪法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原则和规则来引导国民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都是明智政府的原则以及能够最适当地实现这些原则的制度安排的立场的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特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对于这些原则在特定情况下的精确要求是什么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即使他们对此有争议,但是所表现的价值仍旧是被确认的。[12]这样,宪法与其他法律的明显区别是它规定了基本的价值选择。[13]13特定国家的宪法中关于宪法权利的规定都体现出特定的价值秩序,该价值秩序不仅对所有的法律领域具有规范约束力,而且对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具有纲领性的约束力。[14]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因此,它是“应该是”的规范。正如前述,“应该是”表达了事件状态的理想状态,默示地表达了一个价值判断。当我们说“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规范规定了一个基本的价值选择。虽然原则与价值属于实践哲学的不同领域,即前者作为规范属于道义论的领域,后者属于价值论的领域;但是,原则与价值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在价值体系中什么是初始性最好,就是原则体系中什么是初始性的应该是,在价值体系中什么是确定的好,就是原则体系中的什么是确定性的应该是。因此,从宪法上说,某个解决方案是最好的,就可转换为,这个方案是宪法命令的。
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就意味着它是一种确定性命令,具有明显地确定性特征和低程度地初始性特征。这样,宪法权利规范所规定的内容永远具有固定的、确定的、明确的意义,在社会中的实施,就不需要实施者考虑特定的事实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的状况,也不需要实施者考虑与其相竞争的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它适用于任何特定具体情景下都具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观点与宪法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相背离。宪法处理诸如下列问题:政府怎样被组织?人民的哪些生活领域是可以免于政府的干涉?政府具有多大的权威?它在通过权威施加影响或施行权力时必须遵循哪些程序?这些问题都涉及特定共同体存在的根本问题,在根本上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决定。宪法也从来不会最终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是为处理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词汇表”(vocabulary)和一个“过程”(process),虽然它不是唯一的词汇表和过程,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词汇表和过程。[13]18它既然只是一个词汇表和过程,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者在实施它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情景不断地厘清、丰富这些词汇的意义,不断地填充这个过程。这就说明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因为正如前述,原则需要规范主体根据特定场合决定如何实现其所规定的内容,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满足,它实现的程度不仅依赖于案件事实的潜在性,而且依赖于法律的潜在性。例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保障”。但是,国家和社会如何保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再比如,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正常生活,是不是应该由国家出钱为他们每个人购置一部手机?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宪法的实施者或适用者根据特定国家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而确定。另外,如果我们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是确定性命令,就意味着特定国家的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内容就不具有随该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只具有僵死的意义。这就会导致特定国家的宪法文本为了适应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地更新之中,宪法就会丧失其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宪政实践的历史证明,特定国家的社会状况变化了,宪法文本却没有更改。例如在美国,1896年的Plessy v. Ferguson 案件中,法院认为在火车上实施种族隔离是合宪的;但是,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件中,法院认为在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是违宪的;而且法院在这两个判例中都引用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
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特性的人认为,虽然宪法权利规范处于特定法体系的最高层面,它们所赋予的权利是最重要的抽象权利,但是这种规范在根本上与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规范没有区别,即宪法权利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在结构上没有任何根本的不同。[2]132这种观点在实质上预设了任何特定国家的法体系都是由法律规则组成的。我们将其简称为法体系的规则模式。这与我们前述的法体系是个双层模式相违背,也否定了法学界所普遍承认的“法律规范在性质可被区分为规则和原则”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宪法权利规范是规则的命题不能正确地说明在特定国家的法体系中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原理是,宪法是特定国家法体系中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效力,是母法。这意味着,特定国家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的内容来自于宪法或者必须有宪法上的依据,必须与宪法相一致,宪法保证了特定国家的法体系的统一性。如果宪法权利规范是规则,就与其他法律规则在结构上没有区分;那么,宪法怎样在法体系中体现它的最高性和它处于母法的地位?按照前述的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分原理,如果宪法权利是原则,那么其他法律规范就是法律规则。这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规范处于深层次,其他法律规范即规则处于浅层次。从立法的角度看,作为原则的宪法权利规范既指示和约束了立法者,又为立法者行使立法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特定国家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是该国家的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下根据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具体情况,将宪法权利规范即原则具体化的一种结果。从司法的角度看,司法者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该首先适用立法者将法律原则具体化的法律规则即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这既是由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也是优于立法权高于司法权的原理。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原理不允许司法者将宪法权利规范作为法律决定的理由。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以适用于具体案件,或者适用具体法律规则所得的结果与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司法者就可以适用作为原则的宪法权利规范。
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就意味着它的适用方式与其他的法律规则一样是一种涵摄方式,即没有任何的衡量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权利规范是一种免于衡量的规范。从对宪法文本的尊重以及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角度看,这种免于衡量的纯粹规则模式是最具有吸引力的。[8]71这就是说,那些主张宪法权利规范是规则的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这种模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宪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将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作为法的适用的唯一原则和绝对原则了。在法治社会,法的适用不仅要具有确定性也必须具有可接受性,前者是形式法治的要求,后者是实质法治的要求。法律规则具有硬度,保障法律的确定性;法律原则具有弹性,保障法律的可接受性。[5]23另一方面,即使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就一定能够保证它的适用具有最终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与其他法律规定相比较,宪法权利的规定往往适用一些隐晦的省略的套话、惯用语和格言,一般条款和弹性概念的杂乱堆积;这就导致了宪法权利的规定在语言上比较抽象、概括和精简,具有语义学的开放性和结构开放性;其内容缺乏清晰性、简约,缺乏概念的充分性,这样就导致了很多事实都可涵摄宪法权利条款规定之下。因此,规则模式仍然不能免除法律适用者在适用宪法权利规范的过程中进行解释的操作。虽然法律人在解释法律(包括宪法)时遵循法律解释的方法或规准,可以减弱宪法权利规范适用的不确定性。但是,法律解释的方法或规准的数目有多少,没有一致的意见。而且,即使法律解释的方法或规准的数目是确定的,由于不同的解释方法或规准会导致不同的解释结果,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方法或规准进行排序,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确立一个得到大家所同意的固定的法律解释方法或规准的位序。[10]4-5这样,即使主张宪法权利规范是规则也不能保障那些主张规则模式的人们所追求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规则的模式是可怀疑的。
“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是不正确的最后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是,它不能正确地说明下列三种宪法权利的适用情况:无保留的被保障的宪法权利、简单保留的宪法权利和严格保留的宪法权利。[8]71这三种宪法权利的分类只是从宪法文本所显示的状况进行划分的。无保留的被保障的宪法权利是指诸如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简单保留的宪法权利是指诸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严格保留的宪法权利是指诸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阿列克西认为,这三种宪法权利在适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衡量操作。虽然这三种宪法权利不能涵盖所有的宪法权利,但是,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三种类型的宪法权利。既然纯粹的规则模式不能够说明它们,就证明了该模式在一般上是不可接受的。*阿列克西运用大量的德国宪法权利的案例,具体细微地证明了这三种宪法权利在适用中是如何无可避免地必然地要进行衡量操作的。具体内容,请参见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1-79.
综上所述,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更适合宪法或宪法权利的性质和功能。但是,这种观点也遭受到一定的批判。那么,这些批判就能够说明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这些批判是否一定能够推翻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的命题?
三 反思对原则模式的批判
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就意味着宪法权利或宪法权利规范是一种最佳化的命令。既然它是最佳化命令,就意味着它要求立法者在制定其他法律时必须尽可能地保证宪法权利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有人认为,如果这样,立法者在依据宪法权利规范制定其他法律时其所享有的立法权的自主性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是说这样就会大大地限缩立法者的形成余地;如果要避免这种结果,就必须将宪法权利规范视为一种框架秩序。[15]这种观点就是德国宪法权利理论中所谓的“框架秩序”理论,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民主的合法的立法机关应该尽可能多地为社会做决定。如果将宪法权利规范视为原则就可能违背了这个原理。
框架秩序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宪法学家Böckenförde。他认为,原则作为最佳化命令,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满足,其程度依赖于事实和法律上的可能性;因此,原则就具有一种不固定在任何具体内容上的最佳化的倾向,就必然地向被衡量开放。虽然他承认,原则的这个特性能够包括所有宪法权利的功能,能够作为宪法权利教义学中的基本概念发挥作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深远的最终不可接受的结果,即宪法权利在法体系中的功能被根本地改变了。古典的宪法权利即防卫权被限制在法体系的一方,即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将宪法权利作为原则就对整个体系产生影响,即宪法权利的效果扩散到所有的法的领域,也必然导致了宪法权利的第三人或水平效力、宪法权利的客观方面(包括保障、社会安全、组织和程序),而这些就必然要求国家做出积极行为,就不仅仅是消极的行为。这样,宪法权利就成为整个法体系的最高原则,宪法就不仅是国家的法律的基本秩序,而且成为社会的法律基本秩序:从一开始,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关于法律秩序的实质性的内容。立法者的任务只不过是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这将导致以下结果:民主的立法机关失去了它的所有自治性,其功能仅仅是确立什么是宪法已决定的东西;民主的政治过程也将失去它的所有意义;将会从一个民主的立法国转变为一个宪法的司法国。[8]389-390
Böckenförde认为,上述情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中的权利规范属于一种特定情形的最佳命令;根据Böckenförde的观点,这种理解是有失偏颇的。反之,我们应该将宪法关于权利的规定本身作为一种衡量决策与行为的准则。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宪法规定本身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界限;第二,通过立法这一手段,可以为决策行为或者权力行使提供具体的方针政策。划定的界限和方针性规定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填补或具体化,才能成为法律适用上的可行性规范,至于如何填补或具体化则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因此,在宪法教义学上,就必须区分:哪些是宪法在规范上已经给定和规定的事项,哪些是宪法未规定而留有余地的事项,也就是说哪些是确定的内容哪些是需要填补的内容。如此一来,就可以将立法部门与宪法法院之间的各自的权限进行区别,即那些原则性的规定或框架内容的具体化属于立法者的权力,宪法法院的权限只是审查立法者是否逾越了这个界限。[15]总之,Böckenförde认为:框架秩序与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么将宪法权利规范视为框架秩序,要么视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观点是否是一种对立关系?或者说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理论是否就排除了立法机关的形成余地?
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之间是相容的,也就是说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理论能够为立法机关创立一个理性框架。那些将框架秩序与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视为非此即彼关系的认识,在实质上是没有从规范论的视角理解“框架”本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们不清楚“框架”在规范论中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要回答这两种观点是相容的,首先要清楚“框架”这个概念本身在规范的视角下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规范的术语定义框架的概念。[8]391正如前述,规范总是要命令什么(must)、禁止什么(must not)和允许什么(may)。所谓框架就是指宪法所命令和禁止的事项,宪法的命令规范要求立法者必须做一定的行为,宪法的禁止规范就是要求立法者不做一定的行为。如果宪法规范既没有命令什么也没有禁止什么,就是宪法允许立法机关可以自由做的事项。因此,立法的形成余地就是指宪法既没有命令什么也没有禁止什么,放任立法者自由决定的事项。阿列克西将这种源自宪法规范结构的立法余地称为“立法者的结构自由裁量权”。结构自由裁量权就是宪法规范既没有命令什么也没有禁止什么的事项。此外,还有一种立法自由裁量权,即我们不能确定地认识宪法规范命令了什么、禁止了什么和允许了什么,阿列克西将其称为“认识自由裁量权”。[8]395-425这样。我们就从规范的角度证成了两种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就说明了将宪法权利规范作为原则来看待并没有过分地限缩立法者的形成余地。反而说明,将宪法权利规范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一方面为立法者划定了界限即命令和禁止事项,另一方面允许了立法者形成余地的存在。[15]总之,框架秩序理论并不能证明将宪法权利规范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的理论不成立。
宪法权利规范是原则,就意味着它的适用方式是衡量。但是,有人认为,在衡量的过程中不存在理性的标准,衡量或是任意地进行的,或是根据熟悉的标准和序列而无反思地进行的。如果衡量是非理性的,那么,那堵由义务论的法律规范观和法律原则观所建立起来的防火墙就崩溃了。这样,宪法权利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地保障。[16]我们认为这种批判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其一,衡量作为一种与涵摄相对的法律适用方式,其并不是在原则理论出现后产生的,而是有比较长的历史,至少在德国的法学传统中是利益法学首先提出的,然后经过评价法学进一步发展,近年来,阿列克西发展出一套所谓的“三阶模式”将衡量方式精确化,证明了衡量与涵摄一样是一种理性程序。[11]只不过,阿列克西是从规范的角度看待法律适用方式的,如果法律规范被区分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那么前者的适用方式是涵摄,后者的适用方式是衡量。其二,指摘衡量是非理性的观点,与法律实践和法学历史不相符合。[17]衡量作为法律适用方式是随着法律实践与法学研究的发展而出现,现今无论是在公法领域还是在私法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果它是非理性的,那么就意味着法律实践中的很多法律决定都是非理性的。
四 我国的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
如果我们认为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特性的观点是不合适的,那么它就应该具有原则的特性;因为法律规范只被区分规则与原则。现在的问题是,宪法权利规范是原则的模式是否符合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有关宪法权利的规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对宪法权利教义学中的有关宪法权利限制的理论做出说明。
宪法权利限制理论主要有两种,即外在限制理论和内在限制理论。外在理论认为,权利限制的概念本身假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权利,另一个是权利的限制,也就说首先存在着一个权利,然后才存在着对该权利的限制。权利与权利限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即限制关系。[8]178-179这个原理运用到宪法权利理论就意味着,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限制在概念上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我们要对受到限制的宪法权利以及并未受到限制的宪法权利进行区别。未受到限制的权利是一种原始性的权利,似乎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内容;但是受限制的权利是通过宪法实际规定获取的权利。初始性的宪法权利受到限制后才产生有无确定的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18]外在理论承认法体系中的绝大多数权利(包括宪法权利)都是作为受限制的权利出现的,但是该理论仍坚持认为,这些权利本身没有受限制是可以成立的。权利概念与权利限制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们之间产生关系是因为一个权利自身必须要与其他人的权利或其他权利和公共利益相和谐。[8]179内在理论认为,权利限制的概念并没有假设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任何权利都是具有一定内容的权利,也就是说任何权利自身是受限制的。权利受限制的问题不是它受不受限制或受限制的程度大小的问题,而是权利的内容问题。因此,限制的观念应该被程度的观念所代替。[8]179这种理论运用到宪法权利理论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自始就有确定的内容,也就是说任何宪法权利在内容上都有一个界限。既然宪法权利自身有界限,那么如果一个行为处于这个界限之外就是不受宪法权利保护的行为。因此,宪法权利不存在外在理论所认为的外在限制的问题,而只存在宪法权利所真正保障的内容范围是什么的问题。这样,对于内在理论来说,就不存在初始的宪法权利和确定的宪法权利之区分。[18]
从上述内在理论与外在理论的内容看,前者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特性,后者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特性。内在理论认为,任何宪法权利的内容自始就有一个确定的界限,某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该宪法权利的保障范围依赖于该行为是在界限内还是界限外。如果在界限内就处于该宪法权利的保障之下,如果在界限外就不是属于该宪法权利的保障范围。这就是说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方式,因此,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而且由于宪法权利规范在法律上的实现的可能范围是已经确定的和固定的,因此当该规范与其他宪法权利规范或其他法律规范相抵触时,其实现的先后关系自始有固定的次序,也就是说相互抵触的法律规范之间有绝对的优先性关系,而这也正是规则的特性。[18]总之,内在理论认为宪法权利规范具有规则的特性。外在理论认为,虽然任何宪法权利自身是不受限制的,但是任何权利的实现都必然要求该权利与其他权利不相抵触,或者说不要阻止其他权利的实现。因此,一个行为或事件状态落入某一特定的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该行为或事件状态只受到了一个初始性的保障。那么,该行为或事件状态是否是受到确定性的保障依赖于它们的实现是否阻止或侵害了其他宪法权利。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或事件状态是否受到确定的保障,就必须在宪法权利规范与宪法权利规范之间进行衡量。这就说明宪法权利规范具有原则的特性。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结构,清楚地区分了宪法权利的规定与宪法权利限制的规定,即,首先从第三十三条到第五十条分别明文规定了其所保障的宪法权利;其次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宪法权利的限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从这个结构看,我国现行宪法权利的规定具有外在理论的特征,即每个宪法权利条文所规定的权利,是该规范所保障的初始性的宪法权利,只有该权利不阻止或侵犯其他个人的宪法权利或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的时候,该宪法权利才能得到宪法的确定性的保障。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到第五十条所表述的宪法权利规范以及第五十一条所表述的限制宪法权利的规范,都作为原则予以看待。将我国的宪法权利规范作为原则看待,就意味着,如果某一行为或事件状态可以归入到个别宪法权利条文所表达的规范的保护范围,就受到该规范的初始性的保障;至于该行为或事件状态是否受到确定的保护,就依赖于在保障其的宪法权利规范与限制其原则之间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具有相对的优先性,该行为或事件状态就确定地受到保护,如果是后者具有相对的优先性,该行为或事件状态就不能得到保护。依据前述法律原则的衡量原理,在对相互抵触的法律原则之间进行衡量的结果,我们会得到一个具有规则性质的规范,即(P1P P2)C→Q或(P2P P1)C→Q,这个新规范就是一个具有规则性质的派生的宪法权利规范。因此,当我们说宪法权利规范是原则,实质就是说它是原则与规则相混合的模式。前述指出,任何原则的适用就必须要在原则与原则之间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是得出具有规则性质的规范,没有原则是在未对与其相竞争的原则之间进行衡量就可适用的。
但是有人会认为,我们在建构宪法权利规范时没有将对宪法权利限制的理由纳入到该规范的表述之中,因此,宪法权利规范才具有原则的特性;如果我们将对宪法权利的限制纳入到该规范的表述中,宪法权利规范就具有规则的特性。例如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该条表达的规范是(1)“凡公民发表言论的行为,则不得限制之”。如果将限制宪法权利的理由加入到这个规范中,就成为(2)“凡公民发表言论的行为,如果没有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的,则不得限制之”。如果用T代表言论自由的构成要件,F代表限制理由,G代表法律后果,那么(2)就可简写为:(3)如果T而且非F,则G。显然(3)具有规则的特征,即,如果宪法权利规范的构成要件T得到了满足,而且F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就会产生确定的法律后果G。但是,问题在于,(3)对于自身在法律上实现的可能性并没有做出完整的设定,因此,要将一个法律事实逻辑地涵摄在这个规则之下,就必须确定T和F是否得到满足,而要确定F是否被满足,就必须回溯到原则的层面去确定各相关原则之间的优先性关系。这就意味着,在适用(3)时,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原则的衡量。因此,以附带限制条件的方式来重构宪法权利规范只是将衡量问题转移到限制条件是否满足的方面而已。[18]41而且在生活现实中,一个案件事实或行为或事件状态往往不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满足T,就不满足F,要么满足F,就不满足T;而往往可能是,既不完全满足T也不完全满足F,既完全不满足T也完全不满足F。这样,满足不满足T和F都有一个程度问题。既然存在程度问题,就需要衡量程度的大小问题。因此,(3)在适用时就不可能没有衡量的操作。总之,在建构宪法权利规范时,即使将限制理由表述其中,宪法权利规范还是具有原则的特性。
参考文献:
[1]Peczenik. Jumps and Logic in the Law[M]∥Logical Mode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Edited by Henry Prakke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298.
[2]Robert Alexy. Constitutional Rights, Balancing ,and Rationality[J]. Ratio Juris Vol.16 No.2 June, 2003.
[3]G H von Wright. Norm and Action[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ress ,1963:100.
[4]G H von Wright. Practical Reason[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5]Aulis Aarnio. Reason and Authority[M].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7.
[6]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75.
[7]Robert Alexy. 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M]. by Bonnie Litschewski Paulson and Stanley L Paulson. Clarendon Press,2002:70.
[8]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9]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152.
[10]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Robert Alexy. On Balancing and Subsumption-A Structural Comparison[J].Ratio Juris,2003,16(4):433.
[12]Larry Alexander.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M]∥Edited by Larry Alexander.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2003:1-4.
[13]Jay M.Feinman. Law 101[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张嘉伊.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J].台大法学论丛,2006(5):1-17.
[15]王鹏翔.基本权作为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从原则理论初探立法余地[J].东吴法律学报,2008(3):14-26.
[16]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19-320.
[17]王夏昊.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抵触之解决[D].中国政法大学,2007:115-122.
[18]王鹏翔.论基本权的规范结构[J].台大法学论丛,2009(2):3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