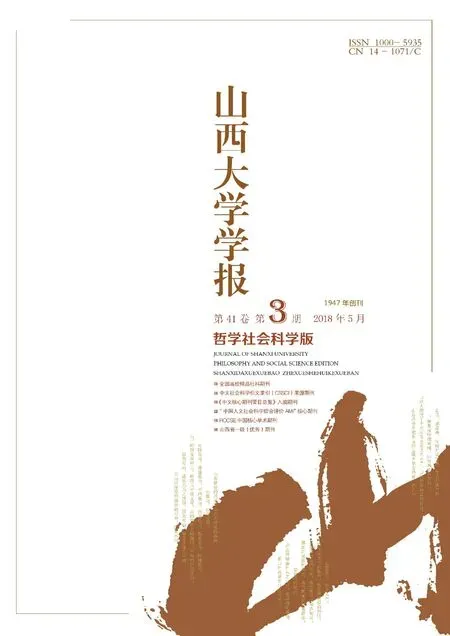祖先崇拜、家国意识、民间情怀
——晋地赵氏孤儿传说的地域扩布与主题延展
段友文,柴春椿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赵氏孤儿”作为民间传说的经典,在典籍文本的凝固与民间叙事的活态传承中,承载了每个时代特有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涵,映射着广大民众丰富的情感世界与道德追求。赵氏孤儿传说最初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展演在民间,后有文人的介入使民间叙事走向文本化,逐渐从活态的口头文本固化为书面文字。在口头与文本的交融中,赵氏孤儿传说故事情节得以扩展、人物形象得以建构,并表现出鲜明的层累性。层累的历史造成传说中心人物——以程婴为核心的忠义之士的突出与放大,并形成忠义的永恒主题。同时由于民众心理、历史背景、流传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赵氏孤儿传说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中心的转移,传说核心人物不再指向单一的对象,而是更换衍生出其他次生主题,不同的主题叠加与延展进而形成主题的流变。赵氏孤儿传说发源于以襄汾为中心的晋南地区,随着赵氏家族政治中心的北移传播至忻州,在民间信仰的推动下辐射至盂县藏山等地,在晋地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传说亚区,三地传说的差异性突出表现在主题的区别上。“忠义”精神是赵氏孤儿传说的“大主题”*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将安达曼人的传说故事分为“大主题”和“小主题”,他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提出:“只有同一个传说有好几个版本的时候,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该传说的所有版本中都出现的,就是大主题,各版本之间互有差异、但对传说本身不造成重大改变的,就是小主题。”对于本文而言,赵氏孤儿传说中的“忠义”主题可以看作该传说体系的“大主题”,在此基础上各地流传的版本中所存在的其他主题可称之为“小主题”。,三地在凸显这一精神的同时,由于实际传承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主题”,即晋南以褒扬赵盾为核心的祖先崇拜、忻州以赞颂程婴为中心的家国意识、盂县藏山以崇信赵武为雨神的民间情怀。在民间传承过程中,赵氏孤儿传说“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1]。民众“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以及不同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着赵氏孤儿传说。
一 祖先崇拜:晋南以赵盾为核心的传说发源
晋南襄汾、新绛一带,作为古晋国都城所在地,是史事“下宫之难”的发生地,由此演绎形成的赵氏孤儿传说,便发源于这片沃土之上。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翔实的文献田野资料,为赵氏孤儿传说发源地的探究提供了佐证,此外,传说的核心人物之一赵盾亦诞生在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赵氏孤儿传说起源于晋南一带,形成了以赵盾为核心探索传说发源的传说圈,并在追根溯源的文化心理之下,蕴含了祖先崇拜的主题内涵。
(一)信史基础上传说的生成
历史不仅指社会过程的客体本身,也指人作为主体和历史叙述者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历史人物的历史事实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过程,是人们进行叙述的对象。历史人物传说就是民众的历史叙事,是民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忆与阐释。[3]主体在阐释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自然会对记忆对象进行重新组合与创造,使其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宣泄内心情感,追求道德教化作用,满足审美娱乐需求,历史人物得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传说化。民间传说中的确映射着历史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只要能达到典型塑造的目的,它“可以将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东西概括在一起……黏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类似的东西……形成历史的多层黏合体”[4]72,赵氏孤儿传说正是整合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是对真实历史的重构。
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传说形成的根脉,是探讨传说发源地的出发点。大部分传说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阐释”[4]71。因此,要探究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还需从史实着手。
赵氏孤儿传说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仅一言以概之,“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5]836。《左传》将其情节加以扩充,赵婴因通于赵庄姬被原、屏放诸齐,庄姬因故以“原、屏将为乱”谮之于晋侯,晋遂讨赵同、赵括。这一事件,史称“下宫之难”,又称“原屏之难”。赵氏之孤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故事情节与《史记》所载差异颇大。
“下宫”乃古晋国之亲庙。古晋国自受封建国起,一直将晋南地区作为王畿之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6]1978唐尧部落的活动地域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河谷地带,考古学已证实唐尧之墟即今襄汾县陶寺遗址。晋献公八年,“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索隐》:“杜预曰‘今平阳绛邑县’。应劭曰‘绛水出西南’也。”[6]1983后景公十五年迁都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或认为今襄汾县城南三十公里处赵康古城遗址乃晋国古都“故绛”所在地。《太平县志》载:“古晋城,在县南二十五里。城故址周九里十三步。献公都此。”[7]该地现存城堡九关八门,北城、西城外有水蚀壕沟痕迹,应原为护城河,城北大约一公里有古烽火台遗迹。“下宫之难”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史记·赵世家》载景公三年,屠岸贾诛赵氏,十五年赵武复立。《韩世家》载景公三年诛赵氏,十七年赵武复立。而《史记·晋世家》载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左传》载成公八年六月,晋讨赵同、赵括。鲁成公八年即晋景公十七年。民间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以《赵世家》所载情节为蓝本,今晋南新绛、襄汾一带仍活跃着大量赵氏孤儿传说。本文虽言信史,但更从民间传说的角度探讨问题,故此处从《赵世家》所载景公三年。,即迁都之前,可见,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或当在晋国古都“故降”,即今襄汾县赵康镇一带。
此外,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现存刻于唐代的“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碑保存基本完好。*碑为青石质,双龙碑首,高足方趺,通高305cm,碑首高77cm,宽82cm,厚23cm。碑身高173cm,宽78cm,厚19cm。碑趺高55cm,宽97cm,厚61cm。东汾阳村东西城门楼上各镶嵌两方石刻门额:东城门楼阳面横刻“升恒”二字,眉上刻“赵宣孟故里”,上款刻“大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吉旦”(1697),下款刻“本庄总理同协创立”,门楼里面横刻“金汤”二字,落款“康熙丁丑”;西城门楼阳面横刻“熙宁门”三字,眉上刻“赵宣子故里”,额右上角刻“康熙己酉吉旦”(1705),门楼里面横刻“咸丰”二字,眉上刻“赵宣子故里”,右上角刻“古汾阳”,落款“雍正四年仲春重建”(1726)。碑刻中“赵宣子、赵宣孟”即赵盾,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当是赵盾故里。另西汾阳村现存赵盾墓与程婴墓,赵雄村留有赵氏家族九冢坟之第七冢,为赵氏孤儿发源地的确立提供了更多佐证。赵氏孤儿传说当发源于故降,即襄汾县赵康古城,并以此为核心辐射至襄汾县赵康镇、汾城镇及新绛县泉掌镇泉掌村、龙兴镇侯庄村、阳王镇苏阳村等地,形成了丰富的民间口承传说,保存了大量真实可信的风物遗迹。
(二)文献记载与田野资料的互证
文献记载在历史的传承与实践中逐渐被解读和使用,经典文本中的英雄人物及其所负载的思想逐步进入底层社会,“影响并模塑了底层社会的历史经验”[8],最终形成种种民间传说与信仰。文献与田野之间存在着互动,凝聚的文本为传说的形成提供了范本,传说的发展为文本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素材,愈是最初形成的传说愈包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近的传说,其信实性也就越高;反之,离真实历史的范畴越远的传说,在历史考证上的可信度也就越低。[9]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契合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传说在不同地域形成的时间早晚。《史记·赵世家》所载的史实作为民间赵氏孤儿传说的蓝本,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传说基本情节在各地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襄汾县赵康镇作为传说的发源地,其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具有更高的契合度,这主要体现在当地把解救赵盾的义士作为描述对象,塑造了鉏麑、提弥明、灵辄等一组光彩照人的“义士”形象。
《左传·宣公二年》:“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5]658襄汾民间流传着一则《鉏麑跟五色槐的故事》,在东汾阳赵盾府第有一苏阳村,村里有一棵槐树,乃鉏麑触死之处,其后槐树开出黄、白、粉、绿、紫五色花,后人将其称为“国槐”,又“五色槐”。*内部资料.王学程.古绛州的传说[M].山西新绛县博物馆,1994:11.《左传·宣公二年》传:“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责公不养士,而更以犬为己用。斗且出,提弥明死之。”[5]659襄汾流传的关于提弥明的传说与之相合,至今赵康一带仍有不养狗、抓狗杀狗的习俗。*内部资料.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材料——赵氏孤儿故里故事[Z].襄汾县政府,2013:8.《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途中遗食救饿夫,灵辄倒戟御徒解盾困。纪君祥杂剧《怨报怨赵氏孤儿》描写灵辄救盾的情节更为详尽,“赵盾出的殿门,便寻他原乘的驷马车。某已使人将驷马摘了二马,双轮去了一轮。上的车来,不能前去。旁边转过一个壮士,一臂扶轮,一手策马,逢山开路,救出赵盾去了。你道其人是谁?就是那桑树下饿夫灵辄。”襄汾一地将史料记载与风物遗迹相结合,传说赵盾在马首山打猎,途径绛州侯庄村遇灵辄救之,后逢赵盾遇难,灵辄遂负盾而亡。*内部资料.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材料——赵氏孤儿故里故事[Z].襄汾县政府,2013:6.
单纯地复制文献的民间传说,存在着被文化精英刻意加工创造的嫌疑,而世代相传的习俗与风物遗迹,使得传说的可信性大大增强。文本记载推动着传说的传承,传说表现着民众对历史记忆的自我叙述,并结合地方风物形成在地化阐释,烙上民众生活的印记。文献记载、口头传说、民间习俗、风物遗迹的相互交织与融合,使得民间传说富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可信度,得以世代传承。鉏麑触“五色槐”,侯村庄救灵辄,赵康不养狗,这承载着历史厚度与民间张力的风物习俗,使得赵氏孤儿传说能够活态地展演在民众的生活之中,顽强地生存在襄汾这片土地上。
襄汾赵康一带三义士的传说,一方面印证了赵康镇作为赵氏孤儿传说发源地的可信性;另一方面,突出了该地传说以赵盾为核心人物的地方特色。每则传说虽然表现“义士”之义,但从侧面烘托出了赵盾故里长久沿袭的对祖先赵盾的崇拜心理。除了指向核心人物的三义士传说,赵康镇还流传着大量有关赵盾辅政的传说,民众依据信史并结合自身的精神需求,刻画出了一个忠诚清廉、仁爱慈善的忠臣形象,这些传说均未见于忻州、盂县两地。襄汾赵氏孤儿传说跨越故事本体的核心人物,即程婴、公孙杵臼等,而以赵盾为主要叙述对象,其中隐含着该地作为故事发源地所形成的民众追根溯源的崇祖观念,并发展为以赵盾为家族代表的祖先崇拜。
(三)祖先崇拜的民间表述
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虽然充满了时空错置与幻想虚构,但如果不去探究其事迹的真实性,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历史信息,那么,就可以解释历史为何要如此记忆与传播,从而对历史有更全面的理解。赵氏孤儿传说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传播者的心态、观念是真实的,这种心态和观念就是传说得以传播的“历史心性”。历史心性是指人们由社会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观念下,人们循以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10]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就是在“祖先崇拜”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动下得以传播的。
祖先崇拜是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形式,这是一种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的对祖先的敬拜思想,“是建立在灵魂不灭和鬼神敬畏观念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丧祭活动来实现的。”[11]襄汾赵氏孤儿传说蕴含的祖先崇拜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宗族制度下形成的祖先崇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二是笃信其祖先神灵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祖先崇拜外化为一系列祭祀活动;三是祖先崇拜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其成为本族的象征,由此转化为一种人文崇拜。
1.血缘观念下的排他性
祖先崇拜包括家族祖先崇拜、民族祖先崇拜、行业祖先崇拜等多种类型。家族祖先崇拜的形成以血缘观念为心理基础,日本学者池田末利指出“祖先崇拜是以家族制度的确立为前提”[12],家族在形成与扩大的过程中,血缘宗法观念得以不断强化,被族人共同敬仰的祖先成为维系家族内部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的核心,祖先崇拜由此生成。在崇拜本族祖先的同时,祖先崇拜还通过对仇敌异姓的排斥来规范族内制度,加强族人凝聚力。
襄汾赵康镇流传着“赵屠两家不结亲”的习俗。《程婴救孤》《赵氏孤儿》《八义图》等剧目在赵康、永固一带上演会引起赵、屠两家发生冲突;赵、屠后裔祭祀各自祖先的日期相去不远,在此期间,赵、屠两家也多发生冲突;屠氏后裔为能在当地生存下去,便将“屠”姓改为“原”姓,赵、屠两家因为宗族之间的对立,立下了两家不结亲的规矩,这一族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内部资料.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材料——赵氏孤儿故里故事[Z].襄汾县政府,2013:46.赵姓族人对仇敌屠氏的排斥,旨在维护家族尊严,凸显了其祖先崇拜情结。
家族祖先崇拜“是整合和凝聚家族的巨大精神力量。家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稳定和谐的组织和聚合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祖先的引导和号召。在家族内部,祖先崇拜还是强化、巩固家族伦理秩序的有效手段。”[13]血缘观念下形成的祖先崇拜的本族认同性与异族排斥性,在赵康镇的民间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认同与排斥的并行演进中,赵氏族人对赵盾的崇拜愈加虔诚,其对祖先的祭祀也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
2.外化的祭祀仪式
宗族祭祀建立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加强祖先崇拜的重要手段,影射着民众追求道德信仰与生活理想的精神需求。“宗族祭祀的祖先,是有选择的祖先,而不是所有的祖先。这个选择,首先就是世代的选择。”[14]赵康古城作为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世代生活在此的赵氏家族选择以忠诚仁爱的赵盾作为其祖先加以崇拜,并将这种祖先崇拜的心理需求外化为祭祀仪式,以此来沟通族人与先祖,期盼得到先祖的庇佑。
赵康镇赵氏一族在对赵盾的世代崇拜之中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祭祀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赵盾生日这天,赵姓八村的赵氏后裔都会聚集在赵盾墓与赵家祠堂前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包括祭前准备、叩头祭拜、祭后活动三个步骤。祭祀之前当地会准备肉类、水果、糖、蛋等祭品,其中肉类多半是半熟或全熟品。人类学家认为祭品的“熟”或“生”代表着信众与被祭者关系的亲密程度,“熟”表示双方关系的熟稔。民众以半熟或全熟的祭品充当着人神沟通的媒介,以此来表达自身与祖先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着血缘的牵连,蕴含着族人对祖先虔诚的崇拜。祭祀过程分为摆供、上香、斟酒、祈祷、叩拜、鸣炮。祭祀完毕,赵氏族人会以分食祭品与祖先共享的方式完成人神间的交流,并希望得到先祖的护祐。完整的祭祀仪式表达了赵氏后裔对祖先的敬畏与依赖,当地民众正循以这种外化的固定模式去强化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
3.伦理观念下的人文崇拜
“祖先崇拜是原始道德信仰生成的基础,祖先崇拜为道德信仰提供了社会秩序伦理基础。”[15]世代选择的祖先,首先必然是道德的楷模,祖先崇拜的内核是忠孝伦理的道德观念。祖先崇拜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紧密相连,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对调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其在传递、弘扬某一族群普遍认可的价值道德观念时,唤起了民众内心的道德感与良知。赵康镇一带赵氏孤儿传说中的祖先崇拜观念赋予当地一种忠义为先的道德教化功能。
当祖先崇拜融入相当浓厚的德育内容时,便超出了宗教范围而具有宗法和道德意义,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标志着祖先崇拜的世俗化。赵氏家族祖先崇拜的形成与延续的根基便是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信仰。祖先崇拜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宗族内部精神与信仰的象征符号,转化成一种人文崇拜。赵康镇赵氏祖先崇拜的世俗人文性,主要表现在对祖先姓名的执念及对祖先故里的追溯之中。
襄汾县赵康镇是赵盾传说的主要传播区域,以东汾阳村为中心形成的“赵姓七村”——赵康、赵雄、赵豹、大赵、小赵、南赵、北赵,相传是从赵氏家族里分居出来的后裔,七村皆以赵氏祖先的姓名命名,以此来纪念先祖。东汾阳村东门外有唐代碑刻“晋大夫赵宣子故里”,东、西城门楼眉上均刻有“赵宣孟(子)故里”。西汾阳村外建有赵盾墓,有碑“晋上大夫赵宣子之墓”,1984年被列入古墓葬保护范围。[16]另外,西汾阳村有赵宣子庙,周围七村春秋奉祀。2007年政府建造“东汾阳忠义文化广场”,立赵盾雕塑。当地民众不忘家族仇恨、怀祖敬祖的祖先崇拜心理,对忠义仁爱道德伦理的信仰追求,通过这种人文崇拜体现在民众的生活当中,塑造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赵康古城作为下宫之难的发生地,赵氏孤儿传说当发源于这片土地之上,以信史为依托,在文献与田野的对读之中可以寻出蛛丝马迹。有别于忻州、盂县两地,该地的民间传说以赵盾为核心,体现出“祖先崇拜”的主题,在血缘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本族认同性与异族排斥性,外化的系列祭祀仪式,在伦理观念下形成的人文崇拜,印证着赵氏孤儿传说在当地的世代传承过程中蕴含着的“祖先崇拜”精神需求。晋南地区的赵氏孤儿传说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性与教化观,随着时代变迁,传说在向其他地域扩布的过程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二 家国意识:忻州以程婴为核心的传说北移
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其流传地域随政治中心的转移而扩大,民间传说被统治阶层借用,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赵氏孤儿传说随赵氏家族北移流传至忻州一带,至宋金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被赋予了家国意识的主题内涵,在国家、文人、民间不同阶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背景下传说的北移
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影响下,赵氏孤儿传说随着赵氏家族活动范围的扩张与政治中心的迁徙而北移,并在自上而下的促动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赵简子归卫士五百家置之晋阳,至赵襄子时“赵北有代(今隶属山西省忻州市),南并知氏,强于韩、魏。”[6]2164后“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6]2165敬侯元年赵始都邯郸,至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资治通鉴》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17],史学界以此为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赵、魏、韩三家分晋之后,分别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安邑(今山西夏县)、韩原(今山西河津)建立政权,并不断扩张迁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6]2182赵武复立延其祖祀之后,赵氏家族历经“简襄功烈”,逐步将其中心势力转移至晋北、晋东北一带,终与魏、韩分晋并立,建立赵国,成就伟业。
忻州,“《禹贡》冀州之域。三代讫秦并同太原府。汉为太原郡阳曲县及汾阳县地。后汉建安二十年,徙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于此,郡为一县,立新兴郡领之,治九原城,即今州治也。”隋开皇十八年“立忻州治之,取州北忻川水为名也。”[18]2567《元史·本纪》载“至元三年七月,以崞、代、坚、臺四州隶忻州。”《明一统志》载“忻州,元初改九原府,置宣抚使。”[18]2568“《檀弓》志晋大夫之葬,直谓之九原。《水经》谓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金代何师常《公孙厚士祠记》:‘今之九原,即古赵氏田邑。’《檀弓·晋献文子成室篇》疏曰:‘九京即九原,文子世家旧葬地也。或云在襄陵,乃武之后,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连三晋,城带九原。卢君窃号之邦,赵氏言归之地。迁史以为南并北代,非此何谓焉。’”[19]今之忻州,当囊括战国时赵之代、云中、九原等地,并占据边塞要地,影响着赵国国势的强衰兴败,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战国时赵国的政治活动中心与军事要塞,统治阶层为巩固政权,势必会在思想上引导当地百姓,决定赵氏一族命脉存亡兴衰的赵氏孤儿传说成了最好的媒介。赵氏孤儿的传说随着赵氏家族势力的北移而在此地生根发芽、广泛流传,传说中蕴含着的忠义精神成为统治阶层凝聚百姓思想的手段与规范民众行为的道德标准。
至宋时,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的发展达到高潮。宋神宗时国家统治制度出现诸多流弊,边境辽与西夏虎视眈眈,靖康之变后,宋被迫南下与金南北而治。国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得宋朝统治阶层对百姓“家国意识”的精神建构迫在眉睫。忻州作为宋与辽的边境之地,屡次遭辽侵犯,战乱不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自觉将守护家国安宁作为自身民族使命,“家国意识”成为跨越阶层的上下共通的民族情感。赵宋与赵孤一脉相承,在忻州具有一定民间基础的赵氏孤儿传说在血脉的联系中,自然成为宗法制与专制制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民族精神的最佳载体,在这动荡的历史时代中走向高潮并一直延续。至元代,屈身异族的民族意识,加深了儒家大一统思想下形成的以汉族统治为中心而排斥异族统治的社会文化心理,文人阶层“反元复宋”的追求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经典的赵氏孤儿民间传说在文人的改编与重构中凸显出愈加浓烈的复仇色彩与家国意识。发轫于上层阶级的对赵氏孤儿传说的推崇能在各个阶层与群体中得到响应并形成互动,正是由于传说中蕴含着的深沉的家国意识主题契合了时代与地域的特征,满足了各个阶层的精神需求。
赵氏孤儿传说随着赵氏家族的北移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引导下流传至忻州一带,传说中蕴含的忠义精神迎合了忻州处于国之边境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战乱频繁的时代,这种忠义精神更被各阶层大力宣扬,在特殊的时空背景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家国意识。程婴作为代表忠义精神的灵魂人物,成为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的核心对象,对家热爱、对国忠诚的民族精神成为上层阶级、文人阶层、广大民众的共同追求。
(二)家国意识的体现
家国意识是民族精神的本源,对促进民族融合、加强社会团结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由家而有国,次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亦如身家连称。又如民族,有了家便成族,族与族相处,便成一大群体,称之曰民族。此亦由人文化成。”[20]由身及家,由家及国,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民族心理,家族、国家的集体利益远高于个人利益,舍生取义、舍家为国的精神体现着华夏民族勇于牺牲自我的家国意识。
家国意识的本源是忠义精神,家国意识最先体现为对家、对国的忠诚。在家国危难之际,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中的忠义精神冲破时空的界限,被赋予“家国意识”的主题,“忠义”并非赵氏一族之忠,也不是程婴一人之义,而是升华为对整个家国的赤诚之心。以程婴为核心的传说体系体现出深刻的家国意识主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即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
1.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
宋时,统治阶层通过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将赵氏孤儿传说的忠义精神提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义士作为忠义精神的象征,成为皇室册封的主要对象,官方通过对传说中典型忠义形象的塑造,来激发民众的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希望以此对抗外族侵扰,维护家国一统。
对程婴三义士册封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敕河东路访寻二人遗迹,乃得其家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21]宋神宗时,始册封程婴、公孙杵臼为侯,于绛州建庙祭祀。《宋史·礼志八》载宋高宗“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22]1722宋高宗时,程婴、公孙杵臼庙数量增多,分布地域更广,且多隔绝。理宗“宝庆二年十一月甲寅,修祚德庙,以严程婴、公孙杵臼之祀”。[22]527这是见于史料中的官方对程婴、公孙杵臼二义士的册封与祭祀。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韩厥始与程婴、公孙杵臼并祀于祚德庙。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封韩厥为义成侯。绍兴十一年(1141)“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22]1722韩厥与程婴、公孙杵臼三义士共享春秋之祀。“绍兴十一年八月戊辰,立祚德庙于临安,祀韩厥。”[22]369宋高宗时,在临安为韩厥建庙祭祀。绍兴十六年(1146),宋高宗对三义士进行加封。“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22]1722
在宋朝国君对赵氏孤儿传说核心人物的册封中,以“忠义”精神为化身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成为主要受封对象,所授封号也直接以“忠、义”为名。官方通过屡次敕封行为,重塑了以程婴为核心的忠义形象在民间的重要地位,为民众树立了忠义的道德楷模,利用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形塑着民众的家国意识。
2.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
文人阶层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传达着自身意愿,民间传说是其改编对象之一,他们有选择地将活跃在民间的传说故事经过文学加工与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与主题内涵。赵氏孤儿传说因其蕴含的忠义精神,成为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宋元文人的主要书写对象,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元代文人纪君祥《冤报冤赵氏孤儿》杂剧,通过置换变形的方式,增加情节戏剧冲突,突出故事复仇母题,表达了自己反元复宋的爱国情怀。
“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中存在的神话结构,要使人信以为真则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手段皆可以划归‘移用’”。[23]移用,即置换变形,又译作移位、移置,“是指无意识的移置、换位或转换的意思”[24]。在文学作品生与死的基本原型中,可以置换出多种母题,而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线索则在于多种母题的“置换变形”。源于信史的赵氏孤儿传说,发展初始阶段围绕程婴三义士之生死形成了单一的忠义主题,传说在传承过程中被植入越来越多的虚构成分,为使得传说更为可信,忠义主题在不同流传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被置换为不同的主题。宋元时期,这种忠义精神在文人笔下转变成了更加深刻的复仇母题。“‘神话幻想’创造出来的情感表现为‘爱与恨、恐惧与希望、欢乐与忧伤’,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象世界’。”[25]“爱与恨”的情感可以置换出复仇母题,复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自然法则的体现,“在这种最基本的形式中,自然法则的观念是以复仇法则的形式起作用的”[26]。赵氏孤儿传说的复仇母题突出体现在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中,纪君祥将《史记》中替孤而死的“他人婴儿”,换作程婴亲生骨肉,以此来激化人物矛盾,为其后复仇之路埋下伏笔。替孤风波后,程婴携赵武投奔屠岸贾门下,命赵武认敌作父并最终手刃仇敌,完成复仇大计。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丰富了人物的感情,在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中,置换出了复仇母题,此时的赵氏孤儿传说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复仇史。
以忠义精神为基础置换出的复仇母题具有伦理性,一脉相承的赵宋与赵孤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复仇行动,更具正义感和使命感,隐喻着元代汉人“反元复宋”的民族抱负与善定胜恶的决心。赵氏孤儿传说时刻警醒着宋代遗民理当与赵孤一样踏上复仇的道路,实现“反元复宋”的政治理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并将这种血亲关系和民族的血脉一直传承下去。
3.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
在国家话语主导与文人阶层创作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以家国意识为主题的赵氏孤儿传说,与忻州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相契合,得以在地方上传承,形成了以忠义人物为核心的传说体系。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以程侯山为中心扩布至南关、北关及城北,相较于晋南、晋东两地,该地传说在传承忠义精神的同时被赋予了浓重的家国意识。忻州地区对蕴含着家国意识的忠义精神的传承,集中体现在以程婴等义士为核心的民间传说当中,这类传说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人物传说
忻州赵氏孤儿人物传说形成以反映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程婴传说系列和以弘扬侠义精神为目的的韩厥传说系列。当地流传程婴以子替孤将赵武救出后,从晋都一路北上逃至忻州一带,由此在该地形成程婴藏孤、育孤的一系列民间传说及与之相附会的风物遗址。如《程婴含辱养孤》*内部资料.政协忻府区委员会.春秋大义[Z].忻州市政府,2013:21.讲述了程婴携赵孤与妻子离开绛州进入九原藏匿金山,金山也因此改名为程侯山,其后多次带着赵武与妻子转移、迁徙各地。这类传说体现了信史随着历史的久远逐渐去真实化与传说化,反映了民众特有的历史记忆。赵武的复立离不开韩厥的仗义举荐,《忻州志》载:“晋卿韩献子厥墓,治南十五里,韩岩村,今有韩家沟,其故里也”。现忻州豆罗镇韩沟村西一公里处,有韩厥墓,故该地形成了以韩厥为核心的系列传说,如忻州百姓得知韩厥率兵抄杀屠岸贾全家,碾米磨面,杀猪宰羊,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在劳师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内部资料.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中国程婴故里文化之乡申报书[Z].忻州市政府,2011:345.忻州人物传说传达了民众的“侠义”观,这些义士在民间传说中虽然仅仅是从属人物,但他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权的侠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2)风物传说
忻州风物传说包括与自然景观相附会的人文遗迹和传说在地化传承中形成的风俗习尚。当地为纪念、祭祀程婴等义士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景观遗迹风物传说群。忻州南关有程婴墓、程婴祠和程婴妻子王阿娘娘庙,南关大街立有“韩献子遗风”坊,北关有“程婴故里坊”,城北逯家庄有公孙杵臼墓、忠烈祠,城北二十公里程侯山有阿后娘娘庙。文庙内建有“忠义祠”,北关、程侯山的七贤庙将赵盾、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灵辄、鉏麑和提弥明尊为祭祀对象。以程婴为核心的风物传说群体现着民众对忠义之士的敬仰,是忠义精神的物化体现与传承载体。此外,民众对忠义精神的追求在历代的传承中逐渐演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当地民众为感念程婴夫妇赐予父老乡亲脆爽可口的白菜,每年农历九月初一白菜收获时都要举行庙会,祭祀程婴。*内部资料.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中国程婴故里文化之乡申报书[Z].忻州市政府,2011:331.《系舟山顶藏儿洞》将忻州系舟山与盂县藏山联系起来,民众以他们独有的智慧为程婴的藏孤路线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内部资料.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中国程婴故里文化之乡申报书[Z].忻州市政府,2011:348.以风物传说形态呈现的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背后表现出的是“在地化”的民众经验,风物的存在是客观性受主观性文化的影响,反映到民众的思想观念中,并将其转化为关乎自身的实践行为。
(3)显灵传说
忻州被誉为“程婴故里”,程婴信仰在当地极其兴盛,程婴显灵的传说经久不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程婴神鞭赠尉迟》:
唐代初年,尉迟恭驻扎在忻州程侯山一带练兵。但当地遭遇灾害,百姓食不果腹,军队难以筹集粮饷。在这危难之际,一位道人赠给尉迟恭一柄钢鞭。尉迟恭用这钢鞭破开山门,山门中满是黄金白银。尉迟恭将这些银两分为三份,一份酬谢众神;一份赈济灾民;一份作为粮饷。原来那老道是程婴显灵而成。*内部资料.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中国程婴故里文化之乡申报书[Z].忻州市政府,2011:332.
除此之外,《程婴赐瓜李孝子》《白马天神赐白马》等传说都讲述了程婴于百姓危难之际显灵的故事,百姓感念程婴恩德,纷纷建祠庙祭拜。民众对程婴的信奉程度在传说中得到转化和加强。不论是真实还是非真实,程婴显灵传说都是对程婴信仰的一种想象性叙事,是对当地程婴祭拜行为的诠释。叙事和诠释的目的在于确认和提升所有与程婴有关的信仰活动的历史文化地位,并注入历史的逻辑力量。为信仰提供的传说一般不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却成为当地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源。[27]程婴显灵传说的出现,表明程婴已从一个历史人物进入到民间信仰的殿堂,作为程婴信仰重要内容的显灵传说是程婴走向神坛的必由之路。除了传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外,程婴的信仰化过程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对程婴的敕封。民间传说当年宋神宗为报答程婴忠义救祖的恩德,追封程婴为“诚信侯”,并下旨让忻州的官员在程婴墓北新建一座程婴祠堂和程婴庙。忻州地区程婴显灵传说的盛行说明,从传说到信仰的文化运动既有民众不自觉的创作,又有上层文化“精英”的合目的的改造,既是传说自身演化规律的展示,又是民众心灵情感依托的必然结果。[28]
赵氏孤儿传说随着政治中心的迁徙而北移至忻州一带,经过官方的塑造、文人的置换、民间的传承,各阶层合力推动了以家国意识为主题的传说在该地的形成与传播,衍生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人物传说、风物传说及显灵传说等,这些传说皆以程婴等忠义之士为主要叙述对象,体现了民众在历史的抉择中树立的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
三 民间情怀:盂县以赵武为核心的传说辐射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在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的过程中,逐渐向生活化的方向发展,走进了民众的生活世界。盂县地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制约,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突出,民众解决生存需求的问题迫在眉睫。赵氏孤儿传说传播至该地后,衍生出浓厚的民间情怀主题内涵,传说的核心人物也因流传地域的差异而发生转移,形成以赵武为核心的传说圈。
(一)民间需求中传说的辐射
赵氏孤儿传说在忻州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开始向周边地区辐射。盂县因其隐蔽的地理环境与赵武藏匿的传说情节相附会,成了藏孤的绝佳之地,并在此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赵氏孤儿传说体系。赵武作为赵氏孤儿传说的核心,是“存孤”“救孤”“育孤”等系列情节的表述对象,但在襄汾、忻州两地的传说中其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更多是作为陪衬他者精神的形象出现。赵氏孤儿传说辐射至盂县一带后,赵武的核心地位才因民间的需求凸显出来,作为该地传说的关键人物,并形成一种民间信仰。
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封赵武为“藏山大王”。《大明一统志》载:“藏山,在盂县北五十里,相传程婴、公孙杵臼藏赵孤之处,山有庙,祀婴及杵臼。”[29]该地现存最早的碑刻为金大定十二年智楫撰《神泉里藏山神庙记》,碑刻云“藏山之迹,乃赵朔友人程公藏遗孤之处也”。可见在金以前最晚至宋时,赵氏孤儿传说就已辐射至盂县一带,藏山成为程婴藏匿赵孤之地。以藏山村为核心,传说在盂县境内乃至周边地区广泛流传。
盂县藏山赵氏孤儿传说在民间生存需求的推动下,形成对赵武的民间信仰。盂县地理位置偏北,处太行山之巅,四周群山环绕,境内山脉纵横,属中纬度地区,虽距海不远,但因山脉屏障受季风影响不大,春季干旱少雨,夏季高温炎热。《神泉里藏山神庙记》载:“我盂之境环处皆山也,土地硗瘠,士庶繁多,既无川泽以出鱼、盐之利,又无商贾以通有无之市,人人无不资力穑以为事。向若一岁之内颇值灾旱,饥寒之患不旋踵而至。”[30]3处在这种交通闭塞、耕种面积小、春季干旱频发的地理环境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当地的主要矛盾。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对自身生存的渴望,促使当地民众自发地寻求守护之神以得到精神寄托。传说中藏匿此地十五载的赵武便成了人们的首选目标,赵武既然有扭转乾坤、平定天下的能力,自然也有拯救百姓于水火的神力,于是赵武被推举为地方司雨之神,赵氏孤儿传说被赋予了一种民间情怀。
(二)赵武信仰生成的渊源
“信仰”是推动传说传播的核心动力。“从民间传说发展到民间信仰,也就是从口头叙事到行为模式,从表层言语到深层民俗心理的演化。”[28]13民间信仰是底层社会在历史的嬗变与传统文化的抉择中形成的对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天象等的崇拜奉祀。赵武作为圣贤的历史人物被传说化,其传说在藏山的在地化传承中逐渐超越表层的口头传承,演变为民众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叙事模式,在当地形成一种广泛的民间信仰,成为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人物传说在特定地域演变为民间信仰,反映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与地域性。
民间信仰多数情况下具有非官方性,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但在藏山,官方对赵武地位的擢升及其雨神功能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宋朝开始,官方曾多次对赵武进行加封,宋元丰四年(1081)神宗封赵武为“河东神主”,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封其为“藏山大王”,赵武在藏山的核心地位得以稳固,成为该地民众崇信的对象。清同治八年(1869)穆宗封其为“翊化尊神”,清光绪五年(1879)德宗封之为“福佑翊化尊神”,赵武信仰继续在该地发展壮大。
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特征,神祇的灵验是推动民间信仰发展的强大动力,民众可以不问信仰对象的出身来历,只要有灵则香火旺盛。藏山赵武信仰的形成与兴盛,并在周边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与其祈雨的灵验性密不可分。盂县藏山神祠现存碑刻共109通,其中记事碑49通,诗词碑8通,助缘、施银、捐资及好事题名碑52通。藏山文化研究会编纂的《藏山文化通览》一书中辑录碑文43通,包括金代1通,元代1通,明代16通,清代24通,清以后1通,这43通碑刻中明确记录向藏山大王求雨应验内容的有14通。金大定十二年(1172)智楫撰《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中记载颇为详尽:
天德间,岁大旱,旬月不雨,邑宰尝往吊之,洎归似有亵慢之意,须臾而雹雨大降;宰复反已致恭虔,俄雨作以获霑,足其灵异。又有如此者,人皆谓我,既往而不足究。予大定戊子来宰是邑之明年也,自春徂夏,阴伏阳愆,旱魃为虐,众口嗸嗸,皆有不平之色,或告之曰:藏山之神,其神至灵,祷之必应。予始未孚勉行之。于是同县僚暨邦人,斋戒沐浴备祀事,洁之以牲,奠之以酒。往迎之,笙镛杂沓,旌旗闪烁,徜徉百舞;既迎之来,恍兮降格,油然而云兴,沛然而雨作,霑霈一境,使旱苗、槁草皆得蕃滋,百谷用成而岁大熟。
又明景泰六年(1455)马能撰《新建藏山大王灵应碑记》载:
景泰甲戌祀,大尹清苑蒋宽莅政之后,适值亢阳之愆,躬拜雨泽之贶,果获圣水,大降甘霖,苗禾浡然,麦豆若然,非惟一邑之蒙其护祐,抑且四方之慕其灵通。乃者,太原守、阳曲令命民耆遣信士越境而来,潜影而入,窃负圣像而去之,过其村则村无不雨,经其乡则乡无不雷,见之无不恐怖,闻之无不惊惶,藩府为之远接,臬司为之近迎,乐音震天,旌旗连地,顷刻中阴云密布,倏忽间大雨淋漓,竟三日而后息。[30]11
从碑文记载可知,藏山一地凡遇亢旱,向赵武祷雨必应,水涝之灾同样灵验。清雍正三年(1725)王珻撰《重修藏山赵文子庙碑记》云,己亥秋八月,山水暴作,“四方以歉告,哀鸿之声延数百里,盂岁独无恙”。[30]47旱干水溢之时,藏山大王无不灵应,满足了民众的生存需求,成为民间的信仰并影响至今,其神职在发展过程中得以扩大,从司雨神上升为全能的地方神。今盂县当地称赵武为灵感大王,司人间风雨及祛病消灾,赐福寿吉祥,招财富晋爵位,有求必应,灵感异常。
在民间与官方的共同推动之下,藏山赵氏孤儿传说的核心人物从代表忠义精神的程婴等义士转变为能解人间疾苦的被神化了的赵武,在当地形成了广泛的民间信仰,信仰对象的灵验程度进一步促进了传说的发展。
(三)传说的多重民间叙事
口头叙事是赵氏孤儿传说传承的主要路径,并一直向着文本化的方向发展。传说的口头传承在民间信仰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积淀为一种深层的民俗心理,表征为模式化的行为方式与风俗习惯,以仪式叙事的方式不断重演。空间叙事为仪式的发生提供了物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有了稳固的、可靠的传承载体,藏山赵氏孤儿传说以多重民间叙事方式在当地展演。
1.文本化的口头叙事
口头性是民间叙事的基本特征,“以口头创作方式出现的民间叙事,是民间叙事的主体”[31]。民间叙事因其口头性特征而具有不稳定、易散失的特点,因此在保存与传承中,口头叙事形式逐渐向文本化、经典化演进。凝聚为文本的口头叙事成为民间文学搜集过程中最易得到的资料,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盂县藏山赵氏孤儿传说文本化口头叙事资料的搜集分析,可按内容将该地传说分为两种类型,即救孤传说和藏山大王传说。
(1)救孤传说
此类传说文本数量较多,内容奇特,救孤主体身份多元,有普通民众、有菩萨圣灵、有灵性动植物等。在流传过程中,救孤传说吸纳融合了新的元素,即佛教圣灵。如《程婴和赵氏孤儿在打围村脱险》讲述了普贤菩萨在程婴与赵武命悬一线之时帮助他们解除了危险。*内部资料.盂县政协.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故事[Z].盂县政府,2009:10.民间信仰的对象在神职功能上能够应付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的信仰者及各式各样愿望和要求,信仰客体不呈体系,宗教之间颇多融合,民间信仰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这是佛教圣灵能够融入赵氏孤儿传说的深层原因。此外,富有灵性的动、植物也成为救孤功臣,盂县流传最广的动物救孤故事有“蝼蛄救孤”“灰鸽子救孤”“鼓肚蜘蛛和绿头大王救孤”“石虎救孤”和“马蹄刨泉救孤”等。这些“动物救孤”情节在王莽赶刘秀传说或其他传说中同样出现,这类传说尽管同特定的风物、人物结合较紧密,但它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的可信物,另一方面又附会到新的风物、人物上,成为同类型的新传说。传说的这种故事本体与所附人、物之间可分离、可移动的特质,正是传说向民间故事转化的表现。[32]从“救孤型”传说可以发现,传说中营救者不仅趋于多元化,内容更为丰富,其情节也在向民间故事转化。
(2)藏山大王传说
由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盛行,赵武逐渐由传说中的人物演变为民间信仰中的雨神,被民众尊为藏山大王,建庙祭拜。每逢天旱少雨,民众便到大王庙中叩拜求雨,藏山现存的许多碑刻都记载了向藏山大王祈雨灵验的故事。藏山大王信仰的兴起,使得其相关传说应运而生,其中赵武于藏山坐化、因德行感动玉帝被封为“藏山大王”等传说解释了赵武名号的由来。更多传说则讲述了赵武被封神后显灵降雨的事迹,如《大王爷和财主侯伯良打赌》,大王爷不仅降雨帮助百姓摆脱了干旱少粮的困窘生活,更用大水淹了黑心财主的家,惩治了财主。*内部资料.盂县政协.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故事[Z].盂县政府,2009:56.同类传说还有《武士豪请大王爷》《藏山大王瓮打磁州》等。赵氏孤儿传说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周围地区辐射传播,在历时的传承过程中逐渐远离传说的原始主题,向着更加生活化的方向发展,表达了民众的生存理想与美好愿望。
2.仪式叙事
“活态民间叙事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是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的叙事——民间行为叙事。”[33]行为叙事使民间传说以身体表演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民众生活之中,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行为叙事在不同的叙事氛围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类型,或为轻松愉悦的游戏叙事,或为神圣庄严的仪式叙事。赵氏孤儿传说中的民间信仰是促成传说神圣叙事特征的重要因素,神圣性的行为叙事即仪式叙事,是藏山赵氏孤儿传说在民间的重要传承形式。
仪式叙事,指祭祀、祷祝、祈求等民俗活动中的叙事。盂县每年都会举行祈雨会,即藏山老会,又称藏山赶老会。藏山老会形成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初成规模,历经元明清三代,已发展到千人规模,民国初期尚且存留,抗日战争爆发后消失。藏山老会是由当地群众自发组织,集祭祀、供奉、集会、娱乐、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是当地百姓天旱祈雨之后回谢藏山大王的一种纪念性表演活动。藏山赶老会队伍由开道锣、门旗、头锣、头牌、高罩、铁炮、大旗、战鼓、围子、八音会、八仙过海、八义救孤、金瓜、钺斧、朝天镫、万人伞、灯笼、銮驾、龙凤扇、随护、敬香盘、执事等组成,参加人数从108人至上千人不等,均身着表演服装,手持道具,按照规定的步伐、动作、节奏统一表演。场地表演分“过街”“踩海眼”两种,古时有东乡会、西乡会、南乡会、北乡会之分,其中清城三月十五的“起神会”最负盛名。赶老会“迎銮驾”仪式最为隆重,每逢农历四月十五,分散在各地的108尊“小大王”同回藏山落驾,享受祭拜。*内部资料.盂县藏山旅游风景名胜区.藏山老会[Z].2013:3-5.现经多年的挖掘与整理,失传约70载的藏山赶老会终在2014年于盂县重新上演,延续着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与祈雨文化。
围绕赵武民间信仰生成的藏山赶老会仪式,在情景化的叙述语境中,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叙述动作,以集体表演的形式在动态中传承。这一系列表象的仪式行为实指向精神层面,是民众心理需求与民间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功能、形式与主题的有机融合。藏山赶老会作为一种仪式叙事,同样蕴含着藏山赵氏孤儿传说的民间情怀。
3.空间叙事
空间与时间同为叙事存在的基本维度,从内部决定着叙事的发展。空间叙事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与理论转向受到重视。物质性是空间存在的第一维度,思想性、观念性是空间领域的第二维度,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的融合及超越形成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是一种既真实又想象化的存在,既是结构化的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具有空间性、社会性与历史性。[34]赵氏孤儿传说以具有特定精神内涵的物质空间为载体,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空间叙事方式。这种物质空间的选择与建构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物化对象与内在精神世界相契合的基础之上,是物质与精神深度融合的第三空间。藏山赵氏孤儿传说的空间叙事集中体现在藏山神祠。
藏山神祠是供奉赵武的主要场所,具体始建年代不详,约建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庙内现存最早的碑刻是金大定十二年(1172)县令智楫所作。神祠从藏山半山腰处一直延展到山谷,前后四进院带两个东跨院,规模较大。南北中轴线自下而上依次为牌楼、山门、戏台、正殿、献殿、寝宫、梳妆楼,加之两侧配殿中的藏山大王祠、双烈祠、韩厥祠,及东二院之报恩殿、八义殿,共有庙宇30余处。牌楼建于明代,为木式结构,三头四柱,造型高大,斗拱密集,外额题有“藏孤圣境”。正殿为明代建筑,殿内供奉赵武,着明代王爷服饰。殿内柱上刻有盘龙一直延伸至梁顶,墙壁上绘有四十二幅壁画,描绘了赵氏家族从蒙灾受难到平反昭雪的整个过程,《崇增藏山神祠之记》曰:“中殿一所,内塑威灵,壁绘行图,乃圣者之根源也。”*明嘉靖四年(1525)碑刻,规格高247cm,宽80cm,现存于寝宫东侧。寝宫为典型的元代建筑,祀奉赵文子夫妇。寝宫东侧是藏山大王殿,内供奉盂县各地藏山大王像近百座;西侧是假孤殿,内祀程婴之子。报恩祠祭程婴、公孙杵臼与韩厥。八义殿供奉程婴、公孙杵臼、假孤、韩厥、灵辄、鉏麑、提弥明和草泽医人。除藏山神祠之外,盂县各村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藏山神庙,据统计,目前县境内藏山神庙有89座,县城西关有2座大型神祠,当地民众反映尚有5座未统计在内,全县约有神庙96座,均以藏山神祠为“庙之祖”,名为藏山神庙、藏山神祠、藏山行祠、藏山大王庙、藏山大王行祠、藏山大王神祠等,这些散布于各村镇的庙宇共同组建起了以藏山神祠为中心的传说风物群。藏山神祠风物群是民众祈祷祭祀的神圣场域,也是赶老会仪式的活动空间,该地以寺庙风物为主的空间叙事形态,是民间信仰的心理需求与行为仪式在物质世界传承中的客观表征,空间叙事是盂县藏山赵氏孤儿传说的主要叙事方式之一。
相较于晋南、忻州两地而言,盂县赵氏孤儿传说中的主人公不再是以程婴为核心的忠义之士,而是被神化了的赵武。赵武也已不再是襄汾、忻州等地文本中所展现的配角人物,民众对他的描述更细致、更传奇、更具神力,其地位因“藏山大王”这一称号的确立而被无限提升,并最终成为民众祭祀的主神。这种寄托在赵氏孤儿形象中的民间情怀,体现着这一传说与当地社会、文化的深入融合,反映着底层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情感世界,民众将自己对生命的期盼、对生活的热爱、对各种世俗欲望的追求依附在了赵氏孤儿传说之中。除了对忠义精神的宣扬,对家国意识的建构,一种植根于底层广大群体中的民间情怀得以在盂县这片土壤上滋生,这是赵氏孤儿传说在此地所展现出的主要精神内涵。由此而形成的种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也使赵氏孤儿传说得以向着生活化的方向继续传承下去。
四 结语
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可以去考证,但世代口承的民间传说跨越时间的局限,打破空间的束缚,体现出无时间性,这“有可能为故事的展开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35]。赵氏孤儿传说便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自由状态中打破地域界限与时间束缚,在晋南、忻州、盂县三地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传说体系并传承至今。赵氏孤儿口承民间叙事经文人记录得以文本化,后经权力者的介入逐渐经典化,经典化的文本反哺民间形成新的民间叙事。在文本与口头的两相融合中,赵氏孤儿传说在晋地形成新老民间叙事和经典化文本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与主题内涵。活态的民间传说从来不会因为经典文本的凝聚而失去其灵性。
民间传说层累的凝聚与转移,使赵氏孤儿传说的核心人物与主题内涵随着传承地域的改变发生转移与延展,在晋地形成三个不同的传说体系:襄汾作为传说的发源地,形成以赵盾为核心,表达祖先崇拜主题的传说体系,在民间体现为血缘观念下的排他性、外化的祭祀仪式及伦理观念下的人文崇拜;赵氏孤儿传说随着政治中心的迁徙北移至忻州一带,在官方对忠义形象的塑造、文人对复仇母题的置换及民间对忠义精神的传承中形成以程婴为核心、以家国意识为主题的传说体系;在民间需求的推动下赵氏孤儿传说辐射至盂县藏山,在当地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信仰,传说以多元的叙事方式展演在民间,形成以赵武为核心、以民间情怀为主题的传说体系。
赵氏孤儿传说以山西为中心传播至河南温县、陕西合阳等地,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传说类型与风俗习惯。赵氏孤儿传说经过历史的沉淀、文人的加工与民间的抉择,在每个历史阶段及不同地域,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主题内涵,从而使得赵氏孤儿传说能够在层累的历史中不断丰富扩展,并逐渐深入民众的精神世界,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象征得以久传不衰。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M]∥钱小柏.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60.
[2]向 轼.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关联:以巫山神女传说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12):92-95.
[3]张 勃.历史人物的传说化与传说人物的历史化:从介子推传说谈起[J].民间文化论坛,2004(6):72-77.
[4]万建中.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J].民族艺术,2005(3):71-75.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张钟秀,周令德.太平县志[O].清乾隆四十年刊本.1775:26.
[8]杜 靖.文献与田野间的双向阅读: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传统人文学相结合的人类学之路[J].探索与争鸣,2017(5):110-117.
[9]何顺果,陈继静.神话、传说与历史[J].史学理论研究,2007(4):42-51.
[1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8.
[12]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与思想[M].东京: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9:183.
[13]赖萱萱.祖先崇拜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4(3):28-31.
[14]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J].世界宗教研究,1999(3):114-124.
[15]任建东.道德信仰生成的文化人类学透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17-20.
[16]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452.
[1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
[18]王 轩,等纂修.山西通志[M].李 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储大文.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97-1398.
[20]钱 穆.晚学盲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7.
[21]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7.
[22]脱 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722.
[23]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50-151.
[24]胡志毅.置换变形、复仇母题与象征意象:《赵氏孤儿》的神话原型阐释[J].同济大学学报,2015(4):76-81.
[25]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
[26]Frye Northrop.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208.
[27]万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机制:以广东汕尾妈祖信仰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2-75.
[28]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11-17.
[29]长泽规矩也等.大明一统志[M].日本:汲古书院,1978:340.
[30]藏山文化研究会.藏山文化通览[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31]董乃斌,程 蔷.民间叙事论纲:上[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2):12-21.
[32]李 扬.简论民间传说和故事的相互转化[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5.
[33]董乃斌,程 蔷.民间叙事论纲:下[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3):38-51.
[34]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7(4):42-47.
[35]卞梦薇.论民间叙事的“无时间性”[J].民间文化论坛,2017(1):64-74.
——观《程婴救孤》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