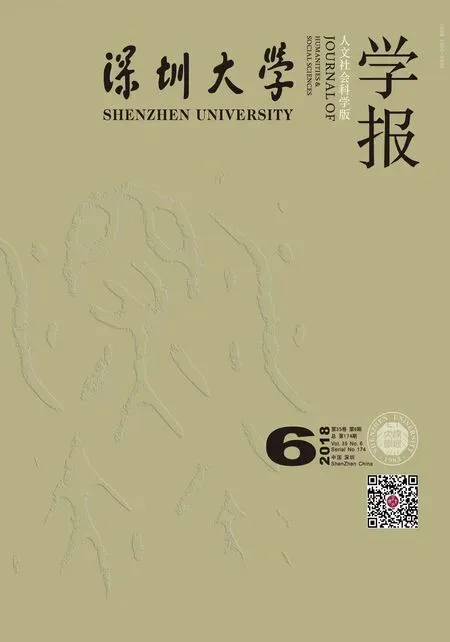“毗尼四法”流变考释
吴蔚琳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巴利 Samantapāsādikā和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中的“毗尼四法”
(一)“毗尼四法”的涵义
“毗尼”是梵语、巴利语词vinaya的音译,本义为调伏,引申为律。“毗尼四法(catubbidha-vinaya)”是上座部佛教概念,出自权威注释家觉音(Buddhaghosa)著的巴利语律藏注释书 《善见律疏》(Samantapāsādikā),在汉译本《善见律毗婆沙》中有对应译文①。《善见律毗婆沙》于公元489年由外国沙门僧伽跋陀罗和汉僧僧猗共同译出。“毗尼四法”是研习上座部律典应遵循的方法原则,分别是:本(sutta),随本(suttānuloma),法师语(ācariyavāda),自意(attanomati)。 其义巴利《善见律疏》和汉译《善见律毗婆沙》文字对照如下:
1.本
巴:suttamnāma sakale vinayapitake pāli.(“本”谓整部巴利律藏经典。)
汉:一切律藏是名本。
Sutta音译修多罗,其他汉译佛典中一般意译作“契经”或“经”。 此处译作“本”,为律本之意,意即巴利律藏是根本,反映出译者对此处sutta涵义的理解非常准确。
2.随本
巴:suttānulomamnāma cattāro mahāpadesā;ye bhagavatā evamvuttā:‘‘yam,bhikkhave,mayā‘ida mna kappatī’ti appatikkhittam,tamce akappiyamanulometi,kappiyampatibāhati,tamvo na kappati.yam,bhikkhave,mayā‘idamna kappatī’ti appatikkhittam,tamce kappiyamanulometi;akappiyampa tibāhati,tamvo kappati.yam,bhikkhave,mayā‘ida m kappatī’ti ananuātam,tam ce akappiyam anulometi,kappiyampatibāhati;tamvo na kappati.yam,bhikkhave,mayā ‘idamkappatī’ti ananuātam,ta m ce kappiyamanulometi,akappiyampatibāhati;tam vo kappatī’’ ti.(随本的意思是四大教法。世尊如是说:“诸比丘,那个不被我以‘此不净’反对的东西,如果它与不净物相符合,与净物相悖,对你们来讲是不净的。诸比丘,那个不被我以‘此不净’反对的东西,如果它与净物相符合,与不净物相悖,对你们来讲是净的。诸比丘,那个不被我以‘此净’听许的东西,如果它与不净物相符合,与净物相悖,对你们来讲是不净的。诸比丘,那个不被我以‘此净’听许的东西,如果它与净物相符合,与不净物相悖,对你们来讲是净的。”)
汉:四大处名为随本。佛告诸比丘:“我说不净而不制,然此随入不净,于净不入,是名不净。”佛告诸比丘:“我说不净而不制,然此随入净,是名净。”佛告诸比丘:“我说听净,然此随入不净,于净不入,此于汝辈不净。”佛告诸比丘:“我说听净,然此随入净,于汝辈净。”是名四大处。
“四大教法(cattāro mahā-apadesā)”出自巴利律藏的《大品》(Mahāvagga),但不是律藏(“本”)中的具体某一条戒律规定。律本是佛陀在世时亲自制定的。律本的各项规定难以面面俱到,因此诸比丘对“净”与“不净”的判断原则产生疑问。“四大教法”即是佛陀就“净”与“不净”的判别依据所作的补充解释,因此称为“随本”,是对“本”的补充。巴利语复合词mahāpadesā应该拆分成mahā (大)和apadesā(教法)。 《善见律毗婆沙》译者译作“四大处”,反映出他对印度语言的连音规则缺乏了解,把mahāpadesā 错误拆分成 mahā 和 padesā(处所)[1]。
3.法师语
汉:集众五百阿罗汉时,佛先说本,五百阿罗汉广分别流通,是名法师语。
佛陀涅槃后第七日进行了五百罗汉结集。根据觉音的记载,参与这次结集的法师对巴利律本的注释称为“法师语”。
4.自意
巴 :attanomati nāma sutta-suttānulomaācariyavāde mucitvā anumānena attano anubuddhiyā nayaggāhena upa tthitākārakathana m.api ca suttantābhidhammavinayatthakathāsu āgato sabbo pi theravādo“attanomati”nāma.tampana attanomatimgahetvā kathentena na da lhaggāha mga-hetvā voharitabbam.kāranamsallakkhetvā atthena pālim,pāliyā ca atthamsamsanditvā kathetabbam.(自意的意思是除本、随本、法师语以外,通过推论,通过自己的随觉,通过摄理趣展示的行相、言论。此外,于经、论、律注释中记录下来的所有高僧大德的言语也称自意。但把握自意之后,不应作为武断的表达。思考了根据之后,结合经典,意义可被讲述,以及结合意义,经典可被讲述。)
汉:置本、置随本、置法师语,以意度,用方便度,以修多罗广说、以阿毗昙广说、以毗尼广说,以法师语者,是名自意。又问:“此义云何?”“莫辄取而行,应先观根本已,次观句义,一一分别,共相度量,后观法师语,若与文句等者而取;若观不等,莫取,是名自意。”
“自意”是习律者对律本的理解,包括经律论三藏注释中流传下来的大德之言,即这些大德对律本的释读。由本、随本、法师语、自意构成的“毗尼四法”是研读律典的四重法。那么,四者的先后次第和重要程度如何?
巴 :attanomati ācariyavāde otāretabbā.sace tattha otarati c’eva sameti ca,gahetabbā.sace n’eva otarati na sameti,na gahetabbā … suttānulomato hi suttam eva balavataram.suttahi appativattiyamkā-rakasaghasadisambuddhānamthitakālasadisam.(自意应被包含进法师语中或等同于法师语,只有这样才可被摄取。因为,所谓的自意最薄弱,法师语比自意更有力量。法师语应被包含进随本中等同于随本……随本也应被包含进本中或等同于本……因为,本是不可违背的、相当于参与结集的诸比丘、相当于诸佛存在的时代。)
汉:从自意者,法师语坚强,法师语应观,随本文句俱等,应当取;若文句不等,勿取。从法师语,随本坚强,若观随本,文义等者,应当取;若不等,莫取。从随本,本皆强坚,不可动摇,如众僧羯磨,亦如佛在世无异。法师曰:“若观随本不能自了者,应观修多罗,本义疏俱等者取。”
这段文字意思是,研读者的释读(“自意”)不能违背五百结集的“法师语”,“法师语”不能违背“随本”,“随本”不能违背巴利律本(“本”)。 “毗尼四法”意指研读上座部律典时应以“本”为权威,“随本”次之,“法师语”再次之,“自意”处于最末位置,最不具备权威性。
(二)“毗尼四法”与部派之争
《善见律毗婆沙》对“毗尼四法”基本涵义的记载与巴利《善见律疏》一致。但如果涉及到上座部与其他部派之争,情况则不同。在巴利《善见律疏》中详细记载了上座部论师与其他部派论师就某一戒律问题发生矛盾时应采取的判定依据和方法,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与其他部派论师(paravādī)所持的依据相比,上座部论师(sakavādī)所持的依据就是权威。哪怕是上座部论师的自意也比其他部派论师的本、随本、法师语都要权威 (tasmā yadā dve bhikkhū sākacchanti,sakavādī suttamgahetvā katheti,paravādī suttānulomam…ath’āyamsuttānuloma mgahetvā katheti,paro attanomatim.attanomati suttānulome otāretabbā.)。 显然,觉音的态度是独尊上座部论师和律典,对其他部派加以严厉驳斥和全盘否定。这一段文字在《善见律毗婆沙》中没有可对应的汉译文。
第二,如果涉及“净”与“不净”的戒律,判断依据应是上座部论师所持的“本”和“随本”。
巴:atha pan’āyam‘‘kappiyan’’ti gahetvā katheti,paro ‘‘akappiyan’’ ti.sutte ca suttānulome ca otāretabbam.sace kappiyamhoti,kappiye thātabbam…sabbaso pana kāranamvinicchayamalabhantena suttamna jahitabbam,suttasmimyeva thātabban ti.evamtasmimsikkhāpade ca sikkhāpadavibhage ca sakale ca vinayavinicchaye kosallampatthayantena ayamcatubbidho vinayo jānitabbo.[2](P231-233)(又,此方摄“净”而谈,彼方摄不净。此二者都应被包含进本和随本中。如果本和随本都认为净,那被确立是净。没从全部本、随本、法师语、自意中获得判定依据的人不可舍弃本。一切仅在本中确立。如是,在这条学处与学处经分别以及所有律判定中,这四毗尼应被需要善巧的人所知。)
汉:有二比丘共相诘问,一比丘言净,第二比丘言不净,更观本及随本。若本与随本,言净者,善;若言不净,莫取。若一比丘观本已净,又文义证多,第二比丘文义寡少,应从第一比丘语。法师曰:“若二比丘文义俱等者,应反复思惟筹量义本,应可取、不可取。此是学四种毗尼人。”[3](P716)
“净”与“不净”之争在佛教史上由来已久,是各个部派戒律争论的焦点。与巴利《善见律疏》相比,《善见律毗婆沙》对此段争论的记载简略得多。译者认为此争论仅是二比丘之争,没有强调是不同部派之争。
与巴利 《善见律疏》不同的是,《善见律毗婆沙》的“毗尼四法”没有凸显部派之争,也没有体现出上座部的独尊地位,究其原因可作如下分析:从《善见律毗婆沙》的翻译可见,译者对上座部以外的其他部派采取兼容的态度。《善见律毗婆沙》大部分内容译自巴利《善见律疏》,但也增添不少法藏部《四分律》的内容,同时也有部分内容反映出其他部派的主张。日本学者长井真琴通过对比《善见律毗婆沙》和《四分律》的框架结构后指出,《善见律毗婆沙》单堕法第85~91条以及犍度部分的排序与巴利《善见律疏》不同,反而与《四分律》一致,反映出译者受到《四分律》的影响[4](P72-73)。 据水野弘元研究,《善见律毗婆沙》的药犍度和皮革犍度不仅与《四分律》排序一致,二者的文字内容也相同,显然是译者直接引用《四分律》的结果[5]。除此外,《善见律毗婆沙》的“佛塔学处”亦出自《四分律》[5]。 除法藏部的影响外,译文中的“杂事”、“八难”、“十三难”等术语还反映出说一切有部等其他部派的来源[6],还存在些目前难以确定的部派学说。比如,《善见律毗婆沙》记载了受三归依的两种方式,一为别受,二为总受:“别受者,归依佛归依佛归依佛竟,归依法归依法归依法竟,归依僧归依僧归依僧竟,是名别受。总受者,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如是三说,是名总受。 ”[3](P788)然而,巴利《善见律疏》规定,先说“归依佛”三次再说其他两句每一句各三次,不予三归依[2](P969)。 巴利律中也没有记载“别受”。“总受”与“别受”在巴利律和巴利本《善见律疏》中都没有对应巴利语词。《十诵律》、《五分律》、《四分律》等其他部派的汉译律典中也没有这组律学概念。此外,目前现存的早于《善见律毗婆沙》的汉译律典中都没有记载“别受”的方式,只有“总受”这一方式②。可见“别受”有特殊的部派来源。上述例证体现了 《善见律毗婆沙》部派来源的多样性,因此,译者笔下的“毗尼四法”不唯上座部独尊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唐宋南山律疏中“毗尼四法”的流变
(一)道宣的吸纳
唐宋以来,四分律宗南山律学日渐成为中国佛教戒律的主流,产生了南山三大部等著述。以道宣(596-667)为首的南山律师吸纳化用“毗尼四法”,对这一概念提出新的释读。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就引用“毗尼四法”来说明解读《四分律》的方法:“今立《四分》为本,若行事之时,必须用诸部者,不可不用。故《善见》云,毗尼有四法,诸大德有神通者,抄出令人知,一本者,谓一切律藏,二随本,三法师语者,谓佛先说本,五百罗汉广分别流通,即论主也,四意用,谓以意方便度用及三藏等广说也。先观根本,次及句义,后观法师语。与文句等者,用;不等者,莫取。 ”[7](P2)道宣的意思是以《四分律》为根本,统合其他部派的汉译律典《十诵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来解释《四分律》。他还把“自意”改作“意用”,篡改依据是《善见律毗婆沙》对“自意”的定义:“置本、置随本、置法师语,以意度,用方便度,以修多罗广说、以阿毗昙广说、以毗尼广说,以法师语者。”根据道宣的理解,“以意方便度用”和“三藏(修多罗、阿毗昙、毗尼)等广说(意即注释)”都属于“意用”。这一理解与巴利《善见律疏》原意不同。据巴利《善见律疏》记载,在经、论、律三藏注释中记录下来的高僧大德的言语才能称作“自意”,而不是三藏的注释都可统称为“自意”。道宣的解读源自翻译上的差异。巴利文suttanta-abhidhamma-vinayatthakathāsu āgato…theravādo,意指在经、论、律注释中记录下来的高僧大德的言语;而《善见律毗婆沙》译文是“以修多罗广说、以阿毗昙广说、以毗尼广说,以法师语”。译者把三藏注释与法师(大德)之语等同起来,构成并列关系,所以道宣说“三藏等广说”。
然后道宣进一步说明如何采纳各部派律典:“若《四分》判文有限,则事不可通行,还用他部之文,以成他部之事。或二律之内,文义双明,则无由取舍,便俱出正法,随意采用。 ”[8](P385)《四分律》禁止的事情,不可违犯,但如果有的为其他部派律典所准许,则可依用它们的羯磨文进行;或者各部派律典虽然有不同说法,但如果都有合理之处,则会一起记录供参考。道宣虽以《四分律》为他的“本”,但不以“本”为权威,也不唯执法藏部,而是融通各部,依意采用,他的“自意”越过了“本”的范畴,甚至与“本”相悖。比如,《四分律》规定没有衣钵不可受戒。道宣却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和《十诵律》说明,若依据说一切有部律典,没有衣钵也可受戒,如此行事对四分律宗没有坏影响[7](P28)。道宣把当时律师对待不同部派律典的态度归纳为六种:一是独尊《四分律》,排斥他部;二是若本部没谈及,则引用他部补充;三是先取本部之说,凸显宗义,再引他部;四是本部律文虽已明晰,但仍援引他部;五是取四部阿含和杂藏来融会;六是以大乘教义为最终归向。前五种都是仅限于小乘,只有第六种是兼通大小二乘的。道宣以第三和第六种方法为主,兼取其他四种[7](P386)。所以,道宣以“毗尼四法”为用,而非取其体。
(二)道宣法嗣的新解
道宣的法嗣大觉 (生卒年不祥)、景霄(?—927)、元照(1048—1116)都是《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传承者,分别著有《四分律行事钞批》(成书于712年)、《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唐代开元年间,大觉对“毗尼四法”又有新的释读:“《善见》云毗尼有四法者,一本,彼文自解谓一切律藏也。一切者,但是佛所制戒,一一之戒为结集者,名律藏也。二随本者,立云,如淫戒,初制不得淫人,后林中过兴,制三趣同犯,将此重制,名为随本也。济云,随本者,谓是随律之经、随律之论等也。其中明戒律者,并名随本也。三法师语者,即五百无著,名为法师,习是论主也。佛先说本者,即大毗尼藏也。灭后五百罗汉流通作论,解释者是也。四意用者,谓是五百论师,意方便度用,非是凡夫意用也。”[8]根据大觉的释读,“本”指结集后所出律藏。随本则有两层含义:一是重制后的戒律,比如淫戒最初规定不得与人行淫,后来由于有比丘在林中与雌猕猴行淫,因此重制淫戒,规定与三趣众生(地狱、饿鬼、畜生)行淫皆犯戒③;二是律藏中解释律的经、论部分。“法师语”的解释与道宣之解一致,都是论主。“意用”被解释成是第一次结集中五百罗汉的意用。大觉对“随本”和“意用”的理解完全不符合《善见律毗婆沙》文义,究其原因是他没有接触到《善见律毗婆沙》的原语本,因此他的解释难免望文生义。他接下来说:
“今引此《论》,意欲取第四句意用义,成今门中之意。从谓宗已下,是释第四句意用文也。言及三藏等广说者,此约三藏教文,即是经律论也。先观根本者,谓观一切律藏中,如来所说制戒,皆有缘起,非无因缘而制也。相承解云,此却释上一本起句文也。次及句义者,却释前二随本句也,谓若有重犯,即便随结,如林中等也。后观法师语者,却释前《善见》论主五百无著之所说也。与文句等者,用。不等,莫取者。立云,释前第四意用文者是也。然今何故引此《论》中四法来?谓此是用他部文意门故。引此《论》中四法者,前三是便明,正意取第四句意用,即方便度用等文也,欲明我既用他部之文,应须效彼《论》文‘方便度用’也。”[8]
大觉进一步认为,“法师语”是《善见律毗婆沙》论主五百罗汉对戒律的解释,与此等同者才被采用。巴利《善见律疏》和《善见律毗婆沙》都没有记载这部律论成书于五百结集时期。把五百罗汉误认为是《善见律毗婆沙》的论主,反映出大觉认识到第一次结集时期就已经产生律本的注释,但他没有说明自己的理解源自何处。他还强调,道宣引用“毗尼四法”,是效仿《善见律毗婆沙》的“方便度用”,引用“本”、“随本”“法师语”前三者都是为“意用”做铺垫。道宣旨在“意用”,他的“意用”成为南山律学的“意用”,即方便度用他部文意来解释《四分律》。同样,因对原语本缺乏了解,大觉对《善见律毗婆沙》的“方便度用”随意揣测,误认为也是结合其他部派“意用”。但是,大觉认为道宣引用“毗尼四法”的重点在于“意用”,指出道宣开辟了南山律学的释律方法,这一理解是正确的。
后唐时期的景霄另有新解:“一本、二随本、三法师语、四意用,是谓四也。……《钞》中引文,意存省约,随标便解也。言一切律藏者,即《四分律》二十犍度,其文不少,故云一切。非谓通八十诵律为一切也。 ”[9](P56)作为“本”的“一切律藏”被景霄解释为“《四分律》二十犍度”,《四分律》(共 60 卷)中犍度部分占有30卷,所以景霄说“其文不少”。由此可见,景霄认为《善见律毗婆沙》这部律论的解释对象是《四分律》。据文献记载,这一误解肇始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定宾律师④,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善见律毗婆沙》在翻译过程中插入了不少《四分律》的内容。其次,《善见律毗婆沙》的解释对象巴利律本在中国古代没有流传开来。《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毗利,齐言宿德律,未详卷数,阙。右二部。齐武皇帝时,外国沙门大乘于广州译出,未至京都。”[10](P13)“他毗利”梵语作 sthavira,上座之意。这部律译于萧齐时代,但生活在齐梁之际的僧佑没见到这部律。后世的佛教经录都沿用僧佑的记载。因此,这部宿德律在译出后没多久就失传了,古代汉传佛教不了解上座部律,亦不了解上座部与《善见律毗婆沙》的关系[11]。景霄继续说:
“二随本,准《论》,是四大处。然释此四大处不同。准《论》即在初戒中明,今约义遍通诸戒。今且于性戒中,对非戒辨,余戒例之。斯之四句,前二句是戒本通缘句,后二是戒本别缘句。第一第三是犯,第二第四是不犯句。第一,佛告诸比丘。我说不净性戒体是恶故而不制痴狂心乱时,开作前事故,然此随入不净虽有开文,有一念心忆识,今作事时,是比丘以便入犯位故,于净不入,是名不净有一念心忆识,是比丘不入开文。是名不净也。第二,佛告诸比丘,我说不净同上而不制,然此随入净是名净作前事时,无一念知,是比丘顺开文,故名净也。第三,佛诸比丘,我说听净而不制初戒遇怨逼缘,许与境合,名不制也,然此随入不净三时中一念生染乐心,即名不净,于净不入,于汝辈不净谓生染乐心,入开文,名于净不入也。第四,告诸比丘,我说听净而不制同上,然此随入净,于汝辈净作前事时,无染乐心,入于开数,无犯,故名净。自余性戒,前二句通缘并同,后二句别缘即异。如盗戒作无主想、亲厚想,杀戒作杭木想等,是别缘也。遮戒亦同于上。 ”[9](P57)
在《善见律毗婆沙》中,“毗尼四法”的上文是对律藏中第一戒条淫戒的解释,所以景霄说“在初戒中明”,并以淫戒为例做注文。邪淫、杀生、偷盗、妄语皆犯波罗夷。此四戒都是性戒,是针对本质性为恶而制定的戒律(“性戒体是恶”),是佛法和世俗法都不可违背的戒条。他认为“随本”的“四大处”适用于所有戒条,因此说“遍通诸戒”、“余戒例之”,认为前二句是通缘,后二句是别缘。“通缘”和“别缘”这组律学概念出自《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犯戒的因缘由通缘和别缘构成。戒律的条目、轻重虽不同,但其持守及违犯都有共同的标准,这一共同标准就是通缘。每一戒条又有自身个别的条件,这一有别于他戒的条件就是该戒的别缘。道宣把通缘归纳为八种:已制广戒、犯戒者是五众出家人、无病缘、期心当境、无命难、无梵行难、称本境、进趣正果[7](P94-95)。 从景霄的注文可知,“痴狂心乱”即指通緣中的无病缘,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有种种非法行为都不计为犯戒。“有一念心忆识”即是通緣中的 “期心当境”(造罪时其心没有进入睡眠不觉等无记状态,明白自己正处在造罪的状态。)或“称本境”(造罪时内心确定无疑,甚至有一种成就感)。在没有原语本对照的情况下,景霄的释读依据只能是汉文佛典。“不制”一词在汉译律典中的涵义是不制定、不制戒。例如,《四分律》记载:“‘长老!佛不制比丘不得行不净耶?’彼答言:‘佛制人女,不制畜生。’”[12]《五分律》记载:“诸长老比丘问言:‘佛岂不制杀生草木耶?’答言:‘我等使人为之,不违佛制。’”[13]所以,据景霄的理解,前二句意思是,尽管戒律对“痴狂心乱”和最初未制戒有开文⑤,但如果比丘行淫时有念心忆识,知道自己在行淫造罪,则不可被原谅(“不净”);反之则可被原谅(“净”)。后二句是淫戒的別缘,包括比丘被怨逼行淫和比丘行淫时心生染乐,意思是若比丘被逼行淫,且行淫时心生染乐,则不可被原谅;若行淫时没生染乐心则可被原谅。同样,偷盗时想着被盗之物没有主人或想着是主人赠予,杀生时把被杀者视为木桩,这都属于犯戒別缘,性戒和遮戒都是一样的道理。宋代元照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对“随本”的解释沿用了景霄的注文,并把误译的“四大处”理解为“一切戒大要之处”[14](P170)。
对“法师语”的解释,景霄承袭了大觉的误解,认为道宣意指五百罗汉是造论之主,即造《善见律毗婆沙》之主。他说:“法师语者,即五百罗汉之言,今文中言云‘即论主也’一句。《钞》主指上诸罗汉,是造论之主故。诸罗汉本拟造论……若终一部,必虑文繁,所以商量,改为宗论。 ”[9](P58)元照也沿用这一误读[14](P169)。在中国古代,汉传佛教对印度早期佛教尤其是佛陀涅槃后一百年左右的佛教史的认识很模糊,这一方面跟印度原始佛教到阿育王(公元前3世纪)引进文字前的口传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佛教东渐汉地与此相隔几百年有关。景霄继续解释:“彼(指《善见律毗婆沙》)云,‘法师曰,律本已具’……言法师者,谓律师也,五百罗汉,解法之人,号法师也;曰者,论词也。”[9](P57)他的误读也与他如何理解《善见律毗婆沙》中的“法师曰”有关。“法师语”和“法师曰”都被他理解为五百罗汉之言。元照也认为:“法师语,先说本者,即上二本。广分别者,即论中解释之文,一一并云‘法师曰’是也,即论主一句,祖师助显,非本论文。 ”[14](P170)据元照之解,“法师曰”所引出的文字都不是《善见律毗婆沙》原语本所有,而是“祖师”添加的。通过对比巴利《善见律疏》和《善见律毗婆沙》可以发现,“法师曰”是《善见律毗婆沙》译者增译之语,在全文中出现260次左右,不见于巴利《善见律疏》中。但“法师曰”所引出内容大部分都能在巴利本中找到对应文句,拟根据所引出内容归类说明:第一,“法师曰”后引出“我当说”、“余自当知”等套语,共120处左右,例如:
《善见律毗婆沙》卷一:“法师曰:‘我今依次第说因缘’。 ”[3](P680)巴利《善见律疏》中对应语句:tatr’āyamanupubbikathā.[2](P8)(此处这是渐进的论述。)
《善见律毗婆沙》卷四:“法师曰:‘我今证一句,余自当知。 此是第二禅定品竟。 ’”[3](P701)巴利《善见律疏》中对应语句:sesa mvuttanayam evā ti.dutiyajjhānakathā nitthitā.[2](P150)(其余的也正是上述方式。第二禅的解说完毕。)
《善见律毗婆沙》卷六:“法师曰:‘若句义难解者,我今当说。 ’”[3](P715)巴利《善见律疏》对应语句:tatr’āyamanuttānapadavannanā.[2](P227)(此处是难懂句子的注解。)
第二,“法师曰”后直接引出律的释文,共130处左右,例如:
《善见律毗婆沙》卷八:“法师曰:‘若户可闭,若户不可闭?’答曰:‘树枝竹枝笄作,若如是为初,余者随作户扇。若扇下有臼,上有纵容,若转户扇者,应闭。 ’”[3](P726)巴利《善见律疏》对应语句:kīdisampana dvāramsamvaritabbam?kīdisamna sa mvaritabbam?rukkhapadara-velupadara-kilaja-pannādīnamyena kenaci kavātamkatvā hetthā udukkhaleupariuttarapāsakecapavesetvākata mparivattakadvāram eva samvaritabbam.[2](P281)(哪种门该闭上?哪种门不该闭上?门扇用树枝、竹枝、草席、叶子等之中任何一种材质做的,下方插入门臼,上方插入上楣,这样做成的转门该闭上。)
第三,“法师曰”引出的内容在巴利 《善见律疏》中无对应语句,不超过10处,例如,《善见律毗婆沙》卷四:“法师曰:‘此义甚广,我今略说’[3](P695)。 《善见律毗婆沙》卷五:“法师曰:‘我未解此义’。 ”[3](P706)《善见律毗婆沙》卷七:“法师曰:‘我不能尽解,次第律本汝自知。 ’”[3](P720)长井真琴认为,助译者僧猗误以为“法师曰”所引出的内容是主译者僧伽跋陀罗说的话,因此以“法师曰”标记下来[4](P110-117)。德国学者封辛伯指出,巴利三藏及其注释是在口头语基础上形成的[15](P22-25)。上述《善见律毗婆沙》诸例中的套语如“我当说”、“余自当知”等反映出,主译者僧伽跋陀罗同时担任了主讲人的角色,通过口耳相传把文本传授给助译者僧猗。僧猗把这些套语记录进正文中,甚至连“我未解此义”、“我不能尽解”这样的话语都融进译文中,反映出译经与讲经是同时进行的。后世的南山律师不了解《善见律毗婆沙》的译出过程,只能“断章取义”了。
景霄、元照对“意用”的解释都是意度三藏,没有提出其他见解。景霄还仿照“毗尼四法”总结出“《钞》家四法”:“仿彼《论》文四法。上虽依论所辨,如然未委《钞》家四法何者是也。今须略名,谓南山欲制疏文,解《四分律》,遂心口相询。若著述疏文,便须次第一一具释。其文繁广,与古何殊?今改为钞文,但宗他《四分》也。一、本者,谓《四分》一律,是造《钞》所宗之本也。二、随本者,谓律中释诸戒句义处有记中将四繁为随本者,恐不然也。三、法师语者,谓今师,有置两序及三十篇,次第辨解,释律文,明行事处,如五百罗汉分别流通也《继宗》将首《疏》或蒿《本》为法师语也。四、意用者,谓以意句三藏中,捈取相应之文,补此一宗之阙,令行事用足,免有滞疑之处也。 ”[9](P58)景霄的意思是,如果对《四分律》的词句逐一作注,则篇幅冗长,因此改为钞文⑥。 “《钞》家四法”以《四分律》为“本”,以《四分律》中解释戒条的语句为“随本”,以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含有总别两序,全书共三十篇)为“法师语”,以三藏为“意用”来补充宗派之不足。景霄的“《钞》家四法”确立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在南山律学传承中的祖师地位,强调道宣解释《四分律》的方法论源自《善见律毗婆沙》这一印度源头。与 “毗尼四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是,“《钞》家四法”尊道宣为祖,对各个部派和大乘经论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其核心是以 “意用”补“本”、“随本”、“法师语”之不足,法脉传承,使宗门之意更加完善。从景霄的注文可知,当时不少律师仿“毗尼四法”来构建自己的“《钞》家四法”说,有人以《四分律》的“四繁”为随本,从志律师的《行事钞继宗记》以智首律师的《四分律疏》或“蒿《本》”为“法师语”⑦。由此可见,唐宋之际南山律师不仅对“毗尼四法”涵义做出各种新解,还活学活用,据此构建出宗门之法。
三、结 语
“毗尼四法”这一术语从巴利《善见律疏》到《善见律毗婆沙》的演变,反映了从唯上座部独尊的严苛到不排斥其他部派的宽容的转变。而从《善见律毗婆沙》到后世的南山律疏,“毗尼四法”涵义中的上座部本义式微,律本不再被视为权威,律师“自我做主”的“意用”大大越过了“本”涵义的范畴,所受重视程度也远远高于“本”。“毗尼四法”被南山律师视为圭臬和化用成解释 《四分律》的方法,并据此创造出南山律学独家的“《钞》家四法”,是对《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山律学依“意用”不依部派(或言依律义不依部派)、依法脉不依原典的释律传统,充分反映出一个印度源头的上座部律学概念中国化的历程,体现了上座部律学与汉传律学的交流与融合。
注:
① 关于《善见律毗婆沙》与巴利《善见律疏》的关系,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讨论。具体参阅J.Takakusu,“Pāli Elements in Chinese Buddhism:A Translation of Buddhaghosa’s Samanta-pāsādikā,a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found in the Chinese Tripit.ak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96,pp.415-439.参阅长井真琴《善见律毗婆沙とサマンタバーサーデイカーの对照研究》,《根本佛典の研究》,东京:天地书房,1922年,第69-133页。水野弘元《善见律毗婆沙とサマンタパーサーディカー》(一),Bukkyō Kenkyū I 《仏教研究》,1937年,第77-100页;同作者《善见律毗婆沙とサマンタパーサーディカー》(二),Bukkyō Kenkyū II《仏教研究》,1938年,第111-139页;此二文均收入水野弘元《仏教文献研究》,春秋社,1996年,第85-142页。中译本见水野弘元著、许洋主译《佛教文献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03-169页。
② 大乘菩萨戒中有“通受(又称总受)”和“别受”的概念,但涵义和《善见律毗婆沙》不一样。据新罗僧义寂的《菩萨戒本疏》记载,总受是牒三聚戒总通受故,所牒三聚即是羯磨;别受是于三聚中别受摄律仪戒一门尽行相故。《菩萨戒本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册,第658页上栏。
③ 《四分律》、《十诵律》、《善见律毗婆沙》都记载了比丘与雌猕猴行淫犯戒之事。参阅《四分律》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第571页上栏;《十诵律》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册,第2页上栏;《善见律毗婆沙》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第715页中栏至下栏。
④定宾是四分律宗相部律师,著有《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参阅《卍新续藏》第42册,第41页上栏至中栏。
⑤ “开文”这一术语出自《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然则性戒文缓而义急,谓随诸重,并有开文,文虽是开,开实结犯,纵成持也。”参阅《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册,第2页上栏。《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三对“开文”有进一步解释:“并有开文者,谓戒戒之下,皆有通开别开。如颠犯心乱痛恼所缠,是通开。怨逼及睡眠,无所觉知是别,如盗戒开作无主想,煞戒开作杭木想,忘语开作非圣法想,及戏笑错悞等,戒戒各有别开,例此委知。云文虽是开者,纵也,谓律中虽有开文,然于开作事时,心与教不相应,不免放逸,故云开实结犯,设使成顺教无违,实当不易,故云纵成持也。”参阅《卍新续藏》第43册,第49页下栏。由此可见,“开文”的意思是指虽犯错但不犯戒的特殊情况。
⑥ 上引《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提到“释论”与“宗论”,根据景霄对“释论”和“宗论”的定义,释论的特征是“从始至末,次第解释”;宗论则不对解释对象进行详细注解,而是就某一宗旨进行疏释,删繁补阙。根据景霄的理解,《善见律毗婆沙》前六卷都是《四分律》条文的依次详解,“本是释论”;从第六卷的四波罗夷法至最后一卷,与《四分律》有诸多差异,是删繁补益、改作宗论的结果。此处他说“今改为钞文,但宗他《四分》,意指《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仿照《善见律毗婆沙》,也是以解释《四分律》为宗旨的宗论。”参阅拙文《〈善见律毗婆沙〉与〈四分律〉关系新探》,《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第117-122页。
⑦ 景霄总结出《四分律》有“四繁”:繁广、繁长、繁滥、繁恶,因此道宣要对《四分律》“删繁补阙”。参阅《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二,《卍新续藏》第43册,第26页中栏至下栏。《行事钞继宗记》仅在《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中存有题名,已佚。参阅《卍新续藏》第44册,第304页中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