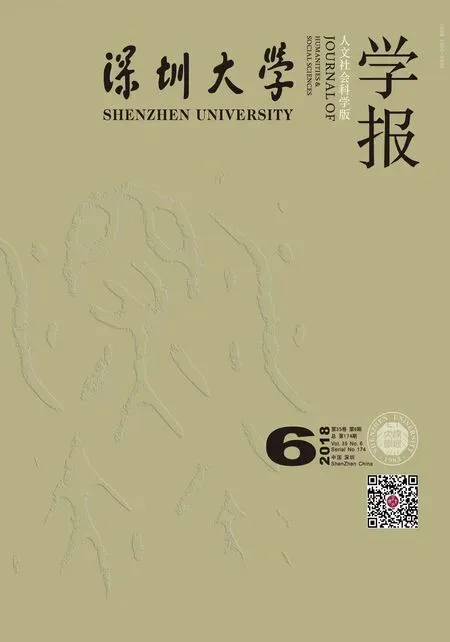“乡愁”的审美表达与“中国”历史流变的文学书写
杨吉华
(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乡愁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从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乡愁”首先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一种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在这个空间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的有序生活,成了乡愁者共同的精神家园。由此,形成了“乡愁”在时间维度上对过往生活的追忆与未来生活的期许双重诉求所触发的具有感伤意味的普遍情感。这些情感共同指向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对故园亲友同胞的思念,还是对旧时风景或故国山河的回忆,其实都是对自我存在安身立命的追寻,因此,“乡愁”不仅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只有在“乡愁”之中,共有的情感模式才能让乡愁者回归自己置身其中的民族生活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乡愁”里所蕴含的情感也就成为了维系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情感纽带之一。
中国文学母题中的“乡愁”,生动地传递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情状、生存图景及情感结构,也在美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形象塑造,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美学视角之一。而“中国”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在历史流动中生成的民族国家与文化概念。本文所谓的“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既不是按照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界限来划分的中国,也不是按照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变迁来划分的中国,而主要是立足于文学作品中“乡愁”的内在审美意蕴表达变化而勾勒出的“中国”。
一、古代中国“乡愁”:回望性淑世情怀坚守
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伦理封建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和聚族而居的地缘空间生活方式保证并维系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稳定性,“安土重迁”的思想与家国同构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将人们通过空间固定居所的生活而彼此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于是,聚族而居的固定村庄,那个被我们因为出生而称为“故乡”的地方,便成了保证农业文明下宗法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之一,这就使得那种以农村生活为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成为了人们对“故乡”最形象直观的认知。这种文化思想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自《诗经》以来就一直高扬着与“乡愁”相关的文学母题。
从《诗经·小雅·采薇》的反复咏叹,到屈原《九章·哀郢》的哀婉,再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比况,以及魏晋时期曹丕“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杂诗》其一)的叹息,还有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甫的《登高》等等,“故乡“始终是古代中国人们情感深处最深情的家园。在这里,“故乡”在时空上都表现出一种“过去”的属性,伴随而来的“乡愁”便更多是一种通过回忆过去的故乡生活和想象重构记忆中的故乡原貌而来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深刻情思,萦绕在离别故乡的异乡漂泊流浪旅程中,唤醒人们对故乡的强烈思念之情。正如叶君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乡愁的生成是由于一种外置视角使然,是离开之后的反观,也是一种精神的流连。”[1]
因此,古代中国的“乡愁”大都是在人们离开故土家园的空间流动生活中生发而来的。游子流客、戍边将士、贬谪文人、羁旅行人等成为“乡愁”的主要咏叹者。在异乡似曾相识的景色风物中,思归杜宇、落花飞絮、晓风细雨,一切都可以触动人们的思乡之情,如南宋蒋捷著名的《一剪梅》等,使古代中国的 “乡愁”在哀婉中带着无比诗意的美感。在离开故土家园的空间流动生活中,空间上的不断流动迁逝消解了人们对于固定家园居所带来的安全归属感所引发的现实人生流浪感,与新的空间中时间流逝引发的心理上无所归依的无根漂泊流浪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流浪感,导致人生无所归依的生存焦虑,使得中国古代的乡愁最终在情感指向上形成一种精神意识层面上的还乡渴望。在身体还乡与精神还乡的双重渴望中,故乡便成为了一个精神回望式的家园所在。如苏轼在《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中的乡愁表达:“霭霭青城云,娟娟峨嵋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2]在他乡途中反复诉说的故乡记忆,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实际空间场所中的故乡了,而是幻化为一种安顿疲惫生命、安抚心灵、弥补现实人生种种缺憾的虚拟精神家园。古代中国“乡愁”的回望性守望里所指向的双重返乡,在时空距离的思乡盼归想象与深情呼唤中,现实的故乡与想象的形而上精神故乡合二为一,诗化为安顿人们自我本真精神情感的终极归宿。
到了易代之际,由于承载自我存在的故乡故国生活的双重断裂,自我个人生活的断裂上升为一种社会层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的断裂,由此引发个体存在社会身份的断裂,在这种多重断裂中,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将置身家国同一宗法社会中的人们彻底抛向国土易主而归不得的深层故国哀思之中,“乡愁”便由单纯的故土家园之思扩大为一种江山易主的动乱流离中强烈而深层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对于具有修齐治平理想的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而言,“家国天下”早已成为他们道德理想的一部分了,“有家而有国,次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也如身家连称。有如民族,有了家便成族,族与族相处,便成一大群体,称之曰民族。此亦由人文化成。”[3]因此,古代中国易代之际的“乡愁”,常常伴随着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断层感、身世漂泊感和人生世事如梦幻泡影的深层喟叹。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从来就不乏反映易代之际失国怀乡的大量优秀作品,但是,此时“乡愁”里对故国家园的回忆与守望,已经是一个身体无法返乡而只能是精神回望式的返乡了,是易代之际的人们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时期对自我所属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理想的一种精神抗争意识。无论是亡国之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的哀怨,还是臣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的悲哀,都潜藏着一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无奈与落寞。这种易代之际反复吟咏的乡愁,在无限哀婉的感伤中试图弥合时空变迁与文化断裂造成的巨大差异,努力在想象中建构精神的家园以弥合现实的缺憾,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再度与过去连接,沟通现在,满足未来自我存在的诉求,“乡愁”于是成为了古代中国在儒家文化传统精神濡染下的淑世情怀象征,也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坚守自我文化信念的重要方式。
因此,古代中国的“乡愁”,首先以在拥有对地理空间上的故土家园的回望性坚守情怀基础上,融入了存在个体对血缘亲情及宗法家族理想的情感因素及自我生命理想的追求,具有了精神层面的意义;同时又在家国一体的文化结构中,自然地与故国、文化传统等连为一体,赋予易代之际的“乡愁”以更宽层面的家国情结和淑世情怀,从而使古代中国的 “乡愁”成为一个包蕴个体生命情感、族群历史、理想信念与文化秩序重建等多重意义的情感意象,传递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生活图景,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乡愁”具有了充沛的文化意蕴,激发着中华民族情感深处对故土家园最为深情的眷恋。
二、近代中国“乡愁”:批判性自我启蒙探索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乡愁”,是在回望性淑世情怀坚守中的一首忧伤而美丽的抒情挽歌,无论何时,都能给我们“诗人怀乡”式的精神抚慰的话,那么,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百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屈辱历史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震荡乃至崩溃,近代中国的“乡愁”与古代中国那种忧伤美丽的“乡愁”相比较而言,则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审美内涵,它也见证了中国在这一段屈辱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与勇敢抗争。
在古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以对文明礼仪制度的拥有而具有政治上绝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如同美国学者列文森说的那样,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不是某一个“国家”,天下中最高文化形态就是中国文化[4]。“也许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次以来,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并不是很大,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明神宗万历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进入中国南方的肇庆并且在那里定居,他们用汉文印刷了《天主教实录》、《天主实义》等书,翻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书,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稍后的金尼阁又携带七千西书入中国,这才标志着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全面进入中国。两三百年后,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并在19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随着坚船利炮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才真正地深入中国,并在19世纪末,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瓦解。”[5]这就是1840年以来所谓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国文化与西方他者文化在战争与不平等的商贸交往中相遇了,结果却是在屈辱的民族独立抗争中,从最早“师夷长技以致夷”的技术学习到政治上君主立宪制的改革努力,乃至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过程中,逐渐瓦解了古代中国本土文化的至尊地位,承载自我个体存在的故乡与中国,在与西方他者文化的对比下,显得彷徨而无所适从。在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界”之中进行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形象塑造的中国,开启了近代历史上面向自我的批判性启蒙探索。
曾经以“居天下之中”和先进文明而存在的古代中国的荣光不再,“中国”的形象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成为了近代启蒙探索者又爱又恨的所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故乡,走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包括日本)文化思想,这批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民族解放、独立自强的理想,思考中国社会该何去何从。当他们满怀深情地回望故乡时,中国抵御外来入侵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变迁形成的城乡生活差异,在中国域外西方(包括日本)他者文化对比刺激下,使得这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学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乡愁”母题里,也融入了此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对国家转向、社会性质发展的新思考,表现出对自我本土传统文化较强的内省性批判色彩。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以鲁迅为突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对民族自我发现的批判性反思中,将批判触角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相对愚昧落后的心理及其对人精神状态的扭曲,反映到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乡愁”,就不再只是对故乡充满乡土气息过往生活的美好追忆,而是在一种具有无限怜悯的心痛之中发现记忆故乡与现实故乡不仅是自然风物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乡愁”里,有着对以乡土村庄为载体的中国“国民性”的发现,并且这种发现是对民族文化结构中制约 “人”的精神生活规约的一种否定,如鲁迅的《故乡》,包括《祝福》、《少年闰土》、萧红的《呼兰河传》、蹇先艾的《水葬》等。在他们的“乡愁”里,“故乡”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主要是指向过去已经完成的时间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故乡”已经是过去时间里一个相对陈旧落后、凋零蔽塞的所在,尤其是国民劣根性最为顽固的滋生地所在,是落后愚昧旧中国的一个隐性象征,潜含着以鲁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批判性启蒙探索梦想。当然,在他们对故乡的追忆与观望中,在直面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自省中,批判与眷恋的复杂情感同时存在,也有着对故乡美好回忆的眷恋。换言之,近代中国的“乡愁”,是在乡土中国农业文明受到西方他者文明的巨大冲击历史背景下,对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沉重感伤和被“乡下人”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引起的沉重悲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将此类小说称为“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在乡土中国传统生活及文化结构受到极大冲击的过程中,行将消逝的古代中国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在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中,成为了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追忆式缅怀的精神故乡,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等。尤其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都是一派和谐宁静,充满温情,所写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构筑出了一个既纯净又完美,飘荡着田园牧歌的艺术世界。”[6]在他们这里,对故乡近乎乌托邦式审美幻化而来的乡愁,亦是对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种坚守。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是对古代中国传统还乡意识的一种回归。当然,作为在传统乡土中国成长起来的“乡下人”,沈从文等人也体验到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民族国家对自我传统进行批评性反思启蒙的阵痛,又深刻感受到了都市文明对自我个体心灵的强烈压迫紧张。在他的湘西故乡世界里,除了田园牧歌般的世外桃源外,或多或少地呈现了湘西世界里相对愚昧落后与野蛮的一面,也揭示了世事的沧桑和淳朴人民命运的悲凉。这批知识分子从相对偏远闭塞的乡村走向都市,民族国家的命运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他们又对承载自我存在的乡土中国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有着无限的热爱之情。在他们的精神漂泊中,故乡成为与都市文明相对的存在,象征的是生命自在自为的美好童年时代和具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光。渴望返乡而不曾返乡的实际,使得他们在精神还乡的白日梦创作过程中,更多转而眷恋那已经经过自我理想化建构的故土家园,在“乡愁”的抒情中,转而向传统文化中温情脉脉的乡土生活和人伦道德皈依中找到心灵的栖居之所,从而将故乡建构为具有浓郁世外桃源般气质的灵魂栖息地。
因此,近代中国的“乡愁”,伴随着中华民族近百年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努力,具有了一种文化救赎的力量。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乡愁”,在“中国”存在的内在危机中,将个体的生存体验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出路联系起来,赋予“乡愁”以一种文化启蒙的建构力量;另一方面,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田园牧歌式的“乡愁”抒怀中,对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危机之间的分裂进行了想象性的美学弥合,使“乡愁”对自我具有了精神拯救的力量。随着中国经历近百年屈辱斗争获得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及随之而来新中国建设历史序幕的拉开,具有批判性自我启蒙探索意义的近代中国“乡愁”,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与“现代性”相对的情感方式而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全新的生活图景。
三、现代中国“乡愁”:“异乡人”的精神漂泊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域内城镇化的急剧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并努力逐步扎根城市,使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出国热”,使一大批怀揣着现代梦的中国人纷纷涌向海外,成为异国他乡的移民群,“乡愁”注入了更多在社会改革和空间漂泊中的“异乡人”对自我社会身份转移的探讨与反思,隐含着现代中国这些“异乡人”的生存困惑和思想文化困惑。
就中国域内而言,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非城市户籍农民工、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漂一族”成为了新的“城市异乡者”。这些城市异乡者从一开始就踏上了一条现代化的漂泊旅途,他们能够在生活方式上逐步接受并融入置身其中的异乡城市,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精神上都能较好地安家其中。对于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非城市户籍农民工而言,强大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城市生活的巨大反差与冲突之间的生活体验,使他们在进入城市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成为了灵魂游离于城市之外的漂泊者。如林坚《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盛可以的《北妹》等打工文学,直面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尤其是孙惠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对“城市异乡者”的“乡愁”表达颇具代表性。这些在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交替中存在的“异乡人”是一群处境较为尴尬的现代人。对于城市而言,他们是寄人篱下的异乡人;对于自己的故乡而言,他们又是一群回不去的出离者。在故乡农耕文明与城市工业文明的共置对比中,“乡愁”主要在他们走出故乡、暂时告别城市工地、返回故乡、再次返回城市的空间移动循环中弥散开来,“乡愁”里的时间维度较多让位于空间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乡愁”成为了一种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所谓“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情感表达,体现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异乡人在“离去”与“归来”的空间置换中的无奈与感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面对城市对乡村的扩张,这些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中的异乡人之“乡愁”意味,还传递出了一种对传统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乡土世界之失落的深沉哀痛。如贾平凹的《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和《秦腔》等作品,都表现了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面临的危机,于是,“乡愁”也成了城市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与传统伦理生活一定程度上的沦陷之感伤表达。
对于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漂一族”而言,日益繁忙的城市生活带来的自我 “空心化”精神困境,常常使他们具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感。在这些城市异乡者的自我身份惆怅中,对城市工业化的疏离与记忆中故土乡情的怀念和对自我身份的塑造与重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乡愁”的重要内容。张炜在他的《古船》和《柏慧》等作品中,都较好地反映了这种现代中国城市异乡人的精神漂泊困境。在《柏慧》中,张炜还从现代历史进程中,描绘了“我”从学校毕业,到03所,再到杂志社……直到逃到海边葡萄园的经历,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现代人在面对中国现代城市工业化进程浪潮中的精神漂泊传记。他似乎在试图提醒人们,面对空间置换下的现代人所无法避免的生存焦虑,只有从物欲的洪流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获得精神上的归宿。
就中国域外而言,那些漂泊异国他乡的海外移民者的“乡愁”,则是一种在他者文化视域下对自我精神家园和文化身份定位进行重新建构的文化乡愁之抒写与表达。在“香蕉人”的尴尬处境中,现代中国的海外移民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怀念和追忆自己的故乡与祖国。而且,这种怀念与追忆不再是对故乡、祖国记忆的重组,更是一种与对自我身在异国他乡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相关的审美性形象建构过程。因此,在他们的乡愁里,有着较为浓郁的中国情结和异乡人的苦闷感伤。
对于移民群来说,他们既想尽量融入异域生活,但又无法彻底截断中国情怀。中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始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正如苏炜说的那样:“我的小说里面有一种 ‘过去情结’。……那里面的人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过去。这种过去情结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情结,是一种群体的重负。”[7]去国离乡之初,他们实际很难真正融入到异国文明之中,80年代赴美作家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便典型地表现了在中西两种文化夹缝中的 “边缘人”生存状态,他们既没有异国中的存在感,也无法失掉“中国”的自己,强烈的客居之感使“乡愁”成了海外移民群体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如在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中,当她告别上海真正踏上美国之路的时候,她痛心地说道:“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8](P557)她也依然满怀深情地说道:“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 ”[8](P560)在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那里,在其《傅家的儿女们》、《友谊》、《江巧玲》、《寻》等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中餐馆和中国礼品店,便是她始终无法割舍的中国情结象征,也是她在文学世界中寄托自我“乡愁”的一种情感符号。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海外移民而言,中餐馆与中国礼品店所承载和象征的故国文化与故土乡情,使他们得以在精神还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存在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因此,在中餐馆与中国礼品店的独特空间中,他们被压抑的思乡之情和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自我 “失根”状态的漂泊苦闷得以充分释放和抚慰。又如在严歌苓这里,《大陆妹》中大陆妹在烦闷时总唱山西民歌和陕西民歌这些充满中国意味的元素存在,也表达了海外移民不同阶层的文化“乡愁”。严歌苓也曾努力想要打破异质文化带来的文化乡愁情结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而上升到一种对超越种族、超越国别的共同人性的探究上来。如在《少女小渔》中便表现出了对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国界与肤色的善良人性给予的美好期许;《海那边》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与细腻描写;《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里对跨文化爱情的思考;《血液的行为》里对不同国度现代人异化命运的关注等,都表现出了对普遍人性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等,说明象严歌苓这样的海外移民群中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愁”的审美表达,开始逐步突破了早期移民群在漂泊感伤中的文化隔膜、怀乡与寻根模式,“乡愁”具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既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蕴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世界性视野。
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坚持用汉语写作来表达移民者“乡愁”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存在的明证,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同表达。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更多来自北上广大城市里那些相对拥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大量加入海外移民群,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世界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许多海外移民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奋斗后,也能够在异国他乡拥有相对优裕的生活,甚至跻身于异国中产阶级,使得这种主要由空间迁移带来的“乡愁”,开始逐渐淡化了地域性差异而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全球化”特征,“乡愁”的审美表达逐渐聚焦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认同。在东西文化的再度相遇中,在经历了80年代以来文化失语和文化焦虑的挣扎之后,经历30余年改革开放建成的现代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的海外移民对于中国文化的再度认识带来的文化自信,不但表达了他们在异国他乡对中国的亲近感,也将一个再度崛起的中国形象推向了世界,“乡愁”成了重塑中国形象的重要表达方式。在全球化不断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过程中,中国的“乡愁”审美意蕴又再一次发生了新的时代变化,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深情回望中,表现出较强的建构性文化传统生产特点。
四、当代中国“乡愁”:建构性文化传统生产
当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现代性”开始逐步全面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时,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多重文化影响,也从一个新的层面激发了当代中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乡愁”。
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地理学和空间学意义上的传统“故乡”不再,人们通过出生地所在而建立的“故乡”概念出现了时空与身心的双重分离状态。许多人离开出生地的情形与古代中国安土重迁背景下的离乡情形不同,是对一种不同于出生地的全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追求,甚至是在一种“生活在远方”的虚构性审美想象驱使下,主动离开出生地而到达一个新地方的离乡行为,表现出了一种较为积极的主动离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方面是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使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快节奏化带来了身心的巨大压力与疲惫;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张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本是蕴含了独特地域个性气质与历史文脉的地域文化景观不断被蚕食,中国本土的生活传统和历史记忆,包括个人成长存在的记忆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下,“故乡”从实际存在的出生地扩大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多元并置对话场域所在,存在者在其中得以存在并显现。在这个精神场域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同在,城市与乡村同在、传统与现代同在,传统意义上较多由于空间迁移诱发的“乡愁”,转变为一种在无可避免的“现代性”包围中,由于存在个体类似于浮士德式的自我追求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孤独、挫折、矛盾与困惑而引发的精神层面上无家可归的“乡愁”,伴随着对自我存在主体的美学性内在反思,再次凸显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
于是,“乡愁”便以对“现代性”一定程度的拒斥与反叛而表现出了一种浓郁的怀旧情结,成为存在主体在现代性中实现自我建构的归宿和落脚点。正如罗伯森所说,怀旧“是现代化的一种心理后果,而且本身便是促使一个人产生对自己在社会中和最终在宇宙中曾有过的某种在家状态的……'的发生器。”[9]在这种怀旧情绪中,“故乡”与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感受和情感道德密切相联,“乡愁”指向了一个值得存在主体追忆与怀念的,且带有一定想象性成分的传统中国那业已逝去的田园牧歌式慢节奏生活方式和人伦道德生活的追忆与缅怀。存在主体通过怀旧实现了与自我存在相关的过去生活的深度回忆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家感,使“乡愁”成为现代性处境包围中的自我个体进行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因此,当代中国的“乡愁”便不仅仅只是乡愁者的自我情感抒发了,也是凸显现代性自我在场的文化建构方式之一。在怀旧的建构性审美力量中,“乡愁”最终上升为一种对理想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的暗喻,寄寓着普通大众对自我当下生存处境的反思与建构努力。
此外,在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中,面对传统生活一定程度的断裂和中国梦的起航,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概念,也正在逐渐消弭地域空间的界限而扩大化为一种具有“中国”气质的生活样态和回归中华民族本土性文化建构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回到民族生活内部,一方面以敬畏之心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意义,比如天人合一生活方式对于当下中国构建出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还要在努力突破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重建中国话语、再塑中国的世界形象,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在文化自信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发展。这既是当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化中的中国坚定民族意识,守护民族文化认同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因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所激发的新时代“乡愁”,孕育着一种对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美好憧憬与期待力量,传统“乡愁”里的感伤意味淡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再出发的理性思考,“乡愁”成为新时代演绎中国故事、讲述中国生活的有效美学视角之一,联结着“中国”的历史传统与被想象、被建构的未来“中国”,承担着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建构性生产责任,继续书写着新时代中国波澜壮阔历史流变的立体情境。
因此,在“乡愁”的审美表达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得以生动跃现,也使我们能够从“乡愁”出发,再次返回中华民族生活之流,近亲本源所在,“乡愁”也因此始终是中国文学中一个蕴含着丰富文化意义的最为重要的母题而具有了无限的诗意和生命力,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