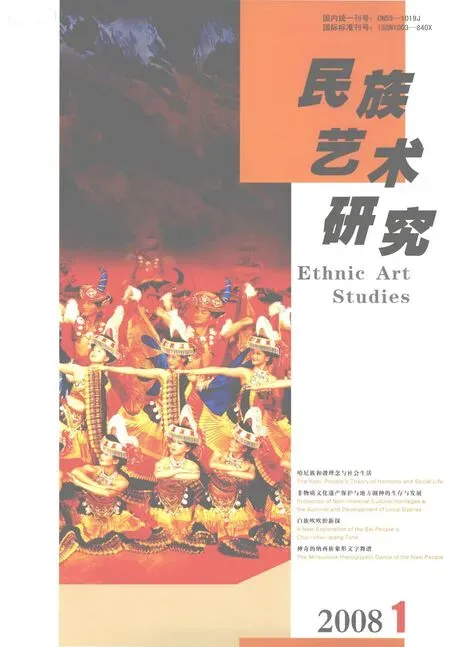何谓中国故事: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观念辨析
杨乘虎,高 云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情状,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良好国家形象、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战略需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引领力的时代需要,更是彰显大国文化责任、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际话语权、重构世界文化版图、提升文化引领力的国家使命。
电影是健康娱乐、沟通情感、传播文明的主要渠道和重要艺术载体之一。纵观全球,各国无不精心谋划,发挥电影独特的媒介传播力、艺术感染力、文化向心力,以达凝聚民众力量、增进文化认同、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之目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国电影产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寻找到战略对接点,并探索出中国电影艺术与文化产业国际传播的路径、模式,是中国电影业义不容辞的国家使命与文化责任。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关乎生产,也关乎传播,贯穿于内容层面的电影故事架构、对象层面的电影受众确认、传播层面的电影叙事艺术等环节。归根结底,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与首要命题,需要在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全球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基础上,明晰“何谓中国故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起源与实践起点。
一、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其国家形象建构的学理路径
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迅猛发展前所未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全国电影总票房、国产影片票房收入、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电影市场银幕数量、观影人次,均呈现出迅猛的增长趋势。截至2017年底,中国电影银幕数量超过4.5万块,跃居世界第一,“近800部电影年产量已经高居世界各国前列;突破500亿人民币全年票房,影院市场稳居全球第二;中国银幕总量和电影观众人次已经超过北美市场,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尹鸿:《中国电影如何“由大到强”》,《人民日报》2017年12月8日。显然,无论是行业体量与规模、还是服务人口与从业人数,中国都堪称全球第一电影大国(参见图1);然而,就总体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而言,中国还不能称之为电影强国,距离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使命达成,中国电影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图1)*数据来源:综合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公开数据以及新华社相关报道。
(一)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尽管近七年来,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份额保持在一个微量增幅的平稳状态,但是与美国等电影强国相比,中国电影在广泛参与并与发达国家展开深度竞争的能力还比较薄弱,缺少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引领潮流的电影文化制高点,缺乏影响世界和领航全球的电影机构、内容精品和模式,中国电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依然处于文化贸易的逆差格局中。
比如: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中仍属冷门与边缘,引起环宇回响与共鸣的代表作屈指可数。在华语电影北美票房榜单上,位列前茅的依然是昔日由李安、张艺谋执导或由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主演的作品,这些作品自上映之日至今已十年有余;北美票房过亿(美元)的华语电影只有《卧虎藏龙》一部。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并未能广泛传播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又如,中国电影海外市场接纳与认同度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近几年在国内电影市场中斩获口碑与票房佳绩的国产电影,在海外屡遭滑铁卢,例如《人在囧途之泰囧》《捉妖记》《滚蛋吧!肿瘤君》等,海外观众并不买账;尤其是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受挫的《战狼2》,虽然国内创造了56亿元人民币票房的历史纪录,但是海外票房收入仅为800万美元。另据一项海外受众对他国电影偏好程度调研的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中国电影的偏好值仅为2.66%,低于缅甸、老挝、阿富汗、巴基斯坦、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电影。*黄会林,李雅琪,马琛等:《中国电影在周边国家的传播现状与文化形象——2016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中国电影的海内外接纳度、认同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再如,中国电影塑造的国家形象仍然较为片面、单一、单薄。武侠片与动作片是海外受众最为偏爱的“功夫电影”,这一电影类型格局尚未得到有效突破,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缺乏文化的内涵与现实的呈现。而且,海外受众“对影片制作的印象始终高于对影片价值的印象”*黄会林,李雅琪,马琛等:《中国电影在周边国家的传播现状与文化形象——2016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这一问题更令人深思,《寻龙诀》主题立意不够明晰,《老炮儿》被称为中国版《教父》,《港囧》《夏洛特烦恼》编织着“直男癌”人夫的初恋梦。这样的故事能否呈现当下真实的中国现状,能否表达中国式情感,能否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制作水准日益提升的中国电影为何难以向世界生动有效地传达中国价值、中国精神?
上述问题的积重,反映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价值观念的割裂与分冶,基于人类基本取向的价值体系构建在中国电影中表现得不平衡与不充分。中国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既是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的呈现与塑造,也必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致力于传播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而实现中国故事价值内涵充实与艺术表达能力的提升,需要探索国家故事的学理认知框架,锻造具备共通性的叙事范式,凸显中国电影的艺术品质与文化品格。
(二)中国故事与国家形象研究的学理路径
梳理国家形象的学术发生与学理旨趣,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肇始与流变。其一是形象学研究的产生。19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从文学的角度,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比较文学由此发端。其二为后殖民理论的影响。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文化角度提出了“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其进而成为后殖民理论的滥觞。其三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兴起。有意味的是,三种学术思想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进入中国,引发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等命题的关注,探讨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生成和演变,探析作为西方现代性“他者”的中国形象的潜在文化结构。
在上述三条学术路径的交互作用下,电影与国家形象、国家故事的学术联系日益凸显。一种观念认为,“电影”与“中国”的概念拆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电影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探讨。一方面是有利于中国电影从容应对家国叙事模式的瓦解;另一方面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隐化家国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淡化跨文化传播的色彩,突显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意味。“由于中国概念的复杂内涵及中国电影的模糊边界,固定、连贯且一致的国族概念产生有赖于故事和图像的建构和详述,因为它被叙述,‘国族’概念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Chris Berry, Marry Farquhar. 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P6原文:“producing this effect of fixity, coherence, and unity depends up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citation of stories and images——the nation exists to some extent because it is narrated”.由是,电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从对“国族电影”(National Cinema)的研究转向对“国家与电影”(Nation and Cinema)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则更关注“跨国电影”(Transnational Cinema)和“跨地性”(Translocality)等概念,探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读解的可能。对比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这一命题的学术考察,依然未能摆脱西方视阈中心下的他者“东方”参照,也就难免更多地将中国电影作为论据来使用。
国内学者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论关注,体现出鲜明的家国情怀与国家立场,对于中国文化主体统一性的高度认同,更倾向于从综合而非对立割裂的方式研究,认同中国作为“一个多元复杂共同体,不能仅仅由国家、族群或文化,各单一角度讨论,却是看作三者的混合体”;*许倬云:《说中——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卷首语第1页。更主张基于国家需要的学术自觉,将一般意义上的电影传播力提升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从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旨在通过研究中国电影如何“指涉人的精神世界,包括影视对自然、社会、历史及人性等所揭示和表达出的观察、体验与思考等”,*胡智锋,周建新:《中国影视行业如何形成世界级竞争力》,《人民论坛》2015年第19期。形成艺术的原创力、空间的传播力、产业的竞争力、思想的影响力、价值的引领力。
但是,相对宏观的战略构想与较为中观的路径设计,都需要微观层面的学理构建与支撑,解决关于中国故事和国家形象等基本命题、核心概念的理论辨析。比如,对何谓中国故事的元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
国家故事是一种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国家形象塑造,国家故事的普遍性是指国家故事对于本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性,体现为国家故事的对内概括度;而特殊性则是指一国之故事与众国之不同的特殊性,即国家故事的对外区分度。对内与对外,概括度与区分度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电影所塑造与呈现的中国形象,“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品牌、中国文化符号或中国代言者等是指艺术品的符号表意系统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及其可感形式。”*王一川等著:《中国故事的文化软实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这种包含了积极国家形象的中国故事,并非单一的扁平构成,包含着国家面貌、国家气质和国家价值三个层次。国家面貌集中体现为“面孔展示”和“身体表演”,国家气质集中体现在“时间背景”与“地域情境”中,国家价值有着“价值底线”与“价值空间”的开拓度量。
如果说,国家面貌乃是一国之静态之形,国家气质乃是一国动态之状,那么,国家价值则是一国内在之魂,三者紧密相关、交相辉映,共同塑造“国家形象”,并形成中国故事塑造的国家形象三大外延——特色性国家形象、积极性国家形象与共享性国家形象。特色性国家形象识别度高,由外而内,从面貌层面至价值层面均有所体现;积极性国家形象倾向性强,具备在气质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流动性;共享性国家形象影响接纳度最为关键,主要居于需要价值层面的核心。三层内涵与三大外延的匹配对位,共同支撑起电影讲述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的三个传播向度与目标:特色传播、积极传播、有效传播。
二、中国面貌:面孔展示与身体表演的文化意涵
“面孔展示”和“身体表演”是电影故事的直观表达,也是中国故事的感性显现。“面孔展示”是指演员与角色的静态之状,肤色与服饰是面孔展示的核心要素;“身体表演”是指演员与角色的动态之状,性别与动作是确立身体表演风格的关键元素。
(一)面孔展示的文化身份
演员与角色的肤色与服饰是电影指涉国家形象最为直白的体现,服饰表征着“我者”文化圈内部的身份之隔,肤色关乎“我者”与“他者”文化圈之间的种族之别。就服饰表征而言,一方面,唐装、文人长衫、女性旗袍、皇帝龙袍、中山装、解放军军装等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族群特色性服饰,已然成为电影故事中具有标志性的中国符号,明确着故事人物的基本国别属性。另一方面,人物服饰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属性,更为故事中人物文化圈层的类型划分奠定了基调。然而,当代中国电影人物服饰的表征愈加浮夸,其文化属性日益模糊、淡化,甚至异邦化。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邀请了设计大师劳伦斯·许进行服饰设计,其奇装异服杂糅了多种元素、莫名文化内涵,甚至美感全无,可谓是一场视觉灾难,观众纷纷吐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虽然博得赞誉,但是故事人物湫的服装造型,不免让观众联想到日本动漫的人物形象;《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大反派混沌的服饰,同样散发着鲜明的日系风格。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制作,人物角色的服饰、妆容、甚至建筑风格,均不同程度地日系化、日源化,令人警醒中国电影在国族服饰表征、特色造型表征方面文化话语权的迷失。
随着中国电影与全球电影的合作与交流的日益深入与广泛,与中国主题相关的国际肤色面孔展示渐成潮流。一方面是国际面孔在中国电影中的符号化存在,热衷于邀请外国演员参演。一如中国面孔大多游离于外国电影故事的圆心之外,中国电影鲜有对异国形象的精心打造,少有对于白色皮肤之下他者文化内涵的展现与探究。作为国际视野的符号载体,外国面孔出现在中国电影的效用主要是传递出世界对于中国的主动示好。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面孔在国际电影中的假性存在,或者是跨肤色扮演。类似英国演员克里斯托弗·李、瑞典裔白人欧兰德等人塑造的傅满洲、陈查理等风靡于西方世界,实际却是有悖于中国文化现实华人形象的,是满足西方想象的中国面孔假性存在。而章子怡、巩俐在《艺伎回忆录》扮演日本艺伎小百合和初桃,周迅在《云图》中所塑造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子形象,则是中国面孔的跨肤色扮演,遵循西方标准塑造的“双重黄脸”*[美]张英进,[澳]胡敏娜:《华语电影明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角色面孔,隐含着对华人演员跨种族表演的讽刺性意味。
(二)身体表演的文化意味
与面孔与服饰的视觉识别形成呼应的,是身体表演传递的文化意味。身体表演是电影人物讲述故事、表达感情、传递思想的重要载体,演员与角色的举手投足、行为动作,无不散发着某一国家与文化的风格气质:如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所塑造的“神探夏洛克”散发着英国的傲气、禁欲与理性;蜘蛛侠、超人、宇航员灵活的身体动作与自如的器械操控,呈现着美国的自信力与掌控欲;在柳时镇(《太阳的后裔》)、千颂伊(《来自星星的你》)、Sunny(《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酒后略显放纵而又不至于越矩的节制中,可见韩国人在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谨慎抉择。“非语言传播是日常传播接触和身份展示不可或缺的特征。为了培养一种特定的印象,我们常常有意识地试图控制我们所发出的非语言信息符号。”*安尼·希尔,詹姆斯·沃森,,马克·乔伊斯等著:《人际传播关键主题:文化、身份与表演》,刘蒙之,景琦译,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27页。电影身体表演包括但不限于演员表演,亦包含电影角色本身的身体化呈现,是由演员与角色共同完成的具有文化意味的身体展演。
在身体表演中,性别因素直接关乎国家面貌的整体风格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气场较量,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故事讲述中尤为重要,因为性别差异暗含权力隐喻,女性主义关乎文化解放。20世纪西方电影中的中国女性角色大多作为西方男性的热情仰慕者存在。从《红灯笼》《海逝》到《苏丝黄的世界》(1960)、《大班》(1986)等电影,塑造了一批向西方男性投怀送抱,或惨遭抛弃或被西方文化驯化的中国女性形象。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喜福会》(1993)《花木兰》(1998)等电影作品里,中国女性形象才得到更新与提升,如《卧虎藏龙》收获的国际赞誉,说明西方世界对以玉娇龙为代表的具有反抗意识的中国女性形象的认可。相比之下,近些年中国电影中虽然出现了抢眼的高票房产品,“鲜花”与“鲜肉”为代表的当红颜值明星如日中天,但是以女性意识作为第一主体的作品依然寥若晨星;红极一时的“小妞电影”并不具备切实的女性主义价值,其夸饰的身体叙事洋溢着时尚气息,充满消费趣味,缺乏文化意味。曾经,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真切探寻与建构中国女性形象,虽未曾抵达人性解放的艺术启蒙与精神自由,却真实地抗争、觉醒过,即使遭遇毁灭。如今,性别意识中的自觉与自信在电视剧中延展出“大女主”的人物系列,但是在中国电影中却依然散落着偏狭、单薄、空洞的女性形象。《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需要约翰·米勒的庇佑,《战狼2》中中国女性形象虚置与缺席,《妖猫传》中女性形象被架空为浮艳下无从反抗的悲情符码,还有《芳华》中女性身体美好展示与时代精神扭曲的错位……反观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巧妙借助女摔跤手的成长故事,隐喻印度女性解放与文化转型理想与现实。如此纷纷,需要反思,中国电影身体叙事为何滞留于性别的基础维度?如何方能充分实践其启示价值及文化意义?
如果将视野再拓宽到历史维度,不难发现,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演员与角色的身体展演勾画出一条从禁锢到夸张的序列行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表演或深受传统社会伦理的约束,含蓄委婉,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恬退隐忍,尽显沧桑之态。从第一代电影导演到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早期作品中,肢体动作的“禁锢与收敛”之态都清晰可见,也不乏“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之风范。自20世纪末始,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表演开始逐渐趋于夸张姿态,于是,《滚蛋吧,肿瘤君!》《夏洛特烦恼》《港囧》《捉妖记》《小时代》《美人鱼》《羞羞的铁拳》等电影中姿态夸张的身体表演,震颤着银幕。恰如《妖猫传》的观众戏称,白居易与空海必是当日各自朋友圈记步第一名;人物故作洒脱的姿态与看似神秘的微笑缺乏切实的支撑,白居易与空海步履匆匆的身体表演与形式浩大、内容浮夸的文化展演形成了空荡荡的文化疏离场域。在浮夸而缺乏实质意义的肢体动作展演中,中华传统文化及当代文化的断裂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中国气质:地域情境与中国历史文化的体现
中国气质是中国故事的内蕴外化,也是国家形象氤之氲之的风格调性,气韵生动、风格独具,在电影通过故事构建国家形象的流程中,中国气质主要体现为地域情境与不同时间背景中中国历史文化的体现。
(一)地域情境中的文化空间
地域是电影讲述国家故事的情境所在,也是营造国家气质的起点。香港、上海等地的城市景观,川蜀之地、沙漠边疆的自然风光,历来是外国导演钟爱的中国取景地,中国地域空间的代表。此类外国电影终究只能抵达中国地域景观的表层,不能充分、或许也根本无意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比如《功夫熊猫》将中国的自然景观、文化符号模仿得惟妙惟肖,却终究不能由表及里、深入展现中国的深层文化基因。
与世界电影固化浅表选取中国地域不同,中国电影对于本土地域的情境编设,经历了由泛化到分化,再到异化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开始之前,中国电影所呈现的地域情境是泛化的,区域性特征弱化而集合性特征鲜明,地域情境具有较为统一的中国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电影故事中的地域情境出现分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地域精神文化差异日益明显,中国的文化地图开始趋于破碎,城市故事应运而生,快速成为主流。第五代导演试图采用“寓言式”的叙事方式,将地域文化碎片糅合为统一整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地域文化图景的完整性。这一努力并未持续很久,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地域在电影中异化为两种地域情境形态:奇异性地域与多地性(Polylocality)地域。
奇异性地域是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地域形态,取景空间追求反现实的特殊性及虚构性,故事讲述在悬浮式的叙事情境中展开,通常采用架空与虚化时间背景或者虚设区域边界两种方式实现。架空型奇异性地域集中存在于魔幻电影中,如《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美人鱼》《寻龙诀》等;反之,边界型奇异性地域恰恰存乎现实题材电影中。《老炮儿》《芳华》等电影的故事情境是“界限分明”的:前者在虚设的胡同情境中,展现了不复存在的老炮儿文化;后者以文工团为“边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故事圈定了怀旧的叙事情境,与整体的时代背景有关联亦有割裂。
多地性地域集中体现为第六代导演及其后来者构建的边缘化城乡空间。“多地性承认繁多不一的地点,因此包含将这些地点连接起来的跨地性。”*张英进:《全球化的中国的电影与多地性》,引自《多元中国:电影与文化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在贾樟柯、王小帅等人的电影故事中,存在典型的多地性地域,他们试图在奉节、汾阳等边缘化地域中嫁接庞大的历史背景以及庞杂的时代文化。然而地域文化图景愈加分裂的现实,导致他们难以在某一具体而微小的地域情境中实现跨地性叙事,表述完整的中国情状。其原因,既有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现实进程因素,也有创作主体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刻意选择边缘的文化身份因素。从多地性到跨地性的情境转变,明确当下中国地域情境的精神内核显然是极为重要的。
电影文本内地域空间的异化并非中国独有之现实,城市空间异化可谓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欧美电影在面临地域异化的问题时,也会选择以奇异型特殊地域的创建来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美国好莱坞电影故事题材较多呈现为奇幻、魔幻即是明证。比如《寻梦环游记》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以他国地域为叙事情境,又在他国地域中呈现本土特色,在他国情境中讲好美国故事,获得全球成功,这应当归功于丰富的叙事经验以及有效的精神内核提炼。这是有益的启示,中国电影也可以探索在跨地性的多地性情境中叙述中国故事、世界故事,避免单一区域情境的局限,从中国地域出发,抵达世界。
(二)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文化景观
纵观中国电影人物与历史时背景之间的关系变化轨迹,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经历了从全景到远景再到缩影的转变。从讲述“历史中的人”,到讲述“人的历史”,再到讲述“人的一瞬”,中国电影故事的时代背景由大到小,又由远及近,直至当前聚焦为一个微缩景观的叙事符码,象征性激增,现实意味弱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时代背景与人物符码关联密切,休戚与共,宏大的历史背景对于个人命运的驾驭几乎是决定性的。如《十字街头》《神女》《马路天使》等电影中的人物故事所传递的特定时代强烈的“命运感”。第四代、第五代中国电影人则倾向于选取故事角色生命长河中决定性阶段与历史转折点的交相辉映,谱写人物的“断代史”。相比之下,当前的中国电影更钟情于松散人物与历史情境的密切关联,任性地选取人物生活中的任意一瞬,标以象征性的时间符码,讲述脱离历史情境的故事。
时间是最具区隔性,又最具同一性的符码。同一时间内,世界各国发生着不同的事件;但同一时间片段或截点上,世界各国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显性或隐性的关联。时代,作为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时间维度,让中国与世界在历时与共时的时间之流中彼此区隔,又连接并行。可以说,中国电影叙事时间在空间层面的分散,或者在时间层面上的切断,是中国故事缺乏世界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抗日题材电影为例,中国电影的抗日战争叙事,往往展现了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程度忽略了抗日战争背后的世界时间背景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跨国性及人性高度。因而,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故事,在广度上常常局限于中国情境,重在国土护卫斗争,对于维护生命人权尊严的斗争主旨表达不充分。
所以,在断代式的、嵌入式的时代背景编设中,当前中国电影不仅割断或弱化了其与世界的联系,也削弱了本土文化的根基,其结果,就是悬浮式故事的盛行。悬浮式故事,本质上是对于时间的反噬与重构,试图以一己之见概括历史之全貌。比如,青春电影试图打造“70后”“80后”“90后”的青春时代属性,召唤群体记忆,却难以摆脱在模糊的时间、割裂的时代氛围中拼贴碎片的俗套。《红日》是电影《致青春》中最具年代感的符号之一,电视剧版《致青春》试图以张震岳的《再见》替换掉《红日》以将故事的发生年代推迟。这种仅靠概念化的时间符码来标记,能够轻易地顺从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有何年代感、文化感可言?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历史必然是重要的,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电影导演过于主观化地赋予了历史一种标签,从而使之既丧失了历史的本真韵味,也使其自身埋没在所谓的当下中。
四、中国价值:价值底线把控与价值空间拓展中的文化共识
中国价值乃是中国故事的内在之魂魄,换言之,艺术化地表达、传播中国价值,既是中国电影正确讲述国家故事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国电影有效讲好国家故事的艺术能力体现。
要准确呈现中国价值,就要对中国价值底线进行把控,在中国价值空间拓展的过程中,达成一种文化共识。在价值底线之上,确定的是基本性、共享性、不易性的价值观念;在价值空间中建构的是特殊性、情境性、变动性的价值观念,如何在底线坚守与空间拓展中寻找到价值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电影智商与情商的综合考量。出于中国故事讲述与国家形象建构的需要,在电影叙事中探寻中国价值的生成与传播,必须将价值底线与价值空间并置考察,寻找文化共识。因为从不同视角切入,价值底线与价值空间可被切割为不同层面的双生概念:在传统价值与当代价值中,传统价值是价值底线,当代价值是价值空间;在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中,主流价值是价值底线,市场价值是价值空间;在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中,社会价值是价值底线,个人价值是价值空间;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中,人类共同价值是价值底线,中国价值是价值空间。如此多元变动、辩证相关的价值关系之间的融通、协同、互洽与通约,是中国电影有效构建积极的国家形象,获得文化共识的重要方式。
(一)传统价值与当代价值的融通。
作为价值底线存在的传统价值,明确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不可否认,中国电影曾经通过展示传统文化的负面内容而获得世界的关注与赞同,这种“污名化”的影响力,导致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的负面塑造与尴尬境遇。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全面对接世界,深入合作,类型化、风格化的发展步履迅捷,但是在实现传统价值与当代价值的融通方面,尚未取得与规模数量相匹配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例如,历史题材电影中,对于历史文化资源采用奇幻创意手法,将归属于不同文化族群的元素拼凑杂糅而成《长城》这般的“非古非今、不中不洋”的畸形产品,何谈中华传统价值?再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从演员服饰到故事内涵,玄幻的情境设置,进一步将传统文化抽离为虚无缥缈的意念,何谈中华文化精髓?还有,《寻龙诀》披着传统的外衣却与传统价值无甚关联,《妖猫传》消耗巨资不过是呈现一场空洞无物、浮华无物的极乐之宴。在现实题材电影中,“价值问题”常常被悬置,标榜人物的当下个性远比展现人物价值观更为重要,有时甚至不惜扭曲人物的价值观以突显其独特性,如《小时代》系列电影等。总之,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模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线,不能淡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采魅力,不能偏离当下正向建构的当代价值空间。
(二)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协同。
在国内语境中,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往往被置于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时不时上演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的尴尬博弈局面,主要原因是“价值底线过高”及“价值空间被滥用”。所谓“价值底线过高”,是对主流价值的一种误读;其实,主流电影不等于红色电影,所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匹配的价值观都属于主流价值的范畴。而所谓“价值空间滥用”,则是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与经济收益而无视艺术创作规律和价值底线的市场行为。在不同时期,“价值底线过高”与“价值空间滥用”都曾导致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对立。比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的明星展演现象,实质是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表面和解的一种尝试,但并没有达成真正协同的价值共识。而《战狼2》等国产大片虽然获得票房成功与专业口碑,为新型商业大片调动与满足国内主流受众、对接主流价值提供了新的样本,但是海外市场遇冷,意味着国内主流价值与外海市场价值的协同还没有获得真正有效的探索。内需外宣如何兼顾,确乎是一大难题,亟须解决。
(三)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互洽。
在中国电影价值体系中,与主流、市场价值之间博弈并存格局极为相似的是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二者常常被放在天平两端,将面临抉择的人物置于两难的境地。不过,主流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博弈主要集中于故事题材选择与受众口味偏好环节,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对立则聚焦在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故事讲述环节。集体与个人在价值认识方面的关系,虽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语境双重因素影响,但是国际传播中更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其对立性更为深刻,更为根本。其实,强调个体奋斗与逆袭的西方电影故事讲述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电影所采纳,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只能在个人与集体的价值对立之间取舍。其实,中国电影如果能够艺术化地探求与表达中国人在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之间的互洽,化解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的矛盾,反而能为世界提供超越二元对立、包含中国智慧与国家价值魅力的新型故事形态。
(四)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通约。
人类共同价值是指具有跨越民族与国家的共享性、基本性价值观,中国价值则是指具备中国特色性、主体性的独立价值观。为满足国际传播中文化折扣与文化适应的需要,中国电影需要在故事讲述中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通约,即取得最大公约数,在满足人类共同价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底线基础上,充分开掘价值空间,呈现中国特色价值。然而,当前中国电影在这一关系的把握上,不善于做加法,时常做减法。有的创作者以人类共同价值减去中国价值,并以“西方价值”迎合西方人的审美眼光,为西方攻击中国价值提供论据,比如独立电影人为了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而创作的边缘题材电影,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另有创作者以中国价值减去人类共同价值,塑造的是负面的中国价值与中国形象。像《金陵十三钗》对于“生命无贵贱,人人都平等”这一基本价值观的违背,不仅使之自身无法通向更为广泛的世界,也招致他国观众对于其电影主题的质疑,导致他们对中国价值的负面印象。
中国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在塑造国家形象时抵达价值层面,在传统与当代、主流与市场、集体与个人、共享与特色的多对关系之中寻找支点,产生积极效应,回避负面效应,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拓展价值表述的空间,打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根本路径。
结 语
中国历史之悠久,民族之多样、文化之多元、价值之丰富、形象之多义,皆为客观存在;中国崛起与强大引发的全球历史性偏见与误解、戒备甚至敌视之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电影业大而不强,国际传播经验与能力欠缺,实乃自身短板。三者叠加混杂,增加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的现实难度。中国故事的讲述能力与水平,关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成败,关乎中国形象塑造及中国精神传达的成败。何谓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宏大的现实命题,也是一个有待不断开掘的学术命题。唯有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以富有国家诚意和民族智慧的精品佳作,在艺术与市场的双重坐标、双重路径中,讲述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赢得中国电影的荣光与声名,方能实现通过中国电影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长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