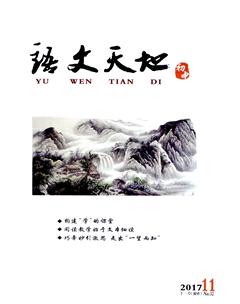播下一颗美的种子
顾杨梅
想起跟我的學生一起学习《寒风吹彻》这篇散文时的情形,纠结沮丧的情绪还历历在心……
“你怎么选这篇难懂的散文上公开课,你有这样深沉的人生感受吗?”面对同事的质疑,我也犹豫过,但是,因为喜欢刘亮程文字中的忧伤、清明和深邃,还是硬着头皮开始备课了。
“来,将你颇有感触的文字大声朗读出来!”带着大提琴曲我期待中的阅读之旅开始了。伴着音乐,学生读出了自己的情绪,甚是动人。
“这真的是一篇易感染人的作品。”我也在心里为学生的感受力点赞,这篇文章虽难懂,但我的学生不是没感觉。“现在你能说说你喜欢这些句子的理由吗?”我期待的阅读交流马上开始,还有点小激动。可是,我这句话抛向他们之后便石沉大海。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有点沉不住气了。直接点名,被选中的不是慢慢吞吞不肯站稳,就是吞吞吐吐不愿开口。此时,我开始走神,在心里千万遍地问到底怎么了?于是带着几个肯开口讲话的学生,生拉硬扯,把我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告诉他们。看着课堂里的压抑、沉寂,我除了自责还是自责。
下课后,我好长时间沉在空落落的情绪里。好在隔着时间的河我望见了方向,跟另一拨学生重读此文时从容了许多……
“许久以后我还记起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围抱火炉,吃咸菜啃馍馍想着一些人和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从这句话中的“人和事”开始提问——“这篇散文大量笔墨回忆这些人和事——十三岁冻坏了一条腿的‘我、冻死的路人、 被冬天留住的姑妈 、苍老的母亲。那么,这些人和事为什么按照这个顺序写呢?”
一阵激烈的讨论之后,大家渐渐明晰:“我”没有人关心,在一个冬夜冻坏了一条腿;老人给“我”一杯水的温暖,但依然冻死在路上;姑妈渴望着“暄暄”,也没能熬过那个冬天;母亲有儿女的关心,还是掩不住苍老的肆意侵袭。原来,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冬天孤独过冬,谁也帮不了谁。而且,哪怕你得到外人再多的关怀,总也逃不掉生命深深的孤独。纵横交错中,文章写出了寒风吹彻之中“彻”字的精髓。
“现在,你能说说对这几句话的理解吗?”他们紧扣其中的关键词句,有的披文入理,有的联想情境,有的诉说自我的心情,甚至有同学写了一段文字表达——“我看着他们,却无能为力。我们远离贫穷与饥饿,我们无视欺骗与谎言,我们还没经历生离与死别,我们隔着故事的堡垒,在悲剧之外流泪。为此,我们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惭愧?但至少,我们应该牢记,这世界本身就充满泪水你能知晓!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也读出我的心情——安静的冬夜,孤守灯下, 苍凉的文字中,我看见那个离开了‘所有熟悉后左顾右盼的我,……当我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独自面对一切时,我的生活里似乎真的只剩下纠结和无助。 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正感受着生命中的那些寒冷。
我知道,我们的阅读应该向更深处漫溯。讨论之后,我向他们推荐林贤治对刘亮程作品的评价:“他的作品,阳光充沛,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无助,快乐和幸福。” 同时,邀请他们同我一起读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与每一个在我生命里停留的人一起穿过岁月,我看见你们在我周围成长和衰老。其实,我何尝没有经受着岁月的淘洗,奔走在时间的荒野里,一次次的风正从我的骨缝吹过。我懂得,我们唯有揣着春天的梦,守着爱的诺言,静待风暖的时候……
同样的文章,同样学段的学生,为什么第一次阅读时不能带着学生抵达阅读的深处?这个问题开始留在我的心里。不久,偶然间又遇到了朱熹的经典名句“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在《寒风吹彻》的第一次教学设计中,我没有考虑到学生喜欢刘亮程的文字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跟我理解的喜欢是错位的。所以当回到理性的分析上时,他们自然是不知所往。第二次设计中,开头对刘亮程笔下那四个人物的分析,无疑是为学生对作者情感的理解由感性到理性搭了座桥, 越过这座桥他们的阅读才更容易越走越远。
我也开始明白,在赏读《将进酒》时,我在问学生“你喜欢诗中什么样的李白”这个问题前一定给他们一个认识的铺垫。只有清楚诗中到底展现了李白哪些形象,才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喜欢,而只有理性的认识才能让感性站得稳,抓得实,留得久。
同时,这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过程更是学生阅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验,尤其在今天这个快时代里,文本解读往往停留在走马观花的阶段,所以好多细节被忽略,好多惊喜被错过,好多成长的机会被剥夺。
其实,让阅读过程有层次感不仅是阅读中的大事,也是艺术的追求。鳞次栉比是美,层峦叠嶂也是美,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教育的圣地播下这颗美的种子?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中学(210012)endprint
——人和事》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