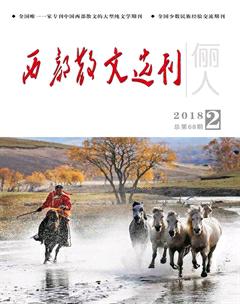饸饹床子记事
徐长玉
荞面饸饹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听着这悠扬欢快的陕北民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陕北人压荞面饸饹时所必用的物件——饸饹床子。
头大尾小的梯状整木床身,扁平、细长的压面杆,圆柱状的实芯子和“开”字形的床桩,便构成了又坚又硬的榆木饸饹床子。床身上,凿有一个盛面团用的圆形容器,容器底部镶嵌一块布满小孔的铁网。压面杆和实芯子套在一起,形成一个支点。床身头部和压面杆头部都固定在床桩上,由此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老家的旧土窑里,至今保存着这样一架已废弃20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特别熟悉的老式榆木饸饹床子。这架饸饹床子是家父上世纪70年代初打制的,距今约有40多年历史了。
至今记得小时候家里压饸饹时的情景:将饸饹床子置放在锅台上,将铁网正对到锅中央,用水反复浇灌芯子、容器和网,将事先和好的面团塞入容器,将芯子对准面团,待锅里的水烧开后,一人,有时两人,或坐或爬在压面杆尾部,使劲朝下用力,稍许,一根根“滑细如粉”的饸饹,伴随着“叭叭叭”的声音,便从铁网顺势而出,缓缓入锅了。这时,另一人须一边用筷子从锅底轻轻把面挑起,以防粘锅或结成疙瘩,一边给锅里倒入一瓢冷水,待水再次沸腾后,即可捞面出锅了。
那时,我们庄只有两个饸饹床子。其中一个又大又旧。可能是“大跃进”期间,庄里为全民“吃食堂”而专门制做的吧。后来,这个大饸饹床子在庄里搞“农田大会战”以及过红白喜事时,也发挥过作用。但那个饸饹床子终究因为太大而不适合小家户使用。所以,才有了70年代初家父亲自做的这个饸饹床子。
我家的饸饹床子由于“一崭新”,且小巧玲珑,所以,就成了全庄各家各户吃饸饹时必借之工具。我家的饸饹床子因此也就一年到头在全庄轮转着,很少有在我家停留的时候。而且,通常一家借走用过以后,并不需要直接还给我家,而是就放在自己家里,等下一家用时来拿。下一家用时也并不需要再给我家打招呼。就这样,长年累月,大家借来借去,丝毫也不客气,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我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人家欠我们的,真的就好像“外国有个‘加拿大,我国有个‘大家拿”似的。
小小的我,也曾因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件“宝贝”可以供庄里人分享而感到莫名的优越和自豪。
在那个食品匮乏的时代,除了红白喜事和给家庭成员过生日等少数场合,老百姓能吃上一碗饸饹真不是一件寻常事。多半在过“时分八节”和招待家里来的尊贵客人,比如多年不见的亲戚朋友和驻队干部等时候才能吃上“一半顿”。
一次,我们庄来了一位家父的“俩姨”,奶奶和几家叔父们挨着叫得吃饭,轮到我家时,吃的便是平时根本舍不得吃的荞麦饸饹。当我和大哥把我们的“俩姨大”从奶奶家叫到我家来时,家里已经“雾蒙蒙”的了。
由于准备的饭少,大人只顾敬让着叫客人吃,并给我们的“俩姨大”诳称孩子们已经吃过了。而我们兄妹几个尚小,又特别害怕父母,所以,未经大人许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一个个还是禁不住诱惑,眼睛直勾勾地瞅着盘子里、热腾腾、香喷喷的“好吃的”。
家父觉着娃娃们惹眼的样子给他丢人了,就先是低声地、后是“恶狠狠”地喊着让我们“往外起走”。我们弟兄几个灰溜溜地出去了,藏在院墙后面,期待着客人走后,能剩下些“饸饹头子”和调汤之类的饭食,好让我们都能“分支”地吃上一点点,只有妹妹一个哭着呆在家里怎么也不出来。不一会儿,只见父亲拉着妹妹,径直走到院墙跟前,把妹妹倒提着一把扔进院墙后面的垃圾坑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先包产到组后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庄成了全乡镇的“先进村”,我家也成了村里的“冒尖户”。于是,吃饸饹就越来越成为寻常事了。
如此以来,全庄只有两个饸饹床子就轮不过来了,而许多家户也有能力请人自己做一个了,特别是随着“分田单干”,庄里人相互之间的走動越来越少,及至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所以,庄里的饸饹床子自然就多起来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城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对饸饹床子的需求不断看涨。受利益驱动,全国生产饸饹床子的厂家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甚至于用各式各样材料制成的新式饸饹床子、特别是铁制饸饹机都运用而生了。于是,那种简陋、笨重的老式木制饸饹床子,一夜之间便在我们庄乃至祖国大地销声匿迹了。我家的那个老式饸饹床子也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回到我家来了。这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这令我蓦地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套用这句话,我便可以说:“老式木制饸饹床子代表的是手工业主为首的社会,新式铁制饸饹机代表的是机器工业主为首的社会。”我还可以说:“老式木制饸饹床子代表的是人民公社时代,新式铁制饸饹机代表的是改革开放时代。”
——选自《红都》2017年第二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