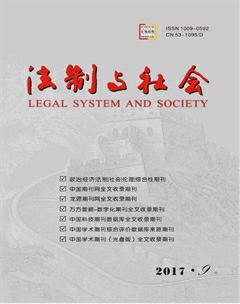自组织理论视角下的德国历史法学派
罗强
摘要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种系统理论,而德国历史法学派则是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学思想流派。表面看来二者在时间维度上相差一个多世纪,但在思想内核上,二者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比如历史法学派对习惯及习惯法的看重,从自组织理论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对社会有机体自组织能力的看重。同时,历史法学派对立法的谨慎拒斥态度,也与自组织理论中关于一个社会生命活力与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的论断相应和。
关键词德国 历史法学派 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产生的一种系统理论。虽然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来讲,这一理论的诞生时间被划定在20世纪,但如果单论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核,其基本理念的萌发则远不止于近现代这一时间限度。同时,自组织理论的理念精髓也并非只能适用于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一种跨越学科界线的普适性。综合这两点,我们将视野放大来考察,就会发现在法律思想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诞生于19世纪初的德国历史法学派,其思想体系内,就有着令人瞩目的自组织理论闪光点。
一、自组织与他组织,习惯与立法
自组织理论正式提出的标志,_般认为是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于1967年发表的论文《结构、耗散和生命》。在这篇文章中,普利高津认为,所谓自组织就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当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通过涨落发生突变及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的现象。。作为一种讨论一个系统是如何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理论,自组织理论一经提出,就被广泛应用到了各个学科领域。这其中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身即是一个充满各种变量和矛盾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如何实现有序化一直是政治学、法学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而笔者认为,自组织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秩序从哪里来?”因此,可以说,在秩序的来源这个点上,自组织理论和法学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
对于秩序的由来,按照自组织理论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依靠外部力量,有目的地形成秩序,这被称为他组织;其二是依靠系统本身的自我调整,自发形成有序状态,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组织。自组织理论中的这一二元范畴结构被拓展应用到了诸多学科,而通过考查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和主张,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着思想内涵完全相通的二元概念。
德国历史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初,以萨维尼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假如我们把法律制度理解为一种秩序,那么,根据历史法学派标志性的看法,这一秩序与其说来自人为的设计和制定,毋宁说,来自于社会生活中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这一习惯和风俗的更深来源则是后来萨维尼提出的经典概念—一‘民族精神”。纵观历史法学派的基本纲领,我们可以发现,对习惯和习惯法的重视和强调是历史法学派所有观点、主张的逻辑起点和基础。例如普塔认为,习惯最接近一切法的基础;习惯应当在法律中占最高地位,在一切法律之上。萨维尼也多次论述说,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事实上,历史法学派对习惯法的推崇与看重是与其对成文立法的怀疑和拒斥相呼应的。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发展的,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进行创建;法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的、有机体的过程,因此法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制定。对此,台湾学者林文雄总结认为,立法(legis-lation)与习惯(custom)相比较时,立法的重要性是站在从属的地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对显著的矛盾范畴一习惯与立法。而这一二元对立的范畴体系,其实就是前述自组织理论中的二元结构。在这里,立法对应的就是他组织,而习惯则代表了自组织。因为所谓习惯,就是久而久之形成的固化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这一模式和观念是纯然自发形成和无意识的结果。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这一习惯显然是自组织的最好表现。相对应的,立法则代表了另外一极,即人的有目的的、理性化的举动。因此,按照历史法学派的看法,一个社会的秩序形成,主要依靠的是该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自我调整力量,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而非由某种人为建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所谓立法机关来进行设计和建设。德国历史法学派对习惯的看重表现出这一学派思想中强烈的自组织理论倾向,这一点使其在法律思想史中独树一帜。
二、正确看待立法的社会功能,重新发现社会自组织能力
德国历史法学派反对统一法典编纂的立场历来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我国学者也多有讨论。不过以往大家多聚焦于民族精神与本土资源、当下中国统一民法典制订的利与弊等问题上。事实上,民事法典的立法问题只是历史法学派思想的表象,透过这一层表象,其内在的重要理念是不可高估立法对一个社会秩序形成的作用,而应该更加尊重和看重社会中自发起作用的那些潜在规则,也即习惯。社会秩序的形成,正是源于这些潜在规则。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自组织理论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即一个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越强,它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反之,假如一个系统总是要依赖他组织才能保持有序化,其生命力也就必然是赢弱的。这个论断完全可以适用到人类社会。而早在19世纪初的德国,萨维尼等法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其所说,社会秩序“都是由内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形成的,而不是按照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換言之,一个社会的他组织只是占据次要地位的秩序来源,而自组织才是秩序形成的核心力量。
对此,国内学者也早有领悟,比如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制定法事实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并不如同法学家想象的那么大,有时甚至是毫无影响;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仅仅是促进人们合作的一种机制。因此,当人们渴求秩序、呼唤法治之际,立法者和法学家的眼光也许应当超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称为‘法律的那些文本以及与之相伴的国家活动,看到、关注并注意研究任何社会中总是存在且并不缺乏的那些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那才是—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这里,苏力所说的在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的那些条件其实就是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力量,也即是前述历史法学派所认为的习惯。让人略感遗憾的是,此类领悟并没有成为国内法学界的共同认识。长久以来,我们的主流思想天然地认为,社会秩序就应该由,且只能由法律制度来建立。因此,立法就是应对社会无序、争端频起的首要任务。一旦社会出现失序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立法,而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之后,问题也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己基本解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社会有机体对立法的高度依赖,这也是美国学者所称的社会对法律(立法)形成的“瘾”(addiccionto law)。这种“瘾”一旦形成,社会自身的白组织能力就开始慢慢退化,由此陷入—种恶性循环一对他组织的依赖导致自组织能力的退化,由此引发更严重的秩序丧失,更进一步加剧社会有机体对他组织的依赖,最终使得社会彻底丧失生命活力。
所以,结合前述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以及自组织理论,笔者认为,我们并非是要放弃立法,而是应该更加科学、客观地评估立法对于一个社会的秩序形成能够起的作用。与此同时,要看重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并为这种作用的发挥努力创造条件。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和执行的社会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法学界、经济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界过去十多年的研究表明,法律的作用被人们大大高估了;社会规范,而非法律规则,才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撑力量。特别是,如果法律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不一致的话,法律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正在迈向一个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