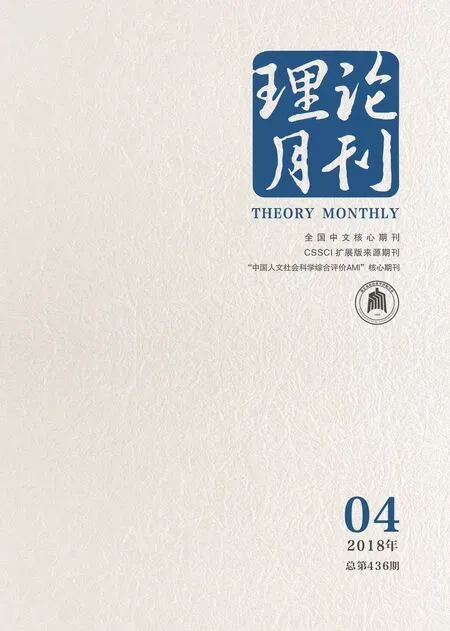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逻辑
□ 乔玉强
(1.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厦门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问题与视角
新航路开辟后,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理空间界限开始被打破,世界逐渐联系在一起。随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资本原始积累,并利用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按意识形态把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美苏主导的国际治理格局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导致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秩序再次重建。战争和经济危机使得全球化进程几经起伏,逐渐形成以资本为纽带,把世界各国捆绑在一起的国际治理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404)毛泽东也对全球化也有过论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2](p161)而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在冷战期间也开始逐渐延伸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部分主权国家内部的事物逐渐上升为国际事务。二战结束后,关于经济、政治、科教文体性质的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有些是区域性质的,有些则是全球性的,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UN)、欧洲联盟(EU)、上海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华沙条约组织(华约)、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在国家间交往频繁和国际合作深化的前提下,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性难题和跨国性的危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性和弱组织性使其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为应对这种全球性质的危机和问题,1990年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首次提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理念和构想,即全球治理理论。
对于全球治理(governance)的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规范。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他认为“全球治理是在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中不能够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时而做出的一种选择”[3](p223)。国内理论界对于全球治理定义比较认同的是北京大学俞可平给出的定义,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4](p25)。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丛书给出这样的定义:“所谓全球治理体制,是指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建立的,管理国际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规范、体制和活动。”[5](p83)这些定义都明确指出全球治理的本质是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治理。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主导的国际治理格局在东欧剧变后解体,随后重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但这种全球治理格局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重创。旧的全球治理体制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不对称性,导致已有的治理秩序紊乱,“治理失灵”现象发生,具体主要表现为经济失衡、政治失序和文化失范。
第一,经济失衡。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以来,世界经济一蹶不振,近十年的时间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复苏本国经济,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被打破,新经济格局逐渐形成,经济重心向后发国家转移。同时,经济全球化被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抵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受到重创,2013年奥巴马政府停摆,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不到一年,推翻了奥巴马政府的大部分决议转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如退出TPP,修建美墨隔离墙等。俄罗斯在金融危机后,卢布一路贬值,2014年介入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事务后受到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制裁,国际油价大跌,出现“卢布之殇”。欧盟各成员国受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内部分裂,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更使欧盟经济增长乏力。反观部分后发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后能够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增速始终保持在6%到8%之间,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也保持高速增长。世界经济中心向发展中国家位移,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动态的不平等状态[6](p7-9)。
第二,政治失序。20世纪70、80年代,世界上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西方世界更加“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7](p171)。福山更是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论断,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更是提出“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一场毫不掩饰的胜利”[8](p4)。然而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见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的衰竭腐败和异化。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达到半月之久,2016年美国民众在华盛顿国会山参加抗议示威,要求抵制政府腐败确保公民选举公正。此外,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中产阶级的严重缩水使美国表面风平浪静的政治之下暗流涌动。近几年欧洲和中东更是笼罩在“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而“伊斯兰国”产生的根本原因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所致,所以资本主义政治自由民主体制并没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真正自由和平等,带来的只有动荡和恐慌。
第三,文化失范。传统的西方全球治理模式认为存在一种普世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主,是一种可以超越民族、宗教、国家和地域的绝对治理体系。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证明各文明之间的演变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对于外来嫁接过来的各种文化需要一个“化”的过程。亨廷顿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联系而是对抗性的,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间。在宏观层面上,最要分裂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7](p161)。西方国家认为西方文明最崇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权力有限等价值观同样适用于其他文明之间,殊不知这种西方社会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是侵略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在伊拉克推翻了所谓的萨达姆独裁政权推行美式民主,但民主投票的美式民主带来的是伊拉克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分崩离析和动荡不安,而20世纪80年代的伊拉克是人人向往的国度,有着现代化的城市和令人羡慕的终身免费医疗和教育。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泰国等国家都成了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失败的试验品,本国内部动乱随时会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
二、中国逻辑:自信、担当和创新
传统全球化本质上仍旧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以资本为驱动力的“恶”全球化的延续。基于启蒙理性的全球化在追求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中容易失去价值判断从而走向价值虚无,其内在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性更是人类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使正义问题由国内正义上升到国际正义。罗尔斯所倡导的“万民社会”就是基于国际正义而建立,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在万民社会中维持人民间的彼此尊重,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政治氛围的一个核心部分”[9](p103)。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国际公共领域,导致全球治理失序。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也促进了全球治理格局重组需求,新全球治理体系急需以变革和超越主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基于人类命运朝着一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和网络治理为目标的方向变革。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来不断阐释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务实的态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思路,彰显了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凸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意识,以及抓住时代机遇进行创新治理模式的天下情怀。
(一)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自信
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摆脱苏联模式影响和突破西方封锁的砥砺前行中,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而获得的。新时代“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5](p90),中国用自身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正确性、先进性、优越性和创新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高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特点理性分析的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复兴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内容上坚持了全面和重点的统一,既会“弹钢琴”,又能够把“钢琴”弹好。在发展过程中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有了发展目标,才会有奋斗方向,发展道路上才不会迷茫。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实际制定了更加详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提出要在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分两步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建国一百年,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决定命运,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15年,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的道路是人间正道,是基于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而制定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中国用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向世界各国人民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新时代呼唤新使命,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但新时代更需要新的先进理论来指导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科学理论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而提出的先进理论指导,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写入党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创造性和创新性,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斗争,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进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建立、推进和完善起来的成功经验的凝结和固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文化的制度体现和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0](p4),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一新发展理念。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但中国能够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之间把握好平衡点,使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这都得益于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综合保障。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消除了其中的缺点和不足,将党领导的方向,人民团结的动力以及依法治国的保障有机高效结合起来,既能够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性地在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实现中国奇迹。十九大开启了新的时代,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改革,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优势也将是中国自信的有力支撑和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形成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团结、稳定、发展的精神纽带,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内在驱动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激活、增强、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现在则用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的精神内核,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共识,实现凝魂聚气和强基固本的思想基础。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此来引领多元社会思潮,才能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甚至有的国家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我们更有自信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会搞文化垄断,也不会搞文化侵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能力也有信心包容多样。
自信而不骄傲,自信而不自负。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创造性的秘诀,因为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嘉兴南湖出发的初心和使命。讲中国自信并不意味中国渴望自信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不够自信,恰恰相反,中国自信是我们国家在国内社会和国际舞台上一举一动的行动中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来的“精气神儿”,是全球社会“生病”后都来找中国“治病”,贡献中国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在发展自身惠及世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就是中国自信在国际舞台的具体体现。
(二)应对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炸毁了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70多年的全球治理格局和模式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剪刀差”压迫中,慢慢修复国内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冷战后全球治理格局的上层建筑同全球生产模式的矛盾。后危机时代,面对全球性质的问题,国家之间更倾向于通过共同协商,建立国际机制体制,通过和平对话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全球金融风暴的摧残都无法独自主导国际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12](p53)。这种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诉求正在召唤一种经济上合作共赢,政治上协商民主,文化上和而不同的治理模式,而这一需求正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深邃的政治视野,统筹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准则”[13](p360)。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强调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14](p566)。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15](p45),“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监、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16](p36)。习近平总书记在更是全球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从政治、安全、发展、文化、生态五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7]。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侵略,受到过西方国家的长期资本剥削。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崛起,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在后危机时代向世界提供中国治国理政经验,通过“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都是一种没有血腥的贸易往来,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观,以及“和而不同”社会观的传统外交体现。近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近百年来,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始终牢记自己成立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用实践证明了西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人类社会追求美好未来注入强大正能量”[18],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代表承当起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三)应对全球治理的中国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创新,又是中国外交的长远的战略性行动指南。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发展有限,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国家压制,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凭借上升的金融实力提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度。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和周边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中大力创新,包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创新率和“一带一路”激活全球经济的创新作用,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由于历史等客观原因,在前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没有能把握时代机遇,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国初期毛泽东在1954年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p329)经过改革开放40年奋起直追,中国的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2015年中国的创新能力达到了欧盟水平的49%(2006年为35%)[20]。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等西方经济科技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认为,当前正处于以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融合为动力和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克劳斯·施瓦布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篇序言就写道:“中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充分具备成为时代先锋和全球领头羊的条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主要领域,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国际合作,完善相应体系,从而管理好此次转型进程,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最大成果。”中国创新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已逐渐进入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高附加值领域,并正在运用其举足轻重的规模经济优势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21]。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实践。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重大战略创新,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它摒弃了以经济和军事力量把国家划分等级的霸权思维,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求同存异,对沿线区域的国家历史、文化习俗、经济发展采取针对性的合作模式,旨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模式,使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而且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案。“一带一路”作为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模式,是由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决策,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实现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最大化,使发展成果由全球共享,同时也是国际正义理念时代化践行的产物。作为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亚投行的成立、丝路基金的启动和新开发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力。从2014年10月亚投行成立到2017年5月,亚投行成员国从成立初的21国变为现在的77国,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完全不同,亚投行的成立过程和运营方式都体现了开放、包容、协商的特性,他的运行将“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导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5](p100)。丝路基金是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资金,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和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为突破区域限制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着眼于长期发展融资,简化金砖国家内部的融资程序,减少对西方货币体系的依赖,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作用。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丝路精神”是历史的积淀,其核心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2]。
三、意义和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由中国提出的一种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但是同西方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全球治理格局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的前途和发展方向掌握在世界各国人民手中,面对全球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等全球问题,世界各国应该在共同可持续发展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个具有依存性、平等性、共赢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点的集合体。中国倡导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平衡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从人作为“类”的前提出发,强调“类”的整体利益,而不以人种、民族、宗教和国家划分等级,不是某个小群体的利益,改变传统倚强凌弱的不公正非正义的国际格局,国与国之间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道路。面对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影响全球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发展路径的理念应该摒弃,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模式和治理理念应该提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型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传统全球化由西方国家主导,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能够实现转移危机、获取利益、输出价值的目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参与,处于弱势和被剥削的地位。新型全球化的背景是“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或出现一个巨大真空,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失序成为常态,全世界都在渴望更公正的国家秩序。这一国际新秩序应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合作,更尊重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更能体现‘休戚与共’与‘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3](p19)。“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利用其先发优势进行全球贸易资本扩张的传统全球化升级为以开放、包容、普惠和共享为核心价值的新型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重振世界经济战略举措,是在人类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实现由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结合推动的“万物互联、人机交换和天地一体”,是对初级互联网的巨大超越和升级。“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巨大而复杂的人类工程,是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一剂良药,如果没有深厚的“天下大同”思想,“和而不同”的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和无产阶级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追求,是不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是没有底气和实力构建这样的宏伟蓝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社会谋发展的初心和使命。“一带一路”虽由中国提出,但是却是一项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并属于全人类的事业,是解决传统全球治理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战略举措。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愿为推动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使命,为促进开放性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思路,与国际社会共同决定人类命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David Held,Anthony McGrew.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M].Policy Press,2003.
[4]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5]陈岳,蒲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6]Facundo Alvaredo,Lucas Chancel,Thomas Piketty,et al.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New Findings from WID.worl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8]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J].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9][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M].陈肖生,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10]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1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2).
[12]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7]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2).
[18]张广昭.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世界意义[N].光明日报,2017-12-01(10).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EuropeanCommission.InnovationUnionScore⁃board2015[EB/OL].http://ec.europa.eu/growth/industry/innovation/facts-figures/scoreboards/files/ius-2015_en.pdf.
[21]World Economic Forum.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Business,Driving Growth[EB/OL].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report_2015.pdf.
[22]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N].人民日报,2017-05-15(3).
[23]王伟光.“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的新长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