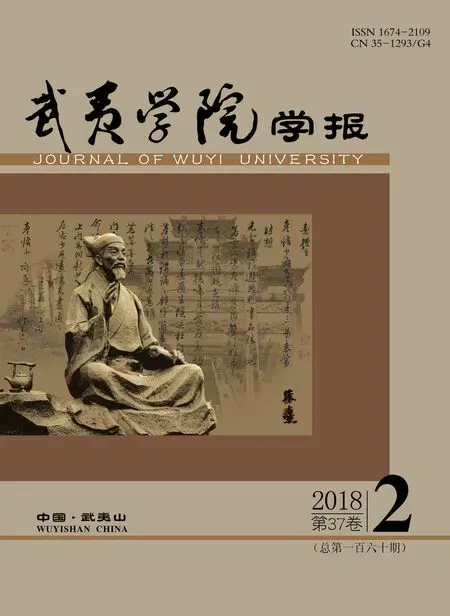简述“格物”的解释史
——以心物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何彦彤
(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格物”这一概念源出于《大学》。自西汉时期《大学》编入《礼记》并被确立为儒家官方经典之后,历代都有经学家和思想家对“格物”作出不同的解说。明末大儒刘蕺山已总结过:“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1]显然,这意味着“格物”的内涵不会如其字面意思所表达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富含价值的思想史命题。因此,重提这一经典命题,从其自身的解释史出发,我们或可窥见其对宋明理学之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的塑造作用。通过与传统的深度对话,本文期望进一步厘清贯穿于宋明理学中的心与物之关系(亦涉及到心与理之关系),进而为心与物之对峙提供一种基于现代社会背景的反思。
一、朱子以前的格物思想
许慎《说文》载:“格,木长貌,从木各声。”此乃“格”之本原义,仅仅就树木之自然生物义而言。后来诸儒当然并未按此单纯的训诂学路线走下去,而是各自另辟蹊径,创造了诸多解释路径。
关于“格物”的诠释,东汉经学家郑玄开其先河,其注《礼记·大学》曰:
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2]
孔颖达则详而疏之曰:
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而来应之,言善恶之来源人所好也。……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2]
在郑玄这里,“格”被训为“来”,“物”被限定为具有道德价值属性的善恶之物。他认为善恶事物的到来取决于人的善恶之知。亦即,人心对善恶的认识才是最终的实践动力。从而,人心与事物在因果关系上被关联起来,“格物”也被赋予了或多或少的伦理道德意蕴。且不论这一解释是否饱含郑玄劝喻君主修己明善以成就圣王的意图,其对人与物所建立的伦理性沟通乃发先人之所未发。
唐人李翱则对此有进一步发挥,其注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复性书》)李翱延续了郑玄对“格”的注释,但把“物”扩展为万物,“格物致知”指的就是万物到来的时候,心能昭明是非,不被外来之物所牵引。其解说虽然仍单纯从伦理学角度而言心性修养,但是已不同于郑玄、孔颖达“善恶之报”的简略涵义,而是要求在道德修养时,将更多的工夫落实到人心“不应于物”上。此种解释有似于禅宗所谓的“无住”,有较浓的佛教色彩。
宋代儒家尤为重视《大学》。到了宋代,较为成熟的格物论才开始形成。清人朱彝尊指出:“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自温公始。”(《经义考》)司马光《致知在格物论》载:“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这一解释显然是对郑玄的反驳,“格物”并不是随人所知而“来物”,而是扞御与人自身相对的外物,亦即“去物”,隔绝外物的诱惑。这与李翱的说法是完全相通的,“格物致知”依旧是心性修养的方法。按理说郑玄和司马光的解释都同意以人心的主观意志先行,但却有着相对的立场。若从心物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郑玄某种程度上强调心与物的沟通及其效验(即使“物”是受动而“来”),司马光则排斥外物,强调人心的定力工夫。心物之间的沟通桥梁在李翱和司马光这里几乎是不明显的。观下文可知,这两种略有分歧的说法一直渗透在后人对“格物”的不同理解中。
与司马光同时代的张载虽然未直接对 “格物”作出解说,但他持与司马光“扞物”说相反的“穷物理”说。张载言:“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明庶物,察人伦,皆穷理也。”[3]又指出:“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既穷物理,又尽人性,然后能至于命。”[3]在横渠这里,穷理是认识世界以及尽性知命的必要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与外物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与佛家的虚无抗衡,宋人极力强调“穷理”也就不足为奇了。张载所讲的“穷理”,实际为二程以及后来朱子对“格物”的诠释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早已有学者指出:“张载关于‘穷理尽性’的学说,与程、朱‘格物致知’论是很接近的。”[4]这已完全不同于司马光“扞御外物”的解释,而是明显有了认识外物之理的要求。如果说“格物”的心灵义在司马光那里已暗藏某种端倪,张载的“穷理”思想则为“格物”的科学义开启了某种端绪。
到了二程这里,“格物”不再是囫囵的 “善恶之报”,也不是单纯的隔绝外物之诱,而是有了更广阔的理论和实践范围。二程曰:“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5]又曰:“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5]二程对“格物”的解释乃包含着两层基本意思:一是“至”,即主动接触外部事物;二是“穷”,将事物的道理穷尽到底。这两层涵义构成了后来朱子格物论的核心元素。从二程这里,可分出两支路子。大程子《识仁篇》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5]此乃是教人庄敬持守,反认心体,识得天地万物一体之理。到了小程子这里,则多了些“穷理致知”的话头。小程子如是说:“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5]这种说法明确提出应事接物的主张,必须到实物实事上钻研而后才能穷尽其理。然而,程颐又反对一味地格万物之理:“世之人务穷天地万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善学者,取诸身而已。自一身以观天地。”[5]质言之,二程力图将穷物理与察诸身统一起来,所谓“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5],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反求诸身”的传统上来。由此可见,二程所理解的“格物”并非单纯获取关于一草一木的知识,而是获取关于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仍然是一种修身的理论,更是自郑玄以来最为自觉的且具备理论高度的对心物关系的考察,因为心与物在“道”的基础上被统贯起来了。
凡是任何一种学说,若在它自身包涵着两点以上的趋向,则此种歧趋必会逐渐扩展以至于分裂。程颢喜从浑然的角度说个 “与物同体”,程颐则分别说个“穷理”与“居敬”。那么,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之外物呢?还是应该立之吾心?这是宋儒争论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6]或许可以说,“格物”的科学义和心灵义在二程这里早已深埋下了各自的种子,到了后朝总归会现出不同的歧趋。与朱子同时代的巨儒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7],从而被归为心学一派。但其实,陆九渊和朱子一样,都认为格物就是要穷究事物之理:“格,至也,与穷字、究字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7]学生伯敏曾问于象山:“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可见,陆子也非常重视穷理。不同的是,他讲格物,更为注重“心”的统领作用。伯敏继续问道:“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7]此处所谓的“明理”已不是单纯地指向外接触并识察天地事物之理,而是立足于“吾心”来明察并反观宇宙之天理。正如陆子所言:“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7]二程是心物兼修,再将二者贯通于“天理”之中;陆子乃是将物统于吾心,心包万物。对前者而言,心物合一是结果;对后者而言,本然便是合一。当然,本文不打算开展关于朱陆之争的论述,只是想指出一点,无论是陆九渊还是朱熹,他们对“格物”的诠释大致都延续了二程的“穷至物理”的格物论。二者的最大差别只是在于德性修养和学问研究何者为先。然而,关于“格物”的诠释阵营在后朝日渐出现观点相对的两大派系。
二、朱子的格物思想
从张载的“穷理尽性”到二程的“穷至物理”,朱子的格物论已具备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宋代理学的地基形态已初现雏形。朱子对二程的格物论甚是服膺,他认为“其宏纲实用固已洞然无可疑者,而微细之间,主宾次第,文义训诂,详密精当,亦无一毫之不合”[8]。朱子之所以摒弃了二程部分门人的格物思想而推崇二程的格物论,主要是因为: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8]
可见,朱子与二程一样,从一开始就极为看重内外兼修的格物工夫,他从来不会因格外部事物而忽视切己的心性修养,只是二者因循有渐,不可邋等。朱子释“格物”云:“格,至也;物,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8]又言“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其极也”[8]。 在二程子释“格”为“至”的基础上,朱子又添了一层“穷尽”的意思,强化了“格物”在实践中的深度和广度。此外,朱子还根据二程子的格物论作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其言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8]
无疑,朱子大力强调并扩展了二程的格物说。其所理解的“格物”首先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穷理”不能悬空去穷,必须接触具体事物且研究其理。关于格物的对象,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其范围涵括“天下之物”。朱子曾言:“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8]又曰:“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8]可见,朱子所言“格物”之“物”,既包括自然界领域的事物,也包括外部道德方面和内部心理方面的事物。因此,可以把朱子所理解的“天下之物”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自然界事物、社会伦理道德以及身心性情。质言之,即是物理和伦理两大范畴,涵盖了知识诉求与德性涵养的双重面向。但统而言之,皆可归入“天理”。“天理”的概念在朱子这里得到最大范围的充实与扩展,作为“大学始教”的首要工夫,“格物”的对象自然也就蕴涵了诸多面向。
至于格物的途径,朱子又言: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8]
读书、讲论、考察这些方法与二程的主张大抵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切己、居敬、积累等工夫,然后才能豁然贯通以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亦即明“天理”。朱子谓:“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8]说到底,朱子所言之“理”乃一客观外在的对象,且是唯一的形而上之存在,“格物”也就是通过格外部对象来把握天理。这就决定了朱子建构其理学体系的取向乃是二重性的,心、物这些经验概念必定不能与“理”同处形而上之层面。朱子说:“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底便是那知觉。”[8]因而,“心”在朱子那里更多地是指具有知觉功能的“心”,为经验概念。黄宗羲也曾说:“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9]既然朱子分心和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其所理解的“心”与“物”又各有其具体范畴和内涵,可以说朱子哲学里包含了心物二元论的成分。其实从二程开始,心与物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自觉主动,朱熹完全继承了这一路线。即使心与理、心与物之间有其分别,但朱子的格物论始终是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获取和积累完全融合于道德践履的过程当中,最终也是以成圣成贤为目的。如朱子所言:“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8]总之,朱子的格物论要求人们用心去把握事物,体贴天理,自然而然地达到心与物豁然贯通的境界。其终极目标乃是“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8]。说到底,心与物的契合程度在朱子这里最终是高度统一的。
三、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格物思想
朱熹的格物论至少能确保人们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和中规中矩的行为举止,但发展下去,未免过于繁琐和僵化。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更是成为了众多士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其道德教化的初衷日益被人遗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阳明对“格物”的重新诠释有其思想史上的必然性。与朱子不同的是,阳明训“格”为“正”:
“格物”如《孟子》之“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传习录上》)[10]
又说“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10]。阳明对“格物”的解释采取了意向性的看法。“物”更多地是指意识或意念的对象,所要“格”的,正是心体被偏颇的意念所遮蔽的部分,所谓“正念头”。可见,阳明格物说的着力点乃在于“心”而不在“物”。所谓“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10]。这都归因于阳明将宋代以来对“心”的经验认识传统扭转到形而上的本体层面来,用“心”来统“物。”所谓“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10],良知即是大头脑所在。到了晚年,阳明更是将“格物”释为“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10],格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完全纳入“致良知”的框架中。阳明指出: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10]
阳明合心与理而为一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考虑的,这与朱子先将心理分成二物而后打并归一的工夫论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朱子的格物论是一种外在的认知方法,阳明对格物的主张则是内在的伦理优先立场。阳明常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这里的“事物”大多指涉伦理行为,与内心的道德意图息息相关。任何与人心无关联的事物是无意义的。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南镇观花: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0]
通过赋予“心”以至高无上的主宰功能,阳明在意义论的基础上重构了格物论,巧妙地将主观乃至客观之物都统入到心体中。这种心物一元论的思路,使得道德主体更为突出和统一,纠正了朱熹格物论的外驰偏向。朱子哲学中的心与物仍须经过多番工夫的积累才能打通,但在阳明看来,世间万事万物的道德原理都存在于主体心中,物本然就是统于心体的。如果说前者仍有认识论的偏向,后者则完全是心性一元论的立场。从郑玄到王阳明,对“格物”的诠释始终围绕着伦理道德修养来展开。随着 “物”的维度越来越窄,“心”的维度越来越宽,心物合一的境界在阳明这里达到了高潮。
为了赓续先师的“致良知”传统,杜绝朱学格物论的外向流弊,在众多阳明后学中更是出现了将格物工夫收缩到自我意识的内敛趋向。江右高徒王龙溪言:
格是天则,良知所本有,犹所谓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应上参勘得过,打叠得下,终落悬空,对境终有动处。[11]
在龙溪这里,格物成了良知所本有的工夫向度,亦即感应天则。这几乎摒弃了朱子格物说的向外穷理要求,也冲淡了阳明对于“事上磨炼”的实践要求,直接将格物的工夫限定于内在心体的明觉感应,往玄虚一面发展。
泰州后学王心斋则如此释格物:
格物致知之义,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
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12]
王艮认为,身是本,格物须是从本做起,于是格物工夫被阐发为安身观念,一切工夫都要以反身为起点,这意味着对“格物”的理解再一次被限定于主体自身。再如后来的罗念庵训“格”为“感通”,王塘南训“格”为“通彻”,都是将“物”视为与主体相通的能动意识,而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天地万物。如另一泰州后学杨起元所言:“格物者,己与物通一无二也。”[9]以上这些主张无疑完全继承了王阳明对道德主体修养的高度重视,将存在论意义上的“物”扭转成意义论上的“物”。结果便是,“物”的客观涵义几乎被消解。在工夫论上,心学家们则愈来愈推崇内向的工夫进路,形成了与朱子学截然不同的另一道风景线。
明末心学殿军刘蕺山延此思路提出了另一创见:
隐微之地,是名曰独。其为何物乎?本无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统会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物之始事也。[1]
在这里,“独”代替“良知”成为了最高本体,“格物”就是要格这一本体,因此刘宗周推崇慎独工夫。“慎独”本是“诚意”的工夫,但蕺山拈出一“独”作为本然最高性体,并将慎独工夫融进格物中,无疑是对“格物”更为内向化的心性论诠释,亦是将“物”的角色彻底退缩到心体的领域。或许可以说,心物一元论在刘宗周这里发展到了顶峰。
四、明清之际及清代的转变
到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这里,貌似出现了一种反转。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诠释,王夫之与朱子的立场更为接近,虽亦有不同。船山言:
凡天下之物接于吾身者,皆可求其得失顺逆之则,以寓吾善恶邪正之几故有象可见,有形可据,有原委终始之可考,无不尽吾心以求格,则诗书礼乐之教,人官物曲之事,皆必察焉,而《大学》之为学,于斯焉极矣。此学之始事必于格物,而详略大小精粗得失无不曲尽,故足以为身心意知之益而通乎天下国家之理。[13]
由上可知,船山大体上还是赞同朱子的格物说,只是所格之物的重点在于伦常教化之事。船山还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13]值得注意的是,“道问学”的传统在船山这里重新被挖掘,并被纳入“格物”的工夫范畴中,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是对朱子学的回归。船山亦言:“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13]他的惟器论反映出“理”或“道”的实体化趋向,对后来的颜李学派和乾嘉学派亦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在心物关系上,受明代心学的影响,王夫之依然持一元论的立场。其言曰:“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13]无论如何,学人对“物”的关注热度毕竟是渐渐增加了。
明亡之惨淡给士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冲击,一批明末清初学人开始批驳明中叶以来的心学,同时也意味着心物一元论开始瓦解。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曾这样说道:“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4]亭林主张 “经学即理学”,呼吁学人重拾先贤典籍中的智慧,可谓开创了清初“实学”的风潮。清初的颜李学派倡导笃行,尤其反对宋明理学家所喜之静坐、主敬、读书等工夫。颜习斋曾言:“二千年道法之坏,苍生之厄,总以物之失耳,秦人贼物,汉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并不知物,宁第过乎物且空乎物矣。”[15]又提出:“故吾断以为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15]“三物”即是六德、六行和六艺,皆与礼乐之事相关。由此可见,这一学派立志要将宋明人所悬空的实物亲身亲手进行践习,不能再空谈心性。“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戴望《颜氏学记》)颜李学派重视兵农礼乐等实事,虽未能对后来的考据训诂派产生影响,但至少将关注点从“心”转到了“物”,与顾炎武等人的实学思潮某种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由上可见,从船山、亭林到习斋,“物”的涵义逐渐由虚变实,学者对形上层面的心性义理也避而不谈,客观意义上的“物”逐渐从本体意义的“心”分离出来。发展到清中叶的乾嘉学派之时,“格物”的实学意味愈加浓厚。阮元在《大学格物说》中云:“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诸事,圣贤之道,无非实践。”[16]又说:“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16]于此,“格物”成了考究器数仪节的代名词,圣贤之道让位于繁文缛节。于是,“格物”完全成为了考据学的同义词,其道德规范功能逐渐淡出学者的关怀。清代学者多相信,真正回归于经书,最终定能经世致用,解决宋学清谈无用的弊病。章学诚就说过:
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习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17]
说到底,清人意图以经术治世,“格物”必然以经世之学为归依。
值得一提的是,明人徐光启受其老师利玛窦的影响,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其内涵早已与前人所言之心性修养毫无关联,而是接近于西人所说的“科学”。徐光启这样说道:
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它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18]
这里所说的“格物穷理”明显只限于自然界的物理规律,其最杰出的先祖可追溯至朱熹。明末的方以智也曾撰《物理小识》等书来探讨自然科学的问题。其实在徐光启之前,医者李时珍早已发其先声:“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本草纲目·凡例》)朱子格物论中的科学分支虽隐微不显,但一直都对后人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华传教士借用“格致”一词来传达来自西方的知识,其指涉科学与技术的含义倍受国人青睐,且在洋务运动中转化为中国谋求富强的理论依据,有志之士无不趋而学之。大批洋务学堂的兴办,民族工业与军事制造业的发展,正是“格致学”风行的见证。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对纯技术的追求进行反省,以严复为首的知识分子自觉将社会科学也纳入“格致学”的范畴。在严复连续发表的《论世亟之变》《原强》《救亡决论》三篇文章中,进化论与群学(亦即今人所说之社会学)也成为“西学格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初年,“科学”一词在中国初现。1906年以后,“科学”完全取代了“格致”,“格致”一词迅速消亡。由是,“格致学”的涵义逐渐由狭义的自然科学向广义的“科学”靠拢,“格物”所蕴含的道德修养义已不复见。从清初到清末,“格物”的涵义在动荡的局势中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格物”的科学义由此延续至今。
小组内的沟通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认真倾听别人的表达是对他人的尊重,敢于去交流自己的想法是对自己的担当;学会沟通,学会合作。
五、在心、物对立的现代潮流中
“格物”的诠释史,简言之便是从心物合一到心物分离的过程,又或者说由道德到科学的转变。晚明心学的玄虚流荡促使清人回归实学,晚清中国的内忧外患促进了全新泰西知识的传入,再加上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心”这一曾经风靡宋明两朝的流行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物”逐渐从“心”中独立出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起来,现代的科学体系也极少将人类道德纳入考查范围之内。这一独立的过程正是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主义发展的体现。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各大宗教中依旧持续着心主宰物的传统。
现代科学精神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于我们今天的舒适生活功不可没。然而,20世纪众多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仍有振聋发聩之效。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异化”的担忧,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鄙视,韦伯对“铁笼”生活的绝望,甚至卓别林电影里对工业革命的讥讽,无不传达了现代理性精神对道德的侵蚀,对人心的疏离。且看当今先进的电子设备,它能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使生活更加便利。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在大家沉迷于电子设备时渐行渐远。随处可见的低头族,地铁车厢中双目呆滞的男男女女,无一不是被电子设备奴役了身体甚至灵魂。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物”几乎主宰了“心”。譬如曾红火一时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居然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这一现象足以说明人工智能已逐渐入侵人类意识,并有取而代之的意图。人工智能是否真的能够取代人类思维?科学与道德的界限到底该如何划分?科学的飞速发展显然不能阻止其对人类意识的影响,哲学的在场感便显得尤为重要。现代科学在向精密化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对社会道德的影响。
在物与心越来越疏离的当代社会中,宋明理学关于“格物”的资源仍然值得我们去汲取和借鉴。“格物”的解释史发展表明,心物统一体的建构对于挽救时弊、改良社会道德风气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现代社会,重建心物统一体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生活的“物”,既有公物,也有私物。前者如政府大楼、医院、军队、甚至国家荣誉等,后者如私人财物、个人价值观等。对于公物而言,显然要用制度性规则来保护,这意味着其惩罚也必定具有威慑性。警察、监狱、法律等包含强制性和引导性的规则联合起来发挥作用,至少能保证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但除还此之外,还需要靠公民的自律。自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行为,并为之负责。这便涉及到伦理领域。一个社会如果靠大家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其文明程度必然较高,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必然较强,人们的公共道德意识便可与制度性规则一起,参与到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去。对于私物而言,则更是需要靠内心的自觉。这就要求严守心中的底线,以道德为本。须是先要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而后才能“推己及人”。儒家强调修身工夫,推崇倚靠良知指引行事,所针对的就是在制度约束之外的大量道德行为。说到底,还是要确立牢固的道德信念,才不会导致公私不分,肆意践踏社会秩序。
可见,当务之急乃是帮助人们在心中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感,而后心物统一体的重建才可能有希望。从古至今,“格物”的关键词都离不开“实践”。朱子和阳明都讲如何修身践履,但朱子的格物论先要确保人的行为合乎纲常规矩,而阳明的格物论则先要解决做人的道德动机。二者的有机结合或可为现代人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物”出发,可保障生活的稳定;从“心”出发,可维持道德的纯洁。何乐而不为?譬如近年来颇受赞扬的“工匠精神”,也许可被视为“心物合一”的现代注脚之一。这种精神要求“格物穷理”的刻苦钻研,并为人们带来“与物同体”的快感,可谓是继承了《庄子》中“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丈夫蹈水”等故事中的精神遗绪。工匠们的格物精神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优秀的实践榜样。现代人更应该多“格物”,多在“事上磨炼”,以锻炼个人应接事物时判断是非的能力,并从复杂多变的生活经验中反思自身的不完满处,使得内心愈加强大。如王艮所言之“安身”,身心找到安顿处,而后方可齐家治国,开物成务。这样的一种“实践理性”从来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谓“知行合一”。延此,文明才能在优秀的心灵之间递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有希望。
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其能随着时代的变换而被赋予相应不同的涵义,从而裨益于社会。“格物”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概念,其对宋明理学传统的塑造作用极大。在这一传统中,“格物”的心灵义以阳明为大,格致科学义以朱子为宗。现代科学正是后者的呼应。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心灵的修炼,尤其在心物疏离的今日。先贤心物合一的智慧在经典解释中是永不落幕的。
参考文献:
[1] 戴琏章,吴光.刘宗周全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771,639.
[2] 孔颖达.礼记正义(六O卷)[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673.
[4]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7-118.
[5]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5,316,16-17,193,188,411,193.
[6] 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9.
[7] 陆九渊.陆九渊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2,253,440.
[8] 朱杰人.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38,529-530,17,18,19,477,507,798,802,78,425,528.
[9]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808.
[10]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吴光,等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7,1018,132,49,91,49,118.
[11] 王畿.答聂双江[M]//王畿集(第 9 卷).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00.
[12] 陈祝生.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11.
[13]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1:48,404,1027,242.
[14]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M]//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40-41.
[15] 颜元.习斋记余[M]//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555,159.
[16] 阮元.大学格物说[M]//揅经室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54-55,471-472.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50.
[18]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M]//徐光启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