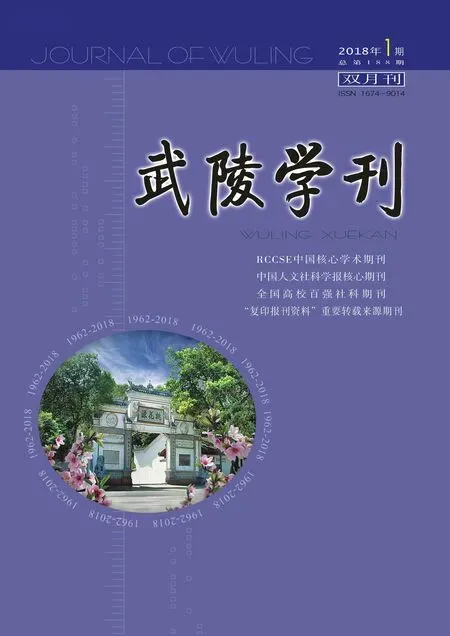《儒林外史》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
林 琼
(湖南文理学院 芙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刻画科举时代儒生群像的优秀文学作品,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了清代儒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既有对明清社会历史长卷式的宏观展示,又有对儒生个体栩栩如生的微观描述。作为以儒生生活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小说,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随处可见,分析小说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对我们全面了解科举制度、了解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点有着重要帮助。
一、小说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书写
(一)关于考试资格和程序的书写
科举考试是明清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是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根据史料可知,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之前还需地方学校进行科举资格考试——童生考试。童生指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1]31。通过了童生考试的读书人叫生员,尊称为“秀才”或者“相公”,考取了生员,方可获得乡试参考资格。生员除了地方学校生员,还有监生。明清最高学府为国子监,在国子监肄业的叫“监生”,监生身份也可以通过向政府缴纳一笔钱获得[2]。监生亦有资格同秀才一样参加乡试。小说第三回写道:“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1]28周进在众人的资助下,捐了二百两银子,得以“纳监进场”[1]28。
小说对这一科举考试资格的认定进行了描写。小说写道:“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1]31范进说:“童生实年五十四岁,……童生从20岁应试,到今考过20余次。”[1]31可见童生参加生员选拔考试的次数是不受限制的。第三回还提到了“录遗”,即选录遗才,是各地科考完毕后集中在省城举行的一次补考。“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1]28周进正是通过录遗进入科举考试正式程序的。
常人所知的科举考试是从乡试开始的,乡试一般在省城贡院举行。乡试考中者获得举人身份,考中举人民间又称“中老爷”,举人方可参加会试。周进“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1]30。会试的地点、结果以及之后的殿试和授官程序,均在这段叙述中反映了出来。会试通过者获得进士身份,方可参加殿试,殿试通过之后,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从周进参加科举考试到做官的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过程。科举制度打破了以血缘身份为基础的选人机制,成为寒门学子孜孜以求的荣身之路。
(二)关于考试内容和形式的书写
小说写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1]13这句话介绍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明清科举考试题目均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四书”“五经”是考试内容,八股文是考试的文体形式。小说借时文选家卫体善的话“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1]190,明确说明了科举考试作文的内容和形式。“代圣贤立言”,即用“四书”“五经”中的儒家观念来统治约束书生的思想,为统治阶级管理国家和人民服务;“有个一定的规矩”,即用八股文的形式写作。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即小说中所提的“时文”“文章”,有固定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吴敬梓对八股文的看法,从小说人物前后矛盾的言行中可以窥知一二。第十一回中鲁编修说:“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17鲁编修以一个科举考试的成功者身份对八股文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学好八股文可以促进读书人诗赋的创作水平,尤其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度挖掘。但从后文马二游西湖作诗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无法令人信服。马二作为八股文的选家,他逢人便宣扬这样的观点:“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1]143想必他八股文写作是得心应手的,但当他观览西湖美景后,却只发出一句感叹:“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156这八股气息浓厚的语言,其思想性和灵动性相比唐代白居易的诗《春题湖上》“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群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或者明代张宁《苏堤春晓》的“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都逊色多了,与前文中的“要诗就诗,要赋就赋”的创作期待完全不符。这说明当时社会对八股文的推崇已经渗透到文人学子的骨髓,严重束缚了其思想和表达。
吴敬梓深刻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借人物王冕之口表达了对八股取士之法的不满:“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1]13说明明清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有局限性的,过度提倡八股文而视其他文体为杂览,阻碍了文学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三)关于科举取士标准的书写
作为决定儒生命运的科举考试,其评价标准应该是科学完善的方才公平公正,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明清科举取士的标准缺乏客观性,考生作文的优劣某种情况下取决于考官主观好恶和阅读理解水平的高低。范进对于自己屡试不第的原因归结为“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1]31,而周学道第一次看范进的文章时认为他确实荒谬不知所云,待他读了三遍之后,却视作“天地之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并发出“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1]32的感叹。由此可知,科举考试的成绩评定与主考官个人的品鉴能力、审美取向、价值标准等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其取士标准缺乏客观公正。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出考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考官的学识水平难以令人信服。吴敬梓借王德之口说:“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甚么文章!”[1]57主考官的水平决定了科举选人的水平,而有些主考官的水平得不到公众认可,科举考试在科学性、公平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小说还反映了明清科举考试以文章优劣作为取士唯一标准的状况。科举取士只重文章,不深入考察考生的品行,故而使得许多品行低劣之徒如张静斋、王惠等能获取举人身份,辱没斯文、祸害乡里的严家老大忝名贡生之列,以致不得不使人们发出“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感叹。
(四)关于科举考试结果和影响的书写
科举考试的成败,直接影响考生的生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周进考中之后,周围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结交、拜会。范进取得秀才身份时,胡屠夫对他仍然是要骂则骂,要贬则贬,因为精明市侩的胡屠夫知道考中了秀才还不算进入了统治阶级的序列,能谋生的手段也仅限于“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1]34。当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之后,胡屠夫则一改以往对他的颐指气使态度,毕恭毕敬,称之为文曲星下凡,就连素来高高在上的张乡绅也立即来攀亲缘关系,“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并赠房赠银,“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1]40,而且“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1]41。由此不难看出,科举考试的成败给考生带来巨大变化。科举成功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带给人的命运改变和精神冲击,不仅关涉到考生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还联系着考生整个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范进的喜极而疯、范进家老太太因欢喜而昏厥最终归天而去等情节,不仅是合乎情理的巧妙安排,更是艺术的真实再现。
科举考试的结果还直接影响考生的社会关系,除亲友邻里关系之外,同窗师生关系也因之发生相应变化。周进首次在学堂见到梅玖,纵然周进年长许多,仍“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而梅玖对周进问话的回答却是“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为‘小友’,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1]19由此不难看出,学校里学生身份地位的高低与考试通过与否相关,而不以年龄的长幼为据,老友在小友面前是趾高气扬的,具有强烈的心理优势。考官与考生的关系被当作师生关系,考生对考官毕恭毕敬。如范进录取之前对周进的态度是“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轿前打恭”,“磕头谢了,起来立着”[1]32,一旦中举,其关系就转变成同僚和朋党关系,相互之间往往是利益共通、提携与帮衬。范进被钦点山东学道之后,周进托他关照录取自己曾经的学生荀玫,范进“专记在心”[1]77,在参考学生试卷中细细搜寻,直到见到荀玫已经录取方才放心。此时的范进和周进已超越纯粹的师生关系,而是同一阵营的互利互惠的同僚关系。
二、小说科举考试书写的特点
《儒林外史》通过再现具体的生活环境,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反映当时社会生态。作品中大量的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写,或在故事情节中出现,或作为社会背景陈述,虽时间、地点和方式各不相同,但其书写都具有以下特点。
(一)真实丰富
高尔基说:“文学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业,它是建立在真实上面的,而且在与它有关的一切方面,要的就是真实!”[3]有真实性品格的作品,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真实是文学审美价值追求的基础。
《儒林外史》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小说之一,它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尊重客观事实,用白描的手法再现生活。小说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相当丰富,提到的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术语有十几种之多,如“同科”“孝廉”“贡院”“龙门”“号板”“岁考”“太学肄业”等,涵盖了科举考试的方方面面,为读者了解科举考试相关内容留下了宝贵资料,真实反映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
小说客观深入地揭示了科举考试对中国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如周进、范进的中举情节展现了科举考试对考生命运的改变;马二劝说匡超人弃商从文反映了科举考试对民众精神生态的影响;关于应举辅导材料选编刊刻的描述再现了科举考试对市场活动的影响[4];科场作弊现象,如匡超人替人代考、安庆童生考试考场纪律混乱等现象的描写,真实反映了科举考试乱象。这些真实且丰富的有关科举考试的描写,为读者了解明清时期儒生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生动素材。
(二)精炼生动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要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环境和人物状态,就要求作者的表达逼真传神,让读者感同身受,有身临其境之感。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儒林外史》对考试的书写是精炼而不失生动的,既有知识性,更有文学性、艺术性。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中,吴敬梓写周进纳监进场,“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魏然中了”。“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署”。作者仅用短短几十个字,就概括叙述了周进从纳监进场到考中进士授官的整个过程,简洁凝练;其叙述似乎也平淡、冷静,但作者却巧妙地运用“魏然”一词暗示人物身份和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不乏生动形象。第七回写荀玫到省试高中之后“忙到布政司衙门里领取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程”,进京会试。精炼的叙述既让读者了解到明清时期的考生在乡试考中之后是可以获得官方资助去参加更高级别考试的惯例制度,也用一个“忙”字逼真地传达出了人物喜悦激动的心情。第十九回写匡超人替金跃考试,匡超人先化妆成军牢夜役,站在考场门口,点名时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躲在人背后,换过衣帽进行替考,“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作者用简洁的语言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科举考试的黑暗与肮脏,让读者在了解“交过五鼓”的科举考试具体时间,“学道三炮升堂”的仪式,军役手持水火棍监考的场面,学道点名领卷、归号答题的流程等的同时,也目睹了看似庄严神圣的科举考试被内外勾结、替考舞弊拉下神坛的混乱一面。
(三)分散呈现
《儒林外史》的结构比较独特,是一部以短篇系列故事串联而成的长篇小说,各个短篇之间相互勾连而形成整体,许多情节前后照应。小说关于考试活动的书写不是集中笔墨呈现的,而是贯穿始终,穿插在不同人物的生命历程中。第三回写范进中举,第七回写荀玫进学,第十六回写匡超人应县考、府试,第十九回写匡超人应岁考,第四十八回写邓质生进学考,这些部分都分别从某一方面再现了科举考试情形。有些章节并不直接写儒生参加考试的情况,而是通过介绍人物,如提到严贡生、严监生、廪生、学道等就让读者了解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人或事,在塑造马二这一人物形象时写到了与科举相关的活动——编写八股文选本等。小说关于科举考试的描写虽然分散零碎,但由于小说长达56回,涉及的社会面广,人物众多,作者有机会将考试中的种种状况得以从容地全面呈现。
吴敬梓之所以对科举考试书写得如此全面深入,与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他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六年探花,曾祖和叔祖两代,共出了6名进士,包括1名榜眼,1名探花,然而在其父辈一代开始走向衰落,其父吴霖起仅为拔贡[5]421。由于家族的影响,他对科场得意和久困场屋并不陌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也是他从小就被设计好的出路。他最初是热衷于科举的,在20岁时就考取了秀才,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几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29岁时参加乡试,却因“文章好而人大怪”遭黜落。屡屡落第加上家族中争夺财产的斗争,使他对科举考试有了深层思考,对科甲世家的虚伪和卑劣有了深刻认识,对现实和人生有了更通透的理解。他“渔猎百家”“涉猎群经诸史”[5]421,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收赋4篇、诗137首、词 48阕,著有《诗说》七卷、《史汉记疑》[5]423。36岁时,他有机会被推荐上京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但坚决推辞了。他不再参加任何科举考试,甚至放弃了秀才的学籍。吴敬梓深厚的文学文化功底和对科举考试的深刻认识,是他写出这部表现科举考试制度和儒生群像的宏篇巨著的主要原因。
三、小说科举考试书写的作用
《儒林外史》通过对一系列儒林人物的刻画,引导读者对八股制艺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世风颓败进行思索。小说中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对于小说批判主题的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讽刺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一)深化了小说的批判主题
《儒林外史》全面生动地展示了儒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作品中关于科举考试的写实书写,除了让读者了解到科举制度的全貌之外,还对深化小说批判科举制度的主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出现,具有选拔人才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意义,但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摧残人才,培植奴性,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为统治阶级选拔贤良英才的功能,成为统治阶级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统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小说通过如替考舞弊、互相提携等种种考场及官场污浊现象的描写,反映了科举考试的腐朽退化。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某些官员才能之平庸、品德之低劣、为官之昏聩,让读者对科举考试的积极意义产生怀疑。范进在丁忧期间言必称守制,行为却毫无顾忌;被称为“绩学有素”的他竟连苏轼也不知道。南昌知府王惠一到任就问当地有什么出产,讼词里有什么通融,一心只想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张静斋表面仁义谦和,实则四处打秋风,做事心狠手辣。严贡生残害乡里,迫害亲友,冷酷凶残之极。众多科举成功者所表现出的迂腐、贪婪和残忍,从侧面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的僵化与反动,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深化了小说的批判主题。
(二)丰富了小说的形象刻画
文学作品多用人物形象来说话。对于作家而言,刻画出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象,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儒林外史》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有的是作为社会时代背景出现的,有的是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出现的,这些书写对丰富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对明清科举制度的深刻认识,就不能如此生动而深刻地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
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周进、范进、马二、匡超人、鲁编修、王玉辉等读书人的心灵备受摧残,严重扭曲,他们有的丧失了人性,有的甚至完全泯灭了人性。本性纯良的匡超人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写假婚书,当枪手,同流合污且忘恩负义。做了30年秀才的王玉辉志在著书立说,劝醒愚民,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儿要殉节,不仅不阻拦,反而认为是青史留名的事,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封建迂腐士子的形象,其思想僵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却不自知,尽管女儿死后也出现过礼教和良知的冲突,但遮掩不住他的愚昧和迂腐[6]。从这些典型形象不难看出,封建愚民思想对儒生思想的禁锢使他们在科举洪流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人性中的真善美,走向了其反面。周进见到号板,眼睛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待到苏醒之后,又是一头撞过去。死不了则放声大哭,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发生在考场的一撞二哭的情景,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备受科举考试折磨的老童生的精神苦痛。在周进看来,不能进学,存在便没有意义。但当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立马成了科举制度的坚定维护者,成为禁锢考生思想的封建帮凶。他训斥童生魏好古:“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1]31周进的思想已经完全被科举制毒害了。如果没有科举考试的书写作为依托,没有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深刻体悟,没有对科举考试戕害人性的透彻认识,周进形象的塑造就难以如此丰满而深刻。
(三)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儒林外史》具有高超的讽刺艺术,其辛辣的讽刺贯穿于对科举考试的描写中。周进、范进中举前后,家人、世人对他们态度的惊人转变,让读者在发笑之余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范进进学回家,丈人胡屠户拿着大肠和酒来祝贺,这“祝贺”实则是一顿贬损和教训。范进找胡屠户借钱参加乡试,胡屠户一口啐在他脸上,骂他个狗血喷头,认为是“就想天鹅屁吃”[1]34。待到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听着风声就提着七八斤肉,带着四五千钱来贺喜,口称“贤婿老爷”,先前被斥为“尖嘴猴腮”的女婿一下就成了“才学又高,品貌又好”[1]39的老爷;胡屠户见范进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细节,使一个前倨后恭的市井小人形象跃然纸上,对胡屠户等势利庸俗之辈进行了辛辣讽刺。小说中,不仅屠户低俗,书生也一样没有品行。梅玖中了个相公就自视甚高取笑周进连个秀才都不是,不肯与他序齿。到了周进高中之后,竟然冒充周进的学生,路遇周进的长生牌,恭恭敬敬拜了几拜。胡屠户、梅玖之流为什么在他人中举前后的表现如此大相径庭呢?因为他们知道中了举人就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除了拥有不菲的俸禄外,还拥有了生杀予夺的特权。小说的这些描写,让读者在哂笑中思索,体现出含而不露的辛辣讽刺效果。小说对考试场面进行了描写:“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石,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1]263看似客观冷静的白描写法,却带有强烈的讽刺效果,形象毕肖地勾画出了主宰考生命运的神圣的科举考试制度千疮百孔之图景。
《儒林外史》在批判科举考试腐朽性的同时,为我们了解科举考试提供了一个入口,也打开了了解明清社会全貌的一扇窗子,小说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写不仅有着鲜明的文学意义,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意义。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龚延明.科举考试与《儒林外史》[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2):18-23.
[3]高尔基.给安叶托勃罗伏尔斯基[M]//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曹葆华,渠建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7.
[4]刘海频.《儒林外史》呈现的科举活动与科举观[J],教育与考试,2008(4):44-49.
[5]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杨德柱.谈《儒林外史》与科举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4):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