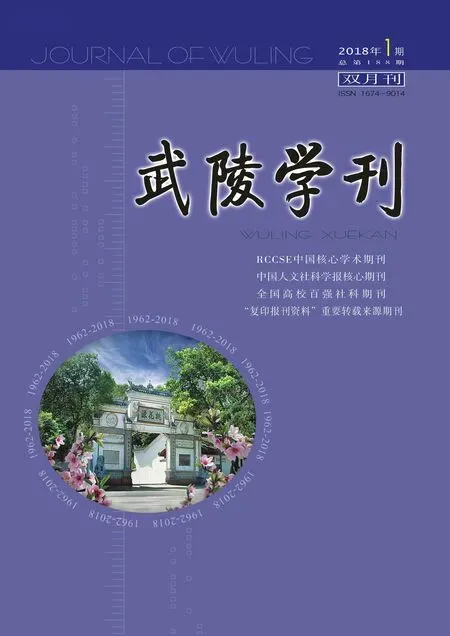自我的确证与救赎
——评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一
严歌苓的《芳华》书写了一群正值芳华之年的男女士兵的青春轶事,展示了特定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对异性之间交往的严格规约,这种规约与青春期特有的荷尔蒙冲动和性成熟阶段的身体觉醒构成激烈冲突,“曲线言情”的含蓄晦涩和“隔空示爱”的身体禁忌,成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支配下异性之间流露好感和爱意的权变之策,由此常常发生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甚至“表错情”“会错意”的尴尬局面。小说的核心情节——“触摸事件”便是引发当事双方以及一众旁观者剧烈心理震荡的极端事例,这一“触摸”引发的身心伤痛不仅改写了主人公刘峰的人生走向,也波及与之相关的何小曼、林丁丁、郝淑雯、萧穗子等人。“触痛”深植于每个人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需要用漫长的未来岁月去反刍、去认知、去审视、去消化,抚平创伤的过程就是个体人格确立和成熟的过程。
在严歌苓以往的作品中,与作者生命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的书写,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包括她与那个操着山东腔汉语的FBI探员周旋、斗智的散文《FBI监视下的婚姻》以及同一题材的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等,都带有鲜明的“有我”写作的特点,就叙事姿态、感知深度、切入角度而言,这些作品不同于《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寄居者》等讲述“别人的故事”“听来的故事”的小说,对于后者,作家发挥才华、精雕细琢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叙事”本身,即使触及灵魂也是人物的灵魂,抽象的灵魂,与作家的生命意识终归有些距离。严歌苓深知采访想象的细节与经历回忆的细节有着质的不同,尽管两种叙事都是虚构。《芳华》的字里行间散发着特有的与作者痛痒相关的体贴和亲近,严歌苓说它是“诚实”之作,而回避了“真实”一词,意在强调基于自我生命体验的一种诚恳求实的写作态度,“诚实”也是小说最终呈现的质地。作者12岁入伍,直到25岁转业,在军营中完成人格和人性最初的觉醒和蜕变,部队文工团的生活是她小说取材的一个蕴藏丰富深厚的矿脉,已多次出现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灰舞鞋》《穗子物语》等小说中,这些“少作”很像一次次的排练和预演,作家一遍遍用理智剖析、用情感浸润那些挥之不去的爱意和痛点。《芳华》是人到中年的严歌苓再次向青春岁月的回眸凝望,也是对蕴含在家国历史之中的个体记忆的再审视——对它的“山山水水”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深度开掘和打捞。作为“有我”写作的又一次倾情试验,《芳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直接回到了成长的原点,从身体出发,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造成了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触痛”既是刘峰、何小曼、萧穗子等人成长的代价,也是迫使他们走上自我确证和救赎之路的出发点和转折点。
二
《芳华》描写一群跳芭蕾的男女士兵在规定情境内(台上)外(台下)的“表演”,从表面看来,这种切换并无太大变化,因为两种“表演”的核心主旨都是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区别是上台要化妆,要起范儿,要有过硬的芭蕾基本功,要摆出夸张的表情和造型,给人的感觉是演员周身每个细胞、毛孔、神经末梢都“紧绷绷”的,被澎湃的革命豪情鼓荡着、沸腾着、燃烧着,将意识形态和革命精神贯注全身,以一种极致化的舞蹈语汇作讴歌鞭挞兼而有之的宣讲,尽情展现宏大壮阔的革命美学。台下则相对松弛些,但也是外松内紧,卸妆并非露出本来面目(所谓“本我”的自然流露),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生有统一的“剧本”和“程式化”的表演规范,大家在“面具”的掩护下隐身,偶然在至为逼仄的个人空间流露一下天性——这种流露往往是下意识的——已属极为不智不慎的危险之举,一俟觉悟到其溢出惯性的异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震悚效应是难以言表、难以估量,甚或难以承受的。小说男主人公刘峰就因一次表演“事故”——对心仪已久的女孩林丁丁的错位表白以及被认定为“性袭击”的身体触碰——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其实,刘峰在台上台下都是个好演员。台上他不靠天赋而靠勤奋,以跟头翻得好著称;台下他乐于助人,他的名字被四川人读成“雷又锋”。就本质和本色而言,他确实当得起“又一个雷锋”的绰号,特别是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境界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因此嘉奖不断,口碑极佳,得到领导和群众上下一致的推崇,早被归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神圣一族”。台上台下的奔波,角色和本我的切换,对刘峰而言不是难事,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秉持一种“去表演化”的诚实和诚恳,不做作,不偷懒,不取巧,宠辱不惊,中道而行。这种特别自然的协调统一的状态与他那个惹眼的形象很是贴切——“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1]6一双脚,两种鞋,被刘峰穿出了深刻的艺术哲学,即生活与表演的合二为一、协同共在。以这种诚实笨拙的方式却收到左右逢源的效果,草根出身的刘峰本该在军中“舞”出一个不错的前程,未料却折戟于芳华之年本来被压抑得近乎沉睡的荷尔蒙的一次意外蠢动——小说中所谓的“触摸事件”。
《芳华》的英文书名叫做You Touched Me,直译便是“你触摸了我”,这里的“你”和“我”自然是两个异性。在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极度提纯,禁欲严苛到荒唐的年代,异性之间的情欲萌动,特别是身体的接触,都被视为犯忌和越轨的行为,类似行为尤其不应该发生在获得“全军学雷锋标兵”荣誉称号的刘峰身上。但森严的禁忌和荷尔蒙冲动较量的结果,证明了刘峰没有“高尚”“纯粹”到丧失人性的地步,尚残存着人所共有的“臭德性”。他暗恋林丁丁,用土法粗制的“甜品”满足三个女兵的口腹之欲,实际只为向林丁丁一个人示爱。本来这种不清不楚的情愫及其表白方式像温吞水一样沿着未明的河床流淌着,也许会流于无形,但从林丁丁灯笼裤里飞出的“半截被血泡糟的卫生纸”袭击了刘峰,彻底点醒了他的懵懂,不容他再自行暧昧下去。正如作者以萧穗子的名义对他的揣想:“他的欲求是很生物的,不高尚的。但他对那追求的压制,一连几年的残酷压制,却是高尚的。他追求得很苦,就苦在这压制上。压制同时提纯,最终提纯成心灵的,最终他对林丁丁发出的那一记触摸,是灵魂驱动了肢体,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1]33刘峰这一压制已久也酝酿已久的“灵魂的触摸”,并没有触发林丁丁的爱意,反因她大呼“救命”而性质骤变,刘峰的单纯之“爱”单向之“爱”被恶意解读,终成他命运急转直下的驱动器。
在众人眼里,刘峰是个“偏执”的“好人”——“无条件、非功利的好”,“充满圣贤的好意和美德”。这样的圣贤式“好人”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有爱情的,因为爱情的自私、排他以及不可避免的“荤腥感”,会大大降低一个“好人”的成色,甚至使其变质。而芳华之年的爱意萌动,永远是身体先于理智,带有盲目、失控的基因缺陷,必须经过试探,乃至试错的曲径,才能悠游于“真爱”的圣境,也只有在“试”和“错”中鉴别他人,认知自我,一个人才能在爱情历练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但刘峰身处一个不允许“试”,更不允许“错”的年代,萧穗子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刘峰的情况更特殊,作为常人的一个例外,他的言行必须符合官方和公众舆论对他的“雷又锋”形象的塑造和期许,偏偏大家都处在那个“混账的年龄”,“你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1]25。别人可以“慢慢咂摸”恋爱之于“身体”的“滋味”——“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是性部位。头发梢、汗毛尖都可以达到高潮。从两只手打颤带汗地握到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厮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1]40,刘峰只能锤炼意志,与身体的出轨欲念激烈抗衡。当刘峰终于等到自认为合适的表白时机时,他设想“满拧”的局面令他惊愕,林丁丁大呼“救命”的背后是三连问的潜台词:“怎么敢?!”“他怎么敢?!”“他怎么敢爱我!”使林丁丁感到受辱的不是刘峰“触摸”了她的身体,而是语言的暴力,“爱”这个字眼从刘峰这个“不对”的人嘴里迸出,不止林丁丁,所有女兵都感到拧巴。并非刘峰“不配”谈情说爱,就身体和外形条件而言,他有充足的本钱,狙击这个“爱”字的是他的“圣人”名誉,说到底,“圣人”不该“惦记”异性的身体,有着“发臭的人性”的女人也不会爱“圣人”。刘峰和林丁丁双方意念的双重错位,是“触摸事件”发作的根苗。
多年后,作为局内人兼旁观者的萧穗子对此事件作了一番心理学和人性论的深度探测和剖析:“如果雷锋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超我人格(Super-ego)’,那么刘峰人格向此进化的每一步,就是脱离了一点正常人格——即弗洛伊德推说的掺兑着‘本能(Id)’的‘自我(Ego)’。反过来说,一个人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同时可以认为,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不可靠,以及他的变幻无穷,不乏罪恶,荤腥肉欲,正是魅力所在。”[1]54-55作为“常人”的一众战友,未必有心理分析的功底,却自具本能的敏感,他们不约而同对刘峰进行了“去身体化”的灵肉肢解,这种执念一方面塑造了刘峰非凡趋圣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所有人对被推上神坛的刘峰不无腹诽和质疑,在“这群充满淡淡的无耻和肮脏小欲念的女人”眼里,过于“素净”的刘峰是缺乏魅力的,同时,“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刘峰就这样被钉在一个表面光鲜实则深受鄙夷的尴尬位置动弹不得,人们一面利用他的善良无私——利用得那么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甚至有些放肆无耻,因为“雷又锋”天生是要做“好人好事”的,“脏活累活”自然归他干;一面又私下期待他暴露人所共有的“丑”和“脏”的侧面,“触摸事件”爆发后,众人一哄而起,协同刘峰本人把他“说得不成人样”,刘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的处分。“雷又锋神话”至此彻底瓦解。
令刘峰始料未及的是,意在“爱抚”的“触摸”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弹力和后坐力,从极端的好人到坏到不像个人,此间的落差,让刘峰体验到那种失重的眩晕和被重力所伤的痛楚。他抛弃了整箱的荣誉证书,带着被辜负被践踏的“爱情”创伤,投身对越反击战的战场,他以一种自虐的冲动意欲在战火中献身,彻底解脱的同时,亦在凤凰涅槃式的壮烈中重塑英名,给强加于他的污名恶意反戈一击,同时让辜负他、作践他的人们愧悔终生。这是他能设想的最决绝最狠毒的报复,但命运只夺去了他的右臂——那只实施“触摸”的手臂,“触摸”留下的烙印式创痛依然扎根在记忆深处,鲜明而生动。此后,身心遭受重创的刘峰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回归平凡的老百姓生活,沦落到芸芸众生的底层,爱情受挫,婚姻不如意,并没有改变他沉淀在血液里的“雷又锋”特质,带着挥之不去的痛感,他结缘风尘女子小惠,善待遭人嫌弃的何小曼,不管林丁丁反应如何,不管别人如何品评议论,他对林丁丁的“爱”始终未曾消泯。刘峰用余生的时间努力扳正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既非纯粹的“雷又锋”,亦非“脏得生蛆”的“资产阶级的茅坑”,他只是刘峰,善良,纯朴,诚恳,一如继往地把凡俗的生活尽可能过得合理且美好,不违逆人性人情。
三
如果说刘峰被定义为“不可触摸”异性的雷锋式“圣人”而尽尝“(被)神圣”苦果,那么,年幼丧父、渴求他人(包括家人、战友和异性)关爱却不可得的何小曼便成了刘峰的镜像——处于“无人触摸”的另一极端。二人各自从高低两个“非人”的起点走向“人”应有的生活界面,何小曼相伴刘峰走过他人生最后的旅程,既是“作者的安排”,更是受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召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何小曼自从到继父家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遭人厌弃的“拖油瓶”宿命便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她,为与这一宿命抗争,她几乎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包括采取自虐的方式乞求爱抚,以毁尸灭迹的办法实施报复。比如,用冷水浸身,炮制高烧,只为享受母亲爱抚病女时那刻骨铭心的拥抱;为与同母异父的妹妹争夺生父送给母亲的那件业已千疮百孔的红毛衣,不惜将之偷偷染黑,重新编织,贴身穿着,毛衣的温暖似乎使她重投父爱的怀抱。参军,当上令人艳羡的文艺兵,成为洋为中用的红色芭蕾舞台上的一员,并没有改变何小曼遭贱视被抛弃的窘境,她在台上台下都属于潲泔零碎、可有可无的角色。当她用海绵填充乳罩的秘密不慎曝光,竟遭众女兵围堵责辱,似乎她不配有爱美之心,更不应有如此明目张胆近于无耻的爱美之举。排练时舞伴朱克公开拒绝托举“馊臭”的何小曼,没有一个男兵愿意“触碰”她的身体,他们甚至放弃了借托举动作“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的机会,只因那个异性是遭众人厌弃的何小曼。何小曼照例用冷漠应对这种意在侮辱和践踏的冷遇,此时,刘峰主动站出来与她搭档,化解尴尬局面,使排练得以进行。这对刘峰而言,或许仍是做了一件屈己助人的“好事”,就像他担任吃力不讨好的“抄功师傅”那般自然,然而,刘峰这番主动给予而非何小曼苦苦索求而来的“好意”,对何小曼而言意义重大,他托举起的不仅是何小曼的身体,更有她一向敝帚自珍而他人熟视无睹的人格尊严。一个动作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一个人,被“触摸”毁掉的刘峰用“托举”成全了何小曼,值得她永远铭记怀想。她所感激的是刘峰那轻柔的“触碰”——借着“公家触碰”向她输送了“私人同情”,所以,何小曼明知刘峰并不爱自己,依然怀着报恩的心情照顾这位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战友,被打入另册的相似遭际使他俩彼此取暖、相依为命。
在被刘峰“托举”之前,20岁的何小曼“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因为珍视母爱,入伍之初,她竟将母亲为她编结的发辫原样保持两周之久,最终满头头发已无法拆解,只能一剪了之。匮乏与渴求是成正比的,对关爱的渴求迫使何小曼小小年纪练就了高超的演技,就像一个上瘾的鸦片烟鬼,驾轻就熟地循着老路抵达妄想的快感。她无时无刻不在“表演”和“酝酿表演”,生活本身异化为一场场充满矫饰的演出。曾以发烧成功博取母亲抚慰的何小曼,在一次高原慰问即将解散的骑兵部队的演出中,故技重演,且愈演愈烈,竟借体温计耍花招,自导自演了一出带“病”上台的“苦情戏”,“持续的发烧”使何小曼获得“轻伤不下火线”“救场如救火”等高调赞誉,领导的嘉许表扬,战友的关怀照顾,观众的热烈掌声,纷至沓来,包围了何小曼,使她沉醉在富贵梦温柔乡中难以自拔,直到真相败露被处理下连队。事过境迁,何小曼并不因受惩罚而懊悔,却像儿时偷尝藏好的美食一样反复品味着虚荣心得到满足时那种直抵巅峰的幸福感。
当这种建立在他人评价上的人生狂想瞬间盛放,骤然蹿升到辉煌顶点时,何小曼也被驱至精神崩溃的临界点,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她不择手段孜孜以求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的梦想,她被梦想成真的一刻猝不及防地“伏击”。身为对越反击战中一名战地护士,何小曼做了一件本分之内却大大超乎其体力之外的事——将一位重伤的战友拖回后方医院,救了他一命。这本不足以令她暴得大名,通讯干事和宣传部主任以生花妙笔将之夸饰成周身洋溢着无私美德和浪漫诗意的“战地天使”,于是,一向不受人待见的何小曼变成了众人面前耀眼的明珠,连多年未曾谋面的母亲也来看望英模女儿。就像乍听中举喜讯的范进一样,命运180度的大逆转令何小曼手足无措,天壤之别的境遇变化使之顿生命运吊诡的云泥之叹,何小曼难以应对急速飙升给身心带来的负重感,无法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为英模量身打造的“剧本”恰到好处地完成这一角色,她的“演技”出了问题,表现出进退失据、言语失范的“病态”,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她恢复了生父的“沈”姓,与刘峰延续着基于复杂背景的单纯交往,历经人生俯仰之间的苦苦挣扎,何小曼终于在“人”的层面落停。
四
关于何小曼人生的全部真相,作者并不否认自己认知上的局限性,“小曼成长为人的根,多么丰富繁杂,多么细密曲折,埋在怎样深和广的黑暗秘密中,想一想就觉得无望梳理清晰”[1]154。关于刘峰更是如此,在昔日战友的闲谈中,“刘峰被我们谈一次就变一点样”。显然,刘峰和何小曼,更多以想象的方式活在她们编撰的语流中。然而,是什么让她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两个背着处分忍着屈辱离开文工团的人呢?追本溯源,当年的“触摸事件”像一枚击中心湖的巨石,给当事人和旁观者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心灵震荡。记忆的反复闪回透露出萧穗子等人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煎熬挣扎,这种情绪上的不适感和道德上的愧疚感折磨着每一个“红楼”中人,她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虐者,在因“触摸事件”引发的针对刘峰的“批判会”上,这些自私虚伪懦弱的人们,不约而同,火力全开,把对自我的“嫌恶”倾泻到已然“落水”的刘峰身上——“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打得再痛也没关系。我们曾经一次次放过自己,饶了自己,现在不必了,所有自我饶恕累计、提炼、凝聚,对着刘峰……通过严惩刘峰,跟自己摆平。”[1]162-163然而,转嫁惩罚终究不是救赎之道,不仅不能“摆平”自己,这种青春华年犯下的错误,历经岁月的累积沉淀,反而加重了各自的罪孽感。
当林丁丁、萧穗子各自携着生活所赐的身心伤痕邂逅刘峰,遥远的“触痛”再次被唤醒,鲜明而犀利,她们无可选择地回到“触痛”的原点审视自我,这不再是私人恩怨的斤斤计较,而是一段自我救赎的艰辛之旅,如同刘峰和何小曼一样,每个人做“人”的价值和权利并非不证自明和先天赋予,而需自我确证和努力争取,所不同者,只是起点和途径的参差错落,交叉缠绕,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内蕴清晰的人性理路。
严歌苓多次化身萧穗子,几近残酷地揭触芳华之痛,青春之殇,正是在以写作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自我,就此而言,《芳华》并未终结,这一母题将会幻化出万花筒般的繁复文本,像关于刘峰的叙述一样,“谈一次就变一点儿样”,《芳华》让我们对严歌苓未来的写作充满期待。
[1]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