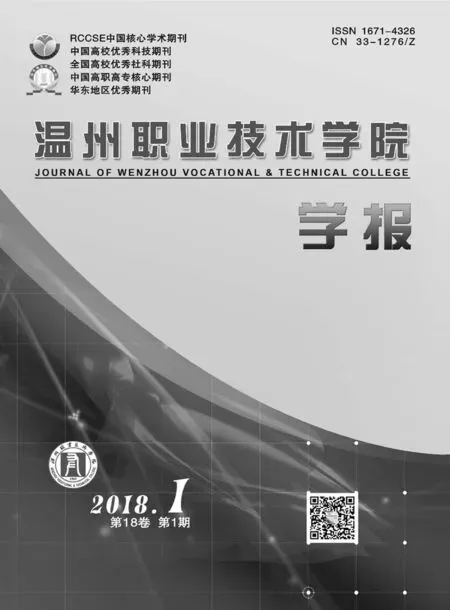表征生活意义、生命意识、生态意向之“蛋”
陈小刚
(中共平塘县委党校,贵州 平塘 558300)
“蛋”,即食即药、即凡即圣的实存之物和生活之相,与之关联的俗、礼、神话(文学)等于空间上分布广泛,于时间上绵延不断,链接生育与生命,确认表象与意义,是管窥生活世界的场域。以“蛋”为焦点和原型,全面剖析关涉它的风俗、礼节、语言、神话、宗教仪式,有助于理解人们意识深处的族群本质,即认知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进而透视它的生命意义和文化价值。
一、表象与意象:“蛋”与生活意义
在身体与外界的交互作用基础上,人们对于“蛋”的感觉印象和记忆图像不是刻板静态型的,而是涌动鲜活的,它们把生活的“蛋”之物(things)与事(events)同认知的表象(representations)、符号和意义相耦合,通向本然的生活世界。这种由文化、社会和个体构成的生活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和场域。不仅仅作为图像和事物的“蛋”于在场和缺席中,还发轫着多样性的表象和意义,是理解生活世界的一种独特场域和视点。
当下,以“蛋”为中心的日常生活(食蛋与节庆)、社会生活(礼仪、民俗)和精神生活(语言、宗教、文艺)交互作用,于心灵的知觉中,形成丰富的表象,即“蛋”既是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也是标记文化心理的特殊符号,是生殖崇拜(生命力)、婚恋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潜藏者。这种以表象的方式思考是其所是、存在之为存在,正好就是生活世界的本然。“蛋”在直观而自明的生活世界中,结构性地联系着人们的日常饮食(食蛋)、时间节点(人生与节庆)、精神活动(语言、神话、宗教),为生活中交互主体之间交流提供共域(文化知识背景)和平台,于这里彼此之间可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作为一种普遍民俗和生活必需[1],“蛋”圆融了世俗与神圣、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结构性地呈现着不同族群的宗教意识(民间信仰)、伦理道德、文化追求和价值认同。
任何族群、个体首先都必须解决生存、生活的物质需要,因为这是生命形态维持新陈代谢等功能的本质规定性。蛋以其食用功能、药用价值、保健作用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经久不息,至今在汉族和苗族、侗族、土家族、毛南族等众多族群中保存着以“蛋”为中心的鲜活世界,即头生蛋、糖蛋(特别是坐月子食用)、彩蛋、红鸡蛋(红喜蛋)、咸鸭蛋等这些“图像和表象(representation)是最为原初的意识之象”[2],是生存和物质需求的深刻记忆。在食蛋过程中,人与“蛋”(人与事、人与物)形成了交互作用,食蛋就变成了关涉人—“蛋”(关联它的事与物)意义场,即维持生活(生命)、祛邪求安、庆生乐寿。有着食用、药用、保健价值的蛋(蛋黄、蛋清)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是维持生命健康运行不息的应有之物;蛋之外壳与内在生命链接,食蛋脱壳意在生命挣脱束缚(脱壳即脱离邪祟、困境),从而期盼平安吉祥;食蛋总是与生命诞生、月子、满岁等联系在一起,意在把“蛋”与人之生命力互拟,庆生之大事(生,命之缘起与开端),生日吃寿面和食蛋追求吉祥长寿,表征生之贵。这些都在凸显一个基本事实,即“蛋”不仅仅是物与事,更是各种生活表象与意象的集合,表征一种人—“蛋”互往的善美生活。
特别是在节日礼俗的社会生活中,“蛋”已成为人与人、人与社群交互的媒介[1]。在春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食蛋、送蛋、斗蛋、碰蛋等习俗广泛流行,成为人与人、不同群体之间交流的场域。春节普遍食蛋,意在驱邪避瘟;三月三上巳节,河南、江南各地均有食蛋风俗,视之为传统节日的壮族要食彩蛋,借助歌会,青年男女交际碰彩蛋,以此表征男女择偶与爱情;寒食节雕画鸡蛋、送彩蛋、斗鸡子,古已有之,东北、山东(即墨、莱阳、东营等地)、台湾地区清明吃蛋,或求庄稼免灾,或喻生生不息;端午节,东北、山东、湖北等各地食蛋之俗,广植民间,“蛋”能祛病辟邪。甚至于众多民族中人生之诞生、周岁、婚娶、丧葬,“蛋”俗遍布其中,成为节日礼俗之必需。将“蛋”圆融于节日礼俗生活中,除上述功能和意义外,更为突出的是,“蛋”表征爱情婚姻,是经验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媒介,如较为典型的有斗蛋(娱乐与交往)、碰蛋(壮族)、抢蛋(侗族)、红喜蛋(毛南族)等习俗。“蛋”在这些民族的心灵和认知中,显示为爱情、婚姻、生育、美满的表(意)象。
“蛋”于日常生活、节日礼俗等生活形式中,不仅养人(营养价值高),更能育人、医人(药用、文化治疗价值)。日常语言中的以卵击石、见卵求时、危如累卵、画卵雕薪(穷奢极欲)、“二卵弃干城”(以小过失而忽略其大节)等是教化人心、阐明道理的符号观念。在“蛋”“卵”互指的基础上,形成的“宇宙鸡子说”“卵生人”等神话及“蛋”俗观念,从另一个视域表征人们的心智运作和精神世界。与这些关联密切且颇具文化价值的蛋卜,衍生出新的意义空间或超越蛋本身的意义,此中人神沟通,丰富了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古者巫医不分,这种观念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医药医疗实践活动中保存至今。蛋卜就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包括烧蛋、滚蛋、打蛋、压蛋、割蛋、砸蛋等形式。作为一种民间医疗方式,蛋卜是巫风存留的映像。这种看似简单而寓意丰富的民俗(或民间信仰),将神药两解,呈现出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和文化心理结构。卜蛋人,神人沟通的媒介,或通灵(萨满)、附体治病救人。依据人类学的观点,认为致病的原因不仅仅由于自然环境(细菌、病毒等)与身体内在结构(新陈代谢、自我复制、休息反应功能等)发生变化,亦缘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和影响。因为不同族群在实践方式、生存发展、资源禀赋、生活形态、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了分殊的生存、生活状态,不同的疾病便会发轫于这些迥异的社会环境之中。当然,与经济社会、民间信仰、宗教仪式、族群交互相关联的蛋卜,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医药实践(却有类似于精神安慰剂的效能),而是一种文化治疗(信仰—精神救赎),是文化机体、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关涉“蛋”的日常生活、节日礼俗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宗教)生活,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关联的表象—意义的生活世界。这里,“蛋”之表象与意义、符号与存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联,绝不是片面的武断或任意性,而是有着内在的心智链接。这种心智链接表征为理据性(motivation)和象似性(iconicity),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中的隐喻认知机制。
二、隐喻与认知:“蛋”与生命意识
于本而言,生活与生命是本然统一的。复杂多样的“蛋”意象、“蛋”俗、“蛋”礼、“蛋”文化现象构成了独特视域的生活世界。“蛋”的形式、内容、结构、意义及相关联的其他意象和事物,不约而同地描述、解释着内在深刻的生命意识。这种“蛋”与生、生育(生殖)、生命、生命力等生命意识的耦合,有赖于背后的隐喻和认知。
像“蛋”一般的无限多样的物体和现象构成了生活世界。在这里有着复杂繁盛的形状、质地、颜色,人们用何种方式去感知和命名呢?实验心理学给出了解释性答案,即用焦点和原型做定点。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文字的起源凝结着古人心智运作的痕迹,便于寻究其中的认知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字上看,“蛋”(),声符“旦”(同蛋音),形符鸟,《说文解字注》云“渴鴠也”,指夜鸣求旦之鸟[3]。“蛋”(形、音、义)实则是一种深层认知方式和心智构造的表达,即旦、鸟直接相关到蛋、鸟密不可分;鸟夜鸣求旦表征一种夜—旦时间轮转,求旦(蛋)之新,即把重新开始与生命(时间延续性)互拟,故蛋有新生之义。这种文字造法,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身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觉知到“蛋”(卵)生育的自然现象。借助这些经验,人们在心灵中运作,将“蛋”与生命内在联结、互拟,这就形成了两个不同概念(却有着某种象似性)的“蛋”与“生命”的隐喻模式。
所谓隐喻(metaphor),实乃一种心智的表征,不仅仅是思维现象,更是认知机制。它基于身体认知和概念的体验性,为类共性或家族相似的概念提供解释。普遍的“蛋”俗和鲜活的日常“蛋”观念,正好凸显这一道理。一种表征生命缘起和自然生机的“蛋”俗文化,是各族民众真实的生活写照,它是一种潜隐—显现的文化符号,表达着一种深刻族群记忆和民族认同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蛋”俗,虽然在背景、具体方式、寓意上存在差异,但从中可呈现各族民众隐喻的认知方式和真善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意义存在的人,天生有着反思自我的官能。生何来,死何去,生死之间何为等这些生命问题,都会成为自我反思的方向。最初的生命现象肇始于宇宙“蛋”,汉、壮、苗、侗、藏等族群中的创世神话,都在以原始思想和隐喻的方式阐明“蛋”生天、地、人、万物的生命意识。“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三五历记》),就是力图把天、地、人之生命与“蛋”互拟,形成共源性和本质性。现实的人之生命的缘起同样借以神话模式(“卵生人”)而表征出来,从而把“蛋”—生命、“卵生人”—鸟图腾(鸟崇拜)聚合形成内在的认知图式,即隐喻。因为谁都不能否认“蛋”(鸡子)具有孕育生命、繁殖后代的功能这一经验事实,基于这点,早期“卵生人”文化、生殖崇拜现象与生命息息关联,既存于意识深处,又被生活表征出来。《诗经》 《史记》等元典都记载“卵生人”神话,如“契母简狄,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和“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其隐喻的基本结构为:玄鸟坠卵—女吞之—生育始祖,鸟、蛋、女—生人。这种“蛋”与神话(“卵生人”、鸟崇拜)喻意生命的方式,在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亦被存续下来,都有关于“蛋”与“卵生人”神话的相关记载,后来,西方复活节以彩蛋习俗承续下去,并将“蛋”视作生命与复活的情感符号和神圣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蛋”除了隐喻生命外,还常与一些指示人之性质的形容词相结合,如糊涂蛋、坏蛋、笨蛋等,都在以“蛋”喻人。
可见,“蛋”俗(“蛋”观念)是各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它不仅表征出各自的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更是理解族群生命意识的新视角。在人的生与死之间,它描述着不同的生命节点:诞生—满月—周岁—成人(冠、笄礼)—婚礼—寿诞(生日)—死亡。在众多族群中,形成一种隐喻投射模式:蛋—社交媒介—爱情信物—婚姻表征—生育表达—生命象征。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碰蛋习俗,表达出“碰蛋—蛋破—孕育生命”“男女结合—孕育生命”“碰蛋—爱情、婚姻”的投射(mapping)过程。在英国、法国、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也有以“蛋”喻爱情、婚姻和生育的习俗。我国北方、西南等地区广泛存有生育食蛋习俗(女性坐月子食蛋),这与早期的生殖崇拜和鸟图腾相关联。“蛋”与“生命”的耦合,是它们的共同主旨。在死生一也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视死如视生,信仰灵魂不朽,以“蛋”喻指生命之魂。傣族以蛋卜择亡者安息之所,黎族投蛋掷地,以蛋破处选吉地(墓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现存生活的印证,而现代考古发现提供了更为生命化的历史图景。大汶口时期东夷人墓地女性死者口含石球、陶球,这是上古“卵生人”神话的遗存,是死归生处,返朴于自然的表现。“卵生人”—生育—鸟图腾与生殖崇拜—生命的认知模式,即把食蛋与吞卵、生圣贤与生人、“蛋”与生命相互结合的隐喻思维,在普遍的“蛋”俗文化中承续下去。
以“蛋”喻身,以“蛋”喻魂,以“蛋”喻命的身体认知,凸显了隐喻机制和文化心理结构。其隐喻认知机制表现为理据性和象似性,在二者的基础上又投射出文化心理模式。所谓理据性,本质上突出了形式与意义、符号与存在之间那种可理解、可论证的非任意性关系(理据性具体表征在词形(复合词)、词义(转喻)、语法(句法结构)上),其集中体现为不同形式的象似性,而象似性又指形式与意义、符号与存在在关系和结构上的相似[4]。那么“蛋”喻生命的认知方式就可借此阐明。“蛋”的基本结构为蛋黄、蛋清、蛋壳,宇宙的基本结构为天、地、人(万物),借助古代天文学中“天圆地方”说和“宇宙鸡子”说,以“蛋”喻宇宙,以蛋喻整体生命(宇宙或天地生命),进一步凸显人文源于天文的基本文化认知图式。“蛋”的基本功能是提供营养(维持生命)和繁殖后代,表现出生育、养育功能;而人(特指女性)为后代提供营养(在子宫内以脐带给婴儿营养和产后母乳提供营养)和生育后代,表征出生育力、养育力等特质,借助古人“卵生人”、鸟图腾(生殖崇拜)等元语言方式,将“蛋”的生殖、养育功能与人之生育、养育功能互拟。“蛋”形圆,人生目标在于完美和圆满,依据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尚圆图式(审美、认知),就把“蛋”—形状圆—完美和人生—幸福—圆满耦合,从而形成追求团圆、完美的善美人生意义原型,也是生命意义的终极表达。
“蛋”俗文化中,一种表征人之生命(善美人生)、自然之生命、天地之生命的场域是自明的,其中潜隐的生生不息之生命意识,正在内化和外显为“共生性”“合一性”的生态意向。
三、共生与合一:“蛋”与生态意向
“生”之功能性,向来作为“蛋”之潜能(生生不息之势能)被广泛接受。在这种背景下,符号象征和生活媒介、生命视域之“蛋”力图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和谐共生(合一),表征族群意识活动的生态意向性。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和根本特征。在关涉“蛋”的民间信仰、图腾崇拜、节日礼俗、情感交互中,表征人的存在和鲜活的本然世界。意识的意向性乃将其指向从“蛋”绵延至人之生命、自然之生命、天地之生命,构建出不息、合一、共生的生态观。而这些是向内、向外探索,天上、人间关注,反省存在方式和寻求大生命(整体生态或生态系统)的意义表征。
存于民间、百姓熟知而传的“蛋”(卵)神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汉族、壮族、侗族的宇宙“蛋”与创世神话,壮族、侗族、苗族、瑶族、仡佬族、毛南族、水族、傣族、黎族等民族的“卵生”型神话,都在呈现一个历史图景和认知图式:宇宙“蛋”即身体,意指之“我”的生命之意义与方向,以神话思维(“实践一精神的思维”)思忖宇宙、生命的缘起,隐喻是它们共同的思维方式。在“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接点是隐喻”[5]的视域下,有其基本叙述结构。汉族:“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天地开辟(自然万物) (《三五历记》);壮族:太古—最初始(道),宇宙—气或气团—三个“蛋”黄结构巨“蛋”—飞爆—一个飞升为天、一个沉降为海、一个居中为地(人类栖居之所) (《神弓宝剑》);纳西族:最初—起点(生命缘起),宇宙—声和气—凝成大白“蛋”(“蛋”内结构为木、火、铁、水、土五种“精威”和白、绿、红、黄、黑五风) —五个彩“蛋”—生成天地、日月、牛羊、神鬼等(《东巴经》);苗族:最初—时间起点,宇宙—云雾—巨“蛋”—孵出科啼、乐啼巨鸟(男女、对偶、阴阳、婚姻)—天地(《古歌》);彝族:巨神黑埃罗波赛—产下巨“蛋”(结构中有天地日月、星辰雷雨、人兽虫鱼) —开裂—“蛋”壳为天、“蛋”黄为地、“蛋”白为世间万物(创世神话);侗族:“蛋”—孵出松恩(男)、松桑(女) —结合繁衍—人类(《龟婆孵蛋》);藏族:太极之初,大“蛋”—生“英雄”—各种图腾的整合(狮、象、虎) —人类始祖。希腊:混沌未开—黑暗神与夜女神—生下大“蛋”—孵出厄洛斯(爱神) (神话);芬兰:混沌之女—鸟在其膝盖造窝生“蛋”—“蛋”破—生成天地日月星辰(《卡列瓦拉》);印度:最初,宇宙—水—金“蛋”—破—上作天、下为地(《外道小乘涅架论》)。文本喻指生命意识的表达,追寻最初生命,敬畏生命,以“蛋”生殖崇拜形成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借助神话模式,将关涉“蛋”的鸟(蛋)图腾、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聚于意向性之中,“给人类在宇宙中确定位置,规定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关系”[6],力图描述宇宙与生命的起源,即天地万物均从“蛋”生,而起初是混沌进而演化成宇宙“蛋”。最终形成“太初(道) —蛋(混沌) —天地生命、人之生命、自然生命”的隐喻图式。
可见,天、地、人、万物本为一体,源于宇宙“蛋”,有着内在的整体性和本质性。这也体现在尚圆心理、天数同源的认知之中。“蛋”是一个圆,宇宙是一个圆,“蛋”生天地人,从而隐喻出人与万物皆从圆生。其中圆与零(数字0)又相耦合,表征完满,起点、终点、无始无终,就像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本原”的观念一样,隐喻“蛋”、宇宙、生命、圆、零等概念,抽象为意识之中那种共生(血缘同构性)、合一(天地人质本于“蛋”)的生态意向性。借助于超凡生命力的“蛋”和背后潜藏的生殖崇拜,一些民族将其投射于大地生命(厚德载物功能)。西藏路巴族米古巴人春耕播种,举行与“蛋”相关的仪式,祈求丰收,水族地区的种棉主妇于夜间用蛋壳(和酒饭)向大地献祭,其隐喻投射过程为:“蛋—生殖—生命—丰收”和“蛋—献祭—补充营养—生命力旺盛—丰收”。这种“蛋”与大地生命的耦合模式,亦将“蛋”、鸟、鸟崇拜与稻作文化相关联,稻谷—维持生命,鸟、稻谷、“蛋”—生命力的象征,意在鸟、稻谷、“蛋”与地的链接,依循既存的大地(厚德载物—生育之功能)生命观念,把鸟、稻谷、蛋、地—内在生命意识和大地生命的身体认知方式表征出来。这不仅表现在我国壮族、侗族和东南亚相关民族中,还存于古籍中,如“厥初生民……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后稷播百谷—大地生育—养育万民) (《诗经·大雅·生民》),“象耕鸟耘”(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意在通过象、鸟的生物习性促进稻谷农作物生长(《越绝书·越绝外传》)。这些不同地域的历史与现实图景,展现了生生不息、生命永恒的诉求,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这些认知图景和生活场域,是理解文化心理和生态意向的重要方面。因此,“蛋”既表征文化关系,又凸显文化过程,借助于不同族群的认知实践活动,使表象—意义之间的理据性、象似性和确定性隐喻得更加澄明[7]。“蛋”创世—天、地、人(宇宙、自然、万物)的血缘同构性—生命共生性、同源性,“蛋”—天地化生—自然与人本为一体(人、天地、万物都归于“蛋”这个混沌整体) —生命整体性,“蛋”—形状—圆—整体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蛋”—特质— (壳)易碎—生态脆弱性—爱护生命,“蛋”—生殖—孕育生命—生生不息—可持续健康发展性,这些“蛋”—“生命”互拟的隐喻特质,正是人们意识意向性、身体意向性和伦理意向性[8]的表征,即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由发展。
如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庄子》)的精神本质一般,作为生殖(性)崇拜、生命意象的“蛋”(卵),在原始宗教仪式、民俗(节庆)、语言神话中广泛持存,是神圣生殖力、生命力的象征,诠释着宇宙与我(人)同一的生态意向:天、地、人共生性、合一性(整体而和谐)、不息性(健行与生生不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态度、行为和内容。
总之,“蛋”作为一种最熟悉而又最深刻的意象和符号,是理解生活、生命、生态的全新向度,它可以表征复杂的生活世界,确证不息的生命意识,凸显共生(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意向。
[参 考 文 献]
[1]殷晶波.一种深层的生命表达方式——试探“蛋”民俗文化内蕴[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34-35.
[2]高秉江.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J].社会科学研究,2013(4):135.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66.
[4]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2-53.
[5]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2.
[6]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0.
[7]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21.
[8]杨晓斌.意识意向性、身体意向性与伦理意向性[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