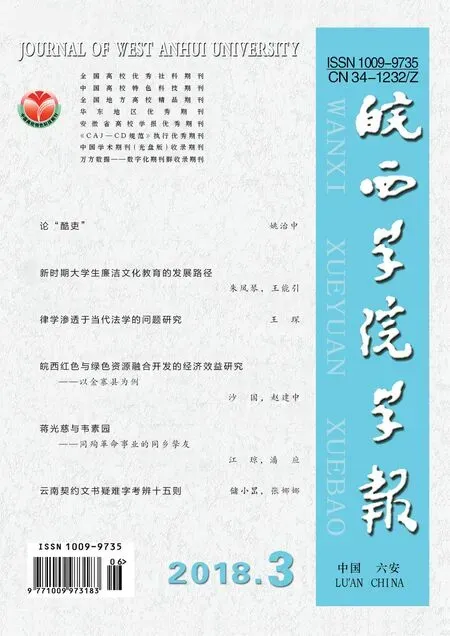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晋书》官学教育主张探微
赵卫齐
(青岛大学 哲学与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在中国数千年的教育长河中,官学对于社会教化、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始终作为主流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关于两晋时期的官学,虽然玄风盛于一时,也直接影响到官学教育主张的士族根基与社会受众,但从《晋书》这部官修正史所记载的教育著述来看,既讲求德治传统,又最大化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儒学教育主张始终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另外两晋时期民族与阶级矛盾突出,完备的官学教育思想主张对于解决治乱问题能够起到“勉其前”的特殊作用,因此儒学核心思想始终作为统治阶级教育改良的出发点与论证点。
一、“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观
官学教育,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培养所需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历代都被统治者给予很高重视。在两晋近两百年时间里,官学的设置始终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时兴时废,又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转型期,所以其教育理想论既有着对秦汉教育思想的继承,也有符合两晋时代特征的发展。
纵观《晋书》所记皇帝诏书,无论政治与阶级背景动乱与否,其“尊儒重教,化民成俗”的主导教育理想却是不曾变更的。以儒术起家的司马氏将“崇儒重教”定为基本文教政策,司马炎即帝位后,“泰始六年,亲临辟雍,行乡饮酒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1](P60)(《晋书·武帝纪》)以表崇儒重教之立场,而作为基本文教政策。“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1](P736)(《晋书·职官志》)武帝早在即位初年就创设性地并举国子学与太学,可见其对世族统治起基建性作用的官学极为重视。不仅如此,早在即位第四年(泰始四年)颁布“敦喻五教诏”,尤其强调“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1](P57)(《晋书·武帝纪》)武帝诏令中“遵孝悌之义”正是对儒家传统孝德教育思想的继承。
史料记载西晋儒学家傅玄在其给皇帝上疏中多次言及儒学为“王教之首”,强调儒学礼仪教育之重要性:“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1](P1318)(《晋书·傅玄传》)以及《陈时务疏》阐述要达到“儒家为典”教育理想,中央与地方的官学教育就成为社会教化必需的实施方式,即“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1](P1319-1320)(《晋书·傅玄传》)傅玄对官学的此番阐述是对痒序之教的再次整合,称为“弘道”,同样也是在晋代尚玄风气下对孔子所倡导的学校价值、教育目标之正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绝非官学模式下的典章制定这么简单,而是在整个社会先形成尊师风气,进而引导整个官学体系以师德用人,这才是真正的“弘道”。
其他如鄱阳内史虞溥“大修痒序、广招学徒”,著令《移告属县广开学业文》“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1](P2140)(《晋书·虞溥传》)杜预镇守荆州“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1](P1031)(《晋书·杜预传》)平原太守李重“修述儒道,义在可嘉……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1](P1312-1313)(《晋书·李重传》)西晋时期,中央与地方官员办学兴教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尊儒敬师”的学风、“正德守礼”的社会风气。
西晋中后期乃至东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政府政令废弛,官学的正常发展自然是不可能的,但“以儒立国”仍然是东晋朝基本文教政策,至于中央与地方是否施行抑或施行情况如何则另当别论。东晋元帝从荀崧奏《请增置博士疏》,乃令《议置博士诏》“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凡九人。”[1](P1977)(《晋书·荀崧传》)经“永嘉南渡”、晋室草创之际,依然针对“儒学尤寡”的现状进行兴学教化;以及辅佐司马氏建立东晋王朝的王导《请修学校表》、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等疏议奏请都强调官学的重要性,以达到“弘儒”之理想;及至晋明帝《尊师傅诏》、袁环《请建国学疏》“崇典训以宏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1](P2166)(《晋书·袁环传》)更加明确地指出官学教育与政治、名教不可或缺的联系,以达到“尊师”之价值观。虽然“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1](P149)(《晋书·元帝纪》)但“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1](P2167)(《晋书·袁环传》)施行情况可见一斑。
甚至到了东晋末年孝武帝时期,外患有淝水之战、内忧是世族把持朝政,皇权日益衰弱,此时的官学形同虚设,更何谈起到教化万民的作用,然而依然有士族不断上疏提出教育改良主张,以希在官学中重塑儒家传统道德规范。谢石《请兴复国学疏》“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惟礼与学……庠序之业,或废或兴……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2](P364-365)(《宋书·礼志一》)其实谢石重塑礼义、兴复国学的主张出发点是好的,但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认识严重不足,空谈崇古宗圣,并没有提出实际行之有效的改良方法。
从两晋教育论述相关史料记载来看,无论皇帝诏令还是士族疏议所主张的教育理想模式都是利用官学作为最直接的教化手段,以实现儒家教育之理想。“化民成俗,修齐治平”治国思想仍是晋代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最大特点;“尊师重教,正德守礼”文教思想仍是官学主导思想,以此来规正“尚玄好虚”的社会风气,根本上维护士族阶层的统治地位。教育目的与价值是教育思想的起点与终点,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这一点尤以两晋时期表现突出,其教育目标的顺利施行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极大影响。实际上两晋时期“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观虽较儒学传统主张有很大不同,但其出发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大力推行“德育”有助于教化人民、安邦定国,以培养个体的理想品德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因为两晋时期民族与阶级矛盾突出,如果仅仅用道德来教导、感化百姓,以使他们用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无疑表现出其教育理想论的局限性。
二、“注重实学”的教育改良论
“九品中正制”是两晋时期士人入仕的主体选拔制度,也是两晋最具时代特色的选官制度,但是这种以门第论品级的中正选举模式带来的流弊势必会极大影响教育的正常发展。士人只会攀缘附会,追求家庭门第、重人际关系而罔顾实学,看似并举的国子学与太学实质形同摆设。
针对这种教育现状,许多士族官员纷纷揭露时弊,提出教育改良论著,如刘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奏《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P1273-1274)(《晋书·刘毅传》)以“八损”高度概括了损政之弊端,深刻揭示出九品制度对于官学教育发展的妨害。刘寔《崇让论》“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1](P1192)(《晋书·刘寔传》)及至东晋后期废“九品中正制”之教育主张仍不绝于耳,李重《请除九品疏》“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3](P47)(《文献通考·选举考三》)“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义日崇矣。”[4](P34)(《通典·选举二》)这些士族官员时刻关注着入仕之途径即官学的发展,对中正官的管辖权限、个人的道德操行、品级的划定直至罢除九品中正等诸多问题进行改良,但其实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在如此重门第、重德行的社会风气之下,许多上疏的士族受各级中正官的评定,换言之,这一阶层本就具有附属性,是九品体制的一部分,又何谈改良的主导性与贯彻性。结局注定是皇帝不予,向门阀势族妥协,寒门“无门”清谈以遁,因而官学日益衰落、学术重心转向家学与私人授学亦是必然。
虽然一方面“实学”对九品体制的改良不符其时代性,但在另一方面对传统儒家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扬弃却是创设性的,诸如吸收佛道教育思想的精华加以糅合、创设“专学”对“经世致用”传统价值观的补充与发扬。虞溥《厉学篇》“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1](P2140)(《晋书·虞溥传》)李充《学箴》“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任意者而已……况乎行止复礼克己。风人司箴,敬贻君子。”[1](P2390)(《晋书·李充传》)其教育主张虽带有盛行的老庄玄学色彩,但根据儒家礼义的基本准则结合所处时代特点,李充还是坚持认为只有克己复礼才能治乱,真正实现教化目的。殷茂(仕于东晋、宋)《请群臣子弟入学并制程课上言》“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2](P371-372)(《宋书·礼志一》)又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艺术理论,培养专门绘画人才,同样属于“实学”内容[5](P77-79)。此外还有书法、律算、医药等方面。
从晋代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办学情况来看,虽然官学“授业入学”的服务对象局限于上品世族,但还是可以看出在文教传播与发展上具有积极性,修习传统典训的同时,又主张以“专学程课”作为补充,注重对士族官员子侄的“德行”与“实学”双向培养。这既是两晋门阀政治特殊体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为了维护其思想垄断的特权地位而必须做出的教育改良;又因为两晋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对于如何“治乱”的讨论就必然先要求“入世”,所谓“入世”就是要求程科内容的社会性,即具备实用价值,从而客观上也促进了“实学”理论的发展。
然而,两晋官学“注重实学”的改良收到的成效并不明显,其只是在形式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门阀特权的士族阶级生活奢靡、不思实学的社会现状并未扭转,从而并未真正达到重振儒家伦理道德之目的。而讲求“实学”客观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形态有密切联系,虽然世族阶层改良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其特权地位,但客观来说,这种对传统“实学”认识观的再造以及教学内容的扩大都对两晋及南朝各代官学教学模式的设置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实学观”教育主张也是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转折点。
三、“正德量才”的才性标准
才性之论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教育论著重点关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德”与“才”如同一根平衡木的两极,如何兼而得之的核心命题。人才的选拔必须通过教育,而官学又在历代教育中发挥着主流作用,因而须要探讨才性论与官学的关系问题。
两晋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彩的时代[6](P11),许多士族官员也身兼教育家纷纷提出论著,打破了以往重德轻才的儒家品评标准,主张“正德量才”更加多样而具体的人才价值观,不再片面强调德之至上,具备儒家倡导的“仁”德即可,而突出了“实才”之用,最大化达到“德才兼备”教育目的。袁准《才性论》“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7](P138)(《艺文类聚·人部五》)所谓贤者并非十全十美,要根据具体才限名其用称为明智之选,这样的才性观已初具“量才而用”思想,代替传统重德之教,因而既为寒门提供了入仕机会,也直接影响到南朝数代的选官标准;既使得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也为更加并包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铺垫了思想基础。
再从官员上疏对于官学试才的奏对来看,纪瞻《举秀才对陆机所试策》“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1](P1817)(《晋书·纪瞻传》)明确阐释如何选官任才的中心命题,即在具有传统“五德”的基础上,考察才能优劣才是可取的方法。熊远《为选官用人上元帝疏》“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1](P1888)(《晋书·熊远传》)认为传统讲仁德、重出身的选官标准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应该最大化网罗人才,从而根本上扩大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
又如陈頵《论取才与王导书》“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1](P1893)(《晋书·陈頵传》)孔坦《策除秀才孝廉奏》“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1](P2055)(《晋书·孔坦传》)这些儒学家主张官学以“明德”和“招贤”两个基本标准改革当时教育选才的弊病,这同样能够激发处于所谓“屠钓”“丘园”之贤良入仕的热情,可视为统治阶层已认识到当时人才培养体制的不足,既是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也是传统才性思想观的新发展。
然而两晋官学始终处于朝局不稳、世族与寒门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针对才性标准的论争并未触碰到根本问题[8](P31)。直到东晋灭亡、南朝继立,因为“南朝以“武功”建国的政治特点也是下层士族权力上升的标志,对门阀世族的瓦解也起到推手作用。”[9](P184)看似人才选拔体制迎来了新的改变,但实质上,新的特权势族产生,官学教育依然未能挣脱“才性之辩”的束缚,这也为南朝选才制度埋下隐患,但两晋针对才性标准的积极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实无论传统的强调仁义道德的人才观,还是重视经世致用的才性论,都是无须置否的,而且二者之间本就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两晋正值乱世之际,更偏向于人才培养的实用性,以期能够扭转危局、安邦定国。因此,德才之辩的人才观是与历史的时代性密不可分的。
四、两晋官学教育主张的意义
讨论历史上的教育发展,不能采用静止的、孤立的、割断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教育活动是个独立的实体。它的发展受到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是有着自己独特发展规律的社会活动。因此两晋时期官学教育本身就似一条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呈现出其独具时代特点的连贯性和继承性。
两晋官学教育主张所体现出的具体内容与理论重心既是对秦汉传统教育思想的一次全面深化与整合,也是对唐宋教育思想的一次奠基性转折[10](P27)。从教育理想观不难看出,在官学中以道德精神的培养为核,具体表现为若干“新质”的教育改良试图在两晋“乱世”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克己复礼”而达到“治乱”之目标,虽然其出发点是维护士族阶级的统治,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样的德育论也包含有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仍然有值得现代教育吸收利用的地方;而从实学论与才性之辩来看,两晋官学教育主张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除了探讨教育与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关系这样的传统命题,更注重个人经世之学的发展以及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探讨,这样强调个人与整体协作发展的入世思想为我们在现代社会如何充分发挥教育的各项功能提供了借鉴之处。
虽然两晋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各种形式的官学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改良成果并未达到预期,但是单就两晋教育论著所记载的教育主张来说,一方面晋代兴办的“专学”及“学馆”教育既是对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补充,即对传统儒学的保护,免遭丧乱而散佚,也进一步丰富了以官学为主要载体的儒家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对南朝时期教派的融合、唐宋教育的兴盛乃至后世教育模式的发展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起到奠基作用。两晋时期的儒学家在改良官学的同时,也有着家学背景,因此这一时期教育论著表现出官私教育思想结构的融合倾向,但官学以儒学教育思想为主导地位却是未曾改变的。及至南朝佛道大兴、多元并综的教育格局也正是由两晋教育的过渡而来,从而起到了思想奠基之用。
《晋书》中所记载的教育著述之于现代教育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为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继承古代教育思想的同时,也要主动地思考思想文化的源头与走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深入挖掘古人的思想结晶,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使古代教育思想再放光彩,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宿白.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6]马秋帆.魏晋南北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0]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