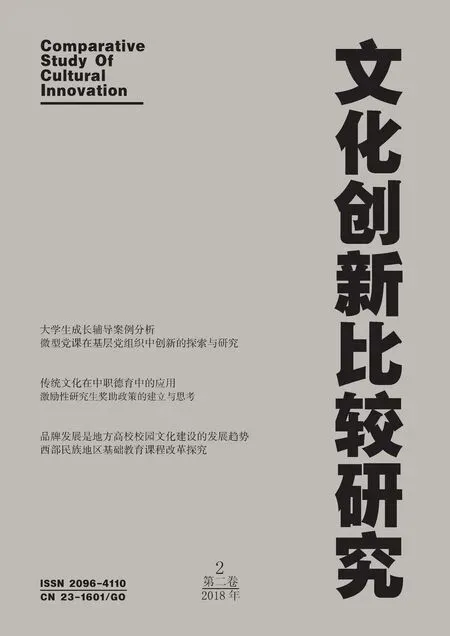弹幕迷群身份认同研究
蒲骊衡
(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 400715)
1 引言
1.1 研究缘起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说过 “媒介即人的延伸”,并认为 “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种比例改变的时候,人就随着改变了。”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不断丰富并改写着受众的日常生活,使受众的精神需求得到极大地满足。而伴随着二次元(ACG)亚文化风靡流行而兴起的弹幕正如一道绚丽的文化景观走进了大众视野,它从一开始的出现便携带着新媒介浑然天成的亚文化因素并给它的忠实用户——弹幕迷群,一个即时、自由、反权威的表演空间。他们通过弹幕构建了“观赏共同体”的想象,产生随时随地与同好者一同观看、互动交流的体验,甚至已成为一种“仪式”奇观。那么,这种以互联网为主要集聚点的参与式文化为何会获得弹幕迷群的追捧?在弹幕的背后迷群们又是如何完成其身份认同与建构?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对于弹幕迷群身份认同进行详细解读的缘由。
为了更好地探讨本文的主题,下面将逐一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阐释,主要包括弹幕、迷与迷群、弹幕迷群以及身份认同。
1.1.1 弹幕
作为一种军事用语——“弹幕”,最早是指炮火射击目标的过程中由于时间过短导致炮火密集就像幕布一样铺陈开来;之后从军事用语中派生出来,用以表示射击游戏中敌人子弹多、火力强的状态。而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Niconico的出现则将“弹幕”一词演变为用户观看视频时可以将评论直接发送到屏幕上的一种互动方式。基于以上理解,该文将弹幕界定为:“是覆于视频流上随播放再现的由字符所构成的注释、评论等。”
1.1.2 迷与迷群
对于“迷”的理解,就迷与媒介文本的关系出发:是指“那些对媒介明星、演员、节目和文本极端投入的迷狂者,固定地、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流行故事或者文本。”“迷”经常被看作是“着迷的孤独者”,他们对于某项事物抱有异乎寻常的情感和关注程度,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缺乏理性的“粉丝”。但在亨利·詹金斯看来,“迷”并非完完全全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能动地“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的“盗猎者”和“游牧民”。此外,约翰·费斯克也指出“迷”与一般受众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 “过度”,也就是说“迷”能够对原始文本进行二度解读和加工,他们不仅在消费文化产品,同时也能对主导文化进行解构和重建。
而说到“迷群”,顾名思义,它是伴随过度的媒介使用和消费狂热所导致的单一个体“迷”的相当数量与规模的集合。在本文中,“迷群”的概念笔者比较认同亨利·詹金斯的阐释:
(1)迷群拥有一种特别的接受方式。
(2)迷群拥有一套特殊的批评性和解释性的实践活动。
(3)迷群促进消费者能动性的产生和发挥。
(4)迷群拥有一些特殊的文化生产、审美传统和实践形式。
(5)迷群建构了另一个社会性群体。
1.1.3 弹幕迷群
本研究所要涉及到的弹幕迷群是属于上文所阐述的迷群范畴的。一方面,网络空间中迷群们因为趣缘而集合,他们拥有统一且自由的表达形式,并进行着大量丰富的围绕ACG亚文化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弹幕视频网站也为迷群提供了一个发挥能动性的基地,正是这样共同建构了当下主导文化狭缝中的乌托邦。因此,笔者将弹幕迷群定义为:个体的弹幕迷出于共同的ACG亚文化认同以及即时评论与吐槽、互动社交、对主导文化再造的需求而聚合,于网络中形成的一系列有组织、有章程、或封闭或开放的能动性群体。
1.1.4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最早用于表现哲学与逻辑学的范畴,被认为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的人物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一种过程”,强调认同是借助外在因素来完成自身的建构。在社会学领域,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对自我身份、群体身份的认同;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身份认同更突出在对个体之间或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认同。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身份认同概述为以下几个部分:(1)自我认同,是一种个体的内在性认同,具体是指个人依据自身的经历所进行的反思性理解与自我实现。(2)群体认同,是指人在特定群体活动中基于对该群体的认识和评价而建立起的一种接近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个体认为自己是该群体的一员的感觉;文化认同,是一种个体被群体文化所影响的感觉,群体内部成员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以及使用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
2 弹幕内容与弹幕亚文化分析
2.1 弹幕内容分析
弹幕的内容是受众研究的重要文本,伴随着视频文本的产生,学者赵毅衡将其视之为影响受众解读视频文本意义的“伴随文本”,并认为“任何符号必然携带着各种伴随文本,同时,每一个符号都靠伴随文本的支撑才成为文本。”基于以上的理解,笔者通过对其具体内容的分类及文本分析,将弹幕初步划分为基于视频文本的弹幕与游离于视频文本的弹幕两大类:(1)基于文本的弹幕,简言之,便是“原创弹幕”和“呼应弹幕”的结合体。一般包括针对专有名词、翻译和典故等的补充说明;针对某一情节、配乐或人物语言行为的调侃、批判和议论,一般也被称作“神回复”、“神吐槽”;对弹幕精彩程度做出的回应或者计数,比如 “+10086”、“+1”等;故意提示甚至泄露剧情走向的弹幕,比如“男主马上就要领便当了,不谢”;用以表达情绪的语气词汇,部分已简化为一串数字、字母以及特殊符号与表情;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空耳对原文本进行的“解构”,选取与原声发音相似的汉字,进行误用式“听写”以达到恶搞与双关的效果,比如阿姨洗铁路(日语“爱してtf”,“我爱你”之意)。(2)游离于文本的弹幕一般会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以彩色弹幕为主,几条弹幕排成队形,形成一个弹幕集合,主要包括原创吐槽、版聊、时事讨论、签到、接龙和吐槽视频播放环境的个几种形式。
2.2 弹幕亚文化分析
通过以上弹幕内容分析以及摘录的典型弹幕可见,对于弹幕内容的有效解读是需要一定的ACG亚文化知识背景的。在这种弹幕特有的亚文化笼罩下弹幕迷群使用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寻找与建构着身份认同,并巩固其社群组织,具有一定的“亚文化壁垒”。
2.2.1 后现代式抵抗:网络吐槽文化
在互联网氛围的当下,“吐槽”从原本的 “戏谑”、“抬杠”和“讽刺”的意味逐渐演化为一种通过娱乐形式来表达观点的评论。而弹幕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产物下的匿名吐槽平台,一方面对于视频的某一句吐槽可能会成为原作的“点睛之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原有评论形式的“吐槽再加工”并结合动画、配乐为原材料进行剪辑、重组、拼贴形成新的文化产品,比如鬼畜视频。由此观之,弹幕视频技术就是用最直观简单的文本表达方法和最夸张的覆屏方式,实现了便捷的受众观点表达、思想交流和规模化的意见讨论,可以说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弹幕迷群对主导文化的吐槽需求,体现了弹幕迷群所代表的的亚文化群体对主流的后现代式抵抗。
2.2.2 迷茫中的认同:互动社交文化
弹幕本质上是一种互动形式,它为亚文化圈子建构了一个独立于视频内容而单独存在的拟态空间,反映了宅男宅女更偏向于在互联网空间中实现社会互动和自我提升,从而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以期得到情感能量的补偿。这个高度“风格化”的空间最初是根据视频内容而建构起来的,其中的圈内成员拥有着一整套联系彼此的隐语、仪式和社群规则等。弹幕迷群在观影过程中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对视频发表各自的评论,并且这些评论也可以被后来的观众所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时空界限的突破,满足了他们独特的社交需求,在迷茫中找到了其身份认同。
2.2.3 多元文化碰撞:再造主导文化
弹幕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它以御宅族为主的弹幕迷群通过戏谑的吐槽与随时随地的互动来实现对社会主导文化的渗透与重塑。比如“XXX发来贺电”形式的弹幕,这显然是对权威媒体带有政治色彩语句的戏谑模仿,身处在网络亚文化框架中的弹幕迷群正是通过 “发射”弹幕来形成对视频中主流文化的对抗解读、协商和再造。值得一提的是,弹幕作为一种大众接受程度高的新型网络亚文化,相较传统亚文化而言,它的收编过程远比想象中的缓和。比如,最近几年A站都会在春节期间发布以日本动漫和影视剧主题歌为集合的“年度迎春联欢晚会”弹幕视频,引来众多网友在除夕夜竞相刷屏。这些视频不仅反映了弹幕迷群节庆方式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主流电视节目春节联欢晚会的另类反讽。
3 奇观/表演理论范式与弹幕迷群实践
3.1 奇观/表演理论范式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人际沟通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自我”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经过掩饰的自我。在新媒体时代,英国社会学家Abercrombie和Longhurst提出的奇观/表演理论范式与拟剧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认为随着媒介影像的迅速发展,大众既是受众又是表演者,受众具有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它更强调网络中的媒介消费和身份认同,尤其适用于对网络中小众文化和内部个体的表达行为的解释。
奇观/表演理论范式中的扩散受众包括四个循环,分别是媒介渗透、日常互动、表演和奇观/自恋。一方面,媒介讯息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讨论,这些讨论进一步使观众更加情绪化,进而加深了他们对媒介内容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为了表达认同,他们会公开地进行展示且视自己为被关注的对象,在这种自恋的心态之下,又引发新一轮的媒介消费。就是在这个往复的过程中,受众的自我认同得到了建构和重构。
3.2 从“迷”到“群”:弹幕影像成就弹幕迷群
3.2.1 媒介渗透
媒介融合的趋势之下,影像、商业与人们的生活完美结合,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扩散的受众,即使不是亲自接触到影像,也很难完全避开被其影响的可能,正如Anderson所说:“当今受众身处于媒体娱乐化潮流之中,他们不仅从自我解构的角度来解构文本,并且还在消费中试图展现自我、寻求认同和重构文本。”而弹幕视频网站上的弹幕迷群无疑归属其中。
这些弹幕迷群和普通的网民比起来,在获取网络信息上具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时间,甚至可以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从而产生新的文化资本,为他们后续的活动提供多种多样的素材。而如何从无孔不入的媒介讯息中挑选资源作为其自我认同的准备资源,则需要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的环节在弹幕迷群构建自我认同的时候尤为重要,它不但可以使自己在有限的精力中选取所需相近的资源类型,同时,它也与大量“他人”的存在建立了潜在的关系。一旦对话开始,这些关系就被正式构建,可以使用匿名并且只是以兴趣为导向形成基本无障碍的交流关系,以此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弹幕生态系统——将个体的“迷”聚合成相当数量的弹幕迷群。
3.2.2 日常生活中的仪式狂欢
詹姆斯·凯瑞在其《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到“传播仪式观”并认为“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使得人们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信息的获取(虽然从中也获取了信息),而是在于某种戏剧行为,并作为戏剧演出的旁观者加入其中。”对于弹幕迷群而言,参与弹幕的生产与再创造过程就是一种“仪式”:弹幕大多都是“吐槽”等意义不大的内容,用户可以通过“弹幕仪式”程序的参与,强化ACG世界中的“二次元”世界观和价值观。比如,游离状态的“签到”弹幕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仪式感十足的“打卡”或者“mark”。除此之外,这种仪式上的狂欢还表现在影像视频剧情高潮、转折的节点,这时屏幕一定会被诸如“某地发来贺电”、“喜大普奔”等弹幕大量覆盖的景象,就好像弹幕迷群进入了剧中的世界和其中人物共同狂欢。而在这个狂欢的过程中,他们对于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增强,这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网络视频观影的常规,形成了一个基于共享“信仰”、爱好为表征,以发弹幕的形式参与观看的新型互动空间。
3.2.3 利用文本进行自我表达
Aberecrombie和Longhurst认为,表演是构建受众的关键,而当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到处都有表演的社会。扩散受众和一般受众的最大区别是他们具有看与被看的双重身份,试图通过他们的个性化表现在互联网上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欢迎。而弹幕作为在吐槽文化浪潮中兴起的一种技术手段,它在促成弹幕迷群“观赏共同体”一方面实现观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网络跨越地理限制与“槽点”同步的人一起分享解构视频文本带来的快感。他们往往从中提取最有趣的主题、人物或情节,附加自己的创作和想象、重组和整理,创造出符合自身表达的新文本。这时“吐槽”已脱离原有的语境渐渐演化为一种投入观看并“表演”自我的观展活动之中。
3.2.4 身份认同的形成:奇观/自恋的循环
自恋与奇观,是两种常见的共同形塑扩散受众的力量。在现实中,缺乏精神交流的孤独受众总是在观看、比较和纠正,试图通过反复欣赏影像的方式寻求自我建构的参照。为了显示身份认同,“迷”们会建立想象的虚拟人格在视频网站上进行公开表演,以达到自己是被关心的对象的一种“假象”来麻痹自己。弹幕迷群也是这样,通过自己的表演激发更多相同兴趣爱好者的共鸣,然后用弹幕评论的方式启动群体会话,加倍放大情感的投入和认同的达成。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受众会有进一步参与或者满足认同的需求,此时,他们将通过掌握到的方式和资源,开展自我的表演,这种方式包括搬运视频、制作的视频字幕和剪辑等等。从抵抗或接受信息的主体的转化为利用媒体进行表演的主体,扩散受众的四个循环构成的奇观或表演范式由此形成,弹幕迷群将自己呈现于弹幕视频网站上的其他受众面前,并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身份形象的认同也由此不断被寻找、建构与再建构。
4 弹幕迷群: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由此观之,大部分弹幕使用者是处于 “普通消费者”与“崇拜者”的范畴之内,这其中就包括了弹幕迷群,而“UP主”以及高级弹幕绘制者等大多处于“崇拜者”到“小规模生产者”之间,可以说是“进化”后的高级弹幕迷群。但不管在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够通过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交换各自的意见,在媒体生产者之处获得相应的表演文本并且截取能够引起共鸣的话语,然后根据自身的认同模式和对社会的认识将它放置在自己建立的叙事框架之中。可以说,这些一个个具有个人特征且处于社会背景中的个体,在网络社区中的聚合本质上只是由于形成了群体意见和身份认同。毫无疑问,这些弹幕迷群对于媒介来说拥有大量的消费和生产能力,他们在文本和现实中进行比较,从而进行自我和群体在文化层面的认同和建构。
4.1 弹幕迷群的自我认同建构
弹幕迷群的自我认同建构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从他者印象的角度来讲,人们是在他者的参照之下,形成个体的想象力,从而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从别人眼中的反射来建构并维持自我认同。弹幕迷群在影像视频上纷纷“发射”弹幕就是为了期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认同与夸奖,网络虚拟社区就成为他们寻找快乐和寻找认同的集聚地;其次,弹幕迷群的行为从符号消费的角度来说,他们在表现自己的喜好、参与讨论和积极应对等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尽管都表现出不同的个体行为,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一系列实践过程就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弹幕只是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符号”——迷群自我认同和想象的表达符号;最后,从个人生产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弹幕群迷其实是具有小规模生产者特性的媒介消费者,为视频影像的不断扩大和吸引更多的迷群做着积极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对抗和颠覆原文本进行原创生产以此传播来扩散影响力。
4.2 弹幕迷群的群体认同建构
弹幕视频网站提供一个平台,在这里,受众不但可以自我寻觅、协商和对抗,还可以讨论ACG亚文化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寻找有相同感觉的个体,从而形成群体的区分和认同。一方面,“二次元”的准入机制是一种机械地区分ACG亚文化的“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方式;另一方面,“风格”作为亚文化的核心问题,它通常与“仪式”相联系,经过某种行为的仪式感,突出“圈子”和其他组织的差异,进而形成群体认同。比如,对于B站而言,“我群”与“他群”的边界是通过采用会员制度的方式来区隔的,具体表现在弹幕行为与弹幕圈内话语上。弹幕群体的准入条件,实际上是考核准入者与群体间具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用户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如果这种区隔边界的准入机制一旦打破或失效,就意味着对群体没有身份认同的人“乱入”了,会直接降低其他弹幕迷群对群体的认同与归属感。
4.3 弹幕迷群的文化认同建构
值得一提的是,弹幕迷群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弹幕文化。首先,弹幕的内容文化反映了弹幕迷群“信念”的共同价值观,这是网络群体凝聚用户的核心。弹幕内容的创作实际是对以视频为主的文本的 “二度加工”,这些被再造后的视频文本通常被赋予了弹幕爱好者的价值,这与初始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其次,通过弹幕的形式,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原本被认可的标志受到了挑战,那些已经成为权威象征的事物变成了弹幕迷群调侃和恶搞的材料,弹幕文化内容中包含着“富有意味的反对形式”;最后,弹幕形式文化是根植于弹幕网站的传播形式,代表着弹幕迷群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独一无二高度风格化的形式。在B站,经常有刷弹幕的情况,一条弹幕可以引出成千上万的弹幕跟随者,以表达出其内心强烈的认同,以至于经常有相同内容的出现。也许这些弹幕在文本内容上并无意义,传播形式在网络主流文化面前依旧处于边缘,但依托弹幕形式却拥有了新的涵义,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于弹幕迷群对其所属的弹幕文化的认同与维护。
5 结语
本文以观展/表演理论范式为框架,通过对弹幕的内容分析,将弹幕划分为基于视频文本与游离于视频文本的两类,多样化的弹幕丰富了伴随文本的形式,起到了解释、链接等作用。在弹幕亚文化的“温室”里弹幕迷群参与弹幕生产、消费以及感知,从中获得了对自我、群体、文化三个层面上的身份认同。这种集表演与想象于一体的“观赏共同体”形成了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文化奇观”,一改以往受众单独观看的习惯,促成了其从消极受众向着积极的扩散受众的转变。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陈一,曹圣琪,王彤.透视弹幕网站与弹幕族:一个青年亚文化的视角[J].青年探索,2013(6):19-24.
[7]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上海:复旦大学,2009.
[8]丁依宁.受众的表演与想象:弹幕使用族群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5(4):87-95.
[9]王佳琪.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弹幕文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5.
[10]雷蔚真.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11]王颖.对弹幕视频网站受众的主动性分析——以AcFan 和 bilibli为例[J].学术探讨,2015(10):54-55.
[12]刘燕.后现代语境下的认同建构——大众传媒的作用及其影响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2007.
[13]张玉佩.从媒体影像观照自己:观展/表演典范之初探[J].新闻学研究,2012,82(1):41-85.
[14]史丹.“非主流”群体的自我建构——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J].当代青年研究,2009(7):19-26.
[15]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78-83.
[16]江含雪.传播学视域中的弹幕视频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17]Anderson,J.A.The pragmatics of audience in research and theory.In J,Hay,L.Grossbery&E.Wartella(Eds.),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acape[M].Boulder,CO:Westciews,1996:75-96.
[18]Abercrombie,N.&Longhurst B.Audiences: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London:Sage,1998.
[19](美)亨利.詹金斯.文化盗猎者[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