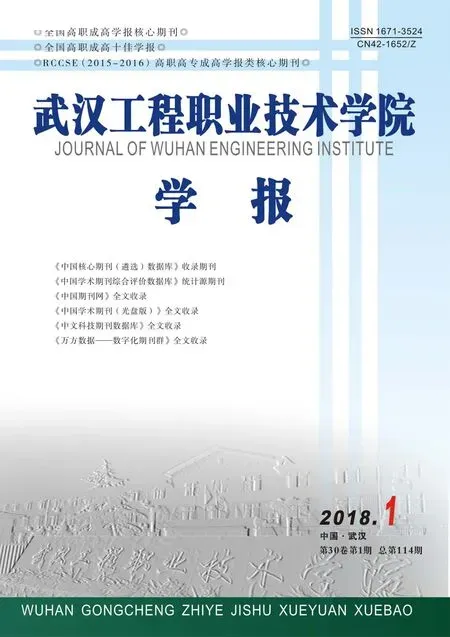试论人的超越性和理想社会的实现
尹 航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475000)
儒家主张通过修身达到“仁”的境界,道家的效法自然,寻求逍遥的境界,柏拉图的正义以实现自身道德的超越,马克思追求人的完美的境界;所说的理想社会,即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先哲们对理想社会的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主张是有其共通之处的,即承担社会责任以达到实现个人价值的目的,实现个人价值以完成自我的超越。
1 人的本质与价值
对人的超越性的理解与认识离不开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即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价值问题。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现实性的社会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相应的实践活动,其本质要从这些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人者,“仁”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具有“仁”的德行,孔子主张通过个人修养以至“仁”的境界,使人本身具有人的本质,主张在协调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认识与把握人的本质,并试图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达到人的自身的完善,实现人自身的价值的目的。
人的价值就是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价值的大小和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他所从事的职业体现出来。“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2]。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要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是整个人类做些什么。人的本质就是人内心存在的追求不断超越,不断完善的人的本性。人只有在创造价值,实现自身价值中才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不断超越的本性,而人的价值只有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中人的本性才能都得到不断的升华,以至达到完美的境界。
2 儒道两家对人的超越性的看法
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人的行为,通过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兼顾修身与实现自我价值。儒家思想认为,通过修身,不仅能够实现个人道德境界的超越,远期而言更能够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在其位,谋其政”,认为要长幼有序,做好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无论是百姓,还是上君下臣;主张通过德化强化人的“规矩”意识,人人都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为修身为本”。修身以实现自我的超越,以至“仁”的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因个人私利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奉献自己中成就别人,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一个更加完善的自己。人还应当在承担责任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完善。“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满怀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主张在协调各种关系中实现自我超越,主张积极入世,济世安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儒家主张不同,道家主张效法自然,在清静无为中实现自身的超越,最终达到自在超脱的逍遥的境界。道家主张出世,并非绝对的不问世事,而是有原则的入世,“若天子有道则入世有为,若无道则出世无为”。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并不是主张要压制人的欲望,而是主张人要克制对名利的贪欲。道家主张消极的“出世之论”与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之论”不仅不相冲突,而且还是对儒家入世思想进一步地补充,使得儒道两家思想相得益彰,而不是两不相容。儒道思想可以这么来概括,人只有首先摆脱名利的诱惑,达到对物欲的超脱,方能回归人的本真,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实现人的价值。
3 孔子的大同社会依赖于人的超越
孔子所追求的个人理想是要通过修身达到“仁”的境界,可以认为,大同世界是孔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所理解和追求的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天下所有人一同共有的,而不是属于某个人或是某个团体的。人人都甘愿奉献自己,人人都有着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这样的大同世界中,所有人都可以明确自身位置,使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地生存与生活,不再受任何的外在的束缚与压迫。
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爱,端正的义利观提升人的品格。“义者,宜也”。在面对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人当如何取舍和选择?“行义以达其道”,“儒家主张行义远利,义高于利,义重于利,为义可舍弃个人私利,甚至可舍生忘死,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3]。在义与利产生矛盾的时候,不见利忘义,必要之时还要做到舍生取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大同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它依赖于每个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超越,依赖于每个人都能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价值。简言之,儒家哲学是道德哲学,主张通过内在修养,使自身道德人格不断得到超越和完善;主张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的价值,进而达到人的境界的超越。
4 柏拉图的正义观和他的理想国
儒家的“仁”和柏拉图的正义,概念虽有不同,但都可以理解为为人处世的原则,儒家的“仁人”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拥有正义的人。柏拉图的理想国依赖于正义。“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4]。每个人都要恪守本分,各司其职。柏拉图的正义正如孔子的“仁”,是一种思想的境界。正义的获取依赖于个人的自律,在协调各种关系中不断实现修正与超越。
从更高的层面,即国家的层面来说,柏拉图主张国家政体分为正义的政体与非正义的政体,并强调国家政体要由“哲学王”来进行统治。柏拉图的正义只是贵族统治阶级的所谓正义,所谓“哲学王”指的是拥有正义的人,只有“哲学王”才能够领导正义的政体。柏拉图主张理想国实行“公有制”,反对私有制,认为只有取消私有制,将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个人的私利合二为一。正义就是各等级理应严格遵循的道德规范,理想国的实现依赖于正义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观。
5 马克思的人的完美与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马克思对于公有制的主张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阶级与阶级的对立会逐渐消失,剥削与压迫已被自由平等所替代,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实行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人们之所以要参加劳动,不仅是因为要生存,更是因为满足社会、满足生活的需要。
社会的一切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将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完美的境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而人达到完美的境界就是人能够最终占有人的本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基础,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把个人道德修养置于首要位置。如果没有个人道德修养作为支撑的话,公有制将是一种空谈,按需分配更是无法立足,“让劳动成为人自身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将是空中楼阁。马克思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想应当理解为一种奉献主义,“自然主义”应当理解为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把奉献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意识,一种道德觉悟,一种自觉的行为,在奉献中实现人的价值,以至达到自身完美的境界。人的完美的境界依赖于个人的不断的超越,自身个性的解放,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而达到的。
6 结束语
理想根源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足,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人有人的个人理想,社会也有社会的共同理想。个人理想的最终目标应是达到自身境界的不断超越和完美,终极目标应是经世致用,肩负社会责任,把个人的荣辱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无论是儒家的“仁”,还是道家的“逍遥”,或是柏拉图的“正义”,又或是马克思的人的完美的境界,他们的主张都是相通的,都是在通过自身修养与肩负社会责任中最终实现境界的超越,个人的理想只有与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相结合,换句话说,只有建立在社会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个人理想才是具有更高价值的理想,只有这样,人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实现对自己的不断超越以至完美的境界。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6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
[3]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的义利观.儒文化社会学[M].人民出版社,1998:241.
[4]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