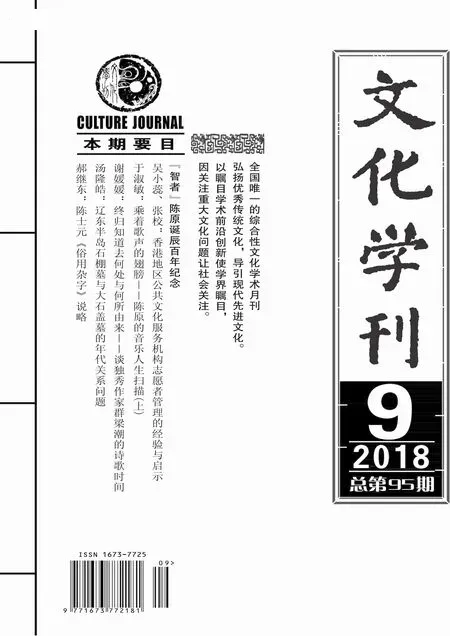陈士元《俗用杂字》说略
郝继东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30024)
陈士元(1516-1599),明代湖北应城西乡陈岭人,字心叔,小字孟卿,号养吾。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深通经学,兼治小学。曾任滦州知州,后辞官归里,潜心著述四十余年,成书400余卷,有《归云别集》等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士元撰述之富,几与杨慎、朱谋?相埒。”[1]著述涉及经、史、子、集,有影响的小学著作有《古俗字略》《俚言解》《古今韵分注撮要》《江汉丛谈》等。
一、陈士元《俗用杂字》概要
陈士元在民俗语汇的收集整理方面颇为用心。他的著述中有《俚言解》,主要是疏证古文献中的俗语词,日本汲古书院将其收入《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一辑)。他还有《古俗字略》,主要是将旧体字与俗体字对照,汇编成书,其实也是俗语词的集成。
《俗用杂字》附在《归云别集》的《古俗字略》之后,列为该书的第25卷。《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全文收录《古俗字略》,并评价道:“是编标题之下题曰‘归云别集’,与所注《周易》同,盖亦其别集之一种也。其例仿颜元孙《干禄字书》而小增损之,亦以韵分字。所列首一字即元孙所谓正也,所列古体及汉碑借用字即元孙所谓通也,所列俗用杂字即元孙所谓俗也。古字多以钟鼎之文改为隶体,已失其真。又不注所出,弥为难据。……而是编疏舛不一而足,亦贪奇爱博之过欤?”[2]可见,《四库全书》对其评价不高。
《俗用杂字》收集了民间俗语词汇共494个,其中单音节词399个,双音节及以上词95个,单音节词占81%,双音节词占19%。陈士元在《俚言解》序中说:“乡俗常言多有证据,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则古圣察迩言何为哉?尝读《方言》与今时所言颇不类,而《通俗文》并《释常谈》等书又指引不广。余暇日著《俚言解》六百八十八章,庶乎陪佳客之诙谐,共鸿儒而博论,不至面墙云尔。未能尽辞,聊录三百余章梓之。”[3]陈士元又在《古俗字略》序中说:“余兹所录者皆今世常用之字,其所谓古,乃楷书之旧,非籀篆之古法也;其所谓俗,则楷书之变,乡俗误用而不察耳。”[4]《俚言解》解俚言,而《古俗字略》收俗字,性质大同小异,我们可从《俚言解》中解出《古俗字略》的创作意图来。而《俗用杂字》附于《古俗字略》之后,虽未有序言,也可略知其收集当俗用字之外的杂用之字耳。
《俗用杂字》虽然所收词条不多,但内容较为丰富,既有日常生活用品及各类百工所用之器具,又有人类的日常动作行为以及人体的部位,还有自然景物和人际关系等。如“性凶恶曰暴躁。发乱曰蓬松。肥脂曰膔。矮短曰矬。乱言曰诌。江湘吴越呼子曰崽。未烧砖瓦曰坯。快性人曰伶俐。小梳理头发曰拢。涂金饰物曰镀。以药合金曰銲一作釬。水戈平木之器曰推铇一曰铇子。沉水取物曰捞。田畔曰塍音丞俗音讹。欲食曰谗。物入目曰眯。以手握物出汁曰挤。小儿吐乳曰哯。草木不鲜曰焉一作菸。瓜瓤花片曰瓣。衣缝解曰绽音盏。四肢寒掉曰颤。与人交换原物曰嬥换。”内容杂而无序,但陈氏不以内容排列,而以韵相从,索词也较为便捷。
《俗用杂字》引书共45处,有《周礼》《礼记》《诗》《老子》《荀子》《国语》《史记》《汉书》《集韵》《篇海》《正韵》《黄氏日抄》《类聚音韵》《唐书》《韵会》《说文注》《集韵注》、石赓《论语注》、岳珂《桯史》、顾元庆《簷曝偶谈》、杜甫画鹰诗、韩愈诗、曾巩冬日诗等。所引诗文是词条的一个例证,也可得知此词条语义的较早出处。
二、陈士元《俗用杂字》的编撰体例及特色
《俗用杂字》附于《古俗字略》之后,从该书所处地位也可知晓陈氏编撰之意图。《俗用杂字》编撰体例与《古俗字略》类同,但又与之有别。通过对比,可以得知二书的编撰体例。大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别。
1.从收字上来看,《古俗字略》收正字、异体字及常用俗字,若该俗字无正字对应,则不收,并且只收单音节词;《俗用杂字》所收正好是《古俗字略》所不收的无正字之俗字,补充了《古俗字略》有俗字而难收录的尴尬境地。例如:
(1)沖(直弓切,和也,深也)盅、蛊(上并同)冲(俗)。
(2)细毛曰氄,一作绒,细布曰绒,细草曰茸。
例(1)为《古俗字略》的体例,可以看出,该书先是收正字“沖”,然后排列了两个异体字“盅”“蛊”,最后列出其俗体“冲”。例(2)为《俗用杂字》的体例,只列出了三个声同声近的俗字“氄”“绒”“茸”。
2.从编排方式上看,《古俗字略》整齐有序,以韵为次,递相而下;《俗用杂字》杂而无章,大体以声为纲,统摄收字,一声之内无序无别。例如:
(3)东、公、躬、空、通、同、中……
(4)性凶恶曰暴躁○发乱曰蓬松○肥脂曰膔……
例(3)为《古俗字略》上平声一东的部分收字,可以看出,这种编排方式类同字典,查找起来十分方便。例(4)为《俗用杂字》的卷首,很明显,这种编排是一种无序状态。可以相见,陈氏将《俗用杂字》附于《古俗字略》之后,实为《古俗字略》编撰的剩余材料。
3.从注释方法上看,《古俗字略》多数情况下只注音、释义,极少其他方面的解释;《俗用杂字》则以释义为主,少数注音,另外还多有引证。例如:
(5)洪,户工切,大也。
(6)细雨如雾曰雾淞。曾南丰冬日诗有霿淞字,黄氏《日钞》霿淞(音梦送)言寒雾凝木上如雪也。
例(5)为《古俗字略》对“洪”字的注释,只注音和释义,且大多如此,符合字典编撰的规范。例(6)为《俗用杂字》的注释,用训诂术语“曰”连接被注释字和释义。同时,有些词条还试图探寻语源,举部分书证。
那么,与《古俗字略》和陈氏的其他民俗语汇著作如《俚言解》相比,《俗用杂字》在收集民俗语汇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有人认为《俗用杂字》是陈氏《俚言解》中未付印的部分,[5]但根据主观感受来看,该书既然附于《古俗字略》之后,和《古俗字略》关系应该更紧密。《俗用杂字》与《俚言解》不同,它更注重的是当地的民俗语汇,更确切地说是方言词汇。它所收的民俗语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地域性。陈士元为湖北应城人,其所著俗语类著作无人带有自身所习有的地域语言特征,《俚言解》《古俗字略》在所多有。而《俗用杂字》尤为明显,更加突出了明代应城地区的方言特色。据邵则遂研究,陈士元的《俗用杂字》记录了明代湖北应城310条方言词,记录了当时语汇的含义和读音。他说:“《俗用杂字》是以十五世纪应城方言为横向参照点撰成的。多数词语(包括释义,读音)纪录的就是应城方言,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400多年前的珍贵的方言史料,对于今天江汉平原方言的研究,特别是应城方言的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6]作为一名湖北人,邵则遂应该对陈士元的撰述极为敏感,所评大致不差。例如:
(7)俗呼欬嗽曰喀嗽(喀音客)潜沔人呼喀为肯。
(8)手握物曰揢,音揢,俗音平声。
例(7)反映了应城方言对咳嗽的读音,一般的俗语词称之为“喀嗽”,喀的读音为客,潜(湖北潜江)沔(湖北沔阳)两地人读喀为肯,这说明通用俗语词和地域方言词的发音还是有区别的。例(8)反映了应城方言的实际读音,揢为入声字,在当时读平声,就体现了应城的入声已经发生了变化。《俗用杂字》中采用“俗呼”“俗音”来记录方言词汇及其语音的比较常见,这反映了陈氏所反映的应城方言语音的实际情况。
第二,示源性。作为一部记录民俗语汇的著作,对其所记录的民俗语汇必然有探源的尝试,这不仅是一部俗语类著作的责任,也是一个语言学家最原始的研究动力。前面所述,《俗用杂字》引书45处,多为早期著作,可见陈氏对所书民俗语汇探源的尝试。当然,陈氏本身对民俗语汇的认识是比较敏锐的,其《俚言解》所收大多为见于古文文献的口语词汇,其《孟子杂记》有方言专章,其中有雅言、方言之辨。可见,学术敏感和文献占有结合在一起,助力陈氏在撰述《俗用杂字》时寻语汇之根,溯语汇之源。例如:
(9)目郭曰眶,一作匡。《史记·淮南王安传》云:“泪满匡而横流。”
(10)斜开门曰闯。(音歪,又音委,又音趂)《篇海注》:“马出门貌。”《公羊传》“开之闯然”注:“闯,出头貌。”《国语》“闯门而与之言”注:“男在限外女在限内也。”又《簷曝偶谈》:“船门曰马门。盖闯字之分也。引首而观谓之闯。或曰非也,马门谓马船之门,船轻疾如马谓之马船。”
例(9)解释了俗语词“眶”,“目郭”即眼睛的外周,“郭”通“廓”也。《说文》未收“眶”字,而关于眼眶义全由“匡”来承担。查《说文》:“匡,饮器,筥也。”可见,“匡”有边界义乃至眼眶义为词义引申。陈氏以《史记》为书证,展示了他的文献功底。例(10)是关于俗语词“闯”的释义。《说文》曰:“闯,马出门貌,从马在门中,读若郴。”看来斜开门之义为词义的引申。陈氏引《公羊传》《国语》为早期书证,皆为“闯”的这一引申义。
第三,简洁性。《俗用杂字》为1卷,计三百余条,解释了近四百个语汇。从体量上就能看出,一卷之中要包含如此多的内容,撰述时当以简洁为主。另外,本书的性质是一部民俗语汇类著作,当然以简洁精炼为要。再者,陈氏大量使用了训诂术语“曰”,这个术语的主要功能就是释义,在清人的训诂成果里多使用,且形式非常简练,一句可成。例如:
(11)田畔曰塍(音丞,俗讹音绳)。
(12)婚礼以瓢为酒器曰合巹(音)。
(13)矮短曰矬。
(14)江湘吴越呼子曰崽。
(15)脱衣解甲折屋下瓦舟车出载皆曰卸(音泻去声)。
(16)以竹苇隔屋尘曰篖,古称承尘,俗呼仰尘。
(17)螮蝀曰虹,曲虹曰霓。南人呼虹为绛,北人呼虹为臬。
(18)强大曰奘(徂朗切)。
以上(11)至(18)例皆为《俗用杂字》最为常见的注释方法,用训诂术语“曰”串连,三言两语,其义立现。
总体来看,《俗用杂字》为《古俗字略》编撰之余料,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编撰体例是自由的,正体现了其书“杂”的特色,但总体上讲又以类相从,杂而不乱。《俗用杂字》所收民俗语汇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它收词是以应城为中心辐射至湖北地区,当然也个别收取通用的民俗语汇。陈氏的注释提示了所收民俗语汇的来源,但由于该书的属性所限,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这些民俗语汇的确切起源。另外,陈氏的注释简洁明快,也与该书的性质有关。
三、陈士元《俗用杂字》的价值
陈氏所著《俗用杂字》虽然自我评价价值不大,《四库全书总目》也颇有微辞,但今天看来,陈氏的《俗用杂字》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陈氏的《俗用杂字》为当下区域方言及民俗语汇研究提供了语料。前面已经论及,陈氏是湖北应城人,他的《俗用杂字》所收语汇明显带有地方特色。最明显的就是前面所例举的“喀嗽”条,甚至还举出了湖北潜江和沔阳两地的不同发音。再如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到“俗呼”“俗音”,如“腹中长虫曰蛔,一作蚘,又作蛕(音回,俗讹音肥。)”就是保留了当地对此条语汇的读音。因此,通过对《俗用杂字》的语汇研究,就可以了解明代湖北应城地区方言及民俗语汇的词类、结构、用字特点、读音情况等。
其次,陈氏的《俗用杂字》对所收民俗语汇进行了探源的尝试。一般来说,探求方言及民俗语汇的来源是一本民俗语汇类著作必要的编撰手段之一,也恰当地体现了作者的学识水平。但这也是编撰此类著作的难点,它需要作者大量的文献积累和丰富的学术经验,文献积累不足就不知语汇出自何处,学术经验不足就不知语汇最早的源头。从所引的45种书证中就可看出,陈氏在《俗用杂字》中对民俗语汇的探源工作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尝试,如“目汁凝结曰眵(音诗,俗音矢)韩昌黎诗:两眼眵昏头雪白。” 词条“眵”出自韩愈《短灯檠歌》,原诗“眼”作“目”。“眵”字《说文》中就有,云:“目伤眥也,从目多声。”但《说文》解释的是一种疾病状态,与陈氏所收俗语词“眵”异,故而陈氏引韩诗为书证而不用《说文》。但方言及民俗语汇的探源并不是该书的重点,这就显示出陈氏《俗用杂字》的探源是有限的、不完整的。
最后,陈氏的《俗用杂字》部分保存了当时民俗事象。民俗事象并不是一部语言类著作的中心内容,但有些民俗语汇的解释是需要民俗事象的说解来辅助的,所以民俗语汇的训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所理解或是当时当地客观存在的民俗事象。例如:“进趋曰夲(音敖又音嚣又音叨)从十大者犹兼十人也,与本字异。《集韵》體俗作軆,《正韵》體亦作躰,见《荀子·修身》篇,未有以体为體者。”这一条主要注释了“夲”字,同时也说明了“体”与“體”的关系。从字体关系上看,“夲”和“本”是有区别的,“体”和“體”也是不同的。民间以“体”代“體”,明显是以讹传讹。再如:“与人交易更换原物曰嬥换(嬥音窕),一作誂,又作挑。《集韵》:嬥嬥,往来貌。”这一条主要解释了“嬥换”,反映了古代以物易物的基本贸易生态,并且说明了这一俗语可能来源于《集韵》的“嬥嬥”。再如:“猪膜脂可洗绢曰子(音移)。”这一条反映出我国古代曾用猪胰脏和草木灰组合成的一种洗涤用品。等等。无论是民俗观念,还是民俗事物,《俗用杂字》都有一定的体现。这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财富。
《俗用杂字》仅为一卷,和《古俗字略》一道,被同道中人和后世接受和珍惜。明代小学家焦竑把《俗用杂字》全文收录在他的《俗书刊误》第十一卷中,略有增删,以致有人误以为该书是焦竑所撰。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后出的张自烈的《正字通》、翟灏的《通俗编》都从中吸收了部分词条。近代应城籍学者胡鸣盛著有《陈士元先生年谱》,依编年体记述陈士元生平著述成就。在《谱序》中指出:“陈养吾先生之在有明也,著作繁富,与杨升庵、朱郁仪齐名,而体大思精,考据赡博。清代诸儒,咸谓迥出两家之上。只以有德无位,僻居在野,既鲜知名朋好,又乏显达故吏,鸿篇巨制,无力付梓,其锓版诸书,亦以易箦未几,流寇蹂躏应城,城郭为墟,人烟灭绝,随之散亡殆尽!”直到康乾之后,汉学渐盛,“愈以先生著作至可宝贵,或不惜重金,购自番舶,或博访耆旧,挈来湖滨;采入丛书者有之,翻刻专集者有之。由是先生著述中外流传日多一日。”[7]胡鸣盛的评价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陈氏著述的价值与影响。陈氏的《俗用杂字》所书民俗语汇无论现在使用与否,都对当今理解这些民俗语汇的含义、读音、民俗事象的演变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