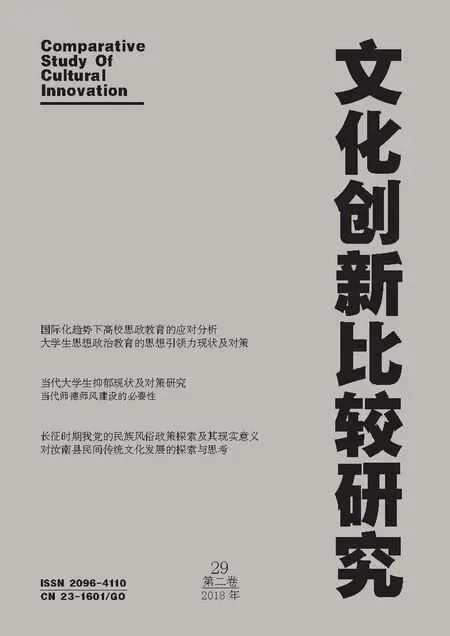长征时期我党的民族风俗政策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莫曲波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风俗习惯是一种群体生活方式,从个体来说,从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而形成,承载着生命的记忆和情感;从群体来说,它作为一种传统代代沿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是一个群体自我认知的标识,是审美观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问题在群体关系、民族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1 民族风俗问题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
风俗习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独特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区域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人们不断的历史积淀。风俗习惯最初是区域性的问题,随着精神、文化因素的渗入,它便具有了超脱区域限制的稳定性。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同一民族中,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但由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相通,不存在沟通障碍,在他们迁徙以后很快就会接纳另一区域同一民族的风俗并融入其中。但在不同民族之间,一个民族即便与其他民族杂居,在同一区域共同生产生活,经济密切相连,但风俗习惯的相通相容则是很困难的,其原因在于对这些风俗习惯起支配作用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的相互排斥。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与民族风俗、宗教习俗的最大区别。因此,同一民族的人们,即使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远走他乡,长期游走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但其共同的风俗习惯却始终保持下来。
民族相容的实质在于相互间精神上的尊重,在形式上表现为对风俗习惯的接纳和认同;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首先表现为对民族风俗习惯的相互排斥和歧视,有的还是因为对他民族风俗习惯的冒犯而直接引发的。古今中外,统治阶级搞民族同化的第一步,就是从企图改变其他民族风俗习惯开始的。因此,风俗习惯政策代表着主体民族的价值取向,推崇民族平等的政策实质,必然体现在尊重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上;强制性的移风易俗,则是大民族主义的外在体现。在历史上及现代各国实践中均可见,风俗政策的不合时宜,或者稍有急功冒进,就会引起重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2 长征时期党对民族风俗政策的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思潮逐步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行动上表现为急功冒进,相应地,在针对成规陋俗的移风易俗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措施。但总的来说,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根据地,涉及的大都是汉族群众,没有对少数民族关系产生实际影响。长征中,红军被迫沿着西南、西北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党和红军开始了与少数民族的正面接触。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左倾指导思想的权威受到冲击,从与少数民族接触开始,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红军处理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问题的实际行动中体现。
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为红军在处理民族风俗问题上提供了正确导向。遵义会议结束后,原总政治部随即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提出了要“绝对”尊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这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于民族及其民族风俗问题的长远解决,立足于民族风俗习惯的发展规律而定。在随后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在红军所经历的羌区、藏区、回区等,不仅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还有不少民族青年真诚认同红军的主张,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足以说明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一致性。
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风俗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2.1 尊重民族服装服饰和语言文字
服装服饰、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在适应不同区域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中,长期演变形成的,当它逐渐融入民族文化和精神信仰因素后,便成为这个民族的特征之一,成为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显著的外在标志。尊重民族穿着服饰,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第一要求。语言文字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与使用不同语言人群进行交流的时候,就会遇到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尽可能地学习和使用对方的语言文字,就是对对方的尊重。
2.2 尊重民族饮食习惯和生活禁忌
饮食习惯和生活禁忌最初同样来源于对生产生活环境的适应,但这些风俗习惯被赋予文化、宗教的成分后,就脱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信仰和精神的体现。如穆斯林就把喜爱牛羊作为他们追求圣洁、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以不吃猪肉表达他们抵制懒惰、愚钝和丑陋的价值取向。同时,他们还有一些特别的禁忌,如回民禁烟忌酒、讲究整洁,藏民忌讳在别人后背拍手掌等。对此,红军战士严格遵循,不好奇追问、不议论取笑,不在回民面前吸烟吃猪肉,不进入藏民视为神山圣水的地方等。
2.3 民族精神需求和宗教信仰
宗教虽是一种虚幻的理念,一旦形成,却会成为人们的心灵归宿和精神支撑,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仍是绝大多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精神源泉。尤其是藏、回民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宗教理念、礼仪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已经完全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民族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原始自发的生活习俗也被纳入宗教规范,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被赋予神的意志,成为信仰与精神的象征。
3 红军民族风俗政策成功经验的现实借鉴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在民族风俗问题上的探索、实践及其积累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3.1 从群众生活细节着手展示政策诚意
我们常用的会议、横幅、标语等营造氛围的宣传形式,是实现工作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是,要让少数民族群众真切感受并真心拥护,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展开和各个细节的完善。细致入微的工作是赢得民心的关键因素,它不仅是提高满意度的问题,更是体现诚意,检验口号、标语真正意图的标尺。政策实施者的内心好恶体现在举手投足之中,潜意识不经意的动作和言语,不是精密、巧妙的伪装能够掩饰的。红军官兵深刻认识民族解放、民族团结与战略转移的长远关系,把对民族风俗的尊重与革命理念的传输、各民族最终解放紧密联系起来,言由心生,言行一致,时时处处体现着由衷的信念和诚意。
和平时期,在市场经济裹挟着人们把精力集中在物质利益上,把价值体现在物质的积累上这种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似乎民族意识已经完全服从于经济利益,风俗习惯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鸡毛小事,这种认识正是我们在民族风俗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障碍。在风俗习惯这些细微的小事中,折射着干部的真情实意或虚情假意,并被引申为对各级政府的诚意与用心的考量。对待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一些不妥的言行,或许暂时不会带来直接的后果,但随着矛盾的积累,它就成为冲突发生的直接导火线。诚意源于理性认识,在民族风俗的研究和政策执行过程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应该以民族团结振兴、共同繁荣发展为己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认真研究、制定和执行民族风俗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落实党的民族风俗政策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战略工程来抓,从民族风俗细微的工作着手,消除影响民族团结的一切不良因素。
3.2 以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树立尊重民族风俗的典范
历史上,藏、回民族曾经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得宗教上层与统治阶级合二为一,不仅经济阶层划分明显,精神意识上的等级划分也是根深蒂固。由此,民族上层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据统治地位,左右着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民族上层代表并引领着民族的生活潮流和风俗习惯,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就如牵牛抓住了牛鼻子,对于党的民族风俗政策的展示和落实必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上层人士虽然在政治上不再具备往日的权威,但在精神上,甚至经济上却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影响。日常生活中,民族风俗文化则只有在民族上层群体中才能完整地体现,他们的生活娱乐方式,成为民族风俗文化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争取、团结好民族上层人士,是民族风俗政策落实的切入点。他们有知识、有个性,思想活跃,但他们又缺乏民族代表人物那种大局和整体意识,也没有一般群众的朴素与单纯,经常有令人不爽的意见建议,各级干部作为具体的政策执行者对他们存在天然的排斥情绪。对此,各级部门和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让干部走到他们的对立面,而要把他们作为朋友,要以宽广的胸怀,积极引导、求同存异,做好团结工作。
3.3 把严格的纪律检查作为风俗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的坚强保障
自进入瑶族地区开始与少数民族正面接触后,红军深感民族关系、民族风俗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对可能面对的少数民族,要求先遣部队在收集军事情报的同时,注意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934年12月,政治部及时下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少数民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战士严格遵从民族风俗。在随后的经历中,红军对违背纪律的行为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不打折扣,毫不含糊。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提升,自然包含着民族经济、民族风俗相关等内容。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和扶持政策,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不可否认,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积习,一年半载难以改变,使党的民族风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党的好政策经过层层变通、打折或加码,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影响了民族感情。究其原因,就是对于不严格执行中央精神、不守规矩,打政策擦边球等的做法,没有认真追究,一味放任。因此,在国家治理机制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加强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监督督察,对渎职失职行为和工作作风问题零容忍,才能切实克服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克服工作对上不对下,脱离群众,应付了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