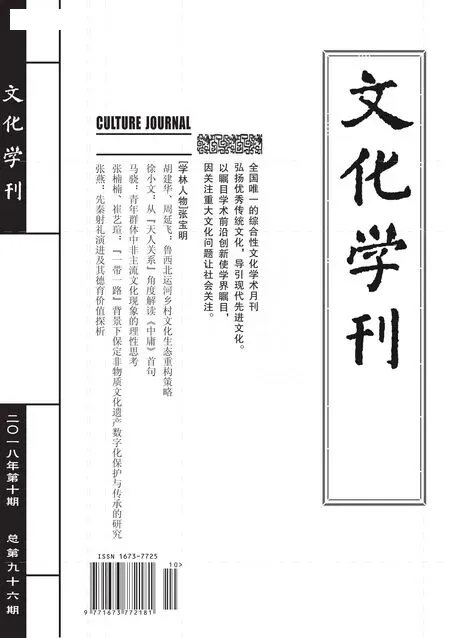王徵天主教信仰发展的两个阶段
孙 赫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
一、引言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就此指出,相比于西方对传播基督宗教的热枕,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却是当时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1]晚明士大夫王徵就是因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阐发和运用而被古今众多学者评价为一名“以耶补儒”来挽救岌岌可危晚明政局的儒家学者。对此,柏堃(1870-1937)评价说道:“先生著《奇器图说》,与双山著《邠风广义》,皆注重实业,兼取外人之长,以救中国末流之失。其精神以敬天爱人为宗旨,悉有功于儒术,非有病于儒教也。”[2]同样,王徵身上所饱含的家国天下之情怀也使得当代学者李之勤将他视为一名“以传统的忠孝仁义为依归,力图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3]的儒家知识分子,认为他仅仅是将天主教作为一种补足儒家传统的思想工具而已。这样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准确的,尤其是从儒家思想史的传统出发去解读王徵的天主教思想。
然而,如果我们以王徵个人的思想历程为解读视角,就会发现他对天主教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
王徵(1571-1644),陕西西安府泾阳县尖担堡(现王家堡)人,字良甫,号葵心,入教后取圣名叫做斐理伯(Philippe),晚年自号支离叟、了一子,因甲申之变不屈殉明,故死后被追谥为端节先生,因为其奉教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故而被称之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中的“明末四贤”[4]。
从1616年王徵初识天主教到1632年遇赦归里,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他天主教信仰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王徵写下了《畏天爱人极论》[注]《畏天爱人极论》不分卷,写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古郎(Gourant)编目号码为6868。原抄本题属为:泾阳王徵葵心父著,武进郑鄤峚父评。然此本中并未见郑氏之评点文字。有向达1937年抄本,及向达弟子宋伯胤抄校本(简称宋氏抄本)。宋氏抄本见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向达所抄,即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本。今据巴黎图书馆藏写本之影印本移录,以宋氏抄本校,见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卷八,第117页。,将畏天爱人作为他天主教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为一名有着深厚儒学背景的士大夫在面对日渐衰颓的晚明政局和空谈心性的学风、士风时,试图借助当时传入的天主教伦理思想来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明政权,此时天主教对于王徵而言重要的是作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工具;从1634年在家乡创办仁会直至1644年以死殉节,可以称之为王徵天主教信仰的第二阶段,这期间王徵在家乡创办了事天爱人的仁会组织,编写了《仁会约》[注]《仁会约》不分卷,明崇祯刻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古郎(Gourant)编目号码为7348。原刻本封面标题为《仁会》。有向达1937年抄本,及宋伯胤抄校本(简称宋氏抄本)。宋氏抄本见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据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之影印本移录,以宋氏抄本。(见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卷九,第139页。),其中不仅制定了会中成员需要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还介绍了关于基督论、天主论以及末日审判等教义教理,据此可以看出他对天主教一些核心内容的认识和掌握;除此之外,王徵在晚年还写下了《祈请解罪启稿》,对早年纳妾的背教罪行进行了书面告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此时对天主教的信仰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经世致用的目的,而转向了对灵魂救赎的渴望,这同样也可以在王徵次年所写的《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注]《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不分卷,写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古郎(Gourant)编目号码为1021。意大利神甫杜奥定(Agustin Tudeschini,字公开,公元1598-1643年)原著,法国神甫方德望(Etienne Faber,Le Fevre,字玉清,公元1598-1659年)口译,王徵笔述。原抄本题署为:方德望玉清神甫译,王徵良甫氏述。有向达1938年2月抄本,及向达弟子宋伯胤抄校本(简称宋氏抄本)。宋氏抄本见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增订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据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写本之影印本移录,以宋氏抄本校。(见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卷十,第157页。)中通过对杜奥定神父不惧危险而拯救世人灵魂的描述中有所体现。
在下文中,笔者将以《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祈请解罪启稿》以及《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作为文本依据,剖析王徵的天主教思想特征,探讨他两个阶段的天主教信仰;并且,笔者还将探讨《七克》[注]《七克》,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所编写的天主教伦理学著作,其中介绍了天主教所禁的七种罪恶以及如何克服的方法。《哀矝行诠》[注]《哀矜行诠》,共有三卷,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所著,有1633年北京刻本。(见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卷九,第140页。)和《天主实义》[注]《天主实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所编写的天主教著作,这本著作是在亚洲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要求下,旨在为儒家士大夫提供哲学论证以作为信仰的预备。(见[法]梅谦立注,谭杰校勘:《天主实义今注》,第6页。)对王徵天主教思想的影响,论述他信仰发生转变的这一过程;最后,笔者将把王徵天主教信仰的转变路径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传教士在传教时所采取的适应策略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为王徵的天主教信仰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寻求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二、第一阶段的天主教信仰:渴求经世致用的工具
崇祯元年(1628),王徵在扬州任官时撰写了他入教之后的第一部天学著作《畏天爱人极论》,文章通过客问主答的方式,一方面对天主教中被称为“吾辈之下学”的针砭克治的小策推崇至极;另一方面则借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之口讲述了生天生地,始创万物的天主的存在,以及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触犯戒律而被逐出天堂,并且天主因此降罪于后人的天主教原罪论内容。[5]通过回答人死后,天主对个人生前行为的审判,王徵也借此阐释了灵魂不灭以及天堂地狱等天主教的许多重要思想。[6]虽说在这部著作中有大量的内容是直接对利玛窦和庞迪我等传教士所著的引用和摘录,但也可以看出王徵身为一名儒家基督徒对于这些教理内容的接受与理解。当回忆起他接受天主教的机缘时,王徵说道:
适友人惠我《七克》一部。读之见其种种会心,且语语刺骨。私喜而跃曰:“是所由不愧不怍之准绳乎哉?”[7]
其中通过王徵“种种会心”“语语刺骨”和“私喜而跃曰”的反应,不难看出《七克》对他接受天主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克》是1614年由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编写的天主教伦理学著作,其中揭示了七种天主教所禁之罪[注]“生傲,生贪,生饕,生淫,生怠及妒忿,枝也。”(《七克》,第9页。),以及克服这七种罪过的方法[注]“一曰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防淫,七曰策怠。”(《七克》,第1页。)。这本在庞迪我看来只是“吾辈下学”和“针砭克治之小策耳”的著作,却使王徵读起来产生了“种种会心”且“语语刺骨”的感受,其中的原因促使我们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七克》补充了儒家思想在克己修德的功夫上一直以来所缺少的操作方法。例如针对“贪欲”,庞迪我提出了以“施舍德”的方式来克服此欲,并且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即:
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己后人,先亲后疏,先善者后恶者。尔欲效天主,勿弃恶者。日光下照,不遗恶人也,贫人虽恶,与视其恶而弃之,无宁视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过尔量,视友如己足矣。[8]
他通过推己及人、亲疏有序的方式,要求人们不论对方贫贱与否,量力而行地进行施舍恩德来克服贪欲的影响。
除了提供帮助个人克己修德的方法之外,《七克》还设置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天主,并且通过列举地狱的永罚之苦来帮助人们祛恶从善。在天主教传统的教理看来,人们获得救赎的原因完全是出自天主绝对无私的恩典,因此人们只有通过对天主的信仰,心怀天主及其美善,不断地对照自己省察罪过,克制私欲,培养德行,最终才能够战胜七宗罪,获得至福。[9]另外,庞迪我还在《七克》中指出,傲、妒、忿、淫等诸罪难以被消除的最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世人对天主的无知,他对此说道:
然而克欲修德,终日论之,毕世务之。而傲妒忿淫诸欲,卒不见消。谦仁贞忍诸德,卒不见积。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向。三曰,不循节次。[10]
其中“本原”就是指始创万物的天主,他提出人们在克欲修德的过程中,首先要认得天主这最初的、善的本原,其次在一定的次第功夫下才能够克服傲、妒、淫、忿等诸欲的影响。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的天主,可以帮助人们在修养时克服人性当中的弱点,有助于世人诚心改过,祛恶向善。
可以说,无论是针砭克制的小策还是全知全能的天主,使得一直以来苦苦追求经世报国之良方和克己修德之法宝的王徵深受启发,激发了他对于天主教的浓厚兴趣。据林乐昌考证,王徵正是在接触到《七克》之后,于第八次赴京会试(1616年)滞留北京期间领洗奉教。[11]
笔者认为,尽管已经领洗,但显然王徵此时尚未对天主教中的核心教理内容有着充分的认识。正如他之后回忆初次接触《七克》时所说的那样:“遂日取《七克》置床头展玩,然恨未遽竟其原也。”[12]其中“未遽竟其原”表明了当时王徵对天主教一些重要教理的不够了解,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当时的天主教信仰不够坚定。天启二年(1622)王徵中第后不久就因为父命严喻的压力而纳妾求嗣,也可见在当时王徵的思想之中,儒家传统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同理,在天启六年(1626)所刊刻发行的他与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 )合著的《西儒耳目资》中,王徵在序里也写道:“先生学本事天,与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无二。”[13]这无疑也表明了他那时并未区别出儒耶两家之间的思想差异和信仰冲突,天主教思想在他看来仍然是补儒、合儒的理论依据。
除了《七克》的影响之外,王徵本人所著的《畏天爱人极论》也为我们展现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天主教思想。不难发现,这篇文章中客问主答的行文方式与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采取的中士与西士的对话体问答极为相似;其次,《畏天爱人极论》中所涉及的天主教灵魂观以及天主观内容也都是直接对《天主实义》的摘录和引用。众所周知,在1616年王徵入教时,《天主实义》已经刊刻出版多年并且在教内教外流传甚广,所以笔者认为尽管在《畏天爱人极论》中王徵只字未提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但是他天主教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应该是与《天主实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撰写的一部旨在向儒家士大夫提供哲学论证以作为信仰预备的天主教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利玛窦并没有谈及太多天主教中那些较为晦涩难懂的教理内容,而是以哲学论证的方式向世人揭示天主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的教理。在《天主实义》的引导下,王徵也接触到了一些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当中所从未涉及过的内容[注]其中涉及天主论的内容:“西士曰:子欲先询所谓始制作天地万物、而时主宰之者,予谓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谁不仰目观天?观天之际,谁不默自叹曰:‘其中必有主之哉!’夫即天主,吾西国所称‘陡斯’是也。”(见《天主实义今注》,第80页。);其中涉及灵魂论的内容:“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长,草木枯萎,魂亦消灭。中品名曰觉魂,则禽兽之魂也。此能附禽兽长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试听,以口鼻啖嗅,以肢体觉物情,但不能推论道理,至死而魂亦灭焉。上品名曰灵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觉魂,能扶人长养,及使人知觉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论事物,明辨理义。”(见《天主实义今注》,第109页。);其中涉及道成肉身的内容:“于是大发慈悲,亲来救世,普觉群品。于一千六百有三年前,岁次庚申,当汉朝哀帝元寿二年冬至后三日,择贞女为母,无所交感,脱胎而生,名号为耶稣—耶稣即谓救世也。躬自立训,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复升归天。此天主实迹云。”(见《天主实义今注》,第217页。)。
这样,在《七克》和《天主实义》等著述的共同影响下,王徵在《畏天爱人极论》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当时对于天主教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得出了畏天爱人的重要思想。
作为当时一名长期沉浸在儒家传统里的奉教学者,王徵畏天思想的产生受到了来自传统儒家和天主教思想双方面的影响和启发。他通过孔子所言的“君子有三畏”而提出想要成为圣贤,首先便要敬畏天命;通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的论断,表明了“知天命”是“畏天命”的必要前提;之后又借“五十而知天命”之论,推断出了天命不易知;最后,认为君子与小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是否知道天命之所出以及是否真正地畏惧天命,其中畏惧天命其实对于王徵而言更多的是指惧怕上天的惩罚。
在此基础上,追问“天”的实在意义成为了他信仰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又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一直以来对于形而上内容的忽视,使他在苦苦追问“天命之所在”以及“天之所以命我者”时常常不得其解。而此时恰好庞迪我向他介绍了有关天主的概念:
撮其大旨,要亦不过令举世之人,认得起初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一大主,尊其命而无逾越,无干犯,无弃逆;于以尽昭事之诚,于以体其爱人之心以相爱,于以共游于天乡云耳。[14]
王徵在庞迪我那里得到了令其满意的答案,他赞同天主教中所设置的这样一个创生万物并且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主宰,也同样认可世人之所以对自己行为的毫无忌惮,是因为对于天主的不够了解和对待天主权威的不够畏惧。对此,他说道:“世之人只知地上有主,而不知天上有主;只知地上主赏罚可畏,而不知天上主更有真正大赏罚之更可畏。”[15]在识得天主的存在后,他豁然开朗而说道:“天而系之以命,则律令灵威,有以所命之者,则必有所以出,是命者所谓主也,有不敢不畏者在矣。”[16]通过让人们明白天之有命并且天命出于天主以及天主之命无不善、无可违、无所祷,顺利地将这可以降祥降殃,至高无上的天主,安放到每个人心上,作为“摄服小人之胆”的工具和促使人们祛恶从善的主宰。由此,王徵也恍然大悟,确信天主教中那具有位格并且主宰世间一切、全知全能的天主比起儒家所讲的苍茫之天而言,可以更为合适地充当起发出天命的最终根源。
“爱”对王徵来说是天主教教义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他指出“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义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以及“爱人之仁乃其吃紧第一义也”[17]在明末清初所有的奉教士大夫之中,也仅有王徵一人的几种崇教著述均是围绕基督教中“爱”的观念而展开的。对此,当今就有学者提出,王徵天主教信仰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他的圣爱观念。[18]
在传统基督宗教中,爱确实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圣经》对此就有说道:“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这种对于天主之爱的反应,在天主教内预设有更为重要的前提,即天主对人绝对无私的爱,正是借此人类才有了获得救赎的机会。但是孙尚扬指出,王徵更重视的是人对天主之爱的响应,即人对天主的信爱以及人对人的爱[19],对他而言,天主教的根本大义只是“爱人之仁”。
对于爱,王徵首先肯定爱人如己是爱天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其爱天主之效,又莫诚乎爱人也。”[20]其次,王徵提出的爱并非虚爱,而是实实在在、必须要付诸实践的爱,这从他对《圣经》里关于形神哀矜之十四条准则的判定可以看出。在传统天主教中,这十四条准则里从属灵魂救赎的神哀矜七则应该更为重要,但是在王徵看来因为晚明所处的社会现实,真切行使形哀矜七则却显得更为紧迫,因此,他竭力主张提供食物和饮水给那些饥饿与干渴的穷人,捐赠衣服和住所给那些无衣遮身,无处避雨的人们,照顾生病的人,赎回被俘虏的人以及妥善的安葬死去的人。[注]“形哀矜之行七端:‘一、食饥者。二、饮渴者。三、衣裸者。四、顾病者。五、舍旅者。六、赎虏者。七、葬死者。’与神哀矜之行七端:‘一、启诲愚蒙。二、以善劝人。三、责有过失者。四、慰忧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为生死者祈天主。’”(见《哀矜行诠》,第35-37页。)可见当时,王徵认为灵魂的获奖并不如落实儒家“爱人之仁”的实践更为重要。
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王徵深切感受到自己关于经世致用的抱负实在无法在这种漫谈心性、日渐衰颓的晚明政权中获得实现,所以他才会试图积极地借鉴天主教思想,企图通过当中相对先进的天学思想来挽救日渐衰退的社会现实。但是笔者认为,不管是关于畏天还是爱人的思想,都是服务于王徵当时经世治国的初衷,虽然此时他已经入教多年,但是在当时仍然是在一名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上诠释着天主教思想,天主教也只是他借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工具。虽说在《畏天爱人极论》中,王徵也对天主教中的一些核心教理有所介绍,但这也只是为了满足他经世致用的目的,并不代表其对天主教思想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三、第二阶段的天主教信仰:渴望灵魂救赎的真理
崇祯七年(1634),距离王徵接触天主教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多年,时年64岁的他在经历过仕途的种种不顺后也已经告老还乡专心奉教了,回乡后的这段事教经历对王徵信仰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西安读到耶稣会士罗雅谷神父(Jacques Rho,1593-1638)所写的《哀矜行诠》之后,王徵制定了《仁会约》,他以中国传统乡约的形式,创办了具有天主教社区特点的仁会,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条款来实践他天主教信仰中关于爱的思想,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的信仰。
在《仁会约》中,王徵引用的大量内容来自于罗雅谷所著的《哀矝行诠》,因此笔者认为《哀矜行诠》对王徵天主教信仰趋于成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罗雅谷在《哀矜行诠》里颠覆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自两汉时董仲舒首次提出“三纲”的说法再到后来宋明理学家们将伦理纲常定为天理,设定成为每个人与生便有且需遵守的道德观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基本准则,这种臣从君、子从父、妻从夫的儒家伦理道德维系了中国近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制度。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利玛窦等传教士起初在传教时,有意地避而不谈那些涉及违悖儒家传统伦理的内容,甚至在《天主实义》中还辩称天主是为世人的“大父母”[21],从而将事天纳入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当中。如果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还未能帮助王徵突破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界限,那受到《哀矝行诠》的影响后,王徵在《仁会约》中说道:“念世人皆天主子,皆我兄弟也”[22]则无疑表露出了他对儒家君臣父子之间等级之差的反思。
除此之外,《哀矜行诠》还介绍了关于基督论的内容。在利玛窦着手撰写《天主实义》时,因为担心儒家学者无法接受那些在中国传统中从未出现过的教理内容,所以仅仅只在第八章的末节稍微提及了原罪论和耶稣降生的内容并且有意地省略了耶稣受难以及复活的内容,根据意大利学者柯毅霖的研究,这样的目的更像是要引导那些已经产生灵性动机的人们去逐步发现基督宗教当中的奥秘。[23]但在《哀矜行诠》当中,罗雅谷似乎并没有坚持利玛窦保守的传教策略,书中所引到“福音书”中的大量内容都有对耶稣降生拯救世人和末日审判进行着详细的描述:
赎虏之功,耶稣为首。盖人类因有原罪,为魔之奴,而堕其诱感。沉沦莫返,天主悯之,因降生而赎人罪。使复还正道焉。(有本论。)且其所赎者非一人,其所为赎者,又非直金币等物,乃即赎以其身,非首功乎?凡今之人,宜体其情,谢其恩,循其迹。[24]
审判日,天主问曰,尔在世曾饮渴者乎?又断罪之言曰,尔等距我今徃就彼永火中(乃天主所造永苦之处,以罚魔鬼及恶魂者。)盖以尔等在世,我渴而不我饮故也。(所施与贫人,与主自受等。)[25]
这些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从未有过的天主教教理内容,王徵在《仁会约》中对其均有所介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此时的信仰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天主教不再只是用来克己修德、经世治国的理论工具,在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王徵个人信仰的追求已经转向了更深一步的层面。
同样,也可以为王徵信仰发生转变提供依据的是,1636年,王徵在人生暮年写下了《祈请解罪启稿》,试图以书面形式为自己所犯之罪做一全面告解以及交代个人信仰的最终所在。在这感情真挚的祈罪稿中,王徵在开篇就对早年不坚、不热、不纯的信仰表示出真心悔过的态度。随即,又对自己早年违戒纳妾的行为作出解释并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于儒耶两教在妻妾问题上的冲突,王徵虽然仍无法彻底地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社会之外,但是他选择一种略具调和性的做法,将其妾室视为宾友,从此断绝邪淫之念,并且给出了书面性的保证,以求获得神父和天主的谅解:
今立誓天主台前:从今以后,视彼妾妇,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倘有再犯,天神谙若,立即诛殛!伏望铎德垂怜,解我从前积罪,代求天主之洪赦。罪某不胜恳祈之至。[26]
在晚年写下这样带有强烈信仰特征的悔罪书,无疑证明了王徵此时对于死后灵魂不灭并将受到天主审判的坚信不疑,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真切的信仰所在。
次年在法国神父方德望(Etienne Faber,1598-1643)的口述下,王徵笔录了《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一书,描述了意大利神父杜奥定(Agustin Tudeschini,1598-1643)从罗马出发历经千辛万苦来华传教的经历。这本著作以杜奥定神父在传教途中所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为例,讲述了世人对于灵魂救赎的渴望以及在追求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书中提到,当船只遭遇海难时,杜奥定神父不顾危险出于于风浪之中,竭尽全力地为人告解以图拯救更多人的灵魂,在他担心遭遇海难的所有人灵魂无法全部得到救赎时,神父更不禁涕泪而言道:“宁我一人死此,决不敢委弃众人灵魂而不救也。”[27]其中关于对灵魂救赎的渴望在此时已经对王徵的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这篇传记的末尾,王徵由衷地表露出了自己对杜奥定神父不顾己身,历经百险百危一心事主救人灵魂的敬佩,他说:“先生不婚不宦,不名不利人也。只为敬天爱人,不远九万里惠顾我东土,历绝尽百险百危,曾不一毫退转。我辈痴迷,盈盈一水之隔,不百里而近,乃惮跋涉苦,弗能时时亲灸德辉,良可笑耳,且可其愧已!”[28]
据此,笔者认为,在此时王徵所具有的身份特征显然不再是一名“以耶补儒”的儒家士大夫而已经转变成为了有着虔诚信仰的天主教教徒。
四、结论
将晚明入教士大夫王徵的天主教思想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为我们认识发生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为了不在一开始就与儒释道三教共同为敌,在传教的初期对违背儒家传统的天主教教理介绍时尤为谨慎,这使得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样的刻意掩盖使得绝大多数的归化者并未对天主教中许多核心教理有所认知,更没有在信仰层面上彻底地皈依天主教。
但是依据本文对王徵天主教思想的探究,可以清晰地看出王徵对天主教思想的认识呈现出了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并且最终彻底完成了在信仰层面上的皈依,而笔者认为这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所采取的传教策略不无关系。从王徵天主教信仰的这两个阶段的内容来说,可以判断利玛窦的这一次传教并非像谢和耐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失败的,儒家士大夫也不只是处于被动的“反应”位置,反倒是积极地从自身情况出发接受了天主教思想。利玛窦这种循序渐进的传教策略不仅不至于在一开始就使士大夫觉得教义荒谬而不可信,反而使得归化者可以更加从容地去沟通原本相差很大的儒耶两教思想,从而接纳天主教。
同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正确评价利玛窦传教策略提供事实依据的是,当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龙华民神父(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由于怀疑利玛窦策略的可靠性,认为由此归化的士大夫事实上并不尊重天主教教理,故而修改了一直以来的传教策略,选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教活动,这却最终导致了利玛窦死后各地教难层出不穷,直至最终也没能逃脱被禁止传教的命运。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今学者对于王徵的个人信仰的判断大都是以他经世致用的个人抱负以及纳妾殉明的人生抉择作为依据的。台湾学者黄一农就认为“天儒合一”是王徵奉教之后的重要思想,中国先秦典籍中所提及的“上帝”,即等同于天主教所称的“天主”,天主教的教理在王徵的心目中或许只停留在形而上的思想层次,而并没有成为生命实践的伦理规范,所以他才会在年过半百且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屈服于周遭的压力而选择纳妾;同理,王徵在亡国后也正是遵循儒家的价值观念而选择了自尽殉节。[29]陕西学者丁锐中也根据王徵纳妾殉明的人生选择,将他视为儒家身份为主的儒家基督徒。[30]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王徵在生死别离之际所写下的临别之语:“精白一生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31]则清晰地表露出了他对自己天主教信仰的坚信不疑。可以看出,对王徵而言,在人生之中的这两次严重违戒,似乎并不妨碍到他对天主教所持有的真切信仰。在笔者看来,这或许也正是因为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发生对话的双方站在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上,以自身所关切的问题作为出发点,积极地会通儒耶两家的思想文化,个人的信仰因此既有从属于儒家的内容也具备天主教的特征。当然,从这点出发也值得我们接下来去做更多深入的研究。